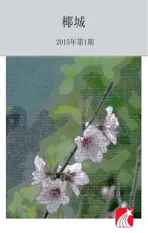怀念一个远去的人
——城市笔记之九十二
2015-02-06莫晓鸣
■莫晓鸣
怀念一个远去的人
——城市笔记之九十二
■莫晓鸣

时光如梭穿行,渐渐空荒,他的离世,不知不觉已五年了。有时我会想起他,内心便会一阵子淡淡的酸楚,一阵子淡淡的惆怅。五年间,有多少繁花碎玉的事在我的世界里发生,纷纷纭纭占据我的头脑,我想,我会偶尔想起他,他大概是盘踞在我心头的一个念想,时强时弱,时大时小,让我不能轻易地一拂而散。
当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不知天高地厚,愣头愣脑,跃跃欲试,很快进了一家人声喧哗群情激昂的报社,遂了自己企图以笔谋食的心愿。那时他也来了记者部,是从海南东部一家农场宣传科长的位置上调动,他走起路来是个胖墩的身影,脸上多肉少笑。记得他还拖家带口,一家四口拥拥挤挤租住在民房里,妻子被安排到报社发行部,一男一女正在上中学。那时我二十出头,他四十有余,因为年龄的差异,还因为他一脸不苟言笑的严肃,我与他没有多少交往。似乎还可以说,工作上的热情放大了,私人间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小,如果没有工作上的交集,我与他大概仅是碰面点点头,或者碰面互相递上一句客气而日常的问候。
一年之后,因管理上的弊端迭出,人心渐渐涣散,报社并不能如我们想象那样逐日发展壮大,更不可能有朝一日大展宏图。前景不可期,良禽择木而栖,他最先离职了,去向何处,当时我并不知晓。我选择留下,一是我没有门路外流,二是我没有外流的资本,再就是我还年轻,不怕熬,熬出一些阅历来也算是收获。
又是几年之后,因一次街头偶遇,一阵握手和呵呵连声之后,旧谊又重回心头,我便有机会与他一起喝茶聊天。谈到他离开报社的那段经历,他说虽然自己早有去意,却不敢主动辞离,毕竟是个拖家带口的人,每个月还指望那点工资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是因为他与报社领导拍桌打椅吵了架,俩人关系势如水火,从此覆水难收,他又不想让自己低三下四去求饶,便只好卷铺盖走人。说到这里,他抬头望向窗外,窗外是炎炎烈日下奔走不息的人和车。他接着说,离开报社后,他应聘到一家小公司,因工资太少,家用捉肘见襟,晚上自己只好到夜市摆摊,挣一点算一点。再后来,他考上了政府公务员,有了一份不问晴雨只按日历计算的工资,生存的窘境才慢慢缓解,做人的底气才慢慢恢复。当他升为处长,儿子又考上研究生后,他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人模人样了,自己历经磨难,终于变成一个足以自慰的男人,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甚至觉得,人活不过自己的命,命里该有的东西,时间一到,便一样不少全都来了。
这次会面后大约两年时间,我不再见过他。海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他居住的地方离我家大概三四公里,不远不近,因彼此忙碌,更因心性不同,即便彼此仍冠着朋友之名,竟可以几年不通往来。这时我从一位昔日女同事那里,知道他不久前因肝癌动了一次手术,如今恢复良好,命大福大,已能坐在办公桌前谈笑风生。生癌症无疑是每个人所忌讳的,对于他,我便装作毫不知情,连问候的电话都省了。
化疗结束后,他急着去上班,急着将自己复原成健康人,至少不是个前癌症病人。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人,没有理由不珍惜生活,也比太多人有理由去享受生活。病愈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既然这样,他必须有正常人的情感,正常人的社交,正常人的成人之美。这期间,当他闻知我大龄未婚,便热心为我张罗,无一遗漏地搜遍自己的关系网,先后为我牵线了一个女孩,又一个女孩,只可惜事与愿违,我与这两位女孩都左右无缘,彼此擦肩而过后便散失于茫茫人海。但是,我却因此铭记住他的这番好意,铭记住他眉头紧皱的焦虑神情。
海南的夏天天空流火,日光粗粗壮壮,连吹在脸颊上的风都微微发烫。但这并不影响一座城市的生活,该繁华的仍旧繁华着,该慵懒的仍旧慵懒着。这天上午,我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在街道上步履匆匆,忽然接到那位女同事的电话,说他的癌症复发了,已在家养病多日,约我下午一起去看他。听后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知道情势不妙,癌症再复发,就等于宣告医术上的回天乏力。在破碎处眺望,人生的无奈会随之升级,生命的脆弱会随之变成一张薄纸,不知什么时候,一捅就破。
他的家住在纵深的旧省委大院里,是一套三居室的旧房。我和那位女同事都是第一次来访,里面路径纵横交错,担心我俩辨不清,他走出好远的一个路口迎接。一见面,我发觉他脸上的肉块消失了,握他的手,硬硬的,已经是皮包骨头。及至在他家的客厅坐定,我认真打量他的脸,虽然他强颜欢笑,故作轻松,仍无法掩饰凄哀的神情。他说,一天里他要喝七锅野生灵芝熬出来的汤,癌细胞却仍是刷刷刷地疯长,简直无法无天了!我一阵心酸,言不由衷地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甚至大胆夸奖野生灵芝的药效,预言奇迹可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他认真地听着,频频地点头。
这之后大概两个月,一天我正在家里吃晚饭,那位女同事又打来电话,说他快不行了,已从家里转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怕是熬不过这几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撒手,邀我马上去看看。记得那是一个雨天,我一时在饭桌前怔住,慌里慌张放下碗筷,便撑着雨伞出门。坐上女同事的车,我脑袋里一片空白,竟想不起任何与他相关的事,连他的面目也变得模糊不清,只是任车载着我,一点点地逼近他,逼近一个我最不愿意逼近的真相,这个真相便是生离死别。
看见我俩进来,他眼睛一亮,但已不能挣扎着坐起来。他躺在病榻上,身上插着许多管子,已瘦得脱了人形。他命妻子将靠背的床板摇高,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要与我俩说说话。他时断时续地说他做了政府的处长,已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只可惜辛苦了几十年,没法再领一分钱的退休金;他说身为公务员的儿子报考海南的市县领导岗位,笔试已榜上有名,这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他还说自己遗憾的是,原先答应过妻子,退休后要带着她游历祖国的山山水水,看来这一夙愿只好等来生了。最后这句话,说得他瘦小的妻子忙手掩着口背过身去,对着白色墙壁一阵哽咽。
确实,当时在那间白色的病房里,每一个人都相信,死神真的要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说不准是哪一刻,他眼睛一闭就永远离场。尽管他身不由己,心有不甘,但上帝不会与他讨论该不该,更不会与他讨论时间是否安排错了。哪怕上帝是一意孤行,他也只有服从。也恰是在这时,处长与平头百姓才算真正平等,都在无力无望中祈盼生路,都没有与上帝讨价还价的机会。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每一声手机铃声响起,都会令我一番紧张,惧怕突然从里面传来他的噩耗。我心里悲凉着,不愿意那个日子的到来,却又不得不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就像等待一片高悬的瓦片忽然坠下,哗啦一声,碎裂一地——事情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逝后就剩下一些如碎瓦般的传闻。当然,再往后这些传闻就会渐渐淡了,渐渐没了。
医院最后对他宣告无治,他眼神凄凉,在一家人的绝望里,又被运回家。不久我竟能收到他手机发来的信息,说他考市县领导岗位的儿子马上要进入面试阶段,请我出力帮忙,算是这一生托我的最后一件事。“最后”二字让我内心无比沉重,久久地呆愣,下不为例是因为他以后无法再在世上向我发出任何请求。不过我有点惊讶,他为什么会将我列为此事的请托对象?身为一介文人,我如何能帮得上他的忙?我不禁又要问,他那些昔日同僚呢?难道人未走茶已凉?但是,为了不拂他的意,我毫不迟疑就答应了下来。说是一定尽力,却是不曾出过一点力,因为我太明白自己的无足轻重。
他逝去的第二天,那位女同事打来电话,未开口就先哽咽。女同事说,他最后的几天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家人将他安置在客厅里,躺在一张草席上。十月海南的地板已透凉,家人竟不在他身底下垫一张毯子。女同事哭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时他大小便已失禁,就图照顾方便,一家老小竟忍心让他受凉受寒!听后我心里酸酸的,泪水禁不住涌上眼眶:一个任劳任怨的丈夫,一个兢兢业业的父亲,就这样在一张凉席上离世了。
逝者已去,不管过程如何,他终究卸下一身尘埃,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之旅。今天,在这样一篇难以登堂入室的文章里,我没有将他的名字标明,通篇只用“他”称呼,我想,如果世上真有魂魄,即便不标明,他也能知道我写的是谁,知道我心里有一缕不散的哀思。如果世上没有魂魄,即便我标明了他的名字,对于他那些活着的家人,以他们冷漠的眼光来看,也绝对谈不上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