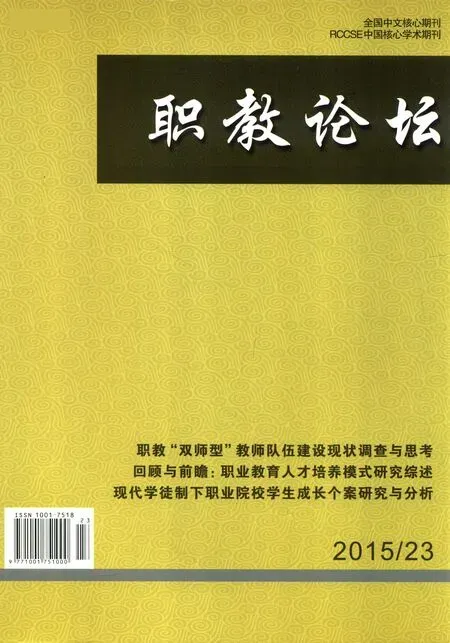基于国际比较视野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研究
2015-01-31孙晓庆
□孙晓庆
基于国际比较视野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研究
□孙晓庆
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平衡和调动利益相关主体的力量,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文章通过实地考察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学院的治理模式改革,以及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职业教育治理制度的源流及创新发展梳理,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角,充分吸收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精髓,提出了我国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关键领域改革的举措,加快构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保障和运行体系。
治理;国际视野;比较;高职院校
我国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745万学生、63万教职工、1321所高职(专科)院校[1],科学的治理手段成为满足社会转型升级亟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诉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我国治理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和实证研究,对高职院校治理现实改革指导力度不大,举步维艰。通过实地考察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学院的治理模式改革,以及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路径的梳理,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角和分析思路,提出了我国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关键领域改革的举措,加快构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保障和运行体系,为提高职业院校治理能力提供了国际视野和有益借鉴。
一、高职院校“治理”的要义
汉语“治理”,在《辞海》中的释义是管理,《商君书·更法》:“治世不一道”[2]。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在传统体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涵义逐渐被突破,特别是欧洲联盟的缔结,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市场的繁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公民精神生活的追求及民主意识的觉醒,诸多因素丰富和拓展了“治理”的内涵。治理成为一个持续互动、协调行动的过程。治理理论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管理方式中行政调节的强制性手段,通过利益相关者主体的联合行动,创建协同、多元的治理结构。
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要义强调的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过程,关键在于设计合理的章程制度,平衡利益相关者对决策权的配置,明确权力分割、责任分担与利益分享,激发大学的本质功能和学术创造力。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对“治理”的要义界定,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规范办学行为和行政权力,“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完善体现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特点的绩效考核内部分配机制。”[3]第二种则是倡导通过共同治理来平衡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4]这两方面的阐述都是基于权力的平衡来实现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目标。由于各国制度受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治理机制在实践运行中不断发展完善,可以进行结构比较和适应性选择借鉴。
二、发达国家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治理实践
(一)德国职业院校治理制度凸显学术自治
追溯整个德国大学治理制度的源流,1348年德意志皇帝卢森堡家族创办布拉格查理大学,标志着德国高等教育正式诞生。19世纪初,在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新人文主义影响下,形成了包含“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新理念,由此确立了德国大学极力维护的核心价值,其根本目的在于唤醒对人性的尊重,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突出人的成长发展,把教育与人的自由、尊严、幸福及终极价值联系在一起。1810年,卡尔·威廉· 冯·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今称柏林洪堡大学,“学术自由”的思想贯彻于大学理念,“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得以深深扎根于德国大学的土壤,不仅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近代全世界大学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德国大学带来巨大影响,政府控制所衍生的行政权力开始出现强化。1990年,德国的统一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教育领域的突出显现是1998年德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总纲法》第四次修正法案,对联邦政府“失去的权力”和“保留的权利”作了重新界定。各州拥有了包括工资、待遇、绩效改革的决定权等,联邦政府无权介入。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州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掌控过大,高校自治权力普遍缺失。2008年10月,废除《高校总纲法》,德国高校自治成为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内在性诉求,推动了德国高校治理进程。现行的《德国基本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大学享有的学术自由权利。笔者此次考察了德国萨克森州,萨克森州早在1993年出现了治理领域的崭新名词“高校委员会”,对德国各联邦产生了辐射影响并逐渐普及。通过考察位于萨克森州中西部的米特韦达应用技术大学,及对德国其他应用技术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研究发现,德国高校不设董事会,校务委员会作为高校最高权力机构,“制定各校校内规章制度、学校发展战略、机构设置、人事任用、财务收支以及推荐与选举并罢免校长委员会成员。”[5]德国的大学教授既是一种职称,又是一种终身荣誉。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占有绝对优势和核心地位。应用技术大学治理结构第二层是负责学校运行的行政机构,主要由大学治理的核心人物校长、副校长等组成,校长、副校长在正教授中产生。第三层是教学研究组织,机构精简,运行高效,充分保障了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突出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不仅是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另一条主干路径职业学院的治理结构,同样凸显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双重制约。理想的院校治理使“双元制”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成为德国制造的坚强后盾。
(二)美国高等职业院校推行共同治理模式
美国高校治理制度受三权分立政治制度运行和制约的影响深远,同时受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求,不断学习欧洲大学制度和治理经验,对治理模式进行不间断创新。美国高职院校治理从最初的以董事会为主导,拓展到以校长为主导。当前,形成了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和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评议会,外部控制权、内部管理权各司其职、共同依存的美国大学治理结构,达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均衡匹配。此外,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同时对大学治理发挥积极影响。由此可见,美国大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实现的是内外部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充分发挥了大学自治、专家治校和学术自由的有机结合。美国由此形成了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同时学术型治理并重的大学治理模式,影响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是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社区学院的管理权限在于各个州。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把握着最高政策和发展方向。董事会由校外知名人士组成,能多方考虑政府、社会民众多方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拓展资金筹集渠道,确保并有效管理各种资源。董事会可以任命校长,社会也通过董事会监督大学,但董事会不能干预大学的日常事务。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委员会处理大学日常行政事务;由评议会处理学术事务,成员包括教授或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层,涵盖管理层、行政人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多个群体。美国社区学院有效形成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立、协调与有效制约的治理模式。美国社区学院共同治理体现分享理念,强调教职工和学生利益诉求的民主监督,并通过完善的司法制度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力。美国社区学院的“共同治理”,客观上为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实现终身教育的社会理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澳大利亚高等职业院校的董事会治理
澳大利亚大学治理模式受英国影响较深,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大学基金制拨款模式的国家[6]。英国大学基本不受行政权力干预,是一些自治机构。澳大利亚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模式类似于英国1992年之前成立的大学治理结构,包含了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独立机构。澳大利亚联邦或州政府把治理的权责机构赋予校董事会,执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和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辅助决策制度。澳大利亚TAFE学院(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办学实体,经政府认可并接受政府监督,主要由各州政府管理。澳大利亚TAFE学院紧贴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主动服务学生成长发展需要,TAFE学院的治理体系,主要基于政府牵头,由行业技能委员会主导,学校、企业、行业、社会专家、顾问共同参与制定职业教育能力标准体系,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严格执行人才标准,严格执行培训质量认证体系和拨款应用体系。
董事会作为TAFE学院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发展战略、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向,负责院校的业绩管理、监督评估、财务管理、问责体系等。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负责,是学校的首席执行官和法人代表。著名高等教育管理评估委员会《Hoare报告》对澳大利亚治理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认为董事会组成规模一般在10-15人之间为宜,组成原则必须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代表,以有效行使推进职业教育改革、质量监控、服务政府、取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等内外部治理权责,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董事会下设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机构,各专门委员会按照职责权限行使权力,对董事会负责。校务委员会拥有重大事务管理监督权力,聘任常务副校长为首席执行官。学术委员会决定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权力,进行内部质量监督,以维持大学教学及研究水准,保障高校学术自由。澳大利亚TAFE学院治理结构划分明晰,权力运行上建有相互制衡机制,确保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地位与声誉。
(四)日本高等职业教育法人化治理结构借鉴
亚洲近邻日本在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结构上有一定的创新之处。日本高校治理制度经历了明治维新时期、帝国大学时代、战后学习美式教育制度等时期。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不断增强,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亟需大量实业型工业技术人才。日本因此建设了一批以实业为主的专科学校。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以高等专科学校为主,此时高等专科学校治理机制上行政权力占据主导之势,实行严格的集权管理。在一段时间的学习模仿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治理模式后,2000年以后,日本逐步走出了一条治理改革的创新之路。
2003年,日本公布和实施了 《国立大学法人法》,此举标志着日本高校治理进入法制化阶段。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后,政府控制方式由之前的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政府主要通过第三方评价方式对教学、科研和经营方面的业绩进行核查评估,决定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日本全国共有各类大学778所,其中16%属于技术类院校。”[7]日本政府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企业培训的作用也非常凸显。在高等专科学校的治理机制设计上,重新定位、科学划分了文部省与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权限,吸收了校内和校外人员共同参与,包括校长选考会、理事会、经营协议会、教育研究评议会的构成。从法人化后的治理设计来看,校长任命方式不再是教授会选举,而由校长选考会由校外人士参与、文部省任命,校长成为法人代表、法人运营和大学运营的双重职责,使校长的权限得到增强。教授会依旧保留关于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任免的审议权,保障了学术权力,为学术自由奠定了前提。经过摸索创新,日本基本形成了法人(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治理结构机制。
三、我国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的适应性选择与创新实践
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决定了高职院校治理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治理模式经验,为我国致力于构建形成政治、行政、学术、民主等力量良性互动的现代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选择和借鉴。
(一)加大政府简政放权,明确权力界定实现共同治理
近年来,中央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政府由直接管理逐渐向间接管理转变。围绕怎样扩大和落实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根据产教深度融合的要求,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办学,鼓励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高职院校事务,明确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职责权限,目标在于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推进高职院校治理结构改革。同时,建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合理确立大学内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利。在确定和保障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上,关键在于加强学术权力的决策机制,允许教职工、学术、校友会成员代表共同参与学校治理,共同分担大学的事务与责任,加强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事务的监督和制约。以教师为根本,在资源、待遇等方面突出教师的教学科研应有的地位,充分保障教师的权益。把学生的需要作为高教改革关注的重点[8],把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学生的尊严、价值和出彩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依靠院校章程制定,发挥章程作用实现有效治理
建立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是规范高职院校治理的必要条件,根据国家及地方教育法律法规制定的进程,及时做好高职院校章程的制定工作,既要体现特色,彰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又要明确权、责、利的边界与利益机制。高职院校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学校,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根本制度保证下,坚持科学定位、分类培养、特色办学,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建立一套科学的治理体系,真正办成一个自我约束、自主发展、自主办学的实体。日本现代大学制度把学术自由上升到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上,《学校教育法》对教授会作了明确的法律定位。我国高职院校在章程制定中也应明确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作用及运行机制;制定师生听证会制度,保障师生对学校重大改革发展问题及学校干部人事任免的参与、监管权;逐步实现党委领导、行政领导的民主选举,合理配置和制衡政治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做到学术自治、职责清晰、民主科学,使各项权力既相对分立,又相互制约。
(三)围绕教育现代化目标,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围绕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首先必须理顺政府、教育和学校的关系,创新体制机制,切实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教育治理的能力。高职院校治理必须关注教育质量和内涵建设,把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作为核心任务,通过创新创业引领支撑新科学新技术,加快学校治理结构机制改革,激发主体内在潜力,自我完善,自主发展。其次应该加快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建立专业与产业行业的关联,建立动态适应的社会机制,以学生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提高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再次,应建立和强化独立的高职教育绩效评估和监督机构,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第三方组织,彰显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唯此,高职院校才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体现科学治理、依法治理和民主治理,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教育统计数据全国基本情况(截至2014年12月15日)[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 business/htmlfiles/moe/s8493/201412/181591.html.
[2]辞海(第1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101.
[3][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4〕19号.
[5]俞可.在夹缝中演绎的德国高校治理[J].复旦教育论坛,2013(5):14-20.
[6]孙晓庆.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标准与绩效评价比较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4(3):128-130.
[7]寺田盛纪(著),闫智勇,等(译).日本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亚洲区域内国际比较视野中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2(7):81-87.
[8]赵德武.高等教育新常态与教育改革创新[N].光明日报,2015-1-6-(16).
责任编辑时红兵
孙晓庆(1980-),女,浙江余姚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与绩效。
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基于国际比较视野的高职院校教育治理结构研究”(编号:2014YGH126),主持人:孙晓庆。
G717
A
1001-7518(2015)23-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