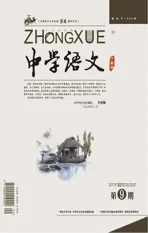《木假山记》主旨探微
2015-01-31秦志强
秦志强
苏教版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选取了北宋散文家苏洵的一篇杂记小品———《木假山记》。文章所记述的只是家中一件小摆饰,乍一看,似非深文,亦无大义。然而,笔者在听了几位同事执教该文的公开课之后,对于本文意旨的挖掘似乎总有一种余意未尽的感觉。自己在反复研读该文的基础上也执教了一节公开课,经再三揣摩,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在看似寻常浅近、自然随意的文字背后,却融入了作者深长的用心,悠远的寄寓,不尽的意蕴。
下面,我们不妨仔细来品一品本文究竟包孕着哪几层意思?
1.对人才遭遇的悲悯
文章起笔并没有将笔墨聚集到“木假山”,而是放谈“木之生”,讲述树木的种种不幸:先写树木“或蘖而殇,或拱而夭”,“任为栋梁则伐”,风拔水漂,“或破折或腐”;继而写“为人之所材”,遭“斧斤之患”;最后写幸运者也不免“漂沉汩没”,被“激射啮食”。作者似乎在写木,其实他是在写人,在写人才。在中国文化里,人们常常将“木”和“人”连在一起,甚至相提并论。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木材”“人才”常常互喻,优秀的人才被比作“栋梁”。正因为这样,讲述树木的种种不幸,其实也就是在讲述人才的不幸。作者机巧地采用由木及人,以木喻人的手法,从树木九死一生的坎坷遭遇,暗示了人才历经磨难,时遭毁灭的境遇,由此生发同情悲悯之心———人才的成长何其难也!
2.对一家身世的庆幸
文章第二节主要写木假山历经坎坷而幸运地到了我家,成为家中案头的珍品。众多的树木或“殇”或“夭”,被砍被伐,风拔水漂既不破折也不腐烂,既没有遭“斧斤之患”,又没有被“人之所薪”,还竟然被“好事者”发现,被雕琢成一座假山,被置放于家中案头。木假山这份传奇的历程,与他们父子历经风波困厄而优裕地供职朝廷,岂不是有着太多的相似相通之处?像树木一样,他们小时候没有饿死早夭,长大后没有被伐除扼杀;虽然历经人世间的风吹雨打,却没有堕落沉沦;虽然一度被埋没,还能被“好事者”发现启用,得以免于被毁弃的命运。就木假山而言,相比起众多被埋没被毁弃的不幸者,它是幸运的;就他们父子而言,相比起众多被埋没被毁弃的人才,他们也是幸运的。木假山之幸,其实正象征着父子三人的一门之幸。作者把这种幸运视为冥冥之中的“数”和“理”。这自然让作者既感慨万端,又庆幸不已。
3.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文章中说:“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可见,面对木假山,作者常常凝思遐想。从三峰形态,他看到父子三人的影子,这种外在之形的相像,加之数目上的巧合,让他心生喜爱。作者笔下对三峰做了人格化的描述:“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不难发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的中峰显然是隐喻自己,“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的二峰显然是隐喻两个儿子。从木假山三峰各自的神态,他又似乎看到父子三人共同的人格精神———端庄伟岸,高傲舒展,严肃峭拔,凛然难犯,无所阿附。这种内在之性的相通,让他心生敬意。我们既可以说这三峰像他们父子三人,也不妨说他们父子三人就像这三峰。这种外在与内在高度一致与冥然巧合,让作者完全把木假山当作他们一家人遭遇命运和人格心灵的象征,木假山其实就成了他们父子三人的精神雕塑和人格符号。对木假山三峰所显示的品格的爱与敬,寄寓了父子三人对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和不卑不亢的生命姿态的追求。
4.对文人宿命的感喟
第三小节两次写到“有所感”:“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其可以有所感也夫!”作者在文中欲言又止,想说而终于没有明说。那么,他到底有何感?又为何没有明写?这是很值得深究的。而苏洵创作此文,时年五十。“闻将召试舍人院;召命下,苏洵上书仁宗,拒不赴试,谓‘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答梅圣俞书》)由此可见,苏洵身在官场却不醉心于官场,想有作为,其抱负却终究难以施展到有价值的地方,虽有“好事者”发现,却“强之以为山”,最终成为了跟木假山一样的摆饰。在当时,不知有多少人才身处厄运甚至被无端毁掉,这是大不幸,固然可悲可叹;偶尔有一个两个被“好事者”看中取用了,却被用来装饰门面,供人赏玩。木假山的这番境遇岂不是让自然作者发生了相关的联想?自己其实不就是一件朝廷内的一件摆饰吗?如今自己沦落到一个摆饰的地步,这是不是一种埋没?算不算一种不幸呢?生命虽然没有遭到毁灭,似乎值得庆幸,可是年华空度,既未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岂不是同样可怜可悲呢?这样说来,从木假山的命运苏洵照见了自身的命运,从他自身的命运照见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苏洵的眼里,木假山是他们一家命运的缩影,更是天下所有知识分子命运共同的缩影,似乎很幸运,其实又是大不幸,用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这奔赴心头的万端感慨里,既有悲哀,也有无奈;既有怨叹,还有不满。这是作者不想明说、也断然不敢明说的事。于是托不尽之意于言外,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涵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