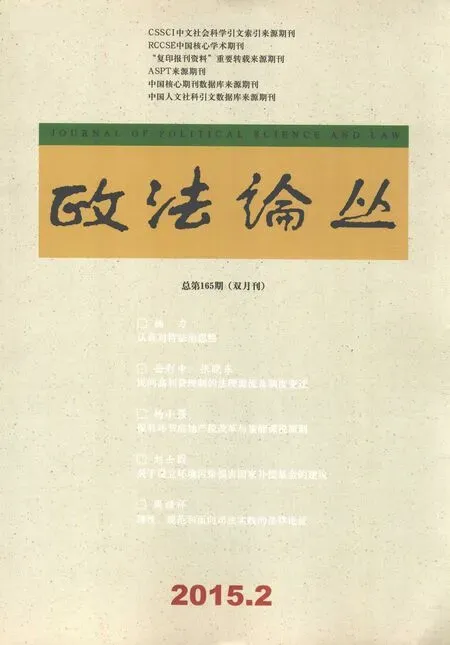依法治国背景下南海争端解决的国际司法途径探究*
2015-01-30杨猛宗刘万啸
杨猛宗 刘万啸
(1.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87;2.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依法治国背景下南海争端解决的
国际司法途径探究*
杨猛宗1刘万啸2
(1.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87;2.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法治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建立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的重大现实需求。依法治国也包括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等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应该成为我国的重要选择之一。我国应加强对高端国际法人才的培养、选拔,并积极向国际司法机构输送相关人才,增强我国运用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
依法治国 南海争端 国际法院 国际仲裁
一、问题的提出
南海亦称南中国海,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多年来南海周边各国与中国就南海海域中一些岛礁一直存有主权争议,并伴随着相关领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争端。在主权争议比较明显的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9个,其中中国大陆占8个,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加之近些年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权益的积极行动,同时美国的外交战略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亚洲,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愈显变幻莫测,如处理不妥,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这已明确写入1997年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和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在金边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以中国的九段线①违反《海洋法公约》为由,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议提交给根据《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法庭,要求进行强制仲裁。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外交部如期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呈交了陈情书和诉状。菲律宾等有关国家正在或者试图通过采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与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对于菲律宾单方面并强推对我国提起的仲裁案,我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②2014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受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重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严正立场,并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③这与中国政府一贯拒绝通过法律途径(司法或仲裁) 解决海洋争议的立场是一致的。对于该仲裁案,学界的观点则出现了一定的争论。对于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仲裁案,有些学者提出,不参与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仲裁庭最终建立起来,则中国应出席仲裁庭,坚持反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1]相反,也有学者认为,“仅就九段线争议而言,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笔者认为暂时不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学者称,“从本质上讲,是否诉诸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取决于在具体条件下该途径能否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九段线的法律性质,该学者主张持“历史性水域说”,认为根据《海洋法公约》,通过国际仲裁途径解决九段线问题并不利于我国的利益最大化。[2]其实,关于九段线的法律性质本来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中国政府(包括之前的民国政府)并未给出明确的定性,在学术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④如果一味坚持九段线的中国利益最大化的主张,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在法理上都很难站住脚,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将势必引起南海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等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那样,不仅我国的主张无法实现,而且很可能使我国在道义上陷入孤立,使中国丧失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丧失和平崛起的大好时机,这将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更大损失。中国历来主张合作共赢,如果一味强调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势必造成其他争端当事方利益的最小化,不可能实现南海各国的合作共赢。就本案而言,中国“不参与”可能会符合中国暂时的国家利益,但也会被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仅欲依靠强权获取更大的海洋利益,而不敢通过国际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会被进一步认为中国的主张在国际法上难以立足。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不宜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但并非其他海洋争端都不适合通过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因此,本文并非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本身作详细探讨,而是就中国与南海邻国间海洋争端的国际司法方法作一般性探讨,以期为我国将来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提供更多可选择的途径,以为中国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并不存在专门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决机制,但在国际法范围内,除国际法院与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之外,还包括全球性和区域性两种可以适用于南海争端的解决机制。[3]P39-40前者为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确立的有关解决海洋争端的程序机制,后者为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四章确立的有关和平解决东南亚地区争端的程序机制。[4]本文所称的国际司法途径,包括上述国际法院和仲裁等依据国际法对争端做出裁决的手段,也可称为国际法律途径。
二、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之缘由
我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南海争端,认为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解决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5]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地位及重要影响力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强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在遵守国际法规则方面做好表率,而且在引领国际法规则方面发挥更好的表率作用。因此,通过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等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应该成为中国的重要选择之一。选择国际司法手段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南海争端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在多元化的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版本之中,国际社会秩序的法治化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首要选择。国际法治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法律受到普遍的尊重,法律既可以约束大国的强权,也可以给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行为体以明确的预期。国际法治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问题发展的一种未来图示,不能仅仅停留在规则形式和操作程序层面。[6]法律最基本的功能是建立一种秩序,一种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判断是非曲直的法治秩序。国际社会同样需要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构建国际法律规则为框架的国际法律秩序,通过制定和执行稳定的国际法律规则来促使整个国际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随着国际社会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进步以及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各国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跨国市民社会”的雏形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现代国际社会需要采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包括国家间争端在内的国际问题。通过国际司法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是一种重要手段。
追求正义是现代法律一个普遍的价值追求目标,国际法也不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价值定位,已经不是以“国际正义”(国家间正义)作为唯一价值追求,而同时还要兼顾强调个人人权的“个人正义”(或称“人类正义”)和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的“全球正义”。[7]P67在追求“国际正义”的基础上,适度兼容“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两种价值观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发展的适当价值定位。同时,正义的价值观的定位调整必然带来现有法律秩序的革新问题,而“秩序”的革新正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发展的进一步发展方向。[8]P128在现代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每个个人获得和平安全环境的“人类正义”以及全人类追求良好安宁秩序的“全球正义”,这不符合当代国际法治所追求的正义。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不会也不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贯的立场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当事国谈判协商手段友好解决南海争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已经明确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要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国际司法途径是人类文明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亨金(Louis Henkin)教授在谈到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说:“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看看18-19世纪欧美列强的某些对外宣示, 拿它们与当代的国际潮流对照,可以清晰地发现: 战争从被强权者直言不讳地加以赞美和无所顾虑地加以运用的征服工具, 逐渐变成受世人憎恶、被绝大多数国家和公众共识所抨击的野蛮手段(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逃道义的这种责难, 如果它在使用武力时缺乏国际法理依据的话)。[9]我们不畏惧战争,但我们更应该避免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动性地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是避免战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国际司法途径可以避免冲突甚至军事冲突,避免争端升级,避免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技术、资本、人员及应对全球反恐、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合作越来越紧密,而且为了使这些联系与合作成果加以固定和完善,国家之间建立了相应的国际组织,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制度,同时还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状态,这些都离不开法律的调节与规制。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这种规范化的融合,除了谈判、调解等方法外,还要求国家之间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全球化时代进步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主流国际法理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 即抑制国家的专制、尊重个人的权利、培植公民的社会主体性以及在国际社会形成批评和抵制霸权的氛围。国际司法途径是抵制霸权的重要手段,是当今文明社会解决争端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大趋势。
(二)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也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参与全球治理的梦想,是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内外政策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对内“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并且强力反腐败,对外则展开积极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庄严昭告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中国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可以树立中国在国际上遵守国际法、爱好和平的良好形象,可以更好地反击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综合实力的逐渐增强,一些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国家和人士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开始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及海洋争端的不断升级,目前中国政府甚至民间捍卫领土主权及国家利益的态度更加坚定和强硬。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对内一心搞好经济建设,“广积粮”,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对外则“不称王”,以便创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人的上任,中国在对捍卫国家利益方面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比如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了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在与菲律宾有争议的黄岩岛对抗中也采取了强硬措施。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手段,中国的行动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特殊时期,这引起了美国、日本等强国的不满,更加剧了与我国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相邻弱小国家的担忧和焦虑,甚至引起了某些与我国并无争端的国家的担心,担心逐渐强大的中国将来在对外关系上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目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不断增强。比如,2014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到中日关系时,称当前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有相似之处,当时英德虽然贸易往来密切,但还是发生了战争,中日需要引以为鉴。安倍晋三将目前中日关系比喻为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⑤当然这是日本领导人的居心叵测,故意混淆视听,试图煽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和焦虑情绪。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这一关键时期,我们不能进入那些居心叵测之人的圈套。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民间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声音更是不断增强,比如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等领土问题上,网上绝大部分网友的言论都是强硬派,很多人表示,不惜一起代价捍卫领土完整,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言论表面上看似爱国,但实际上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严重破坏,成为某些居心叵测散布中国威胁论国家的把柄。中国政府对民间的爱国情怀应予保护,但应该进行合理引导,而不宜骄纵,否则将会使中国陷入不利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
若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建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寻求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⑥以“仁”为核心精神的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儒家文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和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良好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观的基础。这种和平发展观的基础要求我们,与天下人和平相处,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规范来影响和改变天下,形成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王”道,而非“霸”道。《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最终目的是让世界太平,让人民安居乐业。当然,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有影响力,仅仅靠文化软实力是不够的,文化软实力发挥作用离不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但是,如果仅仅靠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往往会形成强权,此乃“霸道”,即当今世界之霸权主义。霸权主义者刚愎自用,依靠自身强大实力为本国夺取利益,而损害他国之利益,必将引起他国的不满,徒增国际争端,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追求世界和平的“王”道的和平发展观,则是在依靠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影响力的基础上,推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行为规范,倡导世界各国友好和平共处,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非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通过国际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国际法院或者国际仲裁等相关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实力较弱的国家更愿意采取的手段,而作为实力强大的大国往往不愿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更希望依靠自己的强大实力通过谈判或者其他更强硬的手段来解决,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不仅是大国政府的意愿,更是大国普通民众的心态。当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时候,普通民众狂热的强权心态很容易对政府产生影响,即使政府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却往往被一些普通民众视为软弱的表现,从而被民众不信任,影响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在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一个缺乏和平仁爱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强势独裁领导人往往会引领这个国家走向侵略和战争,从而带给世界灾难,二战时期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即是典型例证。通过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非软弱的体现,乃是自信的表现,是对国际法的尊重,是对争端对手的尊重。如果不敢通过国际法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才真正是心虚的表现,不自信的表现。通过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也是大国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的机会,获取实力较弱国家的尊重。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均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争端处理不好,很可能会给全世界造成中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形象。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12个字。“仁”意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时小国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或得寸进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是理想的相处之道。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未来的课题是如何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10]要做到大而可亲,首先要平等相待,不居高临下,愿意平等地与周边国家坐下来谈判争端,包括愿意采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对于菲律宾关于将与中国的海洋纠纷提交国际仲裁的争端,我国并非不可以考虑出庭应诉,在法庭上主张中国的合法权利,并通过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和国际法依据来驳斥对方的无理和非法诉求。如此,既维护了我国的合法权利,又树立了中国遵守国际法、愿意通过国际法律途径来解决国际争端的良好形象,反击中国威胁论。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南海争端处理不好,不仅会造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而且可能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环境,影响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是一个快速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 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履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各种义务,‘和谐世界’的倡议最后就可能落空。”[9]正如一个国内法院案件当事人不能因为对法院某个判决的不满而拒绝所有法院的判决,或者不相信所有法院的判决。也许在某个具体纠纷的裁决中,中国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公平待遇,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拒绝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中国失去的可能是某个具体案件的合法利益,但中国可能会因为遵守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而树立了遵守国际法的良好形象,赢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某个具体案件的利益损失相比,这才是中国的更大利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尊重国际法规则,尊重国际司法机构做出的合法裁决,才能赢得争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三)积极利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也是我国建立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重大现实需求
早在古代希腊城邦就已发展出一套体系, 通过中立的第三方解决争议。然而, 这一时期超级大国的崛起(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 中断了这种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占据权力优势的大国对争端倾向于武力压制甚于和平解决。 可见, 大国家不喜欢国家司法古已有之。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 特别是从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重大国际法律规范的态度着眼,不难发现一条明确的线索, 即新中国早期毛泽东时代对于国际体系的态度是某种“拒绝”或“观察”, 邓小平时代改成“加入”与“适应”, 到现在变成“争取更大发言权、承担更多义务”。[9]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也应该随着世界大环境和中国自身环境与实力的变化而改变。以往的中国,经济军事和综合实力不是很强,对于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从能力而言,1949建国初期,中国经历了连年战乱,百废待兴,而且对于一个从未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建设,需要不断摸索,在自身经济和制度建设中走了很多弯路,比如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我们即使想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既没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来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也缺乏制定这些国际规则的专家。随着文革的结束,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一心搞建设,韬光养晦,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有“只管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势,中国自身经济欠发达,需要专注于自身建设,基本无暇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更毋说是引领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国际社会规则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唯有有实力和负责任的大国才有能力和有意愿来提供,而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成员没有这种实力和主动性去制定和引领国际社会规则,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心态。今天,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大国,而且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是当今和未来中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必然而且也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既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应该是遵守国际规则以及引领国际规则。因此,中国不应仅仅是满足于遵守现有国际法规则,而且更应该成为国际法规则的积极参与者和提供者。在国际法律体系中,今日之中国,已经由原来国际法律体系外的“叛逆者”到国际法律体系内的“被动参与者”,再到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身份的改变必然导致中国对国际机构和国际法律规范态度的根本转变。认真遵守乃至主动塑造和维护重大国际法规则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构、国际法院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等通过国际法律手段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将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现代国际司法是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的产物。作为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的大国,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可以为其他国家解决国际争端树立良好的榜样,引领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司法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避免战争,为中国及世界人民获得和平的生活环境,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⑦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议题,是全世界的核心价值。如果中国自身不相信和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组织解决争端的重要法律手段,中国将难以在国际上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难以在国际上树立权威。
我国当代领导人很重视国际法。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构想的基本要素及追求的目标与当代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及发展趋向是一致的、相通的。国际法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法律保障。[11]习近平主席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发表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⑧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以全球性的开放视野为国际法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责无旁贷。
中国不仅要成为国际法治的践行者,更应该成为国际法治的引领者。只有有实力而不去动用军事实力的国家才有能力践行国际法治。只有有实力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引领国际争端通过国际司法途径来解决,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小国弱国当然不希望通过谈判、调解等手段来解决与强国大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因为它们的谈判实力有限;小国弱国当然更不希望通过武力等强力对抗手段来解决与大国强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因为在武力对抗中它们更没有便宜可占。反观强国大国,更希望通过谈判调解甚至武力对抗等直接手段来解决与弱小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因为通过这些手段对强国大国更有优势,而通过国际司法途径来解决与弱小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不如通过强力手段解决对大国强国更有利。历史上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基本都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的。因此,有人认为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这种历史眼光看问题的方法,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用战争手段,并不意味着现在和将来就一定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只有大国强国才有能力阻止战争。当然,解决南海争端最理想的途径是争端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的方法解决,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争端本身很复杂,再加上双方国内各种势力和民众舆论的严重分歧,争端当事方政府可能很难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和解,尤其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往往民众对谈判胜利结果的期望值过高,不能容忍政府作出适当的让步,而作为弱势的一方的国内民众对于本国政府作出的妥协让步更是视为示弱的表现。因此,在双方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双方就争端问题更加对立,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引发冲突,更严重者可能会擦枪走火,发生严重的地区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对争端当事国和地区及世界和平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而国际司法的方法,则可以降低公众对裁决结果的期望值,减少争端双方政府的压力。通过国际司法途径文明地解决争端,使得双方继续保持正常的关系。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总体上将表现出更为强劲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进取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改变在某些问题上被动应对、隐忍待机的做法。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来在与南海周边国家争端方面一定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随着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中国已经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引领国际社会规则包括海洋法规则的制定和解释。作为有实力和负责任的大国,运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国际主权、安全和利益,应该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三、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我国在主观上对国际司法手段缺乏信任
我国目前从民间到官方,尤其是官方,普遍对通过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及国际仲裁等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存在不信任感。很多人认为,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是在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将国家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机构解决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利益。实际上,国际法院的15名法官组成要考虑到地区均衡,尤其是照顾到世界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据此原则,亚洲三名,非洲三名,拉美两名,西欧、北美、大洋洲五名,东欧两名。而且作为特权,作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一直在国际法院有人担任法官。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有中国人担任法官。在对外关系中,我国历来主张并积极实践以谈判和协商、斡旋和调停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仲裁,我国自建国以来很长时间内一直不接受任何仲裁条款。八十年代后期,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非政治性国际条约中,才开始接受仲裁条款并有实践。同时,我国也历来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八十年代开始以来,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对有关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由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一般不作保留。[12]在菲律宾将中国提起国际仲裁的案件中,我国官方的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当然,这里既有我国对国际仲裁的不屑,同时也有对国际仲裁结果的不自信。任何案件的仲裁结果都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一种比较文明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有效方法,我们应该习惯于运用它。
(二)我国目前缺乏能够参与国际司法途径的人才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通过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等司法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不信任,导致我国能够参与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人才培养方面重视不够。因此,我国目前既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又有能力参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程序规则的人才比较缺乏,反过来更加剧了我国对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不自信。因此,为了适应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实际需求,积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能够胜任参与国际诉讼和仲裁的国际法律人才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一项紧迫任务,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有效条件。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地位及重要影响力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强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在遵守国际法规则方面做好表率,并且应该习惯于运用国际法律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作为现行国际规则适应者、接受者的角色还没有真正改变,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不相称。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做国际规则的维护者,还要做国际规则的建设者,这既是维护我国发展利益、营造良好国际形象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支持国际法院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履行职能。曾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大法官表示,今后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考虑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综合运用外交和法律方法解决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争端。⑩因此,通过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等国际司法手段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应该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同时,我国应加强对高端国际法人才的培养、选拔,并且向国际司法机构输送相关人才,增强我国运用国际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
注释:
① 九段线是中国在南海“海疆线”的一种叫法。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在其编绘出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未定国界线标绘了一条由11段断续线组成的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也标绘了这样一条线,但是将十一段断续线改为九段断续线。
②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中方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就南海争议单方面强推仲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6/c_119961856.htm,2014-11-30.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7143.shtml,2014-12-22.
④ 关于九段线的法律含义有不同的主张和解释,大体分为以下四种:1.国界线说,认为该线划定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范围,线内的岛、礁、滩、沙以及海域均属于中国领土,中国对它们享有主权;线外区域则属于其他国家或公海。2.历史性水域线说,认为中国对于线内的岛、礁、滩、沙以及海域均享有历史性权利,线内的整个海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3.历史性权利线说,认为该线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所有权,这一权利包括对于线内的所有岛、礁、滩、沙的主权和对于线内内水以外海域和海底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承认其他国家在这一海域内的航行、飞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自由。4.岛屿范围线说,认为线内的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受中国的管辖和控制。参见《解析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前世今生》,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2-07/1022763069.html。
⑤ 外交部:“安倍现在要做的是承认错误、改弦易辙”,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3/c_119104842.htm,2014-11-5.
⑥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
⑦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
⑧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发表讲话。
⑨ 2014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向“强势中国”演变,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40303/n395931333.shtml,2014-8-7.
⑩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国际法院不可小觑,人民网.http://view.news.qq.com/a/20120509/000027.htm,2014-12-4.
[1] 余民才. 菲律宾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程序与中国的应对[J].现代国际关系,2013,5.
[2] 张磊.对南海九段线争议解决途径的再思考——兼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J]. 太平洋学报,2013,12.
[3] John Collier,Vanghan Lowe.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 罗超.南海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框架初探[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5] 蔡高强,高阳.论解决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
[6] 何志鹏,高胡.作为国际法研究方法的批判现实主义[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3.
[7] [英]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8] 刘志云.直面正义纷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路径——以赫德利·布尔的正义理论为分析起点[A].刘志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二卷)[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9] 王逸舟.重塑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关系——面向以人为本、社会为基的国际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4.
[10]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做“可亲的大国” [EB/OL].http://news.sohu.com/20140303/n395931333.shtml,2014-08-07.
[11] 张谦.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与国际法价值[EB/OL].http://www.gmw.cn/01gmrb/2007-08/07/content_651425.htm,2014-12-2.
[12] 王虎华.论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与实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责任编辑:唐艳秋)
Research on Solvi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Judicial Means
YangMeng-zong1LiuWan-xiao2
(1.Law Schoo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
To solve the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international judicial mean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is also the real requirement of realizing the dream of Chinese nation, that is, the rejuvenations of Chinese nation. Meanwhile it is also our important and practical demand to establish a responsible and powerful nation in peaceful rising. The rule by law also includes the use of legal means to protect China’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interests. To solv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rough international judicial means such as litig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oices in China.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op talents who are good at international law and actively transport related personnel to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and should enhance our ability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judicial means.
rule by law; the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002—6274(2015)02—103—08
*基金項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洋法公约》与中国海洋争端解决政策的选择研究”(13BGJ043)的阶段性成果。
杨猛宗(1977-),男,江西临川人,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及法学方法论;刘万啸(1971-),男,山东聊城人,法学博士,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DF93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