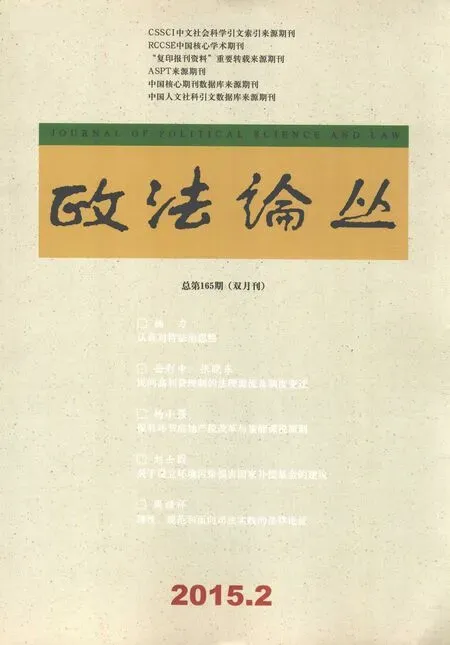刑法亟需确立全面保护原则*
2015-01-30王占启
王占启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刑法亟需确立全面保护原则*
王占启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实现“民主刑法”、“ 公民刑法”、“ 保护刑法”的价值追求,刑法应当确立全面保护原则,保护公民、单位、社会和国家的法益,对公民法益的保护应处于优先地位。确立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有民主主义、人权理论、限制刑罚权思想的根据,但其必然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应该坚持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入宪,在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刑法既要全面保护公民的法益,又不得对罪犯适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残酷刑罚。”并在刑法立法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补充刑法总则的法律空白,开展合理限制下的犯罪化,还应对刑法解释进行规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
法益 全面保护原则 根据
从刑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刑法的发展趋向是文明、人道、轻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刑法具有不同的刑法原则,而刑法的原则从属于刑法的性质。从刑法的性质上讲,中国刑法实际是从“集权刑法”向“民主刑法”、从“国家刑法”向“公民刑法”、从“惩治刑法”向“保护刑法”转变,而“民主刑法”、“ 公民刑法”、“ 保护刑法”①除了要求传统的刑法基本原则之外,还要求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
一、 时代呼唤刑法的全面保护
现代社会中的法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是法益主体的复杂性,不仅包括国家、社会公共、公民个人,还包括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二是法益种类的复杂性,不管哪一种主体的法益都是多样的,尤以公民法益最为复杂多样;三是法益的交叉错杂,一个犯罪行为可能侵害不同主体的多种法益。当前法治国的建设给刑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刑法不仅必须是良法,还同时负有艰巨的全面保护法益的任务。
(一)刑法的目的呼唤全面保护原则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在刑法的目的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的伦理秩序。“保护法益说”一直是最有力的观点,是刑法理论体系的根基。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指出:“刑事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利益。”[1]P223平野龙一进一步指出:“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和财产利益,满足公民的保护需要。”[1]P268“保护社会伦理秩序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②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孤立、对立,实际是适应不同社会阶段、不同国情的产物,“保护法益说”是在民主社会制度起始阶段,针对旧刑法维护专制统治而产生的,它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只有侵害法益的行为才能规定为犯罪。“保护社会伦理秩序说”则是在对“保护法益说”反思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认为“保护法益说”强调了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刑法保护,忽视了对社会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所以,两种观点的实质都是保护法益,不过强调保护法益的侧重点不同。
英美刑法虽然没有保护法益的理论,但就其刑法规定来看,保护法益也是其主要目的,在立法规定上更是竭尽全力,甚至“立法者为了保护公众利益与公共安全的政策性考虑,做出严格责任的规定”。[2]P105严格责任是英美刑法的特色,法官在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时基于保护大众利益的需要,根本不用去考虑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情况。另外,英美刑法还为被告人规定了充足的抗辩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胁迫行为、醉酒、精神障碍、安乐死等等。
我国刑法的目的也是保护法益。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目的有三个层次,一是刑法的整体目的,即保护法益,二是刑法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三是刑法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3]P27在他看来,刑法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法益。冯军教授也坚持同样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修订刑法,要保护所有法益。[4]P3我国《刑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的任务是保护国家、劳动群众集体、公民私人的利益。
(二)现代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呼唤全面保护原则
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也决定了国家权力的使用目的。社会法学派代表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只能是承认和保护社会主体的利益。”[5]P679自然法学派代表爱尔维修指出,刑法的制定要根据一个根本大法,即公共福利或人民幸福,它是最高的、唯一的、不可侵犯的法律。[6]P25《挪威宪法》第110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和尊重人权的责任。[7]P223我国《宪法》第33条也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对保护公民权利、国家、集体利益、外国人合法利益、少数民族利益等有明确的规定。公民建立了国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国家,其他国家机关实质也是公民决定的。满足和实现公民合法利益的需要既是法律的根据,又是国家机关的行动根据。
但是,很多情况下,由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不一定都能在实践中得到完美的贯彻落实,甚至有时会形同虚设。由于公民缺乏主张权利、自由的意识和行动,由于官员不是总是首先考虑保护公民的利益,国家更应该坚决地把维护公民利益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现实情况是,我国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权利很全面、很明确,问题是,这些权利在实践中的实现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因此,国家更重要的责任是必须建立保障公民权益的实现机制,刑法是此机制的坚强后盾和保障,用来维护和恢复被破坏的维权机制。
(三)我国刑法的天然缺陷呼唤全面保护原则
由于立法者的原因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所有法律都必然是有缺陷的。美国批判法学派虽然不是其主要法学流派,但其所持的一种观点是十分有力的: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严存生教授指出,法律作用具有二重性,因为法律必须同时限制或取消被统治阶级的自由,还必须同时保护或限制统治阶级的自由,法律的稳定性也导致其不能适应后来的社会实际情况,以致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总是有缺陷、有漏洞的。[8]P114-116我国刑法也在保护法益上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不仅在于立法者认识的狭隘等原因,“立法者以往没有意识到某种现实存在的法益,或者以往没有意识到某种法益值得刑法保护”,[9]P18还可能因为立法者没有找到保护法益的适当方法,或者立法者由于自身观念的偏差或者立场的原因不愿意去保护某种法益等等。
我国刑法在保护法益上存在的缺陷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刑法的内容简单、粗糙。如果仅仅是为了惩治犯罪,法律不需要明确,简单明白就够了,这才有利于国家运用刑罚权。我国刑法内容明显过于简单,从刑法总则来看,刑法没有关于因果关系的规定,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否均应处罚不清,阻却犯罪事由的种类极少,犯罪既遂标准空白,刑种设置不多,只有五种主刑、四种附加刑,禁止令内容不清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缺乏具体的尺度,没有规定赦免制度、量刑的基准和刑事责任的根据等等。从刑法分则来看,口袋罪仍然存在,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等③;关于具体犯罪的定罪条件规定的非常抽象模糊,将决定案件的权力完全交由司法机关,导致国家刑罚权适用范围有较大的弹性,根本无法有效实现对刑罚权的第二次控制,人本来是法的根据,此时却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第二,对各种社会主体的权益保护不够全面。我国刑法对国家法益保护没有明显的问题,但对其他社会主体的法益保护,特别是对公民的法益保护还存在诸多的不足。首先,刑法对男性的人身权保护不力,既不保护男性性的自主权,又不保护14周岁以上男性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其次,刑法对胎儿和死者的法益保护不够。刑法规定了盗窃、侮辱尸体罪,而在我国基本施行火化制度的实际情况下,对于死者来说,其骨灰、墓地、棺材的法益保护应该是主要的内容。另外,刑法对侵害胎儿健康、死亡的行为缺乏规制。再次,刑法严重忽视对非国有单位的法益保护。为了保护国有单位的权益,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六个罪名,同样的危害行为完全可以发生在非国有单位的经营活动中,刑法却完全置之不理。最后,刑法只规定了某些犯罪行为的常见、主要行为,由于概括性不够全面,导致对某些严重危害行为难以给予刑罚惩罚,如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只规制家庭内部的虐待行为,而在实践中,教师虐待学生、保姆虐待护理对象的情形十分常见。
第三,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刑罚权未给予有效的约束,难以保障公民与罪犯的合法权益。在犯罪构成的规定上就是如此,从外国刑法来看,一般都对阻却犯罪事由有详细全面的规定,各国刑法规定的阻却犯罪事由种类多样: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法令或命令、心智丧失或精神障碍、意外醉酒、认识错误、行使权利、身体或心理被强制、胁迫的行为、不可抗力、医疗行为、科学实验、受害人同意、被允许的危险、义务冲突等等。我国刑法规定的阻却犯罪事由种类较少,虽然国家不一定对前述情形按照犯罪处理,但对公民来说却是极大的危险,黄静索赔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再从刑罚规定上看,我国刑种以监禁刑为主,死刑适用标准模糊,包含死刑的罪名过多,反映出刑罚过于严厉。
二、“法益”是全面保护原则的核心内容
“法益”是全面保护原则的核心内容,这里的“法益”一词,一般认为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二战后,德国学者反思战争时期国家刑罚权滥用的残暴后果,运用法益理念来限制国家的刑罚暴力。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副院长Hassemer认为:“刑罚的运用如果不以法益作为根据,那么国家可能就是在犯错。”[10]P150日本学者西原春夫也提出,刑法既有保护国民法益的机能,又有保护罪犯法益的机能。[11]P45可以说,法益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代名词,法益的保障依赖良好的刑法,但刑法并不是自产生起就是要保护公民法益的,只有随着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公民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在国家政治力量对比中居于主导者的地位,公民才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贯彻到法律中去,刑法才会承担起法益保护的使命。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是指刑法要保护公民个人、单位、社会与国家的非用刑法无法保护的所有重要法益,保护人在不同阶段的法益,即胎儿、自然人与死者的法益。
刑法只允许保护法益一直是大陆法系最重要的刑法立法指导思想,保护法益也是大陆法系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④法益具有 “使刑事立法合理性的功能、刑法惩罚范围合理性的功能、明确刑法处罚界限的功能等等”。[12]P197-203所以,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尽量确定法益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如何合理确定刑法保护法益的范畴,既可以保证刑法足以保护不同社会主体的法益,又不至于使国家刑罚权被滥用,造成负面后果,这是几百年来刑法学者们努力要解决的难题。而且,由于各国刑法多把社会秩序也作为法益进行保护,人们担忧法益的抽象化会造成刑罚滥用的后果。因此,不少学者都在努力给法益划一个合理的界限,我国学者韩瑞丽博士主张:保护法益要坚持法益概念的自由主义内涵,要遵循人性思想的指导,要遵循宪法的规定等等。[13]这样的解释还是过于抽象,人们无法把握。德国法学家克劳斯·罗克信则提出了一些相对明确的界定:“单纯违反道德的行为不值得刑法保护,轻微违反秩序的行为不值得刑法保护,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者纯粹的感情不值得刑法保护。”[14]P12-15克劳斯·罗克信的观点主要从反面介绍了非法益的内容,但对法益的要求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Roxin则强调,违背宪法的刑法条文不保护任何法益。[15]P70
刑法保护法益具有其特殊性。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应当是被严重侵害的法益、必须用刑罚制裁来保护的法益、能被客观认定的法益、运用刑法保护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法益。[3]P70他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刑法保护的法益应当具有客观性、重大性、必要性、可测性。客观性是指刑法保护的法益虽然服从于不同主体的需要,但其是具体的,客观存在的,利益的大小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重大性是指刑法保护的法益值得用刑罚来保护,该法益对于主体来说关系到其生存、健康、自由与安全等根本性的利益,且与可以施加于罪犯的刑罚的恶害在价值上相当,微小的利益不能成为刑法法益。必要性是指使用其他手段无力制止不法侵害,只能用刑法来保护。可测性是指刑法保护的法益可以为人们测量其大小轻重,财产法益可以进行价格评估,健康法益可以进行伤残鉴定,精神损害的法益可以进行鉴定等等。⑤
刑法保护的法益与行政法、经济法、民法保护的法益应该有明确的界限,绝对不能模糊不清。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推进犯罪化,增加不大受历史变化影响的行为犯规定,如胁迫罪等,还应当制定《轻犯罪法》,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等等。”[16]这种观点从保护法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立场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其完全忽视刑法保护法益和其他法律保护法益的区别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首先,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较低,对犯罪与罪犯缺乏理性认识,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仇视犯罪、痛恨罪犯、歧视刑满释放者的文化形态,过于扩大刑法调整范围会造成被贴上罪犯标签的人数剧增,给罪犯本人及其家庭造成重大损害。其次,我国本来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权力强大无比,公民难有抗衡之力,不给国家刑罚权套上严厉的枷锁必然导致刑罚的滥用。所以,刑法的谦抑原则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提倡与认可,⑥刑法保护法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运用其他法律手段足够保护的法益绝对不能适用刑法保护。
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刑法必须保护不同社会主体的法益,但这里存在着位次问题,谁更重要,谁次之。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法益包括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必须优先保护个人法益。”[17]P6这种观点是绝对有道理的,国家对于自身法益的维护从来是毫不吝惜、竭尽全力,一般来说,国家法益的保护不存在障碍和困难。法益理论的产生就是为保护公民法益而出现,该理论坚持的判定犯罪与否的关键标准就是看有没有侵害或威胁个人法益,没有直接或间接侵害公民法益的行为无罪。不可否认,刑法当然要全面保护社会主体的法益,但应当把保护公民法益放在优先地位。
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刑法重点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出现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由于刑法保护不力而只是一纸白文,这是绝对不应出现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刑法规定,就会发现我国刑法对公民的政治权利保护不力。例如,我国刑法规定了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等三个罪名,对侵害公民言论、结社、出版权利的危害行为未规定为犯罪。而且,刑法将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并不认为该罪侵犯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显然是误解了此种行为的实质侵害。另外,刑法对破坏选举罪的法定刑设置过低,惩罚力度不够,因为立法者认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非关系公民重大利益的事项,但事实并非如此。
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刑法重视对公民的其他法益的保护。例如,对私自曝光他人艳照、视频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对非法强制拆迁侵犯他人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行为,对冒名顶替上大学侵犯他人受教育权的行为等等均应规定为犯罪。
全面保护原则禁止刑法只保护部分社会主体的法益,反对只保护一般人的法益,不保护弱势群体的法益,反对只保护国有单位的法益,不保护私有单位的法益。这就要求刑法对犯罪的设置要全面,对同一权益危害相当的不同行为均应规定为犯罪,避免刑法盲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一直都是复杂多样的,应当充分考虑到对同一法益造成严重侵害或威胁的所有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做出同样的刑法规定。在刑法中,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拐卖妇女、儿童是犯罪,拐卖其他人也应规定为犯罪,这两种行为都侵害了他人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强奸女性是犯罪,强奸男性也应规定为犯罪,这两种行为都侵害了他人的性的自主权。
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刑法重视保护人在各个阶段的法益。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基础,人在生存期间的法益要保护,人在生前与死后的法益同样要保护,这是由人的尊严和权利所决定的。因此,刑法必须保护胎儿与死者的法益,将侵害胎儿生命与健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将严重侵犯死者法益的各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全面保护原则要求刑法重视对人类集体法益的保护,集体法益既包括国内全体国民的法益,又包括全人类的法益,还包括某个社会群体的法益。不仅国际公约禁止任何个人或国家侵犯人类集体的利益,不少国家也在国内法中做了明确的刑法规制,以惩治灭绝种族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等,因此,我国刑法越早规定这些犯罪越好。
全面保护原则还要求对同一法益侵害程度显著不同的危害行为规定为不同的犯罪。这是站在控制国家刑罚权角度来说的,如果刑法把对同一法益侵害程度显著不同的危害行为应规定为一罪,法定刑相同,必会大量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故意杀人罪包括一般故意杀人、帮助杀人、安乐死、逼人自杀、骗人自杀、教唆自杀等诸多情况,法定刑却完全相同,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时出现对同样案情的案件,判决结果显著差异的情况,这是十分常见的。上述不同的杀人行为应设立为不同的罪名,如受承诺杀人罪、帮助杀人罪、激情杀人罪等等,并给予不同的法定刑,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法益。
三、全面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
刑法发展的最终归宿必然是 “民主刑法”“保护刑法”,只不过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简单地说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的需要,并不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此,不得不探讨其理论根基所在。美国法学家道格拉斯·N·胡萨克认为,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不外乎“尊重人民”“契约主义”“平等观念”等。[18]P47确实如此,全面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民主主义、人权理论、限制刑罚权思想等。
民主主义的观点是,民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反对国家权力至上。有学者指出,民主是国家立政之本,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19]P64民主是社会群众的理性选择,民主的施行方式就是公民选举代表管理国家的代议制,其最大优势在于避免专制与横行。美国政治家杰斐逊主张,为了保障公民的幸福和权利,人民才成立政府,人民有更换不满意政府的权利,立法权属于人民,法律必须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20]P218-225马里旦认为,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高于国家,国家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人民为了国家。[21]P467民主必须有法治的保障,民主的阶段不同,法治的水平不同,保障力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初级的民主法律体系在体现公民的意志和利益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刑法也是如此。但是,民主主义对刑法的要求就是,刑法为保护法益服务,刑法对犯罪界限的设置、犯罪种类的划分、刑罚体系的规定的评价关键看其对法益保护情况。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就为此设计了递进式的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在刑罚规定上,而且,西方很多国家反对并禁止适用死刑、无期徒刑、没收财产,认为这些刑罚违反人性和人道,不符合公民的利益需求。
人权理论认为,人权是人基于本性或法律规定而享有的利益、自由与资格等,人权包括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三种形式。⑦人权的核心内容是利益,保护公民法益不仅要承认人的天赋权利,更要贯彻落实其法定权利。有的学者认为:“保护权利是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是否把人权作为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是衡量法律善恶的实质标准。”[8]P149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做了详细的规定,刑法就必须把保护这些权利作为自己重要的任务。“在二元化社会结构中,⑧国家权力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保障人权应当是国家权利存在的根据”。[22]P57人权理论要求所有法律都要以保护人权为目标,否定人权的法律是恶法,应该被立即修改或废除。
限制刑罚权思想是以公民立场出发的刑法理论。一直以来,国家经常过分地使用刑罚权,而并非使用不力。所以,合理限制国家刑罚权既是在保护罪犯的法益,也是在保护公民的法益。自然法学派主张的只有刑法才能规定犯罪和刑罚、罪刑之间的比例适当、反对肉刑等实际上是在限制统治阶级的刑罚权。古典法学派主张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客观主义、预防目的论等,这是要求国家使用刑罚权必须循法而行,而且要符合公平的伦理道德观念。近代学派提出的目的刑和主观主义并不是为了加重刑罚,实际是要求对有教育改善可能的罪犯从轻处罚,这是对以前流行的报应刑的纠正。近现代刑法学家提倡的犯罪构成论、恢复主义、废除死刑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达到了限制刑罚权的历史巅峰。另外,我国多数学者都支持谦抑原则,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原则就是国家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效果。[23]P353该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把国家刑罚权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它和全面保护原则有内容互通之处。
四、全面保护原则的践行路径
刑法保护不同社会主体的法益在实践中如何落实,不同的国家均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进行,绝不能盲目照搬他国经验和法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国情显著不同,传统文化观念仇视犯罪、歧视罪犯、罪犯回归社会困难、国家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等是我国独有的国情。因此,刑法全面保护原则的践行路径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一)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入宪
西方国家的一个良好经验就是宪法规定一些基本法律的重要原则,在直接约束基本法律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司法机关适用宪法条款裁判案件。在德国,《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下列基本权利是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的直接有效的法。”[24]P22在美国,于1986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相继裁定对精神病人、15周岁以下的少年犯、有智力障碍的人、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违反美国宪法。虽然我国没有宪法法院,但这种宪法规定法律原则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可以在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刑法既要全面保护公民的法益,又不得对罪犯适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残酷刑罚。”
(二)在刑法立法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
首先,在刑法立法模式上,大陆法系刑法在贯彻保护法益原则上有两种模式:一是德、日刑法为代表的同种法益保护模式,把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按照其侵害法益的不同种类划分成几十种犯罪,分别加以规定;二是以法国刑法为代表,先把所有犯罪分为三类:反人类罪、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民族、国家及公共安宁的犯罪,再设章节具体规定不同种类的犯罪。相比而言,法国刑法的立法模式更加明确犯罪的本质,更值得推崇。
其次,对于刑法总则存在的法律空白应予补充。一是刑法应增加阻却犯罪事由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法令或命令、认识错误(包括法律认识错误和事实认识错误)、行使权利、被害人承诺、被允许的危险、义务冲突、推定的同意等,使公民能够有法律依据对抗国家的刑事指控,也能限制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刑法要明确规定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处罚范围,规定犯罪既遂的标准,规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的具体尺度,规定赦免制度、刑事责任的根据等。三是改进刑法种类和内容,增加规定禁止令的具体内容,废除没收财产,将罚金处罚从数额标准改为日罚金制,将死刑限制为故意致人死亡且罪犯不能将教育改善的情形。
再次,进行合理限制下的犯罪化。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侵犯公民法益的新情况,应开展合理限制下的犯罪化,不能因为畏惧国家刑罚权扩大而毫无作为。有学者认为:“今后我国刑事立法应该拒绝进一步的犯罪化,并适当实行一些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25]这种观点对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不合理扩张具有较好的合理性,但同时必然存在放任严重侵害公民法益行为的结果。所以,理性地讲,应该对犯罪化作如下限制:犯罪化是出于保护公民法益的需要,公民的法益受到重大侵害、一般人均不能容忍、其他法律手段救济无效;新罪确定之前必须广泛征求法学家和广大公民的意见,起码取得绝大多数公民的同意;新罪必须经得起社会实践的考验;对犯罪的设立条件应比外国刑法更为严格;新罪的侵害法益明确、罪状要明确,罪刑相当;新罪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据此,不仅可以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盗掘坟墓罪、侵犯个人隐私罪、冒名顶替入学罪、侵害胎儿罪等等;还要扩大部分犯罪的适用范围,将虐待罪主体从家庭成员扩大到包括负有护理、看护、教育管理义务的人,扩大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对象,对侵犯非国有单位法益的行为同样规定为犯罪。
(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
一是在刑法解释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为了实现全面保护法益的责任,最高司法机关在解释刑法时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保证刑法解释符合保护法益的实际需要,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是人们由于生活习惯而一直实施的行为暂时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或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二,确保定罪条件相当。最高司法机关在确定该罪的定罪条件时,应当保证针对不同法益侵害的定罪条件大体相当,不能悬殊太大,否则必然会违反公平原则,有侵害公民法益的重大嫌疑。第三,确保罪刑均衡。司法机关应当自觉承担合理限制刑罚权的责任和义务,在解释刑法时保证犯罪对法益的侵害价值和刑罚施加于罪犯的侵害价值相当,如果刑罚之害远超于犯罪之害,那就是严重侵害了公民法益。例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走私伪造的货币20万元以上或2万枚以上和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多人轻伤就可以适用死刑,这样的规定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利于保护罪犯的法益。
二是在定罪的考量上,司法机关经常犯的错误有,过于看重法益侵害的结果与威胁,忽视了行为人行为的正当性或有无罪过;或者对于公民涉嫌侵害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案件,过于看重“受害人”的法益,忽视行为人的法益;或者过于重视司法任务,无视被告人合法权益;或者过于机械地理解适用刑法,忽视刑法的目的和精神。因此,法官在定罪时应当坚持保护公民权益优先于维护社会秩序,更优先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坚持保护人权优先于惩治犯罪,危害结果不是决定犯罪成立的最关键因素,还应充分考虑所有的阻却犯罪事由是否存在,决定犯罪既遂与否的关键在于法益有没有受到实际的侵害或威胁等等。
三是在量刑方面,学者们对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不同的主张。旧派学者基于“道义责任论”主张报应刑、客观主义,犯罪恶害是决定刑事责任的最重要因素。新派则主张“社会责任论”,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最重要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学者也有“犯罪构成说” “社会危害性说” “罪过说”⑨等观点。每种学说都有其合理性和历史背景所在,但是,站在保护公民法益角度来说,国家应对决定刑事责任的两大要素均应予以充分考虑,即人身危险性与法益侵害,两者的比重应该是同等重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1条,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兼顾罪犯所犯罪行和人身危险性两个因素,以犯罪危害为主。从该意见来看,我国司法机关量刑时对未成年人、累犯或法定情节均有较好的评价,但对于一般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没有规定,显然是不科学的。犯罪只是罪犯一时的行为,刑事责任必须考虑罪犯的历史表现,量刑时给予人身危险性应有的地位。
四是在行刑中,经常出现保护罪犯权益与行刑活动冲突的情形。例如,罪犯服刑期间身患重病,其家属拒绝出资给其治疗,监狱又无此项经费预算,监狱此时难以给予罪犯合适的处遇方案,致使罪犯面临绝境,此种情况,数不胜数。如果坚持全面保护的原则,监狱不仅要给所有罪犯人道主义的待遇,还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保护罪犯人权。
五、结语
对不同社会主体的法益进行全面保护是刑法发展进步的主线,体现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体现着人权思想的智慧,体现着民主主义的结晶。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刑法在全面保护法益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不管是对集体法益还是对个人法益都还有保护不力的地方。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对受害人、罪犯、私有单位、胎儿、死者、青少年、男性、幼儿等特殊主体的法益保护还有很大值得改进的余地。刑法不仅要在宏观上树立全面保护原则的应有地位,在微观上还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构建对特殊主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机制,如受害人获得赔偿机制、量刑评估机制、人身危险性评价机制、刑种和刑期考查评价机制等等,使刑法能够抛弃专横与任性,趋于理性与科学。
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的全部活动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对其贯彻落实还有不小的障碍与困难,人们应对其内涵、要求与实现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促使中国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进步。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今后数百年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法治国家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刑法。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现有刑法的主要缺陷集中体现在刑法的保护法益不全面,因此尽早确立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集权刑法与民主刑法是从国家政治制度角度进行的划分,专制社会的刑法可以称为集权刑法,民主社会的刑法可以称为民主刑法;国家刑法与公民刑法是从刑法立场角度进行的划分,国家机关完全决定刑法内容,立法目的是维护国家统治的是国家刑法,公民决定刑法内容,立法目的是体现公民意志的是公民刑法;惩治刑法与保护刑法是从刑法的任务角度进行的划分,惩治刑法的任务主要是惩治罪犯,保护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
② 坚持该观点的学者有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等。
③ 虽然学界有个别学者支持“口袋罪”,但多数还是认为“口袋罪”不符合现代刑法精神。
④ 详见黎宏:《日本刑法精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7页;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8页。
⑤ 克劳斯·罗克信也认为,不可抽象的抽象客体不能认作法益,详见[德]克劳斯·罗克信:《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56页。
⑥ 详见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408页;张智辉:《刑法理性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等等。
⑦ 详见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5页。
⑧ 许发民教授认为,根据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否分化,社会结构可以被区别为一元化结构和二元化结构。在一元化社会结构中,刑法自然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难以以人权作为价值导向,难以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擅自发动为目标定位。他最大限度地追求对犯罪的打击和控制,以保证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详见许发民:《刑法的社会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⑨ 详见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1] 周振杰.日本刑法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2] Jonathan Herring.Criminal Law[M].Beijing:Law Press Chiana,2003 .
[3]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 冯军.刑法再修改的理念与规则[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 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6] 马克昌.近现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7] 刘海年,李林.人权与宪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8] 严存生.法的价值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 张明楷.刑法目的论纲[J].环球法律评论,2008,1.
[10] [德]克劳斯·罗克信. 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A] .樊文译. 陈兴良. 刑事法评论(第19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 .顾肖荣,陆庆胜,谈春兰,陆一心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
[12]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3] 韩瑞丽.刑法法益的精神化倾向及其限定原则[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14] [德]克劳斯·罗克信.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15]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1.Aufl. 4,2006, S. 14,70.
[16] 张明楷.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J].当代法学,2006,1.
[17] [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8] [美]美国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9] 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20] 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 张宏生,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2] 许发民.刑法的社会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3]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4] 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5] 刘艳红.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J].法学,2011,11.
(责任编辑:张保芬)
Urgency to Establish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ve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WangZhan-qi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0014)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need to pursue a happy life, we should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inciples to protect the legal interest of citizen , institutions, social and country.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 of citizen should be in priority among of these. By this way,we pursue the value of “democrat penalty law”, “citizens” penalty law’, and “protective penalty law”. we face lots of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to pursue the bas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Restrictions of penalty law”, bu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riminal law to be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Article 33 of our Constitution, we should increase one item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necessary to fully protect the legal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to criminal penalties for violation of the social and moral cruelty.” And we should carry out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in penalty law to fill gaps in general provision of penalty law ,to carry out the 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f criminalization, and strict interpretation explain of the Code, and resolutely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incipl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legal interest; comprehensive protective principles; basis
1002—6274(2015)02—049—08
山东省法学会基金项目“死刑的司法适用标准及控制研究”(SLS[2014]G17)阶段性成果。
王占启(1974-),男,山东巨野人,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DF6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