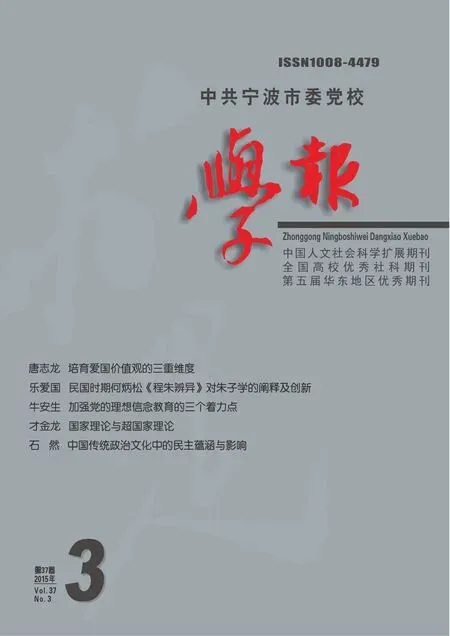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的法律规制与完善
2015-01-30梁平陈焘
梁平 陈焘
(华北电力大学,河北保定071003)
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的法律规制与完善
梁平 陈焘
(华北电力大学,河北保定071003)
调研数据表明,医患双方对协商和解给予较高期待,现实中大部分医疗纠纷亦是通过协商得以解决的,但当事人对其信心度却严重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互信度低、协商和解效率低下以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等;对此,应通过加强医疗资料数据的过程管理、健全医事援助等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程序,使协商和解成为有限度、有特色、有效用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法律规制
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是指医患双方在无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从而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当前,大部分医疗纠纷通过自行协商得以和解,医患双方对该机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却信心不足,实践中协商和解亦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亟待予以法律规制和完善。
一、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的社会认知考察
一般而言,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并非直接寻求第三方解决,而是先行协商,医疗纠纷亦是如此。从调研数据来看,医患双方对协商和解的心理预期更大,现实中也是适用率最高的解决方式,但当事人对该机制的信心明显不足。
(一)当事人对协商和解机制的期待
对544名患者与107名医务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多选),患者首选“与医院协商解决”(368/67.65%),比“向卫生行政部门控告”(221/40.63%)和“法院起诉”(219/40.26%)高出约27个百分点;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应充分发挥“自行协商”(29/27.10%)、“保险公司处理”(26/24.30%)、“行政部门处理”(18/16.82%)、“中介组织(协会、风险基金)处理”(19/17.76%)以及“法院诉讼”(12/11.21%)等多元解决机制的协同作用,但“自行协商”仍是他们最希望的解决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协商和解处理医疗纠纷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文化层面,我国具有悠久的“和合文化”传统,“和为贵”、讲求人际关系和谐是包括儒家、道家等诸多哲学流派的共同取向。正如庞德所言,“中国具有被接受为伦理习俗的传统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可能被转化为一种据以调整关系和影响行为的公认理想”①,这种“公认理想”并非必然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亦非被法治化社会所不容或自然淘汰;相反,法治在讲求规则之治的同时,必须具备充分的道德基础,即法的道德性。以社会和谐或秩序价值为共同目标,传统文化对法治具有积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功能意义上,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与民众需求之间应是有机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因民众的现实需求而具有存在之必要性和可能性,民众也因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能有效满足其需求而得以修复社会关系。”②因此,医患双方对协商和解机制的共同需求是该机制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协商和解机制的适用率
对于“您所在医院,医疗纠纷一般用什么方式解决”,医务人员选择“与患者协商解决”的占62.62%,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行政调解”(12.15%)。对已发生的2138例医疗纠纷予以统计,医患双方协商和解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式,共1600例,占74.74%,远远超过医调委第三方调解(205例/9.59%)、法院判决(195/9.12%)、行政调解(112/5.24%)以及上访(2/0.09%)等其他解决方式。各地法院协商和解机制的适用率甚至更高,比如某医院2002~2009年发生的72例医疗纠纷,84.72%(61例)通过医患双方协商得以和解③;某医院2007~2011年共284例医疗纠纷,双方协商和解率达到94.37%(其中,协商不理赔218例,占76.76%;协商理赔50例,占17.61%)④;某市7家医疗机构2010~2012年发生的660例医疗纠纷,医患协商解决543例。占82.27%⑤;等等。由此可见,实践中大多数医疗纠纷是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的。这种现状的成因在于,除了文化因素外,一般而言,经医患双方的多次沟通协商(不排除医疗机构“怕麻烦”和患者“耗不起”等此类因素),基本上能够全面权衡各种因素形成共同妥协,从而达成和解协议。当然,诉讼等其他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亦是当事人争取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
(三)当事人对协商和解的信心度
尽管医患双方均希望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且实践中该机制的适用率相当高,但当事人对其信心度却严重不足。调研结果表明,57.17%的患者表示“不确定”(311/544)与医院协商能否妥善解决医疗纠纷,而明确表示否定的占18.93%(103/544),对协商和解表示有信心的占23.90%(130/544);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态度亦是如此,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中,医务人员对协商和解的期待(27.10%)远远低于患者(67.65%),而医方最希望“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52.94%),比“找患者协商,希望通过谈判解决”(29.41%)高出23.5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对于“您认为纠纷发生后,医患协商解决会出现哪些问题(多选)”的回答,患者依次选择“医院态度恶劣,推卸责任”(440/80.88%)、“患方缺乏医学知识,会吃亏”(310/56.99%)、“患者与医院对抗,能力资源不对等”(292/53.68%)、“患方敲诈勒索,高额赔偿”(279/51.29%)、“医生逃避刑事等相关责任”(273/50.18%)以及其他(8/1.47%);医务人员认为其面临的最大责任和压力是“患者或家属对工作的不配合”(85.05%),其次是“心理压力大,害怕医闹”和“执业的人身安全性”(各占74.77%),发生医疗纠纷时,医务人员的此种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医患双方对协商和解机制信心度普遍较低的原因在于,该机制在现实中缺乏公正、高效、安全运行的充分保障。
二、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如同公正与效率是司法的两大主题,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不仅应以公正、高效为基本价值取向,而且应保证医患双方安全特别是人身安全。调研结果显示,协商和解机制的实践运行难以达到上述预期。
(一)信息不对称侵蚀患者权利
因知识壁垒的存在,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在疾病诊疗与医疗纠纷处理中均处于优势地位,患者很难掌握与对方同等的信息,因而无法与其展开平等对抗,即“患方缺乏医学知识,会吃亏”。此种现象在医疗纠纷的其他解决机制中同样存在,但与其他机制特别是诉讼不同的是,在协商和解中,患者无权要求医疗机构充分地开示信息,即便要求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予以处理,因无实际拘束力而无法实行。正如患者所反映的,如果过多地“据理力争”,可能导致“医院态度恶劣,推卸责任”。以病历资料的提供时间为例,某项研究数据显示,49.17%的医务人员表示“在解决过程中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提供”,6.20%的医务人员“在发生纠纷后医院主动提供”,二者合计达到55.37%,而“应患方要求随时提供”和“医疗行为结束时医院主动提供”的分别为16.94%和25.62%⑥,此即意味着接近半数的患者在协商和解中很可能无法取得作为认定责任的基础性材料——全部病历资料。运用协商方式解决医疗纠纷,若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得以根除,必然存在着患者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合理怀疑乃至成为现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患者要么对协商和解“避而远之”,要么即便达成了和解协议,亦无法消除患者对其权利是否得以充分实现的怀疑心理。
(二)患者不合理要求使医疗机构受损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患者权利减损;立足于医方的角度,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状态引起医患互信度降低,患者的主张究竟是否合理,在协商和解中没有严格的衡量标准,以致于患者提出不合理要求或漫天要价,对医疗机构带来巨大压力。正是如此,医疗机构在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上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医院在医疗事故纠纷中最看重“名誉”(占73.33%),自然应选择保密性较高的解纷方式,协商和解因无第三方参与当属最佳选择;但另一方面,因协商和解机制既无法赢得患者的足够信赖,也无法保证对医疗机构的公平公正性,医方最希望的解决方式,首选并非“找患者协商,希望通过谈判解决”(29.41%)而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52.94%)。对4502例医疗纠纷的25项发生原因予以统计,“患方期望值过高”(198例/4.40%)居于第9位;某中心城区区属医疗卫生机构2008~2010年发生的519例医疗纠纷,“患方期望值过高”(69例/13.29%)仅次于“治疗并发症”(102例/19.65%)和“患者不理解告知内容”(75例/14.45%),位列第三⑦;某市5所军队医院妇产科医疗纠纷发生因素中,“患者期望过高”的比例高达45.38%⑧。由此可见,不仅患者对协商和解机制的公正性顾虑重重,医方亦对患者的滥用权利行为心存芥蒂。
此外,我国目前仍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其财产属于国有资产,通过协商方式“私了”医疗纠纷,可能出现医疗机构为“息事宁人”予以超额赔偿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三)协商和解效率低下
某种程度上,协商和解是一种超自由的解纷方式,给予了当事人足够的意思自治空间,但另一方面,这种“超自由”亦成为影响协商和解的负面因素,其集中体现为效率低下。一方面,协商和解完全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几乎不存在任何外部强制力(可称为“压力机制”),失去“压力机制”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必须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在动力,或者即便一方当事人具有和解诚意,但另一方故意拖延或置之不理,已进行的和解谈判便归于无效,特别是无和解时限约束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医疗纠纷被拖延。另一方面,即便达成和解协议,由于和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性质,若当事人反悔或不履行,又使得一切协商谈判的努力皆前功尽弃,最终不得不诉诸新的纠纷解决机制。
(四)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以及医疗秩序
调研数据显示,医务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多选)包括“执业的人身安全性”和“心理压力大,害怕医闹”(各占74.77%);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或家属出现的过激行为,居于首位的是“辱骂、威胁、殴打医护人员”(90.65%),然后依次为“在医院内摆设花圈、灵堂”(79.44%)、“将患者或尸体停滞医院”(71.03%)、“打砸医院”(65.42%)乃至“杀害医护人员的恶性事件”(11.21%)等。一般而言,患者或家属的上述过激行为是在协商过程中或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是“辱骂、威胁、殴打医护人员”往往是在双方言语不和时产生的正面冲突,对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心理造成很大危害。此外,基于“医闹成本低、小闹小赔大闹大赔”(在“群体性医闹”发生原因原因中占25.86%,仅次于“诉讼耗时长、成本费用高(占39.65%)”⑨)的逻辑,患者亦坦言协商和解存在着“患方敲诈勒索,高额赔偿”(279/51.29%)的弊端,少数医疗纠纷很可能演化为医闹,严重扰乱医疗秩序。
(五)不利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全民健康,国家对此实行行政监管,其方式之一即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应当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发生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在12小时内报告”,其目的在于通过医疗机构主动报告,便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重大或多发的医疗机构予以监督管理,从而避免此类事件发生,以及对相关人员予以责任追究。医疗纠纷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私了”,为医疗机构和有关责任人逃避卫生行政部门监管提供了制度空间,既无法有效督促医疗机构予以整改,促使医务人员吸取教训,同时使有关责任人无法受到行政或刑事责任追究,导致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或刑事法律规范沦为空文。
三、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的法律规制与完善
对于上述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从程序层面对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予以法律规制和完善,为其划定“边界”或增加程序制约,使之成为有限度、有特色、有效用的解纷机制。
(一)加强医疗资料数据的过程管理
医疗纠纷解决取得医患双方认同的基础条件是对纠纷定性准确、责任明确,而达到此标准的基础之一则是医疗信息公开、透明、对称。客观地讲,知识分化带来的专业壁垒以及信息不对称在诸多领域均是存在的,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并非必然因医方的主观行为所致,而是源自于医疗行为的高度专业性。终极意义上,医患双方无法达到理想的信息对称状态,因为患者不具备相应的医疗知识,对医方的解释说明未必能够充分理解,尤其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信任被破坏的背景下,客观的信息不对称可能演化为患者的主观感觉,即便医方已充分地披露了医疗信息,患者仍然无法冰释对医方优势地位的感受以及对信息是否充分的怀疑。因此,消除患者主观感知层面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医疗资料数据管理与开示,使患者能够获得原始的医疗信息。
具体而言,一是医务人员严格落实《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向患者充分、详细地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使患者对此具有充分的理解。目前,医务人员开具的“天书”般的药方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即时注射性或由医务人员自行配制的药物,患者甚至连药物名称都无法得知,但又不好意思追问或询问后医务人员不予以详细解释,其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治疗的地位,在这种“稀里糊涂”状态下若发生医疗纠纷,即便医务人员如何解释说明,亦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调研数据表明,“缺乏沟通和告知”是已发生的4502例医疗纠纷的首要原因(796例/17.68%),因此,医务人员应转变观念,走出某种狭隘的认识误区,对患者全面告知医疗信息并使其充分理解。二是在经验诊断确实无法确定病因的情况下,及时详细告知患者辅以医技检查,通过器材检查增加诊断的可信度,但当前很多医务人员动辄要求患者做化验或医技检查,因可能涉嫌“过度检查”而引发的医疗费用纠纷频发,对于患者分歧较大的检查,可明确建议患者可去别的医院另行诊断,以消除患者的误会。三是对于客观病历和主观病历,医院除了向患者提供必要的原件外,应允许患者复印不宜提供的病历资料;医疗结束后,医务人员应将病历资料及时归档,并放置在安装监控装备的特定档案室,由专人专管,作为医方自我保护的一种内部管理措施。
(二)健全医事援助等公共服务体系
在双方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中立第三方的专业性介入有助于很好地减小双方的认识分歧。医疗纠纷的协商谈判中,究竟是医方推卸责任还是患者期望值过高,关键在于打开患者的“心结”。为此,可“建立医事援助制度,赋予患者向本地医学会申请医事援助权利,这可弥补患者医疗知识之不足,改变其弱势地位,加强与院方的谈判实力,增强其对抗的能力,保持医患双方力量的平衡,保证和解结果的公正。”4此外,可建立医学院专家数据库,开通网络服务或电话热线,患者对涉及医疗的疑难问题,可随时向其咨询,通过中立第三方专家的答疑解难,进一步明晰医疗纠纷的定性(属于医方过失、正常医疗风险还是患者自身原因),使患者对不良医疗后果的发生原因具有清晰的认识,消除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感,为协商和解奠定基础。
(三)完善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程序
除了医疗信息不对称与医患信任度低外,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的现实障碍主要包括效率低下、医务人员缺乏人身安全保障以及逃避卫生行政监管等。为此,应从协商和解程序入手,通过较为完备的程序堵塞漏洞以增强该机制的实用性。首先,对协商和解的次数予以必要限制,在三次实质性谈判无果或自医疗纠纷发生30日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应明确告知患者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医方故意拖延或患者多次找医院给医疗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便于启动其他程序后,对医疗纠纷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其次,医患双方协商谈判时,医方应至少2人参与,一般情况下当事的医务人员不宜直接参与,以免患者与其发生直接冲突;当患者出现情绪波动时,医方协商谈判人员应及时中止协商,必要时向安保部门报告,让其配合维持医院秩序;如出现患者严重扰乱医疗秩序或出现医闹等过激行为时,医疗机构应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由其出面维持社会治安。再次,卫生行政部门可制定制式的“医疗纠纷和解协议”,一方面规范和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另一方面,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和解协议,要求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医疗纠纷处理条例》的规定向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并接受其监督。最后,为增强和解协议的执行力,可先建立和解与调解的衔接机制,医疗机构可与患者共同持《和解协议》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出具《调解书》,经医调委审查后出具《调解书》,然后双方对《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时机成熟时,实行和解与司法确认的直接衔接,医患双方可共同持有《和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四、结论
尽管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和解机制信心不足,但其对该机制均寄予很高的期待,现实中大量医疗纠纷通过协商得以和解亦表明该机制具有独特的优势,医患双方信心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机制运行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严重地制约着该机制的实际效用。改变这一现状的两个基点包括:一是从困扰医疗纠纷责任确定和患者主观认同度的医疗信息入手,使患者知悉并理解诊疗过程并可获取相应的医疗资料,医疗机构应将医疗资料予以归档,使其具有历史资料的客观性;二是从程序上对协商和解予以细化,使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和效率性。
[注释]
①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
②梁平,陈焘.司法契合民众需求的理论思辨与实践进路——基于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检视[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3):96.
③华立,田光,许德华,周蕾蕾.医疗纠纷的处理及防范措施[J].临床误诊误治,2011,24(5).
④张庆磊.对284例医疗纠纷事件的原因分析[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3,35(4).
⑤张宇,等.某市医疗纠纷发生及诉前处理现状分析[J].中国病案,2013,14(7).
⑥调研组.找寻法律本身——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案件调查报告[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8(5).
⑦钱文昊,李琳,王洋,等.某区属医疗机构医疗纠纷的结构分析与处置思考[J].中国卫生资源,2012,15(6).
⑧高连娣,等.妇产科医疗纠纷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1,18(4).
⑨李大平.基层医疗机构医疗纠纷现状实证研究——对东莞市4家基层医院的调查[J].证据科学,2013,21(2)
⑩卢顺珍.论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的法律规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2).
责任编辑:刘华安
R197.323.4
A
1008-4479(2015)03-0077-05
2015-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治理中社会矛盾化解与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3BFX009)、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实践——以河北法院为例”(项目编号:HB13FX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梁平(1968-),女,河北秦皇岛人,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教授,主要从事纠纷解决与司法制度研究;陈焘(1984-),男,甘肃庆阳人,华北电力大学教师,助教,主要从事纠纷解决与司法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