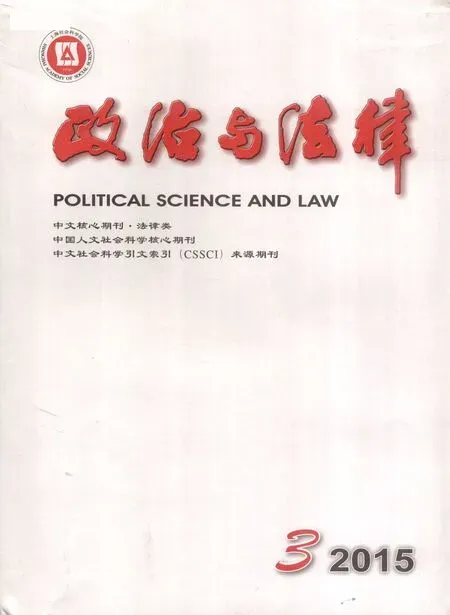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
——多维度的综合分析
2015-01-30陈金林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陈金林(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
——多维度的综合分析
陈金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生物—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结论已经消解了“部分露出说”、“分娩开始说”、“独立呼吸说”、“发声说”、“断带说”的事实根基,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被提前至“受精”或“着床”的时点。当今社会,由于孕育的成本不断上升,早期生命面临的风险与侵害日趋普遍化,通过刑法保护家庭生育利益的期望也就愈加迫切,但因此承认早期生命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将严重侵犯孕妇的利益,只有在与孕妇基本权利不相冲突的前提下,才可以尽可能早地以“禁止杀人”的方式保护早期生命。鼓励生育或控制人口的目的,都应当通过社会政策层面的手段实现,但为了给孕妇同意前提下的计划生育留下空间,不宜将“人”的起点过度前移。道德伦理对生命的尊重,只能够影响刑法是否设置关于保护道德伦理情感的犯罪,对于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则无决定性意义。
生物-医学;生育利益;人口政策;道德伦理;全部露出说;独立存活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这一问题,刑法学上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固的通说,似乎没有过多着墨的必要。但近些年来国内外涌现的一系列案例,足以动摇已经“尘封”多年的教义学格局,使人们对刑法中的“人”的起点进行反思。
案例I:江苏一对双独年轻夫妻不幸因车祸身亡,他们生前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做试管婴儿,并留下4枚冷冻胚胎。①参见佚名:《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案二审大逆转:两对老人共同监管子女遗留胚胎》,《京华时报》2014年9月19日,第A18版。如果医院故意灭活冷冻的胚胎,或者过失导致冷冻胚胎丧失活性,刑法是否有介入的空间?该如何介入?
案例II:妻子怀孕4个月时,丈夫遇事故身亡,其生前所购保险能赔偿400万,婆婆向儿媳承诺,只要儿媳生下孩子,则全部保险赔偿都归她所有。②参见佚名:《丈夫意外去世 公婆愿拿赔偿换孙子:妻子纠结是否生下遗腹子》,《楚天金报》2014年6月7日,第A12版。如果第三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该遗腹子死亡,但并未伤及儿媳,刑法当如何回应?如果儿媳自愿选择堕胎,或者儿媳因为身患疾病不宜继续妊娠而选择堕胎,婆婆是否有权加以阻止?其根据是什么?
案例III,即爱尔兰根案(Erlanger Fall)③Vgl. AG Hersbruck, in: NJW 1992, 3245.:一孕妇因一起车祸严重受伤,腹内有一受孕十五周左右的胎儿。孕妇在被送往医院后,很快被确诊为脑死亡,但身体仍能在外部设备的支撑下存活。胎儿并未在车祸中受到损害。医生有无义务维持孕妇机体的存活以保护其体内的胎儿?其根据是什么?
案例IV:陕西安康已经怀孕7个月的孕妇冯建梅,因未办理二孩生育证且未能缴纳保证金,被强制接受终止妊娠手术。④参见佚名:《陕西安康通报“大月份引产”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县计生局长被撤职》,《海峡都市报》2012年6月27日,第N05版。计生部门能否出于人口政策的考虑强制终止妊娠?如果能,其正当化根据是什么?如果不能,人口政策的目的如何实现?
案例V:R先生已经做了三年的透析,经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可以接受器官移植,但由于组织类型少见,很难找到合适的肾脏来源。R先生的妻子向医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自己先怀上丈夫的孩子,五六个月过后进行人工流产,再将胎儿的肾脏移植给丈夫。⑤引自何伦、施卫星:《生命的困惑:临床生命伦理学导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这种行为能否被允许?其根据是什么?
前述案例交织着家庭、孕妇、国家、社会等多方面的利益,也涉及生物医学、家庭关系、人口政策、道德伦理等多种观察视角。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多种可能的观察视角,造成了确定刑法中的“人”的起点的复杂性。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全面分析各方面诉求,并在复杂的冲突关系之中寻找一种协调各种利益的方案。
二、自然科学的视角:规范与事实之间
生物—医学的发展不断深化着我们对人类生命发展历程的认识,这些认识究竟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刑法意义上的“人”的概念?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既要防止规范结论与客观世界脱节,又要防止经验事实对规范领域的“殖民”。
(一)完全脱离事实的规范
法学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刑法学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也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根基。在有关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这一问题上,有很多居于通说地位的结论完全没有自然科学的依据,或者还建立在早已过时的事实根基之上,这样的理论无疑是不妥当的。
1.“部分露出说”与被独立侵犯的可能性
在日本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居于通说地位的“部分露出说”认为,胎儿身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时,就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人”。其逻辑在于,自身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时起,胎儿就不再完全被母亲的身体所屏蔽,开始独立直接面临外界的侵犯,因此刑法有必要将胎儿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保护。⑥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6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不过,这一观点所依赖的基础事实已经完全过时了。当今,人类已经迈入了风险社会,对各种风险与损害之间的关联也有了非常精确、具体的认知。母腹中的早期生命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社会的重重风险,且胎儿所受的侵害与这些风险源的因果关系并非不可证明。当今,食品、药品、放射性或毒害性物质、环境污染等,已经完全能够绕开狭义的母体直接侵害胎儿。因此,曾经被视为胎儿天然屏障的母体,已经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变成了“马其诺防线”。在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较低的时代,由于只能认识到对胎儿“牛顿力学”意义上的侵犯,因此“部分露出说”的缺陷并不明显;在医学知识高度发达的今天仍坚持“部分露出说”,则无异于刻舟求剑。
2.“分娩开始说”与医疗行为的介入
在德国理论和实践中居于通说地位的理论“分娩开始说”认为,⑦德国理论界的通说和司法实践就自然分娩情形下的“人”的起点所持的意见,具体的判断以“开宫口时的阵痛”(Eröffnungswehen)为标准。剖腹产的情形之下,以子宫被切开的时刻为起点。Vgl. Ulfrid Neumann, in: Urs Kindhäuser/ Ulfrid Neumann/ Hans-Ullrich Paeffgen (Hrsg.), Strafgesetzbuch, 4. Aufl., Nomos 2013, Vorbemerkungen zu §211, Rn. 6; BGH, in: NJW 1984, 674; BGH, in: NStZ 2010, 214; Hans Lüttger, Der Beginn der Geburt und das Strafrecht, in: JR 1971, 133 (135); Albin Eser/ Detlev Sternberg-Lieben, in: Adolf Schönke/ Horst 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29. Aufl., C. H. Beck 2014, Vorbemerkungen zu den §§ 211 ff., Rn. 13.分娩过程是一个对孩子而言高度危险的领域,在此期间尤其容易出现对孩子的过失损害,因此有必要将分娩开始后的生命视为杀人罪和伤害罪的保护对象。⑧Vgl. Eser/ Sternberg-Lieben, Fn. 7, Rn. 13; RG, 9, 131; BGH, 26, 179, BGH, 10, 5. 亦可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修订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与“部分露出说”一样,“分娩开始说”的前提也已经被消解。今天,对早期生命的医疗介入(例如保胎、各种检查与化验、胎位矫正等)和其他风险已经分布到了从受精到分娩的整个过程,认为只有在分娩过程中才具有紧密的医学或其他风险,已经完全不符合社会现实。
3.“独立呼吸说”与人的本质
此外,还有部分观点将并不能体现“人”的本质的生理现象作为界定“人”起点的标准。例如,在我国理论和实践领域居于通说地位的“独立呼吸说”,⑨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57页。当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怀疑这种观点的妥当性,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参见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页;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四版)(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页。就将新生儿的独立呼吸作为刑法中的“人”的起点。在这里,生命与自主的呼吸划上了等号。不过,从现代生物—医学的视角出发,生命的本质并不是自主呼吸,因为不能自主呼吸的人类生命也有可能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例如,由于心肺功能不正常,部分婴儿刚出生时还不能立即进行自主的呼吸,必须依靠外部设备的辅助以完成呼吸动作,但毫无疑问,这种在呼吸上存在障碍的婴儿也应当是刑法意义上的“人”。
基于同样的原理,“发声说”、“断带说”所依据的标准“发声”与“断带”,也都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依据,因为这些生理特征都不能代表生命的本质特征。
(二)盲目跟随事实的规范
作为当今的“显学”,自然科学对规范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法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也在很大程度受到了生物—医学领域最新发展成果的影响。由于生物—医学的研究不断向微观领域和生命的原点推进,法学意义上的“人”的起点也不断被提前。例如,Hilgendorf教授就指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生命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中,法律规范选择任何时间点作为介入的标准,都将是“任意”的,因此,只能将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作为生命的起点。⑩Vgl. Eric Hilgendorf, Scheinargumente in der Abtreibungsdiskussion, in: NJW 1996, 758 (762).不过,法学意义上的“人”是否必须与生物—医学中的“人”保持完全一致?
任何法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因此,法学未必需要也不应当照搬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只能为法学的规范评价提供事实基础,不能替代也未必会决定法学意义上的定义。即便生物—医学领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有关“人”的结论,刑法学仍需要通过规范研究的方法形成自己的“人”的概念。虽然人类对早期生命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虽然生命的发展在生物学上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但不得因此拒绝在法学意义上将生命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赋予各阶段的生命形态以不同的法律地位。
在刑法的意义上将特定对象评价为“人”,会带来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法律后果。因此,是否赋予特定对象以“人”的资格,要考虑这种对象是否与通常意义上的“人”具备价值层面的相当性。如果将受精卵或早期的胚胎视为刑法上的“人”,一个着床失败、丧失生命力的受精卵就是一具“尸体”,流产也就意味着有“人”死亡,警察必须进行“尸检”以判断着床失败或流产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所致。孕妇避孕失败后服用事后紧急避孕药阻碍着床,或者孕妇情绪不好、吃了妊娠期不能吃的食物导致流产,都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同理,大街上的广告“有毓婷、放心爱”、“三分钟梦幻无痛人流”就将等同于赤裸裸的杀人宣传。可见,将早期的生命形态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将严重冲击当前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观念,它未必会使受精卵或胚胎具备“人”的尊贵地位,反倒可能会让“杀人罪”变得与早期流产一样琐碎和常见,并因此稀释刑法上的“人”的价值。
(三)小结
综上所述,有关刑法上的“人”的起点,既要结合自然科学的最新结论,对“部分露出说”、“分娩开始说”、“独立呼吸说”等理论的合理性进行彻底反思,又要防止对最新自然科学理论的盲目跟风。自然科学的视角能为规范研究提供基础,但未必会决定规范意义上的判断结论。
三、家庭的视角:生育利益等于生命权吗
站在家庭的立场上,容易形成将“人”的起点前移的倾向,因为早期生命凝聚着家庭的投入,承载着家庭生育的希望(如案例I与案例II)。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将早期的生命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如果将胎儿视为“人”,如何避免胎儿生命权与母亲权利的冲突?
(一)对刑法介入的期待
一方面,在当今社会,生育早已不再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一种有计划的高投入行为。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与药品、因性观念开放导致的流产经历、教育或职业引发的精神压力、受孕年龄偏高等多方面的原因,给不少适龄夫妻带来了孕育的障碍。①据报道,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已高达12.5%。参见佚名:《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4000万》,《晶报》2012年12月3日,第A17版。如今,不仅受孕需要耗费经济成本,受孕到分娩的漫长过程更需要大量的人工和医疗介入,以确保受孕的稳定和胎儿的健康。此外,孕妇为受孕作出的事业上的牺牲,②在传统社会,女性投入社会生产的程度较低,生育所消耗的时间与机会成本较小。而如今,在一个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女性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者,为此,女性必须接受教育、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不仅增加了受孕与生育的难度(例如孕龄被迫推迟、心理压力更大、体质相对而言更脆弱),也提高了孕育的代价。家庭为早期生命成长、发育支付的代价,都属于早期生命所凝聚的成本。
另一方面,在当今中国,“香火”文化依然有很强盛的生命力,在生育健康的婴儿难度提高、整个孕育过程都布满了风险的年代,对早期生命的保护就具有了很强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家庭会极度厌恶孕育过程中的风险,这又会反过来促使家庭对每一次孕育给出更多的经济投入,以避免风险,确保生育的预期利益。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才能理解当今的家庭在生育过程中甚至在生育之前几近苛刻的自我约束(例如“封山育林”、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看起来未必理性的投入(如孕前教育、胎教等)。
结合前述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得知,不仅早期的生命,甚至生殖细胞都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价值,早期胚胎、胎儿的保护必要性更是毋庸置言。可见,从家庭的视角出发,“受精说”、“着床说”等将“人”的起点提前的观点似乎更应当受到支持。
(二)为保护家庭的生育利益将“人”的起点前移会产生负面效果
不过,保护家庭的生育利益是否以在刑法上承认早期生命的人格权为必要前提?这种方案是否会带来不可控制的负面效果?
一旦承认早期的生命是刑法意义上的“人”,就必然会产生如下法律后果:其一,刑法对早期生命的保护将是绝对的,原则上不能为了任何其他利益牺牲早期生命,①周详教授以具有宫外可存活性作为界定“人”的标准,同时又认为剥夺这种“人”的生命的行为仅在两种情形下构成故意杀人罪:其一,违背孕妇意志堕胎;其二,孕妇自己为了选择胎儿性别而对已经取得了准生证的胎儿实施堕胎。参见周详:《胎儿“生命权”的确认与刑法保护》,《法学》2012年第8期。但刑法对“人”的保护为何要取决于他人(孕妇)是否同意?如果为了计划生育强行堕胎(案例IV)构成故意杀“人”罪(周详教授的观点),为什么孕妇同意就可以将其转变为合法行为?准生证这种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许可为何能决定杀人罪成立与否?因为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合法地剥夺一个无辜者的生命;②正当防卫、警察执行职务、执行死刑是当前制度框架中可能被合法化的故意杀人,但这些行为都不是针对无辜者的,行为对象能够通过事前的自由意志避免被他人合法剥夺生命。其二,早期生命与其他生命一样,享受平等的刑法保护,因为人必须是平等的,当今社会无法容忍将人格分等的观念;③有人提出了一种将出生的人和未出生的人进行区别对待、根据生命成长阶段调整保护力度的观点,参见Horst Dreier, Stufungen des vorgeburtlichen Lebensschutzes, in: ZRP 2002, S. 377 ff. 但刑法学不能接受将人格分为不同等级的观点。即便是此前曾在不少立法例中出现的生母杀婴罪(母亲在生产时或生产后杀死其非婚生子女),也并非是因为行为对象低“人”一等,而是因为责任更低。杀害尊亲属罪的特别之处也不在于行为对象比普通的人更高一等,而在于行为人的责任更高;而且,当前这种立法例大多被认定为与平等原则相冲突,因而被宣告违宪。在国内,周详教授既承认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具有生命权,又认为胎儿的生命权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权“存在差别”。在刑法领域内,这种观点是无法被接受的。其三,刑法将用最严厉的措施全面地保护早期生命,其手段将会包括针对故意杀人罪配置的法定刑,且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侵犯早期胎儿生命、健康的作为与不作为,都将构成犯罪。
可见,将早期生命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的确能够为其提供最强有力、最周全的保护,这无疑是对早期生命享有利益的家庭成员所期待的。但刑法这一利器具有“回旋镖”的效果,它在防止第三人侵害早期生命的同时,也可能会反过来限制家庭成员自己。由于早期生命的不稳定性,加上当今社会无所不在的风险,家庭成员自己也可能侵犯早期生命并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刑法对“人”的保护没有任何理由要在家庭成员面前作出退让。这样,胎儿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与早期生命具有生理上连结的孕妇,在很多情形之下都可能与胎儿产生利益冲突。如果将早期的生命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则陷入利益冲突的孕妇为了自身利益牺牲胎儿的行为,至少会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不法(Unrecht),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构成犯罪。例如,孕妇自愿的堕胎将成立故意杀人罪;孕妇过失导致流产将构成过失杀人罪;即便为了避免生命所面临的危险,孕妇也不得牺牲胎儿以自救,因为生命之间无权衡(Keine Abwägung von Leben gegen Leben),④Vgl.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T, Bd. I, 4. Aufl., C. H. Beck 2006, S. 738.这种情况即便能够在特殊的情形下排除责任,⑤根据Roxin教授的观点,为了拯救生命而牺牲其他人的生命,只能通过基于刑事政策(犯罪预防)考虑的超法规的答责性排除事由(der übergesetzliche, kriminalpolitisch motivierte Verantwortungsausschluss)来排除可罚性。Vgl. a. a. O., S. 1025 ff.也已经构成了不法,为了防止早期生命被牺牲,其他家庭成员甚至可以为了传宗接代的利益而对孕妇的自救进行正当防卫。
可见,以赋予早期生命刑法意义上“人”的地位来保护家庭的生育利益,将会给家庭成员自己带来受惩罚的风险,并陷孕妇于绝境。同时,它也可能为家庭成员内部产生纷争的法律因素,因为家庭成员完全有理由要求保护胎儿而牺牲孕妇。由于这种方案可能将女性作为生殖繁衍的工具,女性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境地,就会刻意避免受孕,最终反倒不利于家庭对于传宗接代的期待。
(三)协调冲突的可能方案
为了避免牺牲孕妇本人利益,同时兼顾家庭生育利益的保护,可以将早期生命形态分以下三种情形,并对其在刑法层面的定性作不同处理。
1.母体之内的早期生命
在早期生命与母体分离之前,胎儿与母体通常构成了自然意义上的一体。在这种情形下,完全可以将胎儿视为母体的一部分进行保护。尽管在生物—医学的意义上,早期的生命可能具有自己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大脑活动甚至宫外存活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妨碍在法学的意义上将胎儿视为母体的一部分。同时,“伤害”完全能涵盖所有给特定对象的身体官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繁殖能力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繁殖能力不仅包括正常受孕的能力,也应当包括怀孕至足月并正常分娩出健康婴儿的功能。
因此,只要胎儿尚未完全脱离母体(包括部分露出狭义“母体”的胎儿),都能够被当作母亲身体的一部分,通过母体获得法律的保护。这种方案能预防第三人对早期生命的侵犯,满足家庭保护生育利益的要求,又能避免侵犯孕妇的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孕妇之外的家庭成员被处罚的风险。①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2014年1月1日起实施),损伤导致早产、死胎或流产(合并轻度休克)属于重伤二级。因此单纯的流产、胎儿伤害都只构成对母体的轻伤以下的伤害,这就排除了过失导致单纯流产、过失伤害胎儿的可罚性。过失导致的流产或死胎属于过失致孕妇重伤,仍应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对于孕妇自己对早期生命造成损害并同时侵犯其他家庭成员的生育利益的情形,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加以救济。例如,丈夫的生育权可以通过提起离婚诉讼加以保障;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第1项规定,确定子女抚养权时,应优先考虑已经做过节育手术的一方。这也是保护生育权的体现。家庭或家族在胎儿身上的投入,可以视为对孕妇附条件的赠与。
2.阴道分娩或经剖腹产分娩的具有独立存活可能性的生命
承认这种意义上的生命是刑法意义上的“人”,不会面临来自孕妇的障碍。其具体的判断以“全部露出”母体为准,这一标准既适用于自然或介入人工干预的阴道分娩(是否“足月”在所不问),也适用于剖腹产。在剖腹产的情形下,早期生命“全部露出”应当解释为胎儿完全从母亲体内取出,而不仅仅是“可以看见”意义上的“露出”。只有将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设定在事实上“全部露出”母体之外,才能避免孕妇利益与胎儿权利的冲突。
当然,要获得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资格,全部露出的早期生命还必须具备另一特征——独立存活的可能性,③这一特征是刑法意义上的“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在事实上与母体完全分离之前,早期生命与狭义的“母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继续存在。仅以宫外独立存活的可能性为标准界定“人”的观点,可参见前注13○,周详文。这是“人”的当然内涵之一。在理解“独立存活的可能性”之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独立”是指独立于他人(主要是孕妇)的身体,④在案例III中,如果承认脑死亡(德国的通说,参见Neumann, Fn. 7, Rn. 18; Rudolf Rengier, Strafrecht BT, Teil Ⅱ, 11. Aufl., C. H. Beck 2010, S. 10),则孕妇遗体提供的环境就已经不再是“规范意义上”的“人体”环境,可以将案例中的胎儿视为“人”;但如果不承认脑死亡,则案例中的胎儿还没有完全独立于母体,仍不能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指不依靠任何外界环境或条件(包括医疗设备甚至他人捐献的器官);第二,“独立”必须是彻底的而不是临时的,即其独立性必须维持其存活的整个期间;第三,“存活”没有时间长短的限制,因此,早产儿或者因为堕胎而排出母体之外的早期生命,只要具备独立存活的可能性,都必须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第四,“独立存活”的本质内容是不依赖于其他人身体提供的生理环境维持生命或发育为通常意义上的“人”;第五,“独立存活可能性”的判断必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抽象、概括的。①不能笼统地以怀孕超过22周或24周为判断标准。例如,如果以脑死亡为死亡的标准,则案例Ⅲ中的胎儿(15周)就具有独立存活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已经孕育28周的胎儿与母体分离之后不具备独立存活的可能性。个案中的早期生命是否具备独立存活的可能性,应当以医学的具体判断为准。
3.在母体之外但不具有独立存活可能性的早期生命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些早期的生命形态能够在母体之外保持活性,但离开他人身体提供的环境条件,不具有独立存活并发育为通常意义上的“人”的可能性,受精卵以及案例I中的冷冻胚胎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受精卵或冷冻胚胎也能够在母体之外保持活性,但为了发展成通常意义上的“人”,还必须借助他人提供的身体环境(通常表现为代孕)。如果将这种临时独立于母体的早期生命形态视为“人”,仍然可能引发将他人(主要是代孕者)当成生命发育“客观环境”的危险,例如,在这种情形下欺骗或强迫他人代孕可能符合紧急避险的特征。不过,这些早期的生命形态仍保持了活性,因此承载着家庭成员生儿育女的期待(案例I),②虽然不可避免要介入代孕这种在我国目前不被允许的行为(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但在事实意义上,其仍承载着家庭“香火”延续的可能性。也是值得保护的。但不能将其等同于“禁止杀人”中的“人”,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将其作为(蕴含着精神价值)的财物加以保护。③在案例I中,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都不否认胚胎属于“物”的一种。日本学者石原明也认为侵犯试管婴儿只能视为对财物的毁坏类犯罪。参见前注⑥,西田典之书,第9页。
与母体之外的受精卵、冷冻胚胎一样,因流产、早产或堕胎而排出体外的早期生命形态,即便能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活性,但只要不具有本文所限定的“独立存活的可能性”,就不应当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
(四)小结
综上所述,无需也不得为了保护家庭的生育利益而将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前移。为了防止孕妇被作为牺牲品,应当以“全部露出”和“独立存活的可能性”作为认定刑法意义上的“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人口政策的视角:有效性与正当性
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律意义上的“人”的认定。④参见唐海山、陈洪兵:《胎儿利益的刑法保护——以日本法为视野》,《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同前注13○,周详文。在这里,隐含着如下逻辑:在鼓励人口增长的社会中,刑法上的“人”的起点会被前移;相反,在控制人口的社会中,“人”的起点会被推迟。
(一)为鼓励生育将“人”的起点前移不具有正当性
首先,为了促进人口增长而将刑法上的“人”的起点提前,必然会限制孕妇的权利,因为一旦在“全部露出”之前承认刑法意义上的“人”,作为胎儿的“人”与母亲之间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如果允许为了人口增长而牺牲孕妇利益,孕妇就会被降格为生育的工具,这无疑是不正当的。⑤即便孕妇体内的生命并没有威胁到孕妇的生命或健康,以“禁止杀人”的刑法规范限制孕妇终止妊娠的权利也难称正当,因为它意味着强制支配孕妇的身体。堕胎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孕妇堕胎的自决权,但其在本质上只限制了中止妊娠的时间范围和方式,且仅限于故意行为,其禁止的手段也远比杀人罪的刑罚轻缓。与设置堕胎罪的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当今中国的受孕决定更容易受家庭或家族的影响,且在中国有关孕育和孩子抚养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其负担主要靠家庭承担,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更没有理由以“禁止杀人”的方式去限制孕妇的自决权。
其次,通过“人”的起点的前移来推行人口政策,在避孕和节育手段日趋有效的社会里,其长远效果也是有限的。女性可能会尽量避免受孕,或者选择在刑法介入的点之前终止早期的生命:如果刑法介入的起点是“着床”,当事人就会尽可能地通过现代医药技术阻碍“着床”;如果以“宫外存活的可能性”为生命的起点,孕妇就会在此之前选择人工流产。即便在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孕妇也可能通过“黑诊所”终止违背自己意愿的妊娠。
实际上,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并没有通过刑法来强迫女性生育,而更多地是在社会政策层面积极作为,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利益诱惑等刺激民众的生育愿望。至于堕胎罪的规定,更多只是为了营造或维持尊重生命的氛围,其作为刑法规范执行的价值非常有限。以德国为例,《德国刑法典》第218条规定了堕胎罪,但该法第218条a规定了一系列适用范围非常广的免罚事由,使堕胎罪对于孕妇的限制非常有限。孕妇在怀孕的前12周之内享有堕胎的最终决定权;当妊娠已经或可能危及孕妇生命或者严重危及孕妇健康时,孕妇堕胎是合法的;如果妊娠是性犯罪导致的结果,孕妇可以在12周之内合法地选择堕胎;孕妇在22周之内、在接受医生咨询后经医生实施的堕胎都不构成犯罪;如孕妇选择堕胎时处于特别的困境(in besonderer Bedrängnis),法官可以免除其刑罚。可见,堕胎罪针对孕妇执行的空间非常有限,它更多是为了防止违背孕妇意志的外界侵犯,这与将胎儿视为母体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在实际执行效果上并没有本质区别。
根据前述规定也可知,堕胎罪所保护的对象绝不是刑法上的“人”,因为一旦在刑法意义上将堕胎罪的对象视为“人”,就不能出于任何理由不处罚孕妇剥夺其生命的行为,除非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但主张对胎儿进行正当防卫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胎儿根本无法实施刑法上的行为,也因此不会构成“不法侵害”。可见,德国有关堕胎罪的规定,并没有改变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观念。
为了促进人口增长,不应限制对于生育具有决定权的孕妇,相反,应当赋予孕妇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例如,提高女性在孕育期间的保障水平,强化政府在孩子抚养方面的担当,减轻孕妇及家庭的负担,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经济压力而放弃生育;国家也完全可以建构相应的制度,让生育成为一种有回报的选择,直接以现实的利益刺激家庭的生育意愿。这比刑法层面的强制规范更仁慈也更有效。
(二)人口控制与“人”的起点
我国当前仍处在控制人口数量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仍非常旺盛。在这种背景之下,限制人口的数量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但控制人口的合法性,并不当然意味着每种人口控制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此外,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人口控制手段是否有效。
1.人口控制手段的正当性
这一问题既涉及孕妇权利,又涉及早期的生命。由于孕妇与早期的生命在生理上的紧密连接,人口控制很难绕开孕妇的基本权利。为了人口控制违背孕妇意志强行堕胎,就不可避免会支配孕妇的身体,侵犯孕妇的尊严。即便是法律,也不应当规定严重侵犯人的尊严的强制措施。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的控制人口的手段是“社会抚养费”,并未规定强制堕胎。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计划生育的任务,仍在行强制堕胎之实(案例IV),这无疑已经构成对孕妇的伤害罪。
不过,即便孕妇为避免交社会抚养费自愿接受堕胎,也需要进一步追问:孕妇是否有权处置其腹内的早期生命?因为只要早期的生命享有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资格,即便国家为了实现人口控制,即便孕妇同意,也不得杀死胎儿。①有学者一方面承认早期生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人”,同时又以计划生育政策将为了控制人口的堕胎这种“杀人”行为合法化。参见前注④,周详文。但很难想象刑法上的“杀人”能通过限制人口这种理由正当化。在当今社会,即便有法律规定可以通过杀人或发动战争限制或减少人口,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否定这种法律的正当性。因此,为了让孕妇同意的生育控制成为可能,就不能将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过于提前。否则,人口控制就只能通过避孕的方式实现,而避孕的有效性很难得到保证。
2.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仅以“社会抚养费”这种经济惩罚手段控制人口,其有效性自然是有限的。对于贫困的家庭而言,社会抚养费一般不具有执行的可能性;对于具有执行可能性的家庭而言,社会抚养费难以在根本上影响生育的决定。因此,要想有效地控制人口,只能考虑从源头上弱化当前仍非常强烈的生育意愿。
在当今中国,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养儿防老”的实用主义考量、“传香火”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人类对生殖的情感依赖,三者紧密交织,相互强化。生育意愿并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或情感,而是具有实用主义的基础,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利益衡量,即便生儿育女在特定环境下对某些社会成员而言并不“划算”,文化传统的惯性或情感依赖也能战胜“理智”,继续维持强烈的生育意愿。例如,向往个人自由的年轻一代也可能会顶不住上一代所给的压力或周围人可能的议论而被迫生儿育女;即便发现养孩子将面临被“坑爹”、“啃老”的高度危险,国民也会基于文化传统或对做父母的向往选择生育。因此,要想有效地控制人口,就只能从弱化这些因素着手。
要想从根本上减弱当前的生育意愿,最重要的是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老人关怀制度,并强化民众对养老体系和社会关怀的信任,以削减国民对子女养老的物质和精神期待。在西方社会,“丁克”文化盛行,不少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并敢于追求个人自由而选择不生育子女,是因为国家建立了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了其后顾之忧。而中国当前之所以有强盛的生育动力,是因为对养老保障缺乏信心,“养儿防老”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种选择模式经过一代代的重复,最终凝固为“香火”文化。农村地区的生育动力要强于城市地区,也是因为农民更不信任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在农村生育的成本相对而言更低。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上一代更有动力要求自己的子女生育下一代,因为其经历让他们更相信家庭养老而不是社会养老,同时他们也更多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更迫近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老无所依。这些原因让当前的青年夫妻放弃个人自由,自愿或不自愿地背负起了生育和抚养的沉重负担,甚至不惜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老年的幸福生活进行实际上未必有保障的投资。
(三)小结
可见,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控制人口,法律上的强制既不正当,也不会有效。促进人口增长,只能通过社会政策层面的举措,以利益刺激民众的生育意愿。限制人口,也只能通过社会政策层面的措施,为子女这种养老保障方式和情感依赖寻找可靠的替代品,并以此消解当前的生育文化,引导国民自愿控制生育。当然,为了给孕妇自愿的生育控制留下法律上的空间,不能将“人”的起点过于前移,否则就会压缩人口控制的空间。
五、道德伦理的视角:以杀人罪的法定刑为手段吗
在道德伦理层面,生命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也会受到绝对的尊重和保护。但这种意义上的保护,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刑法意义上的“人”的判断?
(一)刑法对道德伦理的“阳奉阴违”
“与道德伦理的分离”是现代刑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在“保护人的生命”的道德伦理要求面前,刑法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在顺从这种要求的同时,刑法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它不能跟道德伦理一样,只提出要求,而将其执行交给个人的良知;相反,刑法的禁止或命令,不仅具有行为规制的强制效力,还可能带来刑罚这种带有道德伦理谴责的严重利益剥夺。也正因为在现实层面的落差,道德伦理“敢于”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而刑法必须保持谦抑,只能守卫“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种两难的格局中,面临道德伦理压力的刑法,完全可能呈现出对道德伦理提倡“阳奉阴违”的一面。德国有关堕胎罪的立法,提供了这方面的鲜活实例。
197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堕胎罪中“一定期限(着床后12周)内的堕胎许可”(Fristenlösung)作出了有关胎儿生命权的第一次判决。它认为,母体内的生命是受《德国基本法》保护的独立法益,在整个妊娠期间,它都享有优先于孕妇自决权的地位。①Vgl. BVerfG, NJW 1975, 573.为了顺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要求,《德国第十五次刑法改正法》废除了这种堕胎许可,在表面上服从了“保护未出生的生命”的要求。不过,为了避免过度限制孕妇的权利,该改正法又在《德国刑法典》第218条a中规定了包括“一般的困境适应症”在内的四种正当化事由。这些“适应症”,为堕胎打开了合法通道,大量出于经济考虑的堕胎在这里找到了合法理由,其现实效果与此前的立法相差无几。②Vgl. Reinhard Merkel, in: Kindhäuser u. a., Fn. 7, Vorbemerkungen zu den §§218ff., Rn. 9.
为了统一原东德、西德各州的立法,德国联邦议会于1992年颁布了《孕妇与家庭救助法》,规定受孕前12周之内、经孕妇要求、在至少三天前接受过咨询且由医生实施的堕胎是“合法的”(rechtmäßig)。对此,联邦宪法法院于1993年作出了第二次有关胎儿生命权的判决,指出:国家有义务保护生命,包括未出生的生命,这种义务即便在母亲面前也不得让步;原则上,堕胎是一种应加以禁止的不法(Unrecht),孕妇有怀孕至足月分娩的义务。③Vgl. BVerfG, NJW 1993, 1751.此后,《德国刑法典》第218条a再次被修正,修正后的内容是:符合前述条件的堕胎是“违法的”(rechtswidrig),只不过不符合堕胎罪的构成要件。但只要没有处罚的可能,孕妇就享有是否堕胎的最终决定权,因此这种堕胎实际上仍然是“合法的”。
可见,在早期生命的保护这一问题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与《德国刑法典》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直坚持胎儿生命权享有宪法保护的地位,而刑法一直在为一定条件下的孕妇堕胎自由寻找空间。就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刑事立法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衡:联邦宪法法院在坚持“说法”,而刑事立法在追求实效,同时,双方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对方的立场。其原因在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即便明知在法律上承认胎儿生命权不可行,也不能放弃这一“说法”,否则,有关生命的道德伦理就会出现滑坡;这种坚持是否能够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对于联邦宪法法院而言反倒显得不重要了。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联邦宪法法院的坚持和部门法的效果之间存在的鸿沟。
在德国,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理论上的通说都以分娩的开始作为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在此之前的早期生命绝非刑法意义上的“人”。其他部门法也没有完全遵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立场,而是为符合《德国刑法典》第218条a的堕胎提供了“配套服务”:以这种堕胎为内容的合同是有效的;不得为了救助胎儿生命而对实施这种堕胎行为的孕妇进行正当防卫;堕胎期间孕妇有权继续领取薪水;国家为有需要的堕胎孕妇提供经济上的社会救助,并承担“为堕胎提供充足的、覆盖各地区的医疗机构”的义务。④Vgl. Merkel, Fn. 29, Rn. 20.
由此可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主张的“保护胎儿的生命权”,原本就只是一种道德提倡,其目的在于唤醒或维持民众对未出生的生命的尊重。⑤Vgl. BVerfG, in: NJW 1993, 1751.对刑法而言,法规范的本质不在于如何表述,而在于其适用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⑥Vgl. Merkel, Fn. 29, Rn. 21.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未出生的生命享有生命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抒情诗”(Verfassungslyrik),而并非一种法律现实(Rechtswirklichkeit),⑦Vgl. Norbert Hoerster, Das “Recht auf Leben”der menschlichen Leibesfrucht-Rechtswirklichkeit oder Verfassungslyrik in: JuS 1995, S. 192 ff.即便它能够促使国家采取积极的救助性措施保护早期生命,即便能够因此而设置一些不会严重限制自由的轻微犯罪(如《德国刑法典》第218条规定的堕胎罪、第219条a规定的堕胎宣传罪、第219条b规定的经营堕胎工具罪等),也不能从中推导出“未出生的生命是刑法上的‘人’”这一结论。
(二)刑法介入道德伦理的限度
根据当前理论上的通说,刑法的目的在于法益保护,因此,纯粹违反道德伦理规范的行为,不是刑法规制的对象。但在实践层面,当前的刑法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贯彻某些重要道德伦理规范的推手。例如,德国《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gesetz)规定了一系列的犯罪,包括滥用生殖技术、滥用人类胚胎、非法性别选择、未取得当事人同意的人工授精、对人类生殖细胞的人工更改、人类克隆、运用人类生殖细胞进行杂交等。在我国,虽然相关的行为并没有被规定为犯罪,但如下行为也被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实施代孕技术;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等。
严格依照当前居于通说地位的“法益”理论,根本找不到这些规定的实质依据。就连坚决捍卫法益理论的Roxin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胚胎保护法》设定的犯罪,是他界定的法益概念所无法解释的,因为他的法益概念是“一切为了个人自由发展、个人基本权利实现以及建立在这种目的之上的国家制度运行所必需的事实状态与目的设置”,①Vgl. Roxin, Fn. 16, S. 16.而胚胎毕竟还不是“人”,针对胚胎的行为并不会直接影响已经出生的“人”的自由共存。②A. a. O., S. 30.在这种意义上讲,进入刑法保护范围的动物(德国《动物保护法》设有虐待动物罪)、植物甚至堕胎罪的保护客体等都无法被前述法益概念所涵盖。但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对这些对象的保护或对特定行为(如买卖配子、非法人工代孕、人与动物生殖细胞的杂交、非法性别选择、为了疾病预防与治疗之外的目的更改遗传基因、案例V中的为了摘取器官而怀孕并堕胎)的禁止是不可放弃的。根据当前主流的观点,设置这些犯罪是为了保护一种道德秩序(sittliche Ordnung)、③Vgl. Michael Pfohl, in: Wolfgang Joecks/ Klaus Miebach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StGB, Bd. 6, 2. Auflage, C. H. Beck 2013, TierSchG § 17, Rn. 1.一种信念价值(Gesinnungswert),④Vgl. Wilhelm Gallas, Beiträge zur Verbrechenslehre, de Gruyter 1968, S. 13.因此即便离开法益,也有一定的正当化根据。
然而,这种保护道德伦理情感的刑事立法,在当今社会只能是一种例外。不仅在罪的设立范围上应当严格限制,在规制相应犯罪的手段上也应当保持谦抑和克制。因此,即便在特定的情形之下允许刑法适度引入道德伦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将道德伦理层面的论题直接复制到刑法领域,更不意味着要赋予道德伦理保护对象以“主体”的资格。⑤有学者认为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动物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Vgl. Georg Freund, in: Joecks/Miebach, Fn. 37, Bd. 1, Vorbemerkung zu den §§ 13 ff., Rn. 53. 但如果其生命权、自由权都可以被剥夺,这样的法律地位究竟依附于谁?能够接受的方式是通过立法确立特定的行为犯,配置相对而言比较轻微的法定刑,以规制严重侵犯国民道德伦理情感的行为。可见,对于早期生命所涉的道德伦理情感,即便要动用刑法予以保护,也必须节制刑罚的量,不得随意启用刑法保护“人”的生命这种现实的法益时所用的严厉手段。
(三)小结
由此可见,道德伦理意义上如何看待生命,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刑法是否规制特定的行为,但并不会影响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的确定。
六、结 论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有关刑法中的“人”的起点的理论和实践都体现出了某种不严谨甚至不严肃,它们对“人”的起点的确定,随意得有如欧洲殖民者在地图上瓜分北非的领土。在各种学说背后,既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也未能体系性地分析自己的主张对相关利益主体和当前制度的影响,其无疑是难以被接受的。通过前文多维度的分析,就刑法上的“人”的起点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部分露出说”、“分娩开始说”所依赖的事实根基已经完全过时,“断带说”、“发声说”、“独立呼吸说”等欠缺自然科学的依据,应当被淘汰;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的确定,是一个规范性的判断,没有必要为了追随自然科学的步伐而将“人”的起点提前至“受精”或者“着床”。
第二,保护家庭的生育利益并不需要将早期的生命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否则将严重限制孕妇的权利,在极端的情形之下甚至可能将其推向绝境。对于孕妇体内的早期生命,可以将其作为孕妇身体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对于母体之外的生殖细胞、胚胎或者离开母体环境不能独立存活的早期胎儿,最多只能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果早期生命已经完全独立于母体,且能不借助他人身体提供的环境而存活,则应当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
第三,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限制人口,都应当通过社会政策层面的措施影响民众的生育意愿,而不是通过调整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进行强制。但为了限制人口,不宜将“人”的起点过于提前,否则就会限制孕妇同意情形下的生育控制。
第四,道德伦理层面“保护生命”的提倡,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法是否设置特定的保护民众道德伦理情感的犯罪,但并不影响刑法意义上的“人”的起点的确定。
综合前述分析,只有在如下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才能肯定早期生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人”:其一,早期生命已经在事实上完全与母体分离;其二,早期生命具有独立存活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杜小丽)
DF614
A
1005-9512(2015)03-0077-12
陈金林,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法官释法’的困境分析”(项目编号:2012M5214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受武汉大学“70后”学术团队“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刑事法治问题研究团队”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