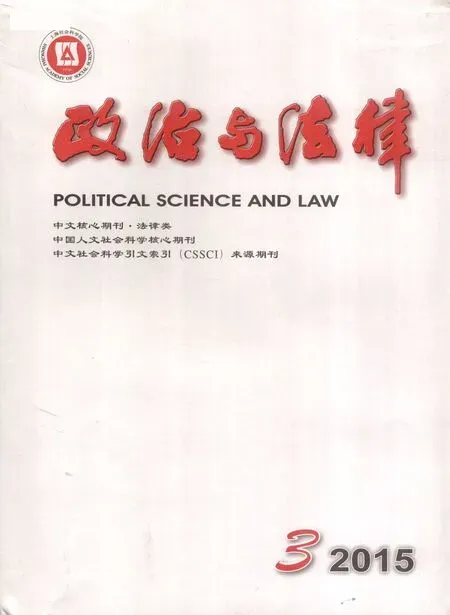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认定与处罚
——从剖析非法占有目的入手
2015-01-30张开骏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3
张开骏(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3)
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认定与处罚
——从剖析非法占有目的入手
张开骏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3)
财产犯中的取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目的内涵是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没有必要。凡是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或者说,凡是以单纯毁坏、隐匿意思以外的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的,都可以评价为利用意思。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场合,行为人对被盗物品具有利用意思,满足了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具有客观窃取行为与主观盗窃故意,因而成立盗窃罪。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单纯体现财产法益的物品时,如果真实具有返还财物的意思,成立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实质一罪,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仅有勒索钱款的意思而无返还财物的意思,以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并罚。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车牌时,由于车牌这一对象的特殊性,勒索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符合多次盗窃或数额较大的标准,成立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两者是法条竞合关系,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不符合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只能论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非法占有目的;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盗窃罪;敲诈勒索罪
行为人实施前后相继的两个行为以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比如,盗窃他人物品以勒索钱款;将借给他人的物品盗回以骗取钱款赔偿;盗窃他人财物后以捡拾者的身份骗取酬谢;侵占他人财物后骗其放弃返还要求等。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前后相继(而不是横向上相互交织)的两个行为,主观上有将一行为作为手段,另一行为作为目的的意思,目的是获取他人财产(多数情况是为了最终获取钱款)。这些日常所见的犯罪行为,其犯罪性质看似简单,却不易厘定,在涉及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及处断等问题时,刑法理论和刑事实务存在着严重分歧。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类型,这对建构分析框架以解决同类犯罪情形将有所裨益。
一、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问题提出:案例裁决与分歧意见
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案件中,勒索金额一般与被盗物品的实际价值大抵相当,也有的低于或高于物品价值(被害人为免予影响生产、生活或者有主观价值,而愿意支付高价赎回)的情况。盗窃对象的不同有时候会影响犯罪认定,这并不限于财产犯。实践中也存在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枪支、弹药等情形,会涉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些对象也具有财产属性,可以评价为特殊财物(比如在处理抽象事实错误时),在侵犯财产法益上具有共同点。下面大致区分两类案例,分别加以讨论。
(一)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和盗车勒索案
案例一,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2002年2月17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李正敏携带起子、钳子潜入乌鲁木齐昆仑公司星火牛场实验室,撬开实验室门锁,从室内盗出一台日本产ET-IN型胚胎冷冻仪(价值36000元),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匿名信放在实验室。被告人李正敏在信中以匿名人的名义和以交换胚胎冷冻仪作为条件,向昆仑公司负责人冯立社索要现金55000元,并要求冯立社将钱交于李正敏(即被告人本人)。随后,被告人李正敏将所盗的胚胎冷冻仪藏于该牛场场区的一旧库房内。2002年2月19日,昆仑公司将一张50000元的存单交给了李正敏,李正敏当时答应取上钱后即将冷冻仪交给冯立社。2002年2月21日,当被告人李正敏持冯立社交予的一张50000元存单到银行取钱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正敏犯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一审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正敏为了非法占有昆仑公司的财产,先盗窃该公司的胚胎冷冻仪,后又以此胚胎冷冻仪向该公司勒索55000元现金,其勒索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又构成盗窃罪,系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断即按盗窃罪定罪处罚。”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于2002年6 月21日判决被告人李正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二审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完全认可一审的判决理由和结论,于2002年8月2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刑事专辑》(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360页。
案例二,盗车勒索案。2009年3月9日晚,被告人徐韩伟在象山县丹东街道文韵路文韵茶馆楼下欲盗窃车内财物。其用砖头砸碎车窗进入戴照敏的牌号为浙BFD427号中华骏捷汽车内后,发现汽车钥匙插在车上,即将汽车开走并摘下车牌号,汽车价值人民币65100元,后将车开至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后花坛处藏匿。同年3月11日,被告人徐韩伟电话联系车主戴照敏,以帮戴找回汽车为由索要人民币20000元。3月15日,被告人徐韩伟再次电话联系戴照敏索要钱财时,被公安民警抓获。案发后,汽车及车内物品均被追回并归还被害人。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一开始指控被告人徐韩伟犯诈骗罪,后变更起诉为盗窃罪。一审象山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韩伟以秘密的手段窃取他人车辆,而后又采用敲诈勒索的行为,以实现其变现的非法占有目的,其已分别实施了盗窃和敲诈勒索行为,因属于牵连犯罪,应择一重罪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判决被告人徐韩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提出上诉,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盗窃车内财物)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其辩护人认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定性。二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徐韩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的手段窃取他人车辆,数额巨大,而后又假借帮助车主找回车辆,对车主实施敲诈行为,数额巨大,其分别实施了盗窃和敲诈勒索行为。鉴于上诉人的二个行为均系针对同一被害人,且敲诈勒索行为最终未完成,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上诉人徐韩伟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参见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象检刑诉[2009]505号起诉书、象检刑诉[2009] 5号变更起诉书;一审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刑事判决书(2009)甬象刑初字第636号;二审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0)甬刑二终字第9号。
盗窃的对象是单纯体现财产法益的普通物品时,可能涉及的罪名是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我国目前存在如下几种意见。其一,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盗窃是手段,敲诈勒索是目的,从一重罪以盗窃罪处罚。这是理论和实务上几乎处于通说的观点,比如前述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的一、二审理由和盗车勒索案的一审理由。其二,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吸收犯,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以盗窃罪处罚。这也是实务上具有普遍性的一种观点,比如前述盗车勒索案的二审理由。其三,敲诈勒索罪一罪。有学者提出:“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就具有以所盗财物进行勒索的打算,由于存在返还的意图,对于所盗财物本身应否定排除意思,不成立盗窃罪;以所盗财物进行勒索的,成立敲诈勒索罪。”③陈洪兵:《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二)盗窃车牌勒索案
案例三,盗窃车牌勒索案。被告人杨伟宁于2008年12月15日晚上至16日凌晨,到广州市海珠区沥滘北村新城路旁,盗得被害人刘良德停放在该处的车牌号码为粤A9K057的出租汽车前车牌1个(价值人民币105元)。同月17日晚至20日凌晨,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伙同同案人覃志为(另案处理)到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的大沙、南洲路等地盗窃机动车的车牌,并在盗窃的机动车上留下被告人杨伟宁的电话号码勒索钱财,先后盗得被害人鲁彬、蔡声海等的15辆机动车车牌17个(上述物品共价值人民币1575元)。同日6时许,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因形迹可疑被抓获,如实交待了上述犯罪事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犯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提起公诉。一审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1日判决两名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杨伟宁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处贝荣坚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机动车号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的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性不准确,法院不予支持。惟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在犯罪后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两被告人盗窃多块机动车号牌,社会影响恶劣,在量刑时酌情从严处罚。”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④参见一审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9)海刑初字第438号;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9)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98号。
围绕盗窃车牌以勒索钱款的具体事例,我国近年来有集中讨论,存在以下不同见解。其一,盗窃罪一罪。有学者认为,“单纯使被害人产生困惑的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例如,盗窃他人车牌后告知对方,如果交付200元即可返还车牌。对此,只能认定为盗窃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⑤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0页。其二,敲诈勒索罪一罪。有实务工作者认为,车牌只是车辆使用凭证载体之一,与其所代表的上路行驶权是分开的,其本身价值甚微,且无法单独流通,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单纯盗窃车牌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也不能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对于记名的权利凭证,刑法评价点不在于前面的非法获取,而在于其后的非法兑现、使用行为,即后续的索财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属于徐行犯的犯罪形态,数额应累计计算。⑥参见吴加明、叶小舟:《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4期。其三,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一罪。有的实务工作者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是要挟车主用钱赎回车牌,而不是将车牌占为己有,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以勒索财物数额较大为必要条件,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该类案件每次作案的数额可以累计、在多长时间内累计。累计每次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本案不宜以敲诈勒索罪处理。汽车号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无须以车牌的价值为定罪量刑的条件,这样有利于解决对车牌价值的争议。①参见李云:《盗窃车牌索财如何定性》,《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其四,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从一重罪以盗窃罪处罚。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机动车号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车牌是手段行为,索要财物为目的行为,成立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即以盗窃罪处罚。②参见王路真:《盗窃机动车号牌索财的案件如何定性》,《中国审判》2010年第9期。也有实务工作者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盗窃车牌后实现其变现的价值,盗窃行为是直接行为,敲诈勒索是盗窃后为实现直接目的而实施的附属或手段行为,目的是将盗窃所得的赃物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盗窃罪名更能体现其主观恶性。③参见赵靖:《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22期。其五,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从一重罪以敲诈勒索罪处罚。有实务工作者认为,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不属于公私财物,没有价值,所以撬盗车牌的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勒索财物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两罪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关系,以敲诈勒索罪处罚。④参见陈建平、韩彦霞:《盗窃车牌勒索钱财案件之定性》,《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4期。其六,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与敲诈勒索罪并罚。有实务工作者认为,盗窃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以所有意思对财物进行使用或处分。在撬盗车牌勒索财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并非意图占有车牌,只是将车牌作为敲诈的筹码,在敲诈未果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对藏匿的车牌废弃不管,并不作销赃处理。故为索钱而盗牌的行为不符合盗窃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构成盗窃罪。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的数额应可累计计算,成立敲诈勒索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与敲诈勒索罪是牵连犯,但对牵连犯应区别情形而定,在两罪都无法完全评价整个行为时,应实行并罚。⑤参见卢雪华:《盗牌索钱行为刑法评价问题探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6期。
盗窃车牌勒索案可能会涉及其他罪名,具有一定特殊性,但与第一类案例面临着许多共同并且是基础性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本文以单纯体现财产法益的普通对象为例进行探讨。
在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情形中,我国研究者往往不加思索地认为,行为人不想要被盗物品,其目的在于勒索钱款,因而否定盗窃罪,主张只成立敲诈勒索罪,或者行为人实际上窃取了物品,就成立盗窃罪,或者成立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或吸收犯(这两种罪数形态经常被滥用)。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本质以及罪数形态等,都缺乏认真研究,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道理。凭着直觉纵然可以轻松地得出结论,却提不出确实的依据和理由,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唯有“既破又立”的论证和结论才有说服力,才有利于推进理论深入和确保司法精确。这些犯罪行为侵犯了财产法益,且大多属于取得罪,非法占有目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
二、非法占有目的国内外学说、判例及本文立场:以盗窃罪为中心
(一)国外学说、判例和国内见解
在日本,对“不法领得的意思”(相当于我国的“非法占有目的”)研究得很精细,学说见解纷呈。日本刑法财产罪没有明文规定“不法领得的意思”,学界对此存在必要说与不要说(大塚仁、曾根威彦等)之争;在必要说内部,又存在着排除、利用意思说(两者需同时具备,平野龙一、大谷实、西田典之、山口厚等),排除意思说(仅有排除意思即可,团藤重光、福田平等),利用意思说(仅有利用意思即可,前田雅英等)的分歧。⑥参见[日]曾根威彦、松原芳博编集:《重点问题刑法各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95页以下。目前,必要说及其内部的排除、利用意思说是日本通说和判例见解。不法领得的意思,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排除意思),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利用意思)。排除意思将不值得处罚的盗用等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利用意思将取得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区分开。一方面,财产罪可以分为取得罪和毁弃罪,盗窃罪等属于取得罪,是获取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犯罪,而毁弃罪是单纯导致对财物不能利用的犯罪,所以取得罪的实行行为必须是出于利用财物目的而实施的。这个意义上的不法领得意思,具有区分取得罪和毁弃罪的机能,而且能够说明二者的法定刑差异。另一方面,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能成立犯罪。暂时使用他人财物的盗用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还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因此不法领得意思具有限制处罚范围的机能。不法领得意思具有区分罪与非罪(限定处罚)、此罪与彼罪(犯罪个别化)的机能,因而成为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内容。①参见[日]中森喜彦:《不法领得の意思》,载[日]阿部纯二等编:《刑法基本讲座》(第5卷),法学书院1993年版,第87页。话虽如此,学者间关于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的理解存在差异。
一方面,关于排除意思,一直占有、永久使用的意思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判例最初的态度仅限于此,则使用盗窃都不可罚,但是后来出现缓和化的倾向。山口厚根据判例进行归纳,认为以下三种情形也具有排除意思。其一,虽然只有一时使用的意思,但没有返还的意思,而是在使用后加以放置或毁弃。比如,盗用他人汽车开到目的地后抛弃的。其二,虽有返还的意思,但侵害了他人的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这需要综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被害人利用财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程度、预定的妨害利用的时间长短、财物本身的价值大小等。比如,在农忙季节盗窃他人耕牛,农忙结束后返还的。其三,虽然返还并对利用可能性的侵害轻微,但取得(消费、消耗)了财物中的价值。比如,为了退货取得现金而从超市窃取商品。②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199页以下。据此,排除意思至少包括“一直排除和支配”(一直占有并使用)、“一直排除、一时支配”(使用后抛弃)、“一时排除和支配”(侵害相当程度利用可能性的使用后返还)、“短时排除和支配”(取得或消耗财物中价值的使用后返还)四种形式。由此可见,日本的理论通说和判例见解对排除意思的认定是比较宽泛的,不限于形式上的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侵害了他人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或者取得(消费、消耗)了财物中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日本判例在要求不法领得意思具有排除意思的前提下,将很多使用盗窃(盗用)行为也认定为盗窃罪。比如,为了搬运赃物多次于夜间使用他人的汽车,次日早晨返还的;深夜无照驾驶他人的汽车,四个小时后被扣押的。事实上,只是将轻微的不具有可罚性的盗用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就实际的认定结论而言,排除意思的肯定与否定的各说之间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肯定论者坚持主观的利用妨害意思不可或缺,而否定论者主张仅根据客观的利用妨害程度即可。另一方面,关于利用意思,日本判例最初认为是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处分,但是后来判例的见解也经历了不断扩大解释的过程,即遵从物品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不限于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和本来用途。比如,男性基于性癖窃取女性内衣;窃取家具烧火取暖;骗取钢材当废品出卖;为了捆木材而切割电线。甚至可以说,凡是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或者说,凡是以单纯毁坏、隐匿意思以外的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的,都可能评价为利用意思。
德国刑法中盗窃罪明文规定“非法占为己有或使第三人占有”(第242条),③《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包括“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两个要素。前者是指意图获取财物本身或其经济价值,而持续性地排斥或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消极要素);后者是指意图使自己或第三者具有类似所有人的地位,而将所取得财物作为自己或第三者所有之财产(积极要素)。刑法理论认为,如果打算在使用后将财物抛弃的,具有排除占有意思;如果具有取得财物价值的意思,仍然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①转引自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除了刑法专门规定的盗用交通工具的犯罪(第248条b),也不排斥其他对象盗用的可罚性。
英国《1968年盗窃罪法》规定盗窃罪要求“永久剥夺他人财产的故意”(第1条第1款),它是指使他人永久性地丧失财产,把属于另一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像处置自己财产一样不顾他人的权利去处置该财产的意图(第6条第1款)。同时其作了扩大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不具有使他人永久性地丧失财产的意图而把属于另一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的,如果行为人具有像处置自己财产一样不顾他人的权利去处置该财产的意图,那就应当被视为他具有永久性地剥夺他人财产的故意。假如,而且仅假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下财产的借入和借出等于完全地处置了财产,这种借入和借出就可以被看做是被告像处置自己财产一样不顾他人权利去处置该财产”(第6条第1款);“在不可能履行归还财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出于他自己的意图而未经他人授权而放弃财产,就等于是像处置自己的财产一样不顾他人权利去处置该财产”(第6条第2款)。另外,其专门规定了“未经授权占用机动车辆或者其他运输工具罪”(第12条)。②《英国刑事制定法精要(1351-1997)》,谢望原主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以下。英国判例认为以下情形成立盗窃罪:在伦敦的饭店为雨所困,窃取他人的伞以在去车站途中遮挡风雨,到达诺丁翰时将伞遗弃在火车上;窃取他人财产,意图使他人购买才能复得该财产;窃取他人的财产并将其质押,意图有一天能将其赎回并返回给他人;窃取他人戒指,除非收到了报酬才返还;从牛奶场盗走牛奶代价券,意图还给他们以换取牛奶;从一个游艺俱乐部所有人手中盗走游戏用的筹码,意图还给他们以换取游戏的权利。③参见[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以下。这些判例态度与日本判例具有相似性。英国不要求盗窃罪主观上具有利用意思,体现出财产罪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还比如侵占被规定在盗窃罪中)。比如,取走他人的信件扔到厕所,使他人的马匹掉进矿井,取走他人的钻石扔进池塘等,都构成盗窃罪,尽管行为人仅是意图使他人遭受损失,而不是为其本人或者任何其他人获得利益。④同上注,J·C·史密斯、B·霍根书,第603页。
德国、英国刑法强调排除意思,是由于刑法对盗窃罪主观要件做了明文规定,限制了学理解释的张力。尽管表面上强调永久性或持续性地排除占有,但制定法、理论和判例都作了扩大认定,无不承认使用后抛弃的可罚性,也认可严重盗用行为的可罚性,其中蕴含了对财物价值的利用这一成分。
随着国外知识引进本土刑法学,我国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展开热议。少数学者主张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⑤参见张红昌:《财产罪中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质疑》,《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比如刘明祥教授认为:“从本义上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意思),这是盗窃等取得罪的故意所包含的内容。”⑥刘明祥:《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必要说在我国是压倒性的通说,但对非法占有目的含义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统编类教科书一般将“非法占有目的”表述为,“将公私财物非法转为自己或者第三者不法所有”(不法所有说),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96页。或者“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己有或归第三者占有”(意图占有说),⑧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6页。但对其内涵语焉不详。不法所有说的缺陷在于,没有完整地认识财产罪的保护法益。财产罪不仅保护所有,也保护合法占有以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意图占有说与故意的内容无异,若如此,非法占有目的就无必要。黎宏教授主张非法占有目的只能从本来意义即“永远占有他人财物的意思”角度加以理解,没必要赋予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的额外内容。他只认可“一直排除和支配”、“一直排除、一时支配”时永远占有财物本身,返还了财物的就不具有对财物本身的非法占有目的。使用盗窃不是对财物本身的盗窃,而是对财产本身的利用价值或者说是利用财物本身所产生的财产性利益的盗窃,行为人也具有永远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①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719页。可以将此称为“永远占有说”。“永远占有他人财物的意思”表述类似于英国制定法中盗窃罪的规定,突出了排除意思。从使用盗窃也可能成立盗窃罪的观点看,黎宏教授不反对一时占有财物的盗窃罪,只不过对对象作了不同理解,即财物的利用价值或财产性利益。这同时也说明,黎宏教授没有忽略非法占有目的中对财物价值的利用这方面内容。有学者完全认同黎宏教授的观点,并且主张将利用意思排除在非法占有目的内容之外,辅以建立占有的理论,以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区分机能。②参见蒋铃:《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内容和机能》,《法律科学》2013年第4期。(2)与上面这些观点和视角不同的是,有的独著类教科书有意识地借鉴国外学说阐述非法占有目的。张明楷教授赞同日本通说和判例见解,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前者重视的是法的侧面,后者重视的是经济的侧面,二者的机能不同”。③同前注⑤,张明楷书,第847页。周光权教授将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永久而非暂时地排除他人的占有,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之物,并遵从财物的经济价值加以利用或者处分的意思。”同时周光权教授认为:“遵从财物的经济价值对财物加以利用或者处分的意思,是指行为人有意享受该财物本身所具有的利益与效用。改变财物用途,但仍然对该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享用的,仍然认为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盗窃他人数量较多的木材,将其砍成小块,然后作为柴火取暖的,构成盗窃罪而非故意毁坏财物罪。”④周光权:《刑法各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可见,他采纳了排除、利用意思说。排除意思使用了“永久而非暂时地排除”的表述,似乎比日本判例限制更多;尽管利用意思表述为遵从财物的“经济价值”,但作了扩大解释,与日本判例差异不大。(3)排除意思说。有学者认为,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内涵是指排除意思,意在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图,利用意思包含在排除意思之中。⑤参见谭明、洪峰:《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分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4)利用意思说。有学者认为:“从机能的角度来说,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必要的。其必要性的根据主要在于我们期待其能够发挥犯罪个别化的机能,即能够划定盗窃罪与器物损坏罪的罪间界限的机能。”“排除意思未必是必须的,排除意思完全可以被包含在盗窃罪的故意之中,与盗窃罪客观上的窃取行为相对应。”⑥王充:《论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
(二)笔者的立场:利用意思说
我国刑法的财产罪没有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规定使用盗窃的专门罪名,严重盗用行为值得刑罚处罚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所认可,同样,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刑罚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些都类似于日本刑法。因此,日本“不法领得的意思”的学说和判例见解,对我国的刑法解释论具有借鉴意义,只是需要观照其学说与判例演变趋势,以发展眼光进行学术鉴别。笔者的立场是,非法占有目的内涵是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没有必要。
首先,非法占有目的是必要的。
财产犯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同于犯罪故意。盗窃罪的客观要件是盗窃公私财物,构成要件具有故意规制机能,盗窃故意是认识到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会发生危害他人财物的结果(他人占有的财物被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并且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但盗窃的本质是对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侵害,仅有转移占有的意思是不够的,还需要像所有人那样进行利用的意思。由此决定了取得罪在犯罪故意之外,还需要包含了利用意思的非法占有目的。
强调非法占有目的,并非意味着只通过目的主观要件区分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而是为了从主、客观两方面更好地进行区分。因为盗窃罪是状态犯,不能单纯根据行为后的状态判断行为性质,既然要根据行为时的情况判断,就需要考虑行为时的意思,①参见前注③,张明楷文。利用意思即是如此。
其次,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利用意思。
笔者赞同日本通说和判例对利用意思的缓和理解,即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其缓和理解可能给人们造成利用意思没有实际意义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缺少了利用意思,对于取得罪与毁弃罪即使在客观上可以区分,但结论也不妥当;而且对于两罪界限模糊的特殊情形,确实无法区分;再者不能说明我国刑法中取得罪的刑罚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实质根据。
在占有或毁坏财物的界限等客观事实明确的场合,强调利用意思会得出更妥当的结论。比如,“A取走与自己珍藏的高价邮票相同而属于B所有的邮票,并加以毁弃,而使自己所有的邮票成为世界上现存独一无二的邮票,以提高其交易价格”,外观上虽是毁损或丢弃他人之物,但实质上是实现自己经济目的的行为,成立盗窃罪,②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修订五版),作者发行2005年版,第329页。根据缓和的利用意思说,便容易解释和理解。再如,行为人窃取了他人的财物,一直藏着,自己也不享用,以免被找到或发现的行为,如果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利用意思,则因为行为人没有利用意思,而只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反之,如果认为不需要利用意思,则成立盗窃罪。确实,排除意思说的学者会主张,只要有隐匿、毁坏的意思,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③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第三版),创文社1990年版,第563页;[日]福田平:《全订刑法各论》(第3版增补版),有斐阁2002年版,第231页。但这样的结论无法被接受,因为盗窃等取得罪是利欲犯,出于单纯隐匿、毁弃意思而取得财物的成立毁弃罪,是非常自然的结论;换句话说,取得财物而不享受可能的效用、利益的,难以称得上是取得罪。比如,“行为人窃取他人之物,可能无意自己使用,而只为了暂时破坏他人的持有,例如:考场外取走劲敌的书籍资料,考试后复归原位。这类故意的窃取,欠缺不法所有意图,不成立窃盗罪”。④林东茂:《刑法综览》(修订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页。又如,强奸犯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而夺走其手机,或者杀人犯为了毁灭证据而夺走被害人身上的贵重手表,扔到别处的,不能认为具有利用意思,对财物不成立抢劫罪或盗窃罪,而是故意毁坏财物罪;行为人窃取他人位于六层房间内的彩电,在没有出现障碍会影响占有的情况下,将彩电从位于五、六层中间的楼梯窗户扔出的,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利用意思,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
有的学者主张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认为用“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分析财产罪的客观方面,就可以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盗窃罪是侵害占有、建立占有,故意毁坏财物罪是侵害占有但没有建立占有。⑤参见尹晓静:《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客观分析之提倡》,《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1期。笔者认为,以上对占有的侵害、建立的分析符合取得罪,毁弃罪在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如此,因而能发挥很大的区分作用,但不能绝对化。其一,行为人基于毁弃的意思,将窃取的财物搬离现场后再抛弃的,毫无疑问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此时行为人也建立了占有,尽管是暂时的。对于侵害了占有而一直隐匿、不使用的情况,根据该观点就是取得罪,但是,一直不使用并不能直接得出利用意思,还是要根据现实情况下主观上有无利用意思进行区分。一方面,如果是“单纯地”隐匿意思,虽然客观上建立了占有,也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比如,为了防止被害人找到被窃财物,行为人不使用也只是为了避免被发现罪证的情况。另一方面,客观上虽然隐匿,也没有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本来用途进行使用,但主观上可以评价为具有利用意思的,应认定为盗窃罪。比如,男性基于性癖窃取女性内衣,或者有盗窃手机癖好的人窃取他人手机后一直锁在柜中的情况。⑥例如,甲有偷手机的癖好,见到别人的手机就想偷来据为己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竟偷到了120部手机,每偷到一部,就将其扔到柜子中锁起来,并无使用或销赃之行为,直到案发。参见左袖阳:《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2期。其二,故意毁坏财物罪也不一定侵害占有。比如,明知是他人的遗忘物而将其毁弃的,毫无疑问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此时是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直接侵害,并未侵害占有。
在短时间转移占有后抛弃、客观上占有与毁弃界限模糊的场合,主观上的利用意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时,利用意思的判断规则如下。其一,如果查明具有利用意思,就属于占有,成立盗窃罪。在财物发生了转移且最终被毁弃,行为人没有主动坦承利用或毁弃意思的场合,应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刑事推定,如果能够肯定利用意思的,可以判定成立盗窃罪。①例如,被告人李某某原系被害人雇用的司机,后不再被雇用,心怀不满,伺机报复,于2004年11月24日晚来到停放被害人车辆的停车场,趁工作人员不备,持未归还的车钥匙将被害人的中巴车(价值人民币12433元)开走。次日20时许,李某某驾车时与路边的电线杆相撞,导致车辆损坏,将车丢弃后逃逸。2004年12日1日公安机关找回该车,发现车上价值2250元的物品被盗。李某某归案后供述只是要报复被害人,并不想占有该车辆。参见黄国盛:《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研究》,《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24期。其二,如果查明不具有利用意思而是单纯的毁弃、隐匿意思,就属于毁弃,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三,如果确实无法查明利用或毁弃意思的,“存疑时从轻”,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认定不具有利用意思,仅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有人认为:“毁弃罪在侵犯财产罪的整个体系中只是处于补充的角色,也就是说,对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侵犯,刑法上应主要考虑取得罪的适用,只有在取得罪不能到达的领域,才考虑毁弃罪。”②同前注④,谭明、洪峰文。笔者不同意该看法,这是因为在取得罪与毁弃罪之间优先考虑取得罪,没有任何依据,成立何罪应由犯罪构成要件来判断,在主、客观存在模糊地带,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存疑有利于被告是合适的原则。
利用意思提供了取得罪的刑罚重于毁弃罪的实质根据。正如西田典之所言:“在法益侵害这一点上,并无恢复可能性的损坏罪可以说更为严重,但盗窃罪的处罚却比损坏罪更为严厉,理由在于试图利用财物这一动机、目的更值得谴责,并且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也更有必要予以抑制。”③[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四版补订版),弘文堂2009年版,第147页。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刑罚也明显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因此该见解对我国的刑法解释论是有益的。
从日本通说和判例的排除意思情形来看,侵害他人的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的“一时排除和支配”,以及虽然返还并对利用可能性的侵害轻微,但取得(消费、消耗)了财物中价值的“短时排除和支配”,无不把重点放在享受他人财物中的价值上,其实在更无争议的“一直排除和支配”、“一直排除、一时支配”排除意思情形中,也蕴含着享受财物本身这一整体价值的内容。可见,利用意思对非法占有目的判断具有关键作用。完全可以说,脱离了利用意思,非法占有目的就没有存在余地。
最后,非法占有目的不需要排除意思。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观点认为排除意思属于故意的内容,不属于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以此批判主张排除意思的学说。这可能只是批判者的个人理解,至少主张排除意思的学说并不这么认为。比如,张明楷教授主张排除、利用意思说,在他看来:“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与作为侵犯财产罪客体的‘占有’不同)与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也不是仅指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因为如果将不法占有理解为单纯事实上的支配或者控制,那么盗用他人财物时,行为人事实上也支配或控制了该财物,于是盗用行为具有不法占有目的,因而成立盗窃罪,这便扩大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只有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不法所有目的,才能使这一主观要件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机能。”④张明楷:《试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载顾军主编:《侵财犯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同样强调排除意思的持“永远占有说”的黎宏教授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超出故意的主观要素,不可能仅仅是将他人财物转为自己占有的认识,其必须是永久性占有的认识”。⑤黎宏:《“非法占有目的”辨析》,载顾军主编:《侵财犯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排除意思这一主观要素是学理和判例解释出来的结果,用于盗用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判断。按照日本学者的理解,排除意思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即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而故意的认识内容是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或者说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排除和建立占有的意思不同于转移占有的意思,前者的违法性重于后者。排除意思属于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不同于故意。由此可见,批判观点的这一条理由误解了主张排除意思学说的本意,是难以成立的。
日本刑法通说和判例承认排除意思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要素,作为主观超过要素,它不要求与之对应的客观事实。这意味着,客观上没有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也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因此,客观上转移了占有的盗用场合,如果具有盗窃故意的转移占有意思,同时具有排除意思,该盗用就是可罚的,成立盗窃罪;如果具有盗窃故意,而不具有排除意思,就是不可罚的盗用行为。根据该思路,比如,使用他人的自行车绕行广场三周后返还的,或者骑车从宿舍到图书馆还书然后返回的,虽然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自行车是他人占有下的财物,具有转移占有的意思,但不具有排除意思,因而不可罚。笔者认为,举例的盗用行为不成立盗窃罪,毋宁说是由于客观上法益侵害不严重,没有达到可罚性的程度,从而在客观不法的阶段就排除出罪,而不应该借助主观的排除意思来限制处罚。持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的曾根威彦就认为,以没有被客观事实证明的单纯意思来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是存在问题的,使用盗窃的不可罚性应根据不存在排除权利者或其危险的客观事实,从客观违法性的见地来提供根据。①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の重要问题(各论)》(第2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143页。而主张利用意思说的前田雅英也认为,一时使用他人财物行为的可罚性,由对权利人利用的实际侵害程度来决定,轻微的占有侵害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不应认为是该当构成要件的侵害行为。②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第5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243页。反过来,如果盗用在客观上造成法益侵害严重,达到了可罚性的程度,只要主观上具有转移占有的意思等盗窃故意,就足以定罪,也没必要再附加主观的排除意思。
固守排除意思的最大理由是,在使用盗窃的场合,它具有区分可罚盗用的盗窃罪与不可罚盗用的非罪行为的机能,但这一所谓的“限定处罚机能”完全可以通过客观要件来完成。事实上,日本通说和判例对排除意思的认定也完全依赖于客观要件,比如,被盗用财物本身的价值大小,被害人利用财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程度高低,妨害被害人利用的时间长短、距离远近,是否使用财物进行其他犯罪等。至于排除意思这一主观要素本身并没有提供额外的判断内容。我国赞成排除、利用意思说的张明楷教授也指出:“不可能事先形式地确定排除意思的含义,然后据此区分盗窃罪与盗用行为,而应根据刑法目的、刑事政策等从实质上划定不值得科处刑罚的盗用行为的范围,再确定排除意思的含义。”③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页。因此,排除意思完全是被客观事实说明的对象,而起不到任何说明其他事项的作用,实际沦为了纯粹形式性的东西。
从日本通说和判例见解来看,除了早期对“一直排除和支配”、“一直排除、一时支配”肯定具有排除意思,后来为了满足对严重盗用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实践需求,连“一时排除和支配”乃至“短时排除和支配”都予以认可。比如,山口厚认为,骗取他人的手机,以便短时间内让被害人用钱款赎回的,存在排除意思。④参见[日]山口厚:《问题探究 刑法各论》,有斐阁1999年版,第180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擅自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类型发生了变化。早期的使用盗窃,对象基本上是自行车,财物自身的价值比较轻微,擅自骑走的时间不长,空间上距离原物主也不是很远,即便说存在使用损耗但也不至于过高,因此,对于这种使用盗窃类型,法院均以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意思为由,将其排除在盗窃罪的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后来,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使用盗窃的对象往往是价值比较昂贵的汽车或者前期投入了大量成本的技术资料等,本身价值不菲;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对财产本身进行保护的意识进一步巩固之外,保护财物本身的利用价值的观念也逐渐被认识。即便是没有占有意思的盗用财物行为,只要该种盗用达到了通常不可能为权利人所允许的程度,就有必要作为盗窃罪加以处罚的观念,被法院所广泛接受。”①同前注③,黎宏文,第58-59页。排除意思被逐渐缓和化,而丧失了实际意义。
将排除意思逐出非法占有目的,根据上述所列的各种客观情形,结合转移占有的意思等盗窃故意和利用意思这一非法占有目的,足以完成将严重盗用行为入罪、不可罚盗用行为出罪的刑法使命。我国主张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的刘明祥教授就认为,“判断对某种使用盗窃行为有无必要动用刑罚处罚,关键要看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严重。而决定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客观方面”。②同前注⑤,刘明祥文。就盗用的处罚范围的认定结论而言,日本坚持排除意思的学说与否定的各说之间并无多大差异,这说明排除意思本身并不能发挥特别的作用。
日本通说和判例主张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在两个要素的性质或体系地位上,一般认为排除意思是主观的违法要素,利用意思是责任要素。③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三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191页。之所以如此,是认为排除意思的机能是区分可罚盗用的盗窃罪与不可罚盗用行为,它使得可罚盗用的违法性增加,而利用意思的机能在于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以及能够说明两者的刑罚差异,它证明了盗窃罪行为人的责任更重。然而,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应该严格限制主观违法要素的范围(彻底的结果无价值论者完全否认主观违法要素)。川端博指出:“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的违法要素来理解的观点,因为其发挥着限定的机能,因此可以说是与物的不法观(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不相符的思考。”④[日]川端博:《盗窃罪における不法领得の意思》,载[日]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第三版),有斐阁2000年版,第165页。主观要素一般是责任要素,因此作为责任要素的利用意思的存在不成问题。确如前述,可罚盗用的盗窃罪与不可罚盗用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客观要件和盗窃故意加以区分,没必要再承认排除意思这一主观违法要素。
笔者认可盗窃罪是状态犯,主观意思对于犯罪性质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利用意思在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时完全适用,却不能适用到排除意思在区分可罚盗用的盗窃罪与不可罚盗用行为的情形。原因在于,利用意思决定的是此罪与彼罪,两罪在客观上已经证明具有刑事可罚性时,完全有必要借助于主观意思承担罪行性质和界限的界分任务;而排除意思被认为是决定了罪与非罪,但是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时,理应是客观不法判断优先,主观责任判断靠后。在得出不法后,再考虑是否具有责任,如果没有不法,就毋需判断责任。因此,根据客观要件可以得出盗用不可罚时,根本不用考虑主观上是否具有排除意思;根据客观要件得出盗用可罚时,结合盗窃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的利用意思,即可完成盗窃罪的认定,此时也无需判断排除意思;如果根据客观要件难以判断客观不法程度,应直接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此时不涉及两罪的区分,而是可罚与不可罚的区分),不作为盗窃罪处罚,因为排除意思作为被说明的对象,此时行为人主观上是排除占有的意思还是转移占有的意思,本身也无法确定,不能以具有所谓的排除意思而增加违法性,使行为入罪。
在可罚性盗用的场合,通过评价为盗窃财产性利益来认定盗窃罪,是富有创意的思路,但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不能穷尽可罚性盗用的认定。尽管盗用房屋、汽车、耕牛等场合,可以通过房屋、汽车和耕牛的出租价格,房屋和汽车损耗所支付的维修费用,因汽车被盗用所导致的被害人打的费用,盗用汽车消耗的汽油费等方式,计算出盗用这些财物的经济价值,⑤黎宏:《论盗窃财产性利益》,《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但在有的盗用情形中,如果评价为针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将很难计算经济价值。比如,行为人临近考试时盗用他人的重要复习资料,考试结束后归还的(市场上租书对象基本是小说、漫画等类型)。其二,可能得出不合理的结论。比如盗用耕牛的场合,假如盗用的次数多,按照租牛价格计算财产性利益,最后得出的数额,可能还要高于耕牛本身的市场交易价格。盗窃耕牛本身的违法性显然要重于盗用行为,这便导致了罪刑不均衡。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财物因其特殊性而不能被转移占有时,才成立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比如,侵入他人非现住的房屋居住,由于不动产的房屋只有变更房产登记才能侵害占有,否则不能成立对房屋本身的盗窃,但盗用行为使被害人房屋损耗折旧或者丧失出租可能性,此时只能评价为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①笔者授课时,一个学生描述了其亲身遭遇:该生来自西宁,父母为其在西宁购置了一套房子,一直未装修,处于闲置状态。该生某次回去看房子,意外发现房子被人装修并出租给了不知情的第三人居住以牟利。事后了解到,该人在小区内以同样方式装修并出租了好几套房子。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应该而且只能认定为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罪。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财物本身可以转移占有时,可以直接评价为对财物本身这一对象的盗窃罪。这可以弥补财产性利益盗窃观点的不足,并且与常识更加吻合。在成立盗窃罪的盗用场合,被盗用的财物是盗窃罪的行为对象,也是日本刑法学的通常观念。当财物可以被转移占有时,针对财物的盗窃罪数额以司法鉴定为准:其一,当财产价值体现为财物的物质载体时,主要以物质载体为鉴定基准,事实上是对财物这一整体价值的鉴定;其二,当物质载体本身价值低廉,财产价值体现为财物中蕴含的价值时,主要以其蕴含的价值为鉴定基准。比如银行卡本身价值低廉,财产价值以卡中存款数额为准。至于盗用评价为对财物本身的盗窃罪,行为人一时占有,事后返还了财物的,性质上可以评价为盗窃罪既遂后的返还赃物行为。也就是说,事后返还不否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影响盗窃罪既遂。
综上所述,取得罪根据客观要件结合主观故意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利用意思即可认定。对于盗窃罪,根据客观上的“窃取”或“转移占有”行为,结合盗窃故意的转移占有意思等,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利用意思,即可认定,并足以区分可罚盗用的盗窃罪与不可罚盗用的非罪行为,以及区分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且能够说明盗窃罪的刑罚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理由。
三、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认定与处罚:案例归结
(一)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和盗车勒索案的评析与认定
在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和盗车勒索案中,被告人盗窃仪器和盗车的前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是开始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理由如下。第一,从客观要件上看,被告人对仪器和汽车排除了被害人的占有,建立了自己的占有。被告人为了勒索钱款而盗窃仪器和汽车,虽有返还的意思,但侵害了他人的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尽管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的时间都不算很长(从案发到侦破分别是四、五天和一周左右),但窃取对象具有特殊性,“日本产ET-IN型胚胎冷冻仪”作为实验室的进口设备,被害人使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很大,窃取该设备必然使得被害人中断科研,可能产生间接的经济损失;汽车如今是人们日常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窃取汽车将妨碍被害人出行,也必然使其产生车辆折旧、汽油损耗或乘坐出租车费用等。而且仪器和汽车本身的价值都较大。退一步说,即使返还了财物并对利用可能性的侵害轻微,但消耗了财物中的价值,也可以说明盗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犯性,达到了刑事可罚性的程度。因为被告人返还仪器和汽车,是以被害人给付远超出物品本身价值(仪器)或者虽低于物品价值(汽车)但颇为不菲的赎金为条件的。敲诈勒索罪一罪的观点以行为人具有最终返还物品的意思,否定排除意思的存在,这是以主观意思优先判断犯罪的思维方法,违反了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这一公认的定罪思路,必然导致先入为主,忽视客观不法对犯罪成立的决定性作用(在犯罪成立要件上,主观责任是对客观不法的限制)。况且,上述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排除意思仅指一直排除被害人占有的情形,也不符合两大法系对排除意思弛缓理解的趋势。第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盗窃故意。被告人认识到是窃取他人占有的物品,具有将被盗物品转移给自己占有的意思。第三,被告人具有利用意思,符合了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超过要素。盗窃罪保护所有或占有,并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形式上的所有权或占有权这一权利属性,其实质上是为了保护所有者或占有者在财物上享有的价值或利益,因为权利背后体现的是实际的利益。行为人主观上也是为了享受财物中的价值,此即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利用意思。利用意思不限于行为人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或本来用途进行使用,而是享受财物的某种效用、利益。享受财物中价值的方式,既可以是自己使用,享受使用价值或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是销赃,享受交换价值;甚至包括赠与,享受由此带来的情感价值;再或者其他。以盗窃物品勒索赎金的,也可以说是享受交换价值,因此,行为人对被盗物品具有利用意思。
如果行为人盗窃物品时具有以该物品勒索钱款的意思,应区分以下情形。
一种情况是,行为人仅有勒索钱款的意思,而根本没有返还财物的意思。盗窃物品的前行为成立盗窃罪,以物品勒索钱款的后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或者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以敲诈勒索罪处罚),盗窃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行为人既侵犯了他人的物品,又侵犯了他人的钱款,使被害人遭受两个财产损失,因此,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应实行并罚。比如,1994年1 月1日晚11时,张某跳舞归来,将一辆进口摩托车(价值2.1万元人民币)停放在宿舍楼入口处。当晚11时50分,张某发现摩托车被盗,在现场发现一封恐吓信,内容是要张某于次日晚11时带现金1万元到某桥下换车,如若不然,定要张某全家死无葬身之地。破案后,查明作案人为同单位的单身汉李某。①参见魏东、魏小红:《盗窃摩托车索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人民公安》1994年第3期。本案中,李某实施敲诈勒索的方法是留下恐吓信,内容主要是以杀死张某全家相威胁,因此以钱换车的说法缺乏可信度,事实上李某自始至终没有归还摩托车的表示与行动。摩托车已脱离所有者张某而置于李某控制之下,李某的前行为已达盗窃罪既遂,勒索钱款的行为另外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应两罪并罚。
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具有真实的返还财物的意思。此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关系。笔者不赞同牵连犯和吸收犯的观点。首先,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不具有牵连关系。关于牵连关系的认定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说、主观说、折衷说和类型说等不同学说。②参见甘添贵:《罪数理论之研究》,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2页。主观说以行为人主观上对实施的前后行为是否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认识为标准,会导致案同人异,流于随意;客观说求之于外在的客观标准,有其可取性,但牵连犯本身是刑事司法上便宜裁断的创造,不可能完全忽视司法实践观念等主观要素;折衷说同时考虑主、客观要素,却并没有提出更加明确的标准;类型说根据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进行类型化的考量。笔者倾向于类型说,即只有当某种手段行为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会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认定为牵连犯。比如,非法侵入住宅罪与盗窃罪、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与招摇撞骗罪。立足于类型说的标准判断,无法得出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具有牵连关系。其次,盗窃犯与敲诈勒索罪不具有吸收犯的关系。吸收犯是指事实上有数个不同的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罪名的犯罪。其特征是:具有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数行为触犯不同的罪名;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的自然结果。笔者认为,如果承认吸收犯的罪数形态,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附随犯,指一个行为引起了数个法益侵害,但对主法益侵害而附随引起的对次法益的侵害部分,不作为处罚对象,仅在侵害主法益的犯罪的法定刑内一并考虑的情形。比如,杀人导致毁坏被害人的价值不菲的衣服。二是不可罚(或共罚)的事后行为,指在状态犯的场合,不处罚结果利用或处分行为的情形。不处罚的原因,要么是没有侵犯新的法益(违法性),比如基于占有的使用行为,已经被侵害了所有或占有的盗窃行为所包含,没有侵害新的法益;要么缺乏期待可能性(有责性),比如销赃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即妨害司法秩序,但法规范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这一通常、自然的事后行为。显然,作为比较常见的两个财产罪,很难说盗窃是敲诈勒索的必经阶段,或者敲诈勒索是盗窃的自然结果,因此不符合附随犯的特征;行为人盗窃了他人物品后,又实施敲诈勒索的,是在被盗物品之外对钱款财产的侵犯,可以说侵害了新的法益,但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显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因此也不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财产罪是侵犯他人财产、使他人遭受财产损失的犯罪,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享受财物中的价值。盗窃罪的故意是认识到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客观上取得(被害人丧失控制、行为人控制)了他人财物就达到犯罪既遂,即使事后向被害人返还了财物,也不影响既遂的成立。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超过要素,它所包含的利用意思是否实现,不影响盗窃既遂,如果最终享受到了财物中的价值,则是盗窃非法占有目的实现。在以被盗物品勒索钱款的场合,享受财物中价值的方式就是获取赎金,赎金就是财物中价值的体现。在此,盗窃罪故意内容中的“财物”与非法占有目的中被享受的“财物中的价值”,事实上是一体的,即本来就是“一个财产”的概念。在侵犯财产法益的范畴内,行为人针对“财物”的盗窃已经既遂,事后实现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即使在刑法上可以被评价为针对“财物中价值”的犯罪,但由于前后行为侵犯两个对象终究只造成“一个财产”损失,法益侵害具有单一性,而且自始至终是在一个概括的意思支配下实施的,主观上是得钱返物的意思,而并无同时取得物品和钱款的意思,因此只能认定为实质的一罪。据此分析,行为人盗窃物品的前行为成立盗窃罪,勒索到钱款并且兑现承诺返回物品不影响盗窃罪既遂的认定,勒索钱款的后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两罪属于“实质的一罪”关系,应从一重罪即盗窃罪处罚。
至于犯罪数额,笔者认为原则上以盗窃物品的犯罪数额认定。在勒索到的钱款数额少于物品的鉴定数额时,不影响以盗窃物品的鉴定数额认定犯罪数额,恰如行为人盗窃他人物品后低价销赃一样。但是,在最终勒索到的钱款多于被盗物品的鉴定数额时,宜以勒索到的数额认定,以便与财产罪行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因为被害人多出物品鉴定数额而支付的钱款,属于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且完全是由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致(不同于行为人高价销赃给第三者,此时高于赃物鉴定数额的价款是第三者因购赃交易行为自愿支付的)。
综合以上分析,盗窃胚胎冷冻仪勒索案中,被告人李正敏成立盗窃罪(既遂)与敲诈勒索罪(既遂)的实质一罪,以盗窃罪处罚,犯罪数额以50000元计算;盗车勒索案中,被告人徐韩伟成立盗窃罪(既遂)与敲诈勒索罪(未遂)的实质一罪,以盗窃罪处罚,犯罪数额以65100元计算。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行为人盗窃物品时没有以该物品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物品得手后才产生勒索意思,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后来产生的勒索钱款的意思和行为,完全不影响盗窃物品的前行为的犯罪性质与认定,可以肯定前行为成立盗窃罪(既遂),勒索钱款的后行为也成立敲诈勒索罪(既遂或未遂)。笔者认为,此时,盗窃和敲诈勒索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行为人在实施前行为时主观上也没有仅侵犯被害人“一个财产”的概括意思,因此,不管行为人最终是否返还了盗窃物品,都应该两罪并罚,犯罪数额以物品鉴定数额和勒索数额合并计算。
(二)盗窃车牌勒索案的认定路径
盗窃车牌勒索案尽管属于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类型,但由于对象的特殊性,犯罪认定与上述案例有差异。
首先,如前所述,行为人主观上对被盗车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可以成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对象。国家机关证件是指有权制作的国家机关颁发的,用以证实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其他事项的凭证。车牌是国家机关(一般是车管所)发给机动车的行车凭证,属于车辆的身份证明,据其可知悉机动车所属地域以及查询到车主。1998年5月8日“两高”、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7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的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可见车牌被司法解释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尽管《刑法》第281条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的对象是“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但可以认为是对警用装备的特殊规定,不能得出警用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正如《刑法》第280条第3款规定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不能得出居民身份证就不是国家机关证件一样,这明显是立法上的特殊规定。①同时,《刑法》第375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和盗窃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3款规定的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的对象是“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法条将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与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作了并列规定,也只是表明针对武装部队车牌的特殊规定,第3款与第1款是法条竞合关系,如同第280条第3款与第1款的关系。
再次,车牌也是财物,可以成为财产罪的对象。尽管车牌的物质表现形式是一块铁片,本身价值不大,但作为权利凭证,具有使用价值,申领牌照时需要支付钱款(在上海等地数额特别巨大),说明牌照具有经济价值。虽然牌照的价值不能等同于车辆的价值,也不宜以申领价格进行认定,但是,当车主没有牌照需要补办时,会产生费用(更不用说车主为此付出的车旅费和劳务支出),至少该费用可以作为牌照的价值进行计算。
再其次,在多次盗窃车牌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成立盗窃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后,“多次盗窃”属于盗窃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之一;在此之前,多次盗窃累计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可以入罪。当然,若不符合基本构成要件,则不成立盗窃罪。
最后,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是,一般情况下适用特别法条,但是如果普通法条的处罚更重,且立法不排斥普通法条的适用(法条中没有“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应适用普通法条。显然,盗窃罪要重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盗窃罪也不排斥行为符合了其他特殊盗窃罪名时盗窃罪法条的适用。因此,当盗窃车牌符合了盗窃罪构成要件时,一般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不符合,则只能适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另外,盗窃车牌以勒索钱款的,不成立敲诈勒索罪。盗窃对象车牌具有特定性,车牌的性质与价值已如前述,盗窃车牌对被害人驾车出行造成不便,即使行为人不返还车牌,被害人仍可补办,且补办的花费数额不大。这就决定了,盗窃车牌及勒索钱款的行为,仅使被害人产生了困惑、苦恼,而不至于产生恐惧心理。而敲诈勒索罪是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行为,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该心理处分财产的犯罪,仅是让对方产生困惑或嫌忌的,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②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第三版增补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273页;参见前注,大谷实书,第279页;参见前注②,西田典之书,第205页。
综上所述,盗窃车牌勒索案中,犯罪数额是1575元,被告人杨伟宁、贝荣坚的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和盗窃罪,两罪是法条竞合关系,应以盗窃罪处罚。
(责任编辑:杜小丽)
DF625
A
1005-9512(2015)03-0042-15
张开骏,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