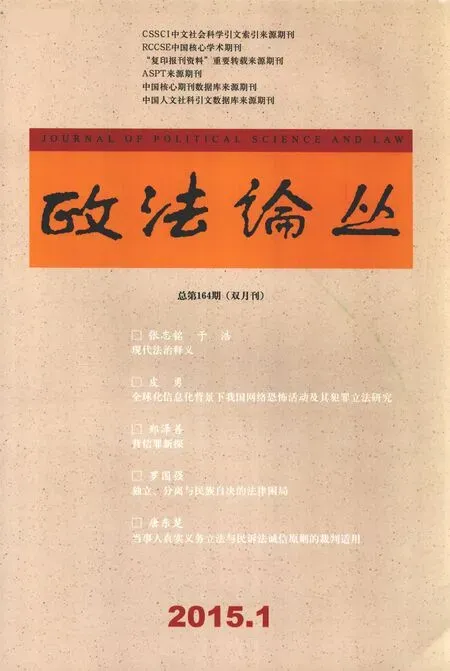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
2015-01-30唐东楚
唐东楚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
唐东楚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不管在理论上的涵摄关系如何,二者都具有同质性,在立法上具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说明的效果。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诚信原则,迄今在裁判中被援引适用的情形极少,这从侧面说明,真实义务原则的立法在我国当下并不急需,也无实效。在现有民诉法框架内,通过直接援引适用诚信原则条款和强制措施来规制当事人的虚假陈述,条件成熟时再将诚信原则的适用主体予以细化,并对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或程序救济予以完善,不失为明智和务实之举。
当事人真实义务 民诉法诚信原则 裁判适用 虚假陈述 强制措施
当事人真实义务又称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或真实义务①,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如实、完整地陈述其已知的事实,不得故意隐瞒、撒谎或欺骗,否则会面临裁判上的不利后果或制裁。虽然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的初衷是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规制,但这种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条款一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并且与民诉法诚信原则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替代性,它往往赋予法官对一些法无明文规定的程序性事项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而非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具体惩罚措施。质言之,当事人真实义务是民诉法诚信原则的体现或者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国2013年新《民诉法》实施以来,直接援引诚信原则条款予以裁判的案例极为少见,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显示,迄今尚无一例。②当然并不排除个别适用了该条款的裁判文书仍未上网的情形,比如许霆诉银行提供对账单一案,广州两级(一、二审)法院均以滥用诉权、“有悖诚信原则”为由,驳回起诉的裁定等。[1]实务和学界不乏呼吁在民诉法中引入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的观点,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诚信原则落到实处。这些观点其实没有意识到,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认识到真实义务的真正内涵及其立法与诚信原则条款裁判适用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对当事人虚假陈述法律规制的立法例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并不少见,或因主观上的不诚实,或因利益上的驱动,各国对此都有规制和处罚的措施。当事人虚假陈述不仅误导法院,影响诉讼的秩序和效率,而且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破坏平等辩论的基础。与虚假证言不同的是,当事人是平等辩论的主体,其虚假陈述具有证据材料和权益主张上的“双重虚假性”,因而会构成对辩论主义的基础性破坏,而证人并非诉讼辩论的主体。
各国法院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制裁,要么是不将其作为证据采信,要么是对其处以罚款或赋予对方当事人的异议救济权,甚至对经过宣誓后的当事人虚假陈述,以犯罪论处,追究其刑事责任。
古罗马法将当事人在诉讼中故意主张非真实的行为,故意违反法律而请求权利保护或进行防御的行为等,规定为违法。[2]它不仅有“虚言罚”,而且规定了被告的不得恶意否认与原告的不得中伤,否则可以通过诬告之诉、反诉、宣誓或者反承诺的方式来对其追责、惩治或对其损害的权益予以救济。[3]
我国古代的盟誓、口供与对当事人的刑讯逼供等,虽然方式原始、野蛮,但其初衷也是想得到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与现代文明社会严禁刑讯逼供所不同的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刑讯逼供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科技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相对合理性”,刑讯几乎是最基本的审讯方式,刑讯逼供不仅被容忍和认可,而且得以合法化、法定化,而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则毫不留情。
唐朝法律规定了“诬告者反坐”,明朝永乐元年制定了诬告法。唐朝的诉讼中往往要求当事人“仰答虚实”、“依实谨辩”,如果法官根据“五听”原则推鞠仍然无法获得伏辩的时候,就可以依法实施刑讯以获取口供。[4]虽然我国古代刑案重拷讯、民案重调处,但在整体的审讯方式和观念上,仍然停留在“刑民不分”的阶段,口供的真实性无疑是刑民案件共同的追求,否则就无法及时公正地断案或者调处成功。学者戴炎辉对“诬告反坐”的法理解释是:“诬告系捏造虚伪情事而告人罪之谓,其保护法益,偏重于个人安全,故采反坐之法则。”[5]
我国1922年的《民事诉讼条例》规定:“当事人故意虚伪陈述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67条规定:“具结而故意虚伪陈述,足以影响裁判之结果者,法院得以裁定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锾。”我国《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385条至第388条,以专章的形式,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恶意诉讼及其所导致的“罚款及损害赔偿”进行了规定。[6]
大陆法系的匈牙利、日本、法国、德国、奥地利等,都有关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1911年《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显系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对他造事实之陈述明显的为毫无理由之争执或其所提出的证据毫无必要者,法院得处以600克鲁念以下之罚鍰。”1996年《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与第230条规定经宣誓的当事人做虚假陈述的,或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出于故意与事实相反去争执文书制作真伪的,均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1976年《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32-1条规定:“以拖延诉讼方式,或者以滥诉方式进行诉讼者,得科以100法郎至10000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7]《德国民事诉讼费用法》第39条规定:“如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致使诉讼程序延滞的,应负担因延滞而产生的费用。”《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宣誓后仍故意虚假陈述的,依照其《刑法》第199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8]可见,大陆法系的当事人虚假陈述制裁措施一般比较具体,法官对制裁措施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小,但在判断什么是虚假陈述的问题上,却又空间较大。
事实上,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并不局限于言辞的陈述上,还表现在前后矛盾的举动,或者“明知故假”“明知故争”等滥诉、拖延诉讼的行为。为了慎重起见,前述的日本、法国、奥地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将“宣誓”或“具结”,规定为对当事人虚假陈述处以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有点类似不少国家关于证人作证必须宣誓的规定。
英美法系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对诉答真实性的程序性保障上,没有大陆法系的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或真实义务这种抽象性的一般条款或一般原则。这种程序上的技术化操作,不仅减少了英美国家法官在判断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是否构成虚假陈述上的困难,而且在处罚措施的适用上,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美国1993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律师签署“真实确认”和当事人宣誓或签名“真实声明”来保证诉答状的真实性,对虚假陈述者予以制裁。[9]1999年《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2.2条、第22.3条和第32.14条规定,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事实声明,对虚假陈述者的证言不予采纳、令其承担诉讼费用或者判处其藐视法庭罪等。[10]
二、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内涵与效力
与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规制相适应的是,大陆法系有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抽象性法律原则或一般条款,有时还将这种义务延伸到诉讼代理人或律师。
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在历史上第一次,首开先河地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后来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诉法都有此立法体例,法律表述也大同小异。③
学理对当事人真实义务一般条款的理解和探讨,可以以德国1933年民诉法典第138条为蓝本来进行分析。德国学理将该条规定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称为“真实完整义务”,具体包括真实义务、完整义务和陈述义务:
其中的真实义务,旨在禁止谎言,当事人不得就自己明知不真实的主张,或者明知真实的对方当事人的主张进行争辩,否则其不实陈述会被法官的自由心证所排除,或者经过宣誓的当事人作伪证会构成犯罪。④这里的“真实”并非客观事实上的真实,而是当事人所理解的真实,是主观认知上的真实。衡量真实与否的标准,关键要看当事人是否“明知”或“不知”;⑤其中的完整义务,旨在禁止半真半假的隐瞒,但也并非要求当事人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一律招来”,其完整陈述的范围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当事人只是在负有证明责任的具体事实问题上,因其不完整的陈述,导致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其中的陈述义务,并非一种行为义务,而是一种行为负担,⑥否则会承担该条第3款“拟制自认”的不利后果。行为负担与行为义务的区别并不在可能面临的惩罚上,而在行为的目的上:行为负担源于行为人自己的利益,而行为义务并非源于行为人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不是第一位地出于自己的利益。当事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但不允许不择手段。学者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诚实义务。真实义务是一种真正的义务,而不仅是负担;因为诚实还是不诚实并不听凭当事人决定。”[11]
日本民诉法学者高桥宏志认为,真实义务并非以“让当事人陈述真实”的积极性义务为内容,而仅仅具有“禁止当事人在不知的前提下提出主张或做出否认”的消极性内容,是一种主观上的率直或诚实义务,它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上的体现,是与辩论主义相互协调的:“因为,辩论主义也不至于说是一个鼓励当事人说谎的原则,作为辩论主义的一种内在性制约,率直义务或诚实义务也是可以获得定位的。”[12]真实义务和完全义务的功能,完全可以由诚实信用原则和辩论权的趣旨来替代,这两种义务与辩论主义是协调的。[12]
至少从倡导的意义上说,德国法上的当事人真实义务,不仅要求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诚实的阐明,而且要求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也要进行诚实的阐明。因此有德国学者认为:“如果无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负担全面的阐明义务,那么发现真实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违法隐瞒信息或者证据手段,而导致对方当事人无法证明之后,又引用了先前隐瞒的信息或证据手段,“那么,他就违背了诚信。这样就出现了违背贯穿整个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情况,或者说自相矛盾的情况”。[13]
关于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效力,在德国1933年民诉法典修正前后,有“无效说”、“无限说”和“有限说”三种观点:其中,“无效说”等于宣布了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名存实亡,使其沦为纯粹的装饰性条款;“无限说”则过于夸大了当事人真实义务的作用,使其他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失去了意义;只有“有限说”能协调、整合当事人真实义务与其他民事诉讼制度的关系,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尽管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界限不能绝对确定,取决于其与辩论原则的此消彼长关系,但其底线仍然是私权保护,而非发现真相。[14]否则就会将真实义务与职权探知主义混同,动摇甚至否定辩论主义。
三、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涵摄关系
当事人真实义务是民诉法诚信原则的体现,是诚信义务的一种表现,二者在运用上,都有可能涉及虚伪自认或反言的认定和禁止等。但在当事人真实义务与诚信原则之间的涵摄关系上,我国当前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多数观点认为,真实义务是使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不致沦为具文的具体化形态,是替代和完成当事人诚信原则功效或任务的较为理想的具体规范之一,而且其功能不同于现行《民诉法》第111条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类似观点可见周艳波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4年11月成都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论民事诉讼的真实义务》;少数观点认为,真实义务的维度要大于诚信原则,从立法的现实性出发,应将诚信内含于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这样不仅具有具体操作上的可行性,而且可以避免诚信原则的抽象性和对客观真实陈述的苛刻要求,类似观点可见赵旭东、常榉瀚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4年11月成都年会提交的论文《诚信原则与当事人真实义务之辨析》。但不管哪种观点,似乎在有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即真实义务的立法,似乎已迫在眉睫。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极端化之嫌,前者是将另一种抽象(当事人真是义务)来代替一种抽象(诚信原则),后者则是混淆了真实义务与诚信原则的种属关系,而且忽视了真实义务与诚信原则共同的“主观真实”要求。
虽然我国以前也有学者反对真实义务立法,认为真实义务源于诚信原则,具有很强的伦理意蕴,难以证明当事人的“主观性事实认识”,而且与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转变的基本精神相抵触,所以不宜将真实义务法律化,而应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予以适度的容忍。[15]但这种观点早已被2012年新修《民诉法》第13条第1款的诚信条款所否定。
当事人是“诉辩审”三角结构中的“两造”,其真实义务不仅针对代表国家公权的法庭,而且针对对方当事人,不像证人、鉴定人、翻译人等的“真实义务”只针对法庭。毕竟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有自己的实体利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相比证人等,更具有可原谅性和可宽宥性。
其实,世界各国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立法,不管在历史上是否已经付诸实施,至少在学术理论上,一直都是且行且争议的,并非像证人必须通过宣誓如实作证,否则就面临伪证的处罚甚至构成伪证罪那样显得“毋庸置疑”。换言之,如果当事人选择宣誓、具结或者签署真实声明等方式之一后,再进行陈述,其陈述的证明力就强,但同时须面临虚假陈述的处罚制裁或责任追究;如果当事人不选择宣誓、具结或签署真实声明等方式之一,而直接进行陈述,其陈述的证明力就弱,但能免于虚假陈述的责任追究。
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立法,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说明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事人真实义务是诚信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达,是诚信原则在当事人陈述上的投影。国内外学者基本上都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视为诚信原则在诉讼上的体现,或是诚信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16]
一般有民诉诚信原则明示立法的国家,就不再在法典中明示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原则性立法,如韩国、日本和我国;反之,在民诉法典中明示了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再在法典中明示诚信原则的立法,如前文所述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只有我国澳门的民诉法典对此采取的是混合制立法,其在将诚信原则分解为合作、善意、行为恰当这三个原则的同时,在第9条的“善意原则”中规定:“一、当事人应当遵守善意原则。二、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亦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6]不管如何,在成文法的国家,即便不要判断何谓“真实义务”,但也必须面对何谓“虚假陈述”的认定,法律的抽象性仍是始终存在的。
从世界范围看,诚信原则或者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抽象立法,主要是针对当事人的。各国在或者规定诚信原则,或者规定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情况下,还会在具体的制度性条文中,规定对虚假陈述的制裁和处罚。只有我国,既没有在诚信原则条款中突出当事人,也没有规定抽象的当事人真实义务,也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和处罚。我国此前报道的一些案例,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虚假陈述的处罚,是在援引《民诉法》第111条关于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强制措施的基础上,而做的扩张性解释。
我国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诚信原则,其文字表述虽然不失明智,就像“菩萨的眼”,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感觉她在看着你。[17]但该条款确实存在弹性大涵括广的一面,也存在过于抽象难以裁判适用的一面。不少学者因此呼吁将当事人真实义务入法,认为这既是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诚信原则的重要环节,对诚信原则的贯彻实施将起到积极作用,类似观点可见于鹏在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2013年11月海口年会提交的论文《诚信原则视角下的当事人真实义务研究》。
当事人真实义务虽然是诚信原则的体现或主要内容,但不宜在新《民诉法》诚信原则尚少裁判适用之前,又匆忙重复立法,规定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抽象原则,这样有悖立法的稳定性和司法的能动性,徒增争议和法律的不确定性。不如在司法适用诚信原则裁判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将现行诚信原则条款的主体予以明确和细化,将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措施予以明确规定。
四、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的功能替代
我国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前,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有相关的法律精神或理念,即实质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比如宪法关于权利不得滥用的规定,以及民诉法对妨害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等,并且出现了诸如1994年杨敏诉姚正祥不实诉讼损害赔偿案之类运用诚信原则的判例。[18]法院在此案中,判决姚正祥赔偿因在前一诉讼中,无根据地将杨敏列为被告,而由此带来的误工与交通费用。
近年来不乏适用现行《民诉法》第111条关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等规定,对虚假陈述的当事人和代理律师进行处罚的案例,兹举两例予以说明:一例是新民诉法施行之前的2012年8月,徐州市鼓楼区法院,对原告张某在追索借款案中,故意将同一笔借款说成两笔不同借款的虚假陈述,做出罚款1万元的决定;[19]另一例是新民诉法施行之后的2013年6月,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审理原告陈某和代理律师王某故意隐瞒合同和凭据,企图改变法院管辖地和否认已收被告部分还款事实的目的,认为其违背了诚信原则,最后依据新《民诉法》,对其做出各罚款7000元的决定。⑦而本文一开头提及的许霆诉银行案,两审法院则均以许霆滥用诉权、违背诚信原则驳回起诉。遗憾的是,这些案例的裁判文书原文不得而知,不知法官对诚信原则适用的具体说理如何,以及援引具体法律条款的依据何在。
我国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的立法是在法院职权主义向当事人辩论主义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完成的,没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和诉讼观念作支撑,只是为了尽快遏制实践中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表现出明显的立法仓促和实用主义功利性。其立法背景与动机,与建立在辩论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西方民诉法诚信原则,是完全不同的。相对而言,后者更具从容和理性,更“谋全局”非“图一时”。[20]我国民事诉讼一直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新中国第一部民诉法典《民诉法(试行)》第5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虽然这种规定在1991年正式实施的《民诉法》第64条有所变动,不仅规定了具有当事人主义色彩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且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进行了限定,但仍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只要是其“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就应当调查收集。后来的司法解释虽然有进一步朝向辩论主义发展的趋势,⑧但《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甚至条文序号,在后来的2007年、2012年两次修正中都没有任何变动。我国至今仍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了真正的辩论主义,更谈不上要通过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立法来对其予以修正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当前不充分发挥已有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的裁判适用功能,而一味抱着“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心态,再去折腾什么当事人真实义务的一般条款立法,是一种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司法上的不自信。现有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的搁置未用,侧面说明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立法,既不急需,也不一定有实效,因为它同样需要面临类似诚信原则适用上的判断(是否主观真实或者是否主观诚信)困难。所以务实的做法,应当是在既谨慎探索,又大胆创新的基础上,通过直接适用民诉法诚信原则的判例积累,以达到诚信原则或真实义务立法的目的。
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的裁判适用既是挑战也有风险:一方面,诚信原则与衡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能以其弹性扩大、变更或者更改现行法律以符舆情;[21]另一方面,这种适用需要有较高的裁判智慧和衡平、说理技巧,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法官毕竟不是“孟德斯鸠式的自动售货机”,能动性司法或曰创造性司法,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
首先,民诉法诚信原则的适用分为间接适用和直接适用,前者是通过宣示来约束心理,后者是通过援引来裁判行为。[20]尤其是对诚信原则的间接适用而言,切忌空洞无物的宣教,要能做到合情合理、让人信服。对于直接适用,尤其要注意裁判的说理。诚信原则条款的直接适用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诚信原则既不能滥用,又不能不用,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对其进行直接适用。相较而言,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习惯于“以礼代法”、“以经决狱”或者“一准乎礼”,而不太讲究法律的技术化操作或诉讼原理的遵循,所以也就习惯于运用实质意义上的诚信原则,而非仅形式上的诚信原则条款来进行宣传和教化,而当我们真正面对诚信原则条款的直接援引适用时,反而变得格外小心甚至不敢适用了。
其次,直接适用民诉法诚信原则进行裁判时,尤其要注意法律原则适用的4个“不得”:一是不得适用不是以成文形式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二是不得绕开具体的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一般条款),除非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会导致明显的不公,这就是所谓的“禁止躲入一般条款”或“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三是不得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则但有类推等适用补充方法予以填补时,绕开类推适用等补充方法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四是不得在适用法律原则时,不对适用该原则的正当性进行充分的论证。[22]同时,要注意诚信原则对辩论和处分原则的辅助性和补充性,要以不损害辩论和处分原则为前提。这是因为法律原则是有“分量”的,有些原则比另一些原则具有更大的分量,在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23]当适用诚信原则与适用处分原则或者辩论原则发生冲突时,要优先适用处分或者辩论原则。
再次,要尽量探索和创新直接适用《民诉法》第13条第1款予以裁判的案例,在裁判说理上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必要时可以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发布。正如前文所述德国学理探讨的真实义务一样,在诚信原则的适用上,既要摒弃盲目空洞的“无限说”,又要摒弃无所作为的“无效说”,而要坚持和践行“有限说”。具体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转型,对民诉法诚信原则的适用,要有别于民法诚信原则的适用,不能将其仅仅视为授予法官对程序性权利进行自由裁量的“大棒”,而要将其视为对所有诉讼主体的心理提示,法官要尽量少用空洞的宣示性(或曰间接)适用,而要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直接援引该条款进行裁判。同时应该保持谦抑,就像学者孙记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4年11月成都年会提交的论文《论我国民事诉讼转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中所指出的那样。并且在程序设计上,赋予当事人的救济机会,与来自法院或检察院的“审判监督”。
最后,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救济权。当事人的参与是法律实施的生命力所在之一,赋予对方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利,是防范虚假陈述的有力措施之一,这在两大法系都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比如前文所述的法国新民诉法典规定对拖延诉讼或者滥诉者,在处以罚款的基础上,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而在这方面,我国的官方惩戒较多,对方当事人的索赔或者权利救济措施较少。当然这种救济权不仅针对对方当事人,而且针对被制裁的违背真实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学者因此建议,在直接适用民诉法诚信原则裁判时,应以裁定为之,并可越级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4]以裁定方式直接适用民诉法诚信原则即法典的第13条第1款,可能是出于对程序性权利救济的考虑,但越级上诉在我国并无相应的制度依据,倒不妨可以利用最高法院的批复或者案例指导制度等现有的制度资源。
学者对我国民法诚信原则司法适用的研究表明,我国法官尚无适用诚信原则而创立某种制度的痕迹,反而向宣示性、向一般条款逃避式的适用诚信原则情形却不少,这是将来应当努力和避免的。[25]这说明我国法官在适用诚信原则这种抽象性的一般条款时,存在知识储备不足或司法能动性欠缺的问题。面对新实施的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结语
法贵实施,并非立法或法律条文的“拆迁工程”或叠床架屋。相对而言,我国民诉法的条款性缺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反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按照已有的法律条款办,文字上的法或者条款中的法,没有转化为观念中的法或者行动中的法。当前不宜置已有的诚信原则条款于不顾,一味强调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入法或者重复立法,而要探索诚信原则条款的裁判适用。尤其是针对当事人在正常诉讼中的虚假陈述,而非仅仅针对原本恶意的虚假诉讼、虚假调解或恶意逃债等情形,直接适用诚信条款予以规制,以保辩论原则或辩论主义的真正开展和实行。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将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的主体范围和诚信义务予以明确和细化,将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予以完善。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观念上的诚信原则相较专业化的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更具有某种亲和力和可接受性。
注释:
① 后文如无特别的说明,均简称为真实义务或当事人真实义务。
②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以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27日的信息,输入关键词“民诉法诚信原则”后的检索结果显示,没有一例法院的裁判,直接援引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予以裁定或判决的,倒有起诉或答辩状中提到诚信原则或“恶意诉讼”。参见http://www.court.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7日。
③ 德国1933年民诉法典第138条的表述是:“当事人必须完全且真实地就事实上的状态作陈述”;意大利1942年民诉法典第88条的表述是:“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 南斯拉夫1980年民诉法典第242条的表述是,各当事人的陈述及立证应就所必要的一切情况,逐一依据事实为完全且明确之陈述;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典第195条第1款的表述是:“当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实应为真实及完全之陈述。”
④ 分别参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和第580条。[德]德国贝克出版社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2000年版》,谢怀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0、138页。
⑤ 该条第4款规定:“对于某种事实,只有它既非当事人自己的行为,又非当事人自己所亲自感知的对象时,才准许说‘不知’。”
⑥ 德国学者把将当事人自己决定在诉讼中如何行为,并且自己承担疏忽实施诉讼的责任,称为“行为负担”,以区别于对他人的“行为义务”。
⑦ 参见浙江新闻网:《宁波一原告及律师为谋利益法庭上做虚假陈述被罚款》,http://news.zj.com/detail/1462819.shtml,2013年6月18日发布,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9月6日。
⑧ 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限定为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性事项。并且在第1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这两种情形外,其他一律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1] 魏微微.许霆诉银行二审仍败诉[N].信息时报,2014-04-05(A9).
[2] 蔡章麟.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A].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C].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
[3] [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M]. 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4] 陈玺.唐朝诉讼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 戴炎辉.唐律通论[M].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70.转引自罗昶.伦理司法: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8] 吴云.论对我国民事诉讼中虚假陈述的法律规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9] 汤维建.美国民事诉讼规则[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10] 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1]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第27版)[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3] [德]彼得·阿伦斯,弗莱堡.民事诉讼中无证明责任当事人的阐明义务[A].[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C].赵秀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4] 任重.民事诉讼真实义务边界问题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2,5.
[15] 赵德玖.民事诉讼法不应确立当事人真实义务[J].法学杂志,2006,2.
[16] 柯阳友,吴英旗.民事诉讼当事人真实义务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议资料D145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11.
[17] 唐东楚,李毅.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18] 叶自强.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9] 韩正元,周琪.作虚假陈述干扰审判被罚款万元[N].江苏经济报,2012-08-29(B02).
[20] 王福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可适用性[J].中国法学,2013,5.
[21] 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2.
[22] 刘治斌.论法律原则的可诉性[J].法商研究,2003,4.
[23] [美]贝勒斯(Bayles,M.D.).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4] 董少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适用[J].民事程序法研究,2014,下,总第12辑.
[25] 徐国栋.我国司法适用诚信原则考察[J].法学,2012,4.
(责任编辑:张保芬)
The Legislation of Litigant’s Truthfulness Oblig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Judgments for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ivil Procedure Law
TangDong-chu
(Law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No matter what theoretically subsum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igant’s truthfulness obligation and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ivil Procedure Law, they have homogeneity to replace and explain each other in legislation.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the article 13 and paragraph 1 of the new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haven’t been quoted. It seems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litigant’s truthfulness obligation is not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We should prevent false state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ivil procedure and compulsory measures directly in the current frame of the civil procedure code. It’s a sensible and pragmatic move to refine the subject of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and complete the compulsory measures and procedure relief.
litigant’s truthfulness obligation;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ivil procedure law; application of the judgments; false statement; compulsory measures
1002—6274(2015)01—104—07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沉默权、真实陈述义务和诚信原则立法的伦理基础研究”(批准号:12BZX067)的阶段性成果。
唐东楚(1968-),男,法学博士、伦理学博士后,美国东北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
DF72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