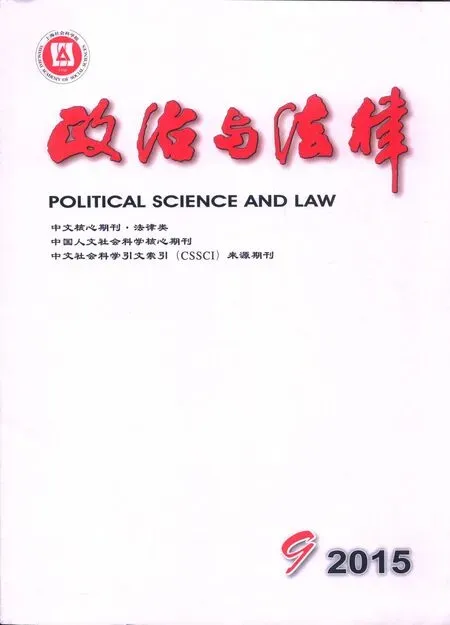对行政行为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的司法审查
——兼评指导案例41号
2015-01-30张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张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对行政行为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的司法审查
——兼评指导案例41号
张亮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行政行为作出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在外形上是程序瑕疵,目前在司法审查中不宜以程序违法直接否定行政行为的法效力;该形式问题也不能等同于行政行为实体上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学理上对此作何定性的思辨难以契合审判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指导案例41号明确了对“未引用”问题进行实质审查的裁判思路,通过不予定性、事实审查、违法推定的三层次路径,法院可以将“未引用”有条件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这种裁判进路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行政法秩序、相对人权益以及司法谦抑,但其只是法治发展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结合新修订《行政诉讼法》中对程序轻微违法的确认违法判决,可以对“未引用”问题的程序价值作进一步主张。
行政行为;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程序轻微违法;瑕疵;推定;适用法律错误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在文书上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以下简称“未引用”),是日常行政中频繁发生却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未引用”可能是行政行为实质上欠缺法律依据,或者仅仅是形式上未明示法律依据,本文探讨的就是针对后者的司法审查问题,即行政机关适用了相关法律依据,却未在书面决定中予以准确援引。该问题一般表现为只引用了法律名称,而未具体至条、款、项,或未引用任何法律名称与规范条款。通过考察相关学理与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学界对此未能提供充分关注与解释,审判实践中亦没有统一认识。正因如此,何海波教授认为该问题是理论与行政诉讼实践发生龃龉的一个具体例子,由此看出行政法学理论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存在“两张皮”现象。①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公布的指导案例41号“宣懿成等18人诉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争议案”(以下简称:“宣懿成案”)中,法院将“未引用”推定为“适用法律错误”,而非对“未引用”情况单独定性后直接指向行政违法,明确了对该类案件作实质审查的裁判思路。在法律未作具体规定而学理又不明晰之际,这种规则示范具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图梳理1995年至2014年的相关案例,结合指导案例41号的裁判路径以及相关学理,阐释如下问题:(1)“未引用”问题的司法审查现状以及不同判断背后的法理渊源;(2)指导案例41号的司法逻辑与参照要件;(3)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对程序价值的主张空间。
一、“未引用”问题的学理分析
要求行政行为引用具体法律条款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双重意义,因此对“未引用”问题的学理分析,存在“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两种认知进路。一方面,行政机关向相对人告知明确的法律依据是行政程序法中说明理由制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透过“未引用”这一形式,亦可能存在实体违法的多种可能,当形式简陋到一定程度时,会被认定为行政行为在实体上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
(一)程序违法与瑕疵
在行政过程中,“当行政相对人收到行政行为并表示不服时,若行政行为有明确、具体的法条,他就可以从中找到为救济而要攻击的‘靶心’;若他认同了行政机关适用的法条,则有助于他接受该行政行为的内容”。②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可见这种说明理由义务存在需要保障的法益,但学理上对“未引用”是否能够触及“程序违法”并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对程序的严格要求是出于法治原则的考虑,无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导致何种结果的产生,人民法院都应判决撤销。”③林莉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这种观点有其积极意义,尤其我国行政法发展过程中,行政程序长期未得到行政机关的足够重视。但是,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其二十余年的实践中,学界与实务界对“违反法定程序”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认定违法与否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考虑‘是否损害行政相对人实体法上的合法权益’”。④参见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现实中涉及“未引用”的案例一般对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影响甚微,于是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的案例也极少。⑤参见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因此,“未引用”在行政法理论上通常被视为行政决定理由说明的程序瑕疵。⑥参见前注①,何海波文。此处的“瑕疵”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相对人,通过实施行政处理的方式来表达授予其权益或者课处义务的意思表示时,因不慎而出现的,不属于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的非法律性错误。⑦参见姜明安、余凌云主编:《行政法》,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264页。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会关联到职权、程序、内容、救济等全方位依据,要求其一一准确援引,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若没有伤及行政决定的实体法益,基于行政法秩序与效率的考虑,这类形式违法可以认定为不影响行政行为法效力的瑕疵。⑧参见前注②,章剑生书,第306页。
(二)适用法律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是指“行政行为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⑨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2页。但是“未引用”不同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应如何理解,需要进行一定的解释。对此,学理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为“等同说”,它直接将“未引用”归入“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范畴,从而指向相同的法律效果。胡建淼教授认为:“(适用法律错误包括)对于必须有直接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作出该行政行为,但没有列明法律依据。”⑩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翻阅相关立法工作者的解释,也可以发现类似观点,即“实践中,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应当适用某一条款,却没有说明所依据的法律或者援引具体法律条文”。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第二种是“形式推定说”,将“未引用”形式推定为“适用法律错误”。最高院官方刊物在回复地方法院法官询问时表示:“具体行政行为仅引用了法律、法规的名称,未引用具体条款,无法判断其究竟是依据哪些有关定性和处理的条款作出的,故属于没有适用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质的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没有问题,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并不能得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问题上没有错误的必然结论。”②本刊研究组:《对未引用法律条款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如何判决?》,《人民司法》1995年第7期。也就是说,“未引用”导致法官无法审查行政行为作出时行政主体适用法律的真实意图,无论实体上的合法性如何,均不能消除“未引用”形式的违法性。
二、审判机关的观点
“未引用”的学理观点存在分歧,那么审判实践中又是如何看待它的呢?笔者搜集到1995年至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120份判决书,在裁判理由中对“未引用”问题作出了评价,③笔者在中国法律知识总库(http://corpus.classiclaw.com/search)中通过“具体引用”、“未引用”等关键词搜索,筛选裁判理由中对“未引用”问题进行具体说理的判决书,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1日。在此选取最高院的相关观点以及特定时期的下级法院观点进行分析。
(一)最高院的观点变化
1995年至2014年,最高院对“未引用”问题明确表达观点的判决书有8份,④包括5份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可被视为最高院认可的裁判观点。从中可见其在不同时期对“未引用”问题的观点有变化。1997年,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与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等行政纠纷上诉案中,⑤最高人民法院(1997)行终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最高院认为“注销登记通知书中亦未引用有关法律依据”是“缺乏法律依据”。1999年,在赵立新不服宁夏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产权界定案中,由于原告提出异议的依据不适用于该案,最高院认为“宁国资发(1997)46号批复未引用前述规定的条、款、项,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4期刊登的“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中,最高院则认为,行政机关所作批复只笼统提到有关规定,未引出适用的具体条文,违反了法定程序。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4期,第142-144页。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刊登的“路世伟不服靖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有关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没有说明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第106-108页。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5期上刊登的“罗伦富诉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中,有关法院在先予确定行政机关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附随认定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笼统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没有指明适用哪一款的具体情况,属适用法律错误。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5期,第178-180页。2002年,在开封市豫东房地产实业公司与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政府等撤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诉案中,⑩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2)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最高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决定未引用法律条款,形式上存在瑕疵。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5期中,最高院通过“宣懿成案”,首次明确提出审理“未引用”问题的裁判要点,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应当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5期,第35-38页。自此,最高院的立场趋于稳定,再没有将“未引用”当作程序问题对待,并且在2014年将该案确定为指导案例41号。
2014年最高院公布了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其中有一件“如果爱婚姻服务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案”(以下简称:“如果爱案”)。在该案中,有关法院认为:“被诉告知书有可援引的法律依据而未援引,应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院在解析部分进一步指出:“行政机关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援引具体的法律条款并说明理由。本案判决认定被告有可援引的法律依据而未援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适用,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说理性。”②参见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9/id/1437694.shtml。
可以发现,虽然2014年推出的指导案例41号与“如果爱案”都将“未引用”问题判定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但是两者的司法逻辑还是存在差异的,前者系通过实质审查认定法律适用的主要证据不足,进而推定“未引用”为适用法律错误;后者则在强调形式上的援引义务,只是选择了“适用法律错误”的合法性标准来作评价。可见,最高院在避免适用程序标准的同时,尚没有明确厘清实体标准的适用逻辑。当然,从效力上来讲,审判实践中应当选择指导性案例进行参照。
(二)地方法院的观点差异
如上所述,至少在2004年后,最高院对“未引用”问题的裁判观点已经不再变化,但是从2005年至2014年期间全国范围的93份判决书可以看出,作为统一法律适用的经验示范,“宣懿成案”并未达到预期的司法示范效果。就评价结论而言,地方法院对“未引用”问题的判断有四类,分别为“未明确”(有9件)、“违反法定程序”(有3件)、“瑕疵”(有39件)以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有42件)。
1.未明确
“未明确”是指审理法院虽然在判决理由中提到了“未引用”问题,但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实际上隐含了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肯定,该类表述具体包括以下几种。(1)否定违法性的评价。如“行政文书中是否必须引用职权依据,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况且,职权依据引用与否,并不影响行政机关的职权效力”、③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2)思行初字第107号行政判决书。“以未引用……到‘目’为由,将复议决定撤销属判决不当”;④参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行终字第171号行政判决书。“未引用……不意味该决定书中未适用上述法律法规”。⑤参见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2014)沙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2)肯定合法性的评价。如“决定事实符合具体款项,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⑥参见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没有引用相关的法规依据,但是被告在庭审中能够讲明并举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其内容与……一致”⑦参见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台行终字第130号行政判决书。。(3)不予置否的陈述。⑧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行初字第316号行政判决书。现实中存在大量案例,尽管当事人对“未引用”提出了异议,但法院的判决书中未作回应。
2.违反法定程序
行政机关在程序上应当引用具体法律条款,现行法中有若干表达。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行政处罚依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根据上述法律条文中的“载明”、“告知”等,可以推知“应当引用”的规范意图。即使我国还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地方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已对该类规范作了进一步细化。⑨如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条例》第62条、第78条、第88条。无论学理还是规范,将援引具体法律条款作为程序义务已经没有太大争议,但审判实践中判定其违反法定程序是比较罕见的。最高院曾在早期的“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中认可“违反法定程序”的判断,但在之后发布的一系列公报案例中,最高院对同类案例的观点发生了明显转变。2005年至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判决书中,也仅有3份认定“未引用”为“违反法定程序”,⑩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4)二七行初字第86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3)鄂建始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且这些判决中的判断并非单独针对“未引用”问题,同时还兼顾其他程序违法情形。所以,可以推断,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愿以程序标准来评价“未引用”情况。原因在于,2014年修订前的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程序违法,法技术上只有撤销与否的选择。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对“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确认违法情形也属于应当撤销一类。而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一般保持谦抑,法官不会轻易因这种程序违法而否定原行政行为的法效力。
3.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审判实践中的普遍观点,但是其中的裁判路径仍有不同。
其一,实质审查后一体两面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与“瑕疵”。法院在司法审查中要求(允许)行政机关说明法律适用的相关依据,结合案件事实,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与否作实质审查。②在鸡西市医疗保险管理局等与鸡西市百佳煤矿社会保障行政给付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鸡西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能向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该约定,应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且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并未引用相关依据,其在法定期限内所举《工伤保险条例》第60条也不是其作出不予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依据,应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陕西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鸡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在对适法效果作出评价的同时,也一并强调行政机关的援引义务。但是,这里的“未引用”实际上只依附于其他违法情形的判断,已经丧失单独定性的价值。在此路径中,“瑕疵”判断通常与行政行为的实质审查相结合。一定程度上,“瑕疵”标准其实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另一个面向。一旦经实质审查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由于“未引用”未影响相对人的实体权益,法院往往会在法技术上认定为“瑕疵”,③在陈爱宝与平阳县公安局等处罚上诉案中,法院认为:“被诉行政决定送达给陈爱宝的文书遗漏了该引用的法律条文,但已在行政程序中进行补正,所适用法律条文符合案件事实,正确得当,说明平阳县公安局在作出决定时已经结合法律规定对查明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和判断。行政决定文书遗漏法律条文可能会使陈爱宝不能理解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适用过程、执法人员的内心心证、逻辑判断,但并未导致陈爱宝实体权利义务的增减。故法律条文的遗漏不等同于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不能因此认定被诉行政决定缺乏法律适用……程序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行终字第164号行政判决书。从案例数量上可以看出这种偏好。同时,考察具体案例可以发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瑕疵”的概念理解有所泛化,基本上将未影响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轻微违法都称为瑕疵,以便运用。如实体上的“不当”、“不妥”、“法律适用瑕疵”,或程序与形式上的“不完备”、“程序瑕疵”或“有失规范”。虽然与前述“未明确”类型一样,“瑕疵”判定并没有伤及行政行为的法效力,但法院此举旨在认可行政瑕疵的治愈与补正,并对“未引用”行为作出了微弱的否定性评价。
其二,将“未引用”形式等同为“适用法律错误”,即单独作为违法事由,进而以三段论得出结论。④在汤某诉贺州市某水利电力局水利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5条共有三款,每一款是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规定的不同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贺州市某水利电力局对上诉人汤某萍修建拦河坝的行为作出贺八水电罚字(2012)67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进行处罚,没有明确具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5条哪一款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贺行终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这种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对形式问题直接以实体标准作出裁判,以此否定行政行为的法效力,在逻辑上无法自洽,法院不免有懈怠之嫌,而且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未必有益。
也有观点认为,行政依据应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规则。⑤在吕习追与濮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濮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上诉称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规定,被上诉人吕习追符合劳动教养情形,但该规定在上诉人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中并未引用,不能作为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濮中法行终字第51号行政判决书。循此思路,法院若认定行政行为作出时没有引用具体法律条款,行政机关在事后也不得进行补正,视为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实际上是将行政依据等同于证据对待,但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⑥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提供依据的行为参照适用证据规则,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可以将逾期不提供依据认定为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但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对此作出修改,其第1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43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据此,该司法解释改变了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将行政依据排除出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即行政机关事后可以补充相关依据,且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2014年修订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沿袭了该司法解释的思路。
三、指导案例41号的审查路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学理上的概念定性并不能与个案处理良好衔接,审判实践中针对“未引用”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是作形式审查,抑或实质审查。若进入实质审查,还能否以适当的合法标准来评价“未引用”问题。指导案例41号选择的实质审查路径,可以为日后的同类案件所“参照”。
(一)事实概要与裁判思路
1.案例事实
原告宣懿成等18人(以下简称:原告)系衢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2002年12月9日,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以下简称:第三人)的报告,经审查同意其在原有的营业综合大楼东南侧扩建营业用房建设项目。同日,衢州市规划局制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第三人为扩大营业用房等,拟自行收购、拆除占地面积为205平方米的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改建为露天停车场,具体按规划详图实施。18日,衢州市规划局又规划出第三人扩建营业用房建设用地平面红线图。20日,衢州市规划局发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用地面积756平方米。25日,被告衢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被告)请示收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住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187.6平方米,报衢州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同月31日,被告作出衢市国土(2002)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告知原告其正在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收回及诉权等内容。该通知说明了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律名称,但没有对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款予以说明。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被告的《通知》,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2.裁判思路
该案的争点在于被告没有告知原告行政行为的具体法律依据,以及第三人的用地需要属于“公共利益”或“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对此,法院的裁判思路如下。(1)被告在作出《通知》时仅说明了所依据的法律名称,未引用具体法律依据。(2)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补正了具体法律依据,即《土地管理法》第58条的有关规定,依该条第1项“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和第2项“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被告有权作出收回原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3)被告所举的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35号《关于同意扩建营业用房项目建设计划的批复》、《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审批表》、《建设银行衢州分行扩建营业用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等证据,难以证明行政行为符合上述具体依据,故法院不认可被告所补正的依据,认定行政行为作出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4)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其不能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和依据,法院认定该行政行为没有证据和依据,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二)三层次路径
指导案例的要点指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应当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而言,其可以提炼一个三层次的审查路径。
1.不予定性
法律依据是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故无论原告有无对援引问题提出异议,法院都应当主动审查,但不能对“未引用”形式直接定性,原因在于以下两点。(1)行政法秩序暂时优位。“未引用”在实体上的违法可能并非违法事实,更多情况下,某些行政行为的审查仅可得出程序或形式上的瑕疵,并不能导致行政行为实体上的效力缺陷,或影响到相对人的实质权利,“若遽然将此种瑕疵行政处分撤销,有时反而会损害到人民之信赖利益,影响法律之安定性并妨碍行政效率”。⑦洪家殷:《论瑕疵行政处分之补正》,《宪政时代》第12卷第3期。因而,此时对行政法秩序的合理维护是优于程序价值的,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保障仍在观望。(2)司法认知限制。单一的法规范蕴含特定的规范要件与法律效果,而行政诉讼是法院对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过程的复审,区别于终审法院对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审查,⑧司法裁判的依据引用标准比较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时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而且,我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据此,终审法院可依审理情况直接补正具体依据(适用正确的法律、法规)。行政行为的依据并非司法认知的范畴。因此,法院对待“未引用”问题,既不能依事实认定自行补正相关依据或代行政机关进行法律解释,也不宜忽视实质的法律适用效果而直接判决违法。
综上,“未引用”不等同于行政行为作出时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应当要求(允许)行政机关补正具体法律条款,而不能直接跳越事实认定与法律解释的审查。目前,虽然行政依据已经被排除出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逾期提供依据不会承担举证责任上的不利后果,但是,法官依职权主动查明依据的完整情况是对法律适用的审查。若行政机关在法庭释明后仍未予(无法)补正,可直接认定行政行为实体上没有适用正确的法律依据。
2.事实审查
在行政机关补正具体依据后,法院以事实要素为主导,进一步审查法律适用情况。行政行为的依据要件完整后,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法律适用所认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且只能举证行政行为作出时的证据来涵摄补正依据,若认定法律适用的主要证据不足,则可同时评价“未引用”形式的违法性。虽然该种进路对行政行为的形式要求有所降低,但行政机关仍不可在事后随意选择相关依据。实际上,在2014年修订前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违反法定程序”只能判决撤销与否的情况下,⑨法院在判决中只需指出多种违法情形中的一种的主张,只看到行政诉讼解决眼前特定纠纷的功能,没有看到行政诉讼确定原、被告权利义务的功能,更没有看到行政诉讼为潜在的诉讼当事人确定权利义务的功能。为了减少当事人重复起诉,法院应当尽可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并在行政判决中宣示行政行为不合法的全部理由。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将“未引用”的效果判断依附于实质审查结果,既表明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情况主张全面审查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高院在强调援引义务的重要性。否则,法院只需审查依据补正后的行政行为即可,是否评价“未引用”问题并不影响审查结果。该案中,行政机关举证的事实无法涵摄至具体规定的“公共利益”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据此,法院不认可行政机关补正的依据,行政行为再次被还原为没有法律依据之状态(没有适用应当适用之依据)。
3.违法推定
“应当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是最高院通过司法拟制的解释技术确定的法律效果。司法上的“视为”是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将系争不同的法律事实在规范上给予相同评价的裁判过程。⑩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法律对“未引用”的效果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并不意味这是评价欠缺型的法律漏洞。①需要加以规整的情形没有被考虑进去,形成了一种评价欠缺型法律漏洞。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从体系解释可以得出,引用具体法律条款是行政行为合法包涵的应有之义。当这种违法情形出现后,在对“未引用”作否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如何判断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则落实到司法层面,需要均衡行政法秩序、相对人权益、司法谦抑等多重价值。法院进行实质审查时,发现行政机关的证据无法支持其适用补正依据时,在认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同时,反向将“适用法律错误“的构成要件规则转用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未引用”,二者在没有引用(无法证明引用了)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的重要观点上类似,由此附带对“未引用”形式作出评价。
四、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新标准
指导案例41号的裁判规则已基本确定,但是结合2014年修订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可以对其裁判法理作进一步推动。
(一)程序价值的解释空间
“未引用”可以推定为“适用法律错误”,但若补正后的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正确,对“未引用”形式应作何判断,指导案例41号并没有明确。审判实践中多将这种情形认定为“瑕疵”,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尽管“未引用”的程序轻微违法对行政实效及相对人权益影响甚微。上文已述,法律依据既是实质合法性的效力来源,又是形式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对行政机关而言,依法作为并明确法定依据是其专业常识及义务,引用具体法律条款区别于“说明理由”中的其他因素,是行政行为必要的合法性理由,而非提高可接受性的正当性理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全面展示法律的规则,杜绝任何保留、部分保留或者误导的展示或者指明的行为。②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48页。因而,“未引用”实际隐含了行政机关消极作为的主观态度,如果不在司法审查中强调程序上的援引义务,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会更加忽视这项要求。除此之外,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援引具体依据,则相对人在事后更难以获知相关信息。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法院审理相对人要求公开行政行为依据的诉求,一般都认定为“要求行政机关对如何理解与适用法律进行解释”,③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行终字第417号行政判决书。而这不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
(二)援引义务的例外
准确引用依据有助于相对人理解与接受行政行为的内容,促使行政机关周全考虑适用依据的正确性,方便法院审理法律适用是否合法妥当。基于上述考虑,行政行为作出时原则上都应当尽到援引义务。但是,为确保行政效率,仍可以由法律规定援引义务的例外情形。④这一点在比较法上可以有所借鉴,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9条。而且法律难以事无巨细地规范社会生活,除明确规定之外,还可以权衡行政行为侵害权益的可能与程度,归纳相关行为的类型化要件:(1)不产生法律效果之事实行为,如行政指导、信息提供等,行政机关可以不引用具体依据;(2)与相对人充分沟通之行政行为,包括已经过听证程序之单方行为以及行政双方行为(行政协议),上述行为中,因程序上必然告知具体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允许相对人充分申辩、陈述,或者相对人可以斟酌后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建立,故不必苛求行政行为必须援引依据;(3)适用简易程序或应急程序的行政行为,在情节简单、争议不大或情势危急之下,执法人员可以口头告知或省略相关程序义务;(4)非法律适用内容的规范,如与行政行为相关的职权依据、程序条款、救济途径等,只需具备合法外形或直接告知、实施即可,纵使这类问题发生争议,在司法过程中也容易查明。
此外,有无必要区分负担行为与授益行为的援引强度呢?对干预形态之负担行为,司法谨慎进行严格审查的观点,在审判实践中的确得到了认同。⑤在重庆市无线电话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财政局产权界定上诉案中,法院认为:“《通知》作为界定产权的行政行为与行政处罚不同,未引用具体条款,属于法律适用的瑕疵,不构成撤销的法定理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行终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换言之,有关法院认为行政处罚这类行政行为应当引用具体法律条款。而且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中,适当放宽给付行政的法律保留要求也已形成共识,⑥参见翁岳生:《行政的概念与种类》,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这种发展自然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援引义务强度。但是,负担与授益只是相对而言的,对相对人之授益,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能就是不利益,甚至针对特定主体的授益行为可能会损害不特定的群体利益。因此,无论负担行为抑或授益行为,都应当以准确援引为原则。
(三)司法审查标准的改进可能
诚然,“以程序违法为由的撤销判决并没有提示实体方面的司法判断,也就不能保证这种争议不会再次发展为行政诉讼”。⑦王天华:《程序违法与实体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问题的一个侧面》,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涉及“未引用”的案例在现实中频繁出现,若一律因程序违法而撤销,只会让行政机关纯粹重复行政行为,对结果毫无影响,仅就满足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保障而言得不偿失。因此,在主张程序价值之前,应当先进行全面的实质审查。嗣后,针对适用法律正确且又不对相对人权利产生实质影响的程序轻微违法,“从行政成本和诉讼经济考虑,不宜撤销该行政行为,但仍需对该行政行为予以否定性判决”。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相应的规范基础已经具备,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项可以对程序轻微违法的行政行为作出确认违法判决。⑨2014年修订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利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由此,通过让行政机关承担一定败诉后果可以提醒其遵循程序义务,胜诉结果以及避免诉讼费用等实际利益也可以让相对人的救济情绪得到满足,同时被诉行政行为不予撤销,其效力仍继续存在,行政法秩序的稳定也得以保持。
当然,这种合法性标准的改进并非毫无问题——从内涵上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项描述的“程序轻微违法”与传统理论的“程序瑕疵”几近一致,似乎可以就此将“程序瑕疵”纳入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对象。但是,尽管“瑕疵”概念在规范文本上并未明确,我国学理与实践中却早已普遍使用,若此时将其全盘替代,不但在理论体系上有突兀,实践操作中也会面临诸多问题,因为行政违法可能会随之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等连锁反应。未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项的“确认判决”如何适当运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代结论:从公报案例到指导性案例
综上所述,对“未引用”问题的司法审查,由于行政法秩序暂时优位与司法认知限制,法官不宜直接对“未引用”形式作出定性,而应当要求(允许)行政机关在诉讼中补正依据,若既有的举证事实无法涵摄至具体依据,则不认可事后补正的具体依据,推定“未引用”为“适用法律错误”。指导案例41号的裁判思路虽然对长期以来的司法混乱进行了归一,却仍不能对明显的程序问题作直接评价,这种司法审查强度的松动更像是程序价值式微后的权宜之计。2014年修订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所创设的对程序轻微违法的确认违法判决,能否发展出程序审查的新标准,是值得尝试与探讨的。也就是说,即使补正依据后的行政行为经审查适用法律正确,原则上依然可以确认违法。
在此也应指出,虽然“宣懿成案”在被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前,早已刊登于2004年第4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但是公报案例与指导性案例在法效力上有着本质区别。基于审判法官的视角,我国的案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法效力的案例、有事实效力的案例以及有说服力的案例。第一种指的是指导性案例,最高院以司法解释明确了该类案例应当参照及引述为裁判理由的法效力。第二种是指审判法院的上级法院推出的典型案例,由于上级法院的司法观点会直接影响上诉案件的二审结果,基于制度因素,这类案例具有事实效力。第三种是指没有直接法效力或制度影响力的各类案例,比如最高院推出的公报案例、各类科研机构的案例汇编、学者编写的案例评释等,对于该类案例中的裁判要旨及理由,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偏好提取利用。这种效力认知与我国司法系统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适用层面,指导性案例的法效力直接体现为,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对裁判要点“应当参照”以及“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9条、第10条、第11条。目前在审判实践中,最高院通过判例明确了公报案例与指导性案例在适用上的差异。①在李艺东等与黄木兴一般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院认为:“关于黄木兴主张本案应参照本院公报案例处理的问题,经查,黄木兴援引的本院公报案例并非是本院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其主张本案应参照该案例处理没有依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441号民事裁定书。而且,已有相关案例对指导案例41号予以“参照”。②如周口市双立商贸有限公司与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纠纷案。参见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漯行初字第51号行政判决书。其中清晰呈现当事人诉称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法院不予参照并说明理由的审理过程。当然,类似“宣懿成案”这种公报案例上升为指导性案例的发展,也可能是案例指导制度趋向保守的表现。③虽然公报案例与指导性案例是两套独立的案例系统,但是笔者经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5月1日最高院推出的52个指导性案例中,有37个曾是公报案例。
(责任编辑:姚魏)
D F743
A
1005-9512(2015)09-0151-10
张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