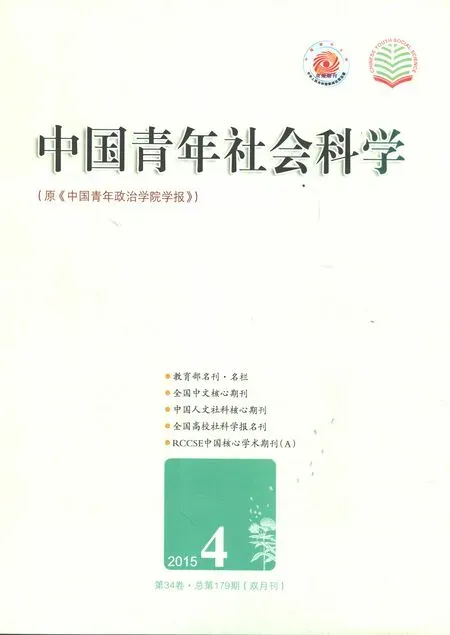社会建构理论框架下的青少年网络欺凌
2015-01-29■方伟
■ 方 伟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社会建构理论框架下的青少年网络欺凌
■ 方 伟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随着网络深入到青少年生活的各个层面,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模式正在发生着改变。其中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及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广泛普及,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了自我表达、社会互动与交往及获得社会帮助的平台,实现了更广泛的网络参与和社会交往,促进了青少年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包括网络欺凌在内的一系列对青少年发展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为。要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分析框架,促进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环境的建立,以青少年自身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为切入点,强化定性研究,开展新媒体使用媒介素养教育。
社会建构理论 青少年 网络欺凌
一、社会建构论视角的网络欺凌分析框架
提到网络欺凌,很多成年人视其为洪水猛兽,认为网络的匿名性特征使得人的行为缺少了社会监督,减轻了实施欺凌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从而助长了欺凌行为;网络同时又提供了新的多样化的欺凌平台,增加了欺凌出现的概率。总而言之,互联网的出现决定了网上欺凌的存在及特征,并且对青少年的生活、学习和成长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对网络技术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青少年避免在网络上受到欺凌的“好”技术。
以上对网络欺凌的认知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属于从技术决定论视角审视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在技术决定论视角下,技术决定了人如何使用技术以及社会如何发展,忽略了社会和人对技术的制约和影响。此种视角下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认识,过分关注技术要素,而缺乏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实施者、被欺凌者以及旁观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环境及青少年自身发展阶段的特征等因素与欺凌行为之间关系的完整认识。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问题的存在,便无从谈起如何有效预防和制止网络欺凌行为。
鉴于此,笔者建议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框架出发去认识媒介、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及其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是社会建构理论向技术研究领域的延伸,由荷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比克(Bijker)和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平齐(Pinch)提出,提供了与技术决定论不同的技术研究视角。在此种框架下,技术并非独立于社会和人而存在并且对人的行为与社会产生决定作用,而是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其如何产生、如何为人所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与人和社会密不可分的。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网络欺凌研究,不仅关注网络的技术特征所提供的可能性,也关注青少年所处的社会、学校、家庭等环境与青少年自身发展特征如何影响其网络使用行为以及网上欺凌经历,以期完整、全面地从青少年视角出发,描绘和解读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为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青少年对媒介在欺凌中角色的建构
互联网的出现及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互联网的一些技术特性,如相对匿名、自由的网络互动平台以及大量用户,拓宽了青少年互动和交往的空间。一方面,在网络空间内,青少年既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好友互动,也可以与陌生人交流,从而开阔视野,提升与人沟通和交往能力;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也有可能为欺凌提供新的平台和空间,使得互联网成为青少年欺凌的工具,这也是很多成年人对网络产生忧虑的重要原因。
网络的技术特征虽然提供了以上可能性,但青少年对其在网络欺凌中的角色也进行了建构。当成年人对网络欺凌的关注点集中于包括匿名性在内的技术特征时,青少年独特的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他们有着和成年人不同的需求,青少年对媒介在欺凌中的角色认知和建构会反映其群体特征。例如,在一项对加拿大6-9年级学生的网络欺凌研究中,当问及学生为何在网上欺凌他人时,他们给出的理由如下:不喜欢对方;对方惹他们不高兴;他们先被对方欺凌,所以理所应当以同样方式反击;他们的朋友在网上欺凌过他人,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被接受的行为[1]。在以上给出的理由中,无一涉及技术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在网上实施欺凌并不是因为网络为欺凌提供了便利,才决定充分利用此便利去欺凌他人,而是反映了青少年自身的经历和心理。
网络的技术特性一定程度上不会促使本不想欺凌他人的青少年去进行欺凌,而是为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想实施欺凌的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更大空间,便于他们实施欺凌行为。在此种情境下,网络的技术特征确实使得欺凌表现出独特之处。在密西拿等学者的研究中,青少年视角的网络欺凌和现实生活中的欺凌相比,其独特之处包括两方面:一是欺凌无处不在。研究中的青少年用无休止的欺凌(non-stop bullying)来形容网络欺凌。一些青少年认为,当放学后回到家里,他们期待的是远离欺凌,是安全和受到保护的环境,因此在家中上网时受到欺凌让他们尤其感觉受到了侵犯,造成心理上极大的落差;此外,网络欺凌也存在于校园环境,手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流行,为青少年在学校里上网以及进行欺凌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有关。有些青少年承认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有些人对在网上欺凌别人无所顾忌,而且有时候因为不知道被哪些人欺凌,受害者无法向成年人报告。但很多青少年谈到,他们经历的大部分网络欺凌来自他们的社交网络,也就是并非来自陌生人。有些青少年描绘道:我认为网络欺凌非常恐怖,因为有时候当你被欺凌时你不知道对方是谁,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是谁做的你也会感觉非常难过,因为你看不到他(她),因此不能当面告知他(她)你的真实感受[2]。此研究中青少年对媒介特征在网络欺凌中角色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作为媒介使用者的青少年,网络是嵌入其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种形式的媒介,其技术特征并非决定青少年的使用行为;相反,技术的存在满足了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为其相关行为提供了便利。
三、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
青少年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中坚力量及网络欺凌的参与者、受害者与旁观者,其在网络欺凌的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由于很多相关研究证实了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学术界对网络欺凌一直比较关注,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界定网络欺凌的严重程度。但很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有很大差异,如帕特金与辛杜佳对35个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进行回顾,发现这些研究中网络欺凌发生的概率差异巨大,最小的为5.5%,最大的为72%,其中平均欺凌率为24.4%[3]。有学者认为,造成如此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样本的选择、测量方法以及时间跨度等因素的不同[4]。从建构论视角来看,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并未真正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研究他们对网络欺凌的建构,导致学者们所界定的与青少年群体建构的网络欺凌脱节。
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与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在网络互动中,对语言使用或者互动方式的选择,在有些群体青少年看来,只是为了交流而非实施欺凌,而来自另一群体的青少年却认为受到了歧视和侮辱。以笔者之前做过的城乡青少年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研究为例,某位农村男生通过QQ加了某城市女生为好友,因城市女生对网上与陌生人交友不感兴趣,因此开始交流时反应比较冷淡,具体表现为用很简短的回答去敷衍农村男生。对女生来说,她仅仅在表明自己对与陌生人聊天不感兴趣的态度,她无意也并非在对男生进行欺凌;而男生则恰恰相反,因为从女生QQ空间中的照片和日志识别出女生为城市女孩,所以男生认为女生的冷漠所表现出的是城市女孩的傲慢,本质是对来自农村的他的歧视,因此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与欺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伤害,而事实上女孩并不知道他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此案例虽然不符合主流研究对网络欺凌的定义,但上述例子中男生把自己定义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的这种建构虽然与个人敏感的性格有关,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我国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关系中农村的弱势地位。此外,贝朗等学者在对美国、加拿大中学生与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欺凌研究中发现,两国学生报告的网络欺凌比率存在差异,美国学生中出现网络欺凌的比率要高于加拿大学生[5]。虽然作者对此差异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如样本中男女比例的差异,但两国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此差异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研究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
家庭与学校环境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建构也会形成重要影响。对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其主要的活动空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学校中欺凌行为是否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及老师和学校对欺凌的容忍度和处理方式,塑造着青少年在网络中对欺凌的建构。同样在家庭中,家庭关系是否平等和民主,父母与人交往时是否存在欺凌行为,以及受到欺凌时的处理方式,也在时刻影响着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是把其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对欺凌的建构延伸到了网络空间。因此,对青少年网络欺凌建构的研究不能忽视对其家庭和学校环境的考察。
此外,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一般都会延续到人生下一阶段,依赖理论(Attachment Theory)被用来对此做出解释。青少年在成长早期与其照料者(caregiver)建立的没有安全感的情感联系,可能使其对与包括同龄人在内的他人建立关系产生负面期望和影响。比如,在家庭中未体验过与父母的信任关系的青少年可能会难以信任他人,而且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更容易表现出敌意和攻击性。贝朗对美国和加拿大青少年的研究证实了两个国家青少年中学阶段的欺凌都会延续到大学阶段,而且中学阶段的欺凌形式和大学阶段的形式也有极强的一致性[6]。因此,我们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关注点不能只集中在学校环境之中,而应充分了解家庭环境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青少年欺凌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
青少年作为一个群体,其成长与发展阶段对其建构网络欺凌也产生着影响。对青少年来说,朋友关系是社交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其成长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朋友在网上的互动也影响着其对欺凌的认知和建构。密西拿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朋友之间有些行为也被归类为欺凌,如一个12岁女孩举例说,当你和最好的朋友吵架,她因为非常生气以致想通过一些行为实施报复,你认为你能信任她,但她能把你的某些事情放在网上对你进行网络欺凌[7]。而在成人世界中,好朋友之间的吵架及相关行为不一定能归入欺凌,成年人与青少年由于发展阶段及生活经历不同,导致他们对欺凌的建构可能有很大差异。还有研究证明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网络欺凌的不同,具体来说,年纪大的青少年较之年纪小的更爱在网上实施欺凌行为。如密西拿等研究发现,12-14岁的青少年中有25%以上的学生报告曾在网上对他人进行过欺凌,而11岁的学生报告欺凌过他人的比率为17%。因为作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获取的仅是关于欺凌比率的数据,并未探讨具体原因,但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欺凌实施者的年龄差异[8]。
四、措施与建议
发生在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欺凌会对青少年成长造成严重危害。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群体,其身体和心理健康与其对归属感和社会联系的认知密切相关。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欺凌破坏了青少年的归属感,使其感觉到被同龄人排斥,易于引发精神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较差的学习表现和对学校的排斥。笔者建议应采取如下措施。
1.构建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学校、家庭环境
青少年、媒介都是社会和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媒介的发明、发展及其如何被使用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结构。在一个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大家都与人为善,极少有恃强凌弱的现象出现,家庭成员间和睦信任,学校同学间团结友爱,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媒介以及青少年群体会出现欺凌吗?因此,要想解决网络欺凌问题,最根本的是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不存在欺凌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环境。
改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非空话,而是对问题本质以及现今社会主流应对政策的反思。现今国内外的应对措施,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者部分解决某些青少年面临的网络欺凌问题,但由于未能从社会和文化上对网络欺凌建构的视角去认识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以来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善,虽非一己之力可以实现、一日之功可以达成,但社会政策制定者若以此为立足点所制定的网络欺凌干预政策,势必更有前瞻性。
2.以青少年自身应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为切入点
考虑到目前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广泛性、危害性以及社会环境改善的长远性,仍需从微观视角关注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治理机制,从策略层面给出指导。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以及政策报告中给出了很多实用性意见,并已付诸实施,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不一一赘述。由于本文提议从建构论视角认识青少年网络欺凌,在此仅从青少年自身对网络欺凌应对方式的建构视角提出应对措施。
很多青少年面对网络欺凌,并未选择向家长、学校或者相关人士报告,而是选择沉默。他们选择沉默而非向家长、老师、学校报告的原因主要在于怕受到报复和怕在同龄人之中形成告密者的坏名声以致被孤立。被欺凌者以及旁观欺凌者的沉默,一方面不利于学校和家长了解网络欺凌发生的机制以及对青少年所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欺凌者的威风,使其更加无所顾忌地欺凌他人。因此,需要从青少年沉默的原因出发采取措施,打破青少年的沉默。比如,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建立网络平台,使青少年可以进行匿名举报,清除其担心受到报复或被同学知道后对其名声造成影响的顾虑。
3.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面对网络欺凌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盛行以及对青少年发展造成的危害,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对网络欺凌进行研究。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络欺凌问题及其危害、分析网络欺凌的界定及特点、介绍国内外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研究现状、关注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的最新进展、了解发达国家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对策等。这些研究为我们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网络欺凌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对网络欺凌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们也需要相关的实证研究,要深入了解青少年自身对网络欺凌的建构及倾向于采取的应对策略。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谨记的是,由于成人与青少年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研究者很容易站在成人视角对网络欺凌进行建构,这可能导致对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认识的偏差。
国外的实证研究主要采取定量的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大量的样本研究,更容易得出有代表性的结论,获取关于青少年群体特征的信息;而其劣势在于,由于缺少从青少年视角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从而很难获知青少年自身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信息。知名青少年与互联网研究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利文斯敦教授与同事曾提出,学界研究很少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或者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我们对青少年自身的经历、看法或者符合他们日常生活实际的网上行为知之甚少[9]。因此,建议我们的研究应采用定性或者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深入了解我国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现状、特征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4.开展新媒体使用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及其使用者都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新媒体所拥有的技术特征为其使用者提供了一定可能,但并不决定青少年如何对其进行使用,对于网络欺凌问题也是如此。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大学生群体较之于中小学生群体,虽然对新媒体使用的时间更长、频率更高,但此群体的网络欺凌现象并不比中小学生群体多。因此,思考如何解决青少年网络欺凌,并非一定采用限制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方式,而是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让青少年充分了解媒介的特征以及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引导青少年形成对媒介的正确认识,积极、正面地使用媒介。
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全方位配合。各种形式的媒体可通过媒介素养的宣传,形成舆论影响;学校以课上教育和课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把媒介素养理念传播到青少年群体;家庭则需要父母以身作则辅以正确引导,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意识。而青少年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接受者,更应主动参与其中,表达自身的教育需求。
[1]Cassidy, W., Jackson, M. & Brown, K. N., Sticks and Stones Can Break My Bones, But How Can Pixels Hurt Me? Students’ Experiences with Cyber-Bullying,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2009(4).
[2][7][8]Mishna, F. , Saini, M., & Solomon, S., Ongoing and Online: Children and Youth's Perceptions of Cyber Bullyi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09(31).
[3]Patchin, J. W., & Hinduja, S. Cyberbullying: An Update and Synthesis on the Research. In J. W. Patchin & S. Hinduja (Eds.), Cyberbullying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Exper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2012,pp. 13-36.
[4]Sabella, R. A., Patchin, J. W., & Hinduja, S. Cyberbullying Myths and Realit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6).
[5][6]Beran, T.N., Rinaldi, C., Bickham, D. S. & Rich, M., Evidence for the Need to Support Adolescents Dealing with Harassment and Cyber-harassment: Prevalence, Progression, and Impact,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2012(5).
[9]Livingstone, S., & Haddon, L. Risky Experiences for Children Online: Charting European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the Internet. Children & Society, 2008(22).
(策划:方 奕;责任编辑:邢 哲)
2015-04-25
方 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青少年与互联网、传播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