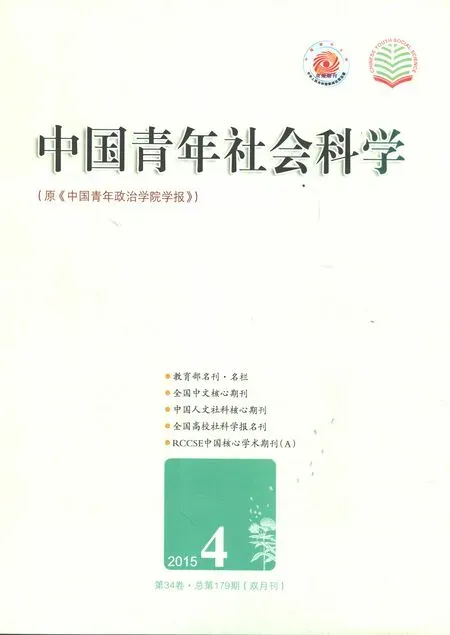网络欺凌与学校责任
2015-01-29宋雁慧
■ 宋雁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工作系,北京100089)
网络欺凌与学校责任
■ 宋雁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工作系,北京100089)
网络欺凌是当前社会凸显的校园安全问题,学校在防治欺凌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学校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内容包括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网络安全人员配备、网络安全教育与培训、网络欺凌事件处理4个方面;范围包括学校的网络设备、由学校赞助的网络设备以及冠以学校名称的知名虚拟组织所在网站的相应网络设备等。学校在网络欺凌事件中的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学校只要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学生网络行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按照合理的程序提供服务,对侵权信息及时地进行了处理,就可免除侵权责任。
网络欺凌 学校责任 侵权责任 归责原则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也叫网络欺负,是指个人或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如电子邮件、手机、即时短信、个人网站和网络个人投票网站等,有意、重复地实施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
美国网络欺凌研究中心(Cyberbully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CRC)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调查研究,2014年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11-14岁的青少年中,34.6%的青少年曾经受到过网络欺凌,17%承认曾在网络中欺负过他人[1]。随着网络欺凌问题的凸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正努力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但无论是立法的规制方式,还是综合治理方式,各国都非常重视学校这一重要的防治主体。实证研究也表明,网络欺凌与学校其他问题紧密相关,学校采取了防治和管理措施,学生发生该行为的频率就会显著降低[2]。目前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有严重的恶性网络欺凌事件才会纳入刑法的管辖范畴。因此,从法律上明确网络欺凌的责任主体,明确学校监管与保护的法律责任及内容范围,对防治网络欺凌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校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
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一样,属于侵权范畴。我国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条明确了网络侵权这一侵权类型,为网络欺凌主体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等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这些条款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为“教育法律关系”,这是一种基于教育关系而确立的公权性质的法律关系。而对学校管理和保护责任与义务的规定是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属于学校教育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梳理相关法律条文,学校的管理、保护义务包括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安全人员的配备、安全教育以及对安全事故的事后处理4个方面,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分为常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两部分,前者包括门卫制度、进出校门登记制度、校服制度、校内安全校长负责制、安全教育制度、制定犯罪预防计划制度、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等;后者包括突发事件预案制度、及时救助受害学生原则、程序化处理、事故档案制度等。
第二,安全人员的配备。安全人员主要负责法制教育、心理教育、学校日常的安全维护以及安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到位、有效制止与发生之后的处理辅导等工作。学校应配备法制副校长或法律辅导员、门卫或保安、心理咨询员和法律咨询员、卫生保健教师等安全人员。
第三,安全教育和培训。安全教育包括人身安全教育、自护自救教育、法制教育以及对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个别教育等,通过开展安全培训、相关主题活动、配备相应设施以及必要的演练等方式进行。
第四,安全事故的事后处理。发生安全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制止有害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行为,及时救助受伤害的学生,践行优先救助未成年人等原则。
以上4个方面是学校依照教育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管理和保护学生的义务,明确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保护义务,有利于对网络欺凌事件中的学校责任进行归结。网络欺凌是故意实施的伤害行为,因此实施欺凌的一方要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学校负有对未成年学生人身的管理和保护义务,因此判断学校是否有责任的依据是学校是否有过错。如果学校严格履行了以上4方面的管理和保护义务,并且在程序上也按照法律的要求去执行了,那么学校便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学校在明知可能发生网络欺凌却放任其发生,或者在收到受欺凌学生要求删除相关不良信息内容的请求后仍然不作为,放任网络欺凌事件发展,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与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涉及一个重要概念——“在校期间”,在现实层面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时空概念,从以往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在校期间”在时间上是指“从上学时起到放学时止”,一般包括正常的上学、放学路上的时间;在空间上是指物理的学校范围,包括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也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但这样的界定显然没有考虑到互联网跨时空的特性,互联网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并存的特性使传统的时空界定失去了监管意义,因此,必须重新界定学校的监管范围。
从学术界目前的讨论来看,有两种划分标准: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欺凌行为可以分为行为的实施地和行为的结果地,两者只要有一个发生在校内就可以认定为校内网络欺凌行为,学校对此具有监管的权力与义务;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利用学校的网络设备或由学校赞助的网络设备所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均可以认定为校内网络欺凌行为,学校对此具有监管的权力与义务。比较两种观点,前者将网络欺凌作为传统欺凌行为的延伸,但问题是在网络时代很难界定行为的实施地或者结果地,又将绕进“在校”这个时空概念中,而且会将学校的监管责任无限扩大,变相承认了学校对所有的网络欺凌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监管义务,这也超出了学校的管理能力范围。后者主要考虑了学校对网络设备的管理能力,缩小了学校对网络欺凌的监管范围,但可能出现监管漏洞,因为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在校园网的范围内进行的。2009-2013年期间3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的结果皆显示:腾讯QQ是中小学生使用最多的网络平台或工具,且这种趋势从PC电脑端顺延到手机等移动端;第二位是微信。中小学生热衷的社交SNS网站主要有:人人网、开心网、百度贴吧等,80.6%的未成年人在网上交往的圈子是熟人[3]。但这些网站和客户端既非学校的网络设备,也非学校赞助的网络设备,如果将这些学生使用和交流频繁的网络空间排除在学校监管范围之外,那么加强学校对网络欺凌的监管,效果和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如何在学校监管能力和学校监管效果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划定学校的监管范围?
从网络社会的构成来看,一部分实体性组织如学校等,会在网络空间中有一个或多个与之对应的“映射”,该网络空间的“映射”也被冠以现实空间学校或组织的名称,为组织成员交流、对话提供了虚拟平台,而其中的社交主体仍然是现实物理空间的组织成员。像这种以学校命名并聚集了大量在校生的网络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具有匿名性和指向性双重特性。匿名性是指个体可以隐藏在数字ID背后,没有人知道发言的是谁;指向性是指这一特定空间是现实中组织成员在网络中聚集的空间。以“百度贴吧”为例,“吧”内提供了以各个中学为名的“贴吧”空间,该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可能光顾这个空间,查看其中的帖子。如果在“本校吧”内针对某教师或学生进行攻击或散布不良信息,其影响力类似于学校内的“大字报”,点击阅览这个“吧”空间的人都可以看到,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承担的对学生管理和保护的责任范围不仅包括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网站、网络设备如校园网等,还应该包括这些冠有学校名称的虚拟组织所在的知名商业性网站,如腾讯QQ、微信群、人人网、开心网、百度贴吧等,在这些空间中发生的网络欺凌事件,无论是影响范围、影响力还是对被欺凌者的伤害都远远大于其他网络空间。这些网站的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需要将后台管理的权限让渡给学校,让学校相关部门具有审查、删除和处理不良信息的权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监管范围应该包括学校的网络设备、由学校赞助的网络设备以及冠以学校名称的知名虚拟组织所在网站的相应网络设备。
明确了网络时代“在校期间”的概念,学校应该承担的防治网络欺凌的法律责任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网络不良信息拦截过滤制度、学生安全信息举报制度、网络安全教育制度、网络安全预案制度、“提醒—取下”(Notice and Take Down)制度——该制度是为应对网络侵权行为而对网络服务商提出的要求,一旦网络服务商接到网络侵权的提醒,不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都必须做出答复。如果提醒符合侵权条件,网络服务商就必须采取措施删除侵权性信息或者禁止该信息被访问。反之,如果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信息或证据,那么中间服务商可以做出不作为的答复。
第二,网络安全人员配备。网络安全人员主要负责网络安全教育、学校网站的日常安全维护,以及校外网站的信息监督与审查。特别是当有网络欺凌的相关举报或提醒时,应尽快查清楚并对信息做出相应处理。另外,学校还可以邀请青少年常用的门户网站,如腾讯QQ、百度贴吧等网站的管理人员,与他们交流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名誉免受损害、如何处理视频暴力的帖子等问题。
第三,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安全培训之外,学校还应开展针对网络欺凌受害者的专项教育。“沉默文化”在网络欺凌中愈发明显是因为受害学生担心的不仅是老师和家长的干预会使欺凌变得更糟糕,害怕举报后可能面临到更大的报复,同时也担心家长会因此禁止他们继续上网或使用手机[4]。由于网络欺凌具有隐蔽性、匿名性等特征,同辈群体、特别是同班或同校的同学在网络空间中接触较多,较之成年人更容易获得关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信息,由他们来帮助或举报将是很好的尝试。
第四,网络欺凌事件处理。学校应当定期审查负有管辖义务的网络空间,并对网络欺凌的举报进行回应和及时处理。一般来说,在处理网络欺凌事件中,学校应遵循“提醒—取下”程序。在网络服务商授权的基础上,学校一旦收到学生在其管辖空间内遭到欺凌的举报或提醒,必须采取措施及时将信息删除或屏蔽,然后再查清事实做出相应处理。
在传统校园安全管理方面,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是一对基本矛盾,学校管理权越大,学生权利就越小,反之亦然。在网络空间中,同样需要平衡学校监管权与学生的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等权利。在目前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会把1969年廷克判例(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中所确立的言论自由标准运用到学校对网络欺凌行为的规制上,该标准认为,除非学生在表达时能够合理预见到自己的言论将实质性地或者充分地扰乱了学校合理的管理规定,或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否则学校不得对学生的表达进行压制。但如果学校发现学生在网络空间传播侵害他人或学校管理的不良网络信息或者接收到关于学生网络欺凌的相关举报时,学校有权对传播不良信息的学生及其言论进行管制和处理,而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学校在网络欺凌事件中的法律责任认定与归责原则
从法律要件上来看,网络欺凌是故意实施的侵权行为,实施欺凌的一方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了损害事实并且其过错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只要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那么,根据侵权行为法与过错责任原则,欺凌者必须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学校在网络欺凌中的法律责任认定就复杂得多。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这是一种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往往要依据具体的标准或某种注意义务来确定其是否履行了适当的教育、监督和管理义务,进而确定其是否存在安全注意义务的缺失,即可归责的过失。
在判断网络欺凌事件中学校是否存在过失可借鉴两点:一是传统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确立的学校合理注意义务(Duty of reasonable care),二是网络侵权中对网络服务商适用的避风港抗辩体系(Safe harbor defense system)。在英美法系中,通过司法判例逐步完善学校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从最初的“谨慎的父母的标准”到“可预见的风险”理论[5]——即在判断学校是否尽到了适当的监管和保护义务、其行为是否有过失时,可以看它是否能够防止可预见的危险发生,如果能够防止但却发生了危险,则说明它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在网络侵权方面,美国确立了“避风港抗辩体系”以平衡网络服务商的基本权利。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简称DMCA)的第二部分“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限制”规定了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限制,即只要网络服务商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按照合理的程序提供服务,对侵权信息及时地进行了处理,就可免除侵权责任。我国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二条也采用了对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抗辩体系”,确定了其免责的基本条件。这种方式有利于规范网络服务商的安全注意责任,让规范经营的服务商不必对侵权责任的风险过于担心,因为每天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进行逐一审查是不现实的。这两项标准同样适用于学校在网络欺凌中的免责,只要学校对学生在校范围的网络行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按照合理的程序提供服务,对侵权信息及时地进行处理,就可免除侵权责任。那些认为学校对网络欺凌承担无限责任,要求学校不仅关注学生校内网络行为的发生或影响,而且还要关注他们在校外网络中的表现,对学生的校外网络行为进行管理的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损害时,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在网络欺凌事件中,欺凌者应当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而学校则应使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这是因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依据教育法而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因此学校行使对学生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行为属于公法规定的行为,类似于行政行为。因此,如果学校没有按照规定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而导致网络欺凌的侵权行为,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即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从另一角度讲,受害的学生由于身份所限,往往很难知晓学校在网络安全管理和保护方面所实施的措施及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处理措施,无法举证学校有过错,因此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学校不能证明自己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完善、网络安全人员配备、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网络欺凌事件处理方面没有过错的,就构成侵权行为,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学校能够证明自己尽到了应有的义务,日常已经做好了对网络欺凌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在收到欺凌举报时能够及时处理相关不良信息而没有过错的,则可以免除责任。
结语:立法是打击网络欺凌的有力措施,这一点各国政府都比较认同。近年来,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应对青少年的网络欺凌问题,并规定了欺凌的行为后果以及政府、学校、网络服务商、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部分网络保护条例远不能满足校园欺凌问题凸显的现状和相关保护与责任确认的需求,除非严重到危及生命安全的网络欺凌事件,受害者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获得相关保护和惩治欺凌者,更多的、危及身心健康的网络欺凌往往得不到有效防治。
《校园安全法》在多年呼吁之下仍然没有出台,网络环境下校园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因此本文中所谈及的学校安全管理与保护的网络范围、公共网络服务商对学校冠名空间的部分授权、网络欺凌事件中学校过失的判断、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等都是理论上的探讨,只有在立法中得以确认才能真正为网络欺凌的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
[1]Cyberbullying Research Centre,http://www.cyberbullying.us/Cyberbullying_Research_In_Review.pdf
[2]Sameer Hinduja,Justin W.Patchin,Cyberbullying: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Offending and Victimization,Deviant Behavior,2008(2).
[3]李文革 沈 杰等:《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4]陈 钢:《网络欺凌:青少年网民的新困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4期。
[5]熊进光:《侵权行为法上的安全注意义务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
2015-04-20
宋雁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校园安全与校园暴力、青少年社会问题。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校园暴力中旁观者的角色建构过程研究”(课题编号:11JYC0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