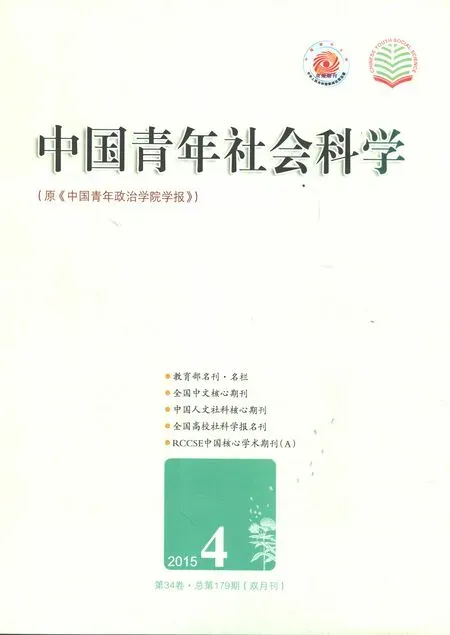媒介与青少年发展视野下的网络欺凌
2015-01-29■黄佩王琳
■ 黄 佩 王 琳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媒介与青少年发展视野下的网络欺凌
■ 黄 佩 王 琳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媒介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媒介的发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青少年的成长方式。网络欺凌便是在媒介与青少年生活世界双向互动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从媒介发展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出发观察网络欺凌,从宏观环境、媒介特性、道德伦理3个方面对青少年之间的网络欺凌行为进行解读,必须通过父母和学校的正确教育、公益组织的积极引导及政府立法的有力保障来综合应对这一问题。
媒介 青少年发展 网络欺凌
一、电子媒介与青少年发展:“围墙”的拆与建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青少年的生活越来越被电子媒介所包围,从最初的电视、电脑到现在的手机、平板技术,电子媒介种类越来越多,媒介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无序。电子媒介在给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带来便利和趣味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
青少年与成人之间曾经有着分明的界限。文化知识和信息的传承曾大量依附于口耳相传或文字印刷的方式,这些方式受限于时空,并依赖读写能力,因而从儿童到青少年、再到成人世界,需要翻越储备着不同知识和信息的“围墙”,正如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所言,从童年到成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暴露更多的信息以及继续受制于其他社会信息。可以说,青少年的成长原本是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有了电视之后,支撑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塌了。电视极大地扫除了时空障碍和读写约束,让青少年从小小的屏幕上开始窥探成人世界的秘密。于是,“围墙”被轻易地跨越,电视去除了过去根据不同年龄和阅读能力将人分成不同社会场景的障碍[1]。青少年在早期的成长阶段就已开始面对成人世界的各种关系,要处理电视构建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欺凌,原来存在于青少年的校园生活当中,后来走向电视,又走进网络。与传统的电子媒介不同,互联网不仅可以向受众提供信息,而且可以让受众之间进行线上互动。青少年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习惯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递与表达,网络社区、即时通讯以及社交网站等使得青少年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即时有效。与此同时,以往面对面的欺凌行为被转移到互联网上,网络欺凌行为被大量地暴露出来,其中既包括传统的欺凌行为通过画面呈现在网络中,也包括利用互联网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或是出于利用互联网来进行自我呈现与行为表达的习惯,或是出于对成人世界的好奇与模仿,近些年青少年利用互联网来进行网络欺凌的现象愈演愈烈。看似只是网络中的信息传播,但它却能导致青少年遭受严重的心理伤害,甚至出现自杀这种极端的自我伤害行为,这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网络对青少年成长所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思考网络欺凌仅仅是反映了一种微观的负面行为,还是其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媒介变迁、青少年生活方式改变的宏观因素?
二、网络对青少年生活的重新界定:反思网络欺凌
提到网络欺凌,大家会马上联想到由其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反应,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自杀案件,让人唏嘘不已。网络欺凌是一种新的欺凌方式,指的是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个人或群体进行威胁、羞辱、伤害。帕特金等研究者指出,网络欺凌是通过计算机、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有意的、重复的[2]。欺凌这一行为原来更多地存在于青少年间和学校范围之内,是在直接接触中实施的身体的、语言的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伤害行为。而网络欺凌更多的是通过技术中介化的文本、图像等方式对他人的心理造成伤害。
大量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关注了网络欺凌施害者的动机、行为以及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但是很少从媒介发展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观察网络欺凌。事实上,网络欺凌是在媒介与青少年生活世界双向互动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理解青少年对技术的认知、在中介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对道德的认识和实践,有利于我们更为多元化地看待网络欺凌。
从宏观环境上看,成人社会(主要为父母和学校)与青少年对技术的认知差异造成了对网络欺凌界定的差异。父辈的成长并未与网络相伴相随,他们更多的是利用网络来达到寻求信息和促成沟通的实用性目的,网络再好也是一种辅助现实生活的工具。在这一实用性目的的指导下,老师和家长都认为,技术对青少年接触新知识、促进学习是最有用的。青少年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把技术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之后,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具有身份构建和社会交往功能的博客、社交网站等媒介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间平行生活。事实上,网络欺凌就是高度融入网络化社会且紧密互动的一种后果。在成人看来,网络欺凌与现实欺凌都如同洪水猛兽,然而许多青少年却会将成人社会可能认定为欺凌的行为又细分为网络笑话、网络嬉戏和网络吵架。梵德波士等对10-18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会根据行为是引发负面情绪还是为了找乐子进行分类,而且他们认为行为实施者和接受者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至于到底是不是网络欺凌,还得看施受双方的现实关系[3]。
从媒介特性上看,网络独有的中介化特点使网络欺凌变得较为复杂。传统的欺凌定义来自于瑞典籍学者奥维斯,他为欺凌界定的范围是:(1)带有攻击性的行为;(2)重复并持续发生;(3)身体或语言的;(4)权力失衡。在这一定义下,欺凌是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的。但是,网络欺凌不是一种面对面发生的现象,而是通过网络技术中介化之后而产生的,它让虚拟和现实交融。网络具有匿名性、传播网络化等技术特征,其被人们社会化地应用之后,则相应地出现了虚假性、病毒性传播、无限复制和重复、去个人化等特点,这些都使得我们无法清晰地描画网络欺凌的权责边界。例如,与传统的欺凌不同,网络欺凌的重复性像滚雪球一样,会把效应翻倍。一张照片如果发出,那么可传达的人数以千万。由于有匿名性和虚拟性,一个欺凌者的传播行为可能会被很多人重复,伤害会无尽地持续。传统的欺凌所表现出的权力不均衡指的是身体、性别和数量上的,而网络欺凌的权力则与对数字技术的熟练程度、网络圈子的大小及互动程度等相关,这类新型的权力对比并不十分清晰。另外,网络的匿名性让欺凌行为没有负罪感,网络欺凌缺乏即时的言语反馈,降低了情感交流,网络欺凌被“分享”的可能性更大,网络欺凌中的围观者很难施加影响。互联网让青少年有机会尝试新的角色和身份。如果说,以往孩子们在课堂上通过传纸条来进行信息传递,那是一个避开了老师和其他孩子的相对私密的空间;而今天,“纸条”通过短信、邮件进行传递,其面对的是拥有海量观众的公共空间。习惯于将媒介使用当成生活方式的青少年,未必能意识到网络欺凌内容通过媒介传播社会化之后的风险,加上此类内容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治理手段,因而无法预测其后果。
从道德伦理上看,网络将道德的围墙重重击碎,促使网络欺凌不易受到约束。网络是一种企图跨越地点和时间限制的媒介技术,它对原本受限于时空和共同体的道德规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道德规范的形成和遵守有赖于直接的人际互动,但是当个人参与到大的群体、社区、公共空间甚至是无一相熟的全球网络当中,原先基于本地的道德视角也许就不适用了。网络欺凌的各种形式,诸如传播他人隐私、联合他人对某些人进行社会排斥、持续地发送带有负面信息的电子内容等,都带有跨越本土区域、冲破时空阻碍的特征。另外,由于网络具有高度的商业化特征,在追求商业利润时会利用大量低俗的内容来吸引眼球。青少年的网络生活与这些低俗内容相伴而行,成人世界的内容更多地向青少年涌来,“成人化的儿童”正是一个极好的比喻。对这些内容的耳濡目染使得青少年在网络中容易无视道德的束缚,为求好奇或者在冲动之下向他人传出低俗内容。实施网络欺凌的人认为,欺凌是正常的,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并不感到有什么道德负罪感。
三、网络欺凌的社会影响:无边界之“困境”
网络欺凌之所以在当下引起广泛关注,与网络移动化、社交化引发新的信息流通及社交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移动化让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连接上网;社交化则让人们的生活沉浸在圈子文化当中。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展阶段恰恰和“圈子”相关,也就是他们的同伴关系及群体认同。因此,他们更多地使用网络中的社交网站、视频分享服务、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媒介,让自己更好地融入到有意义的网络社群之中。这种网络社群与早期的社群相比,不是因兴趣、话题而聚合,而是更注重和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进行沟通。青少年的网络生存更注重所属的网络群体对他们的看法,因为群体是一面镜子,会对他们寻找“自己是谁”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他们维系和周边环境关系的重要纽带。由于网络使各种生活场景、各种观众以及各类身份都变得“跨界”和“混搭”,如果对此没有清晰的分析和有力的管理,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网络欺凌的社会影响正是和这种“无边界”密切相关。
首先,网络欺凌循环出现的可能性高,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变得同样具有风险。以往不同年龄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欺凌行为,但在网络上,欺凌行为的持续传播会跨越年龄的限制,被不同的人群复制和模仿,从而可能会循环出现。另外,因为通过网络欺凌所产生的侵扰很容易被复仇,所以青少年认为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是一种反欺凌方式,同时又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网络欺凌的循环往复让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可能快速转换。有研究证明,实施网络欺凌者成为被欺凌者的风险是其他人的20倍。网络欺凌的循环性,还在于许多围观的青少年习惯于“分享”这种行为,他们的再次传播可能只考虑到对同辈群体的呼应和维系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但是却无法预料到这种传播的示范效应和严重后果。
其次,网络欺凌行为能跨越空间及社会原有的身份秩序发生伤害。从原本大量存在于校园的欺凌,到网络中小伙伴们互相的挑衅,网络欺凌正开始发生在青少年处理与成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14岁的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老师和校长非常不满,他创建了一个网站,在网站上用低俗的语言对老师进行攻击,并且把老师画像的头部换成了希特勒,写着“为什么她要死”。另外他又配了一幅图,图中老师的头已经没了,而且鲜血从脖子上流下来,旁边写着“我们都希望这会发生”。被攻击的数学老师已经有26年教龄,她害怕被人杀害,心情郁闷,并且失眠、厌食。她无法完成该学期的教学工作,因而请了一年的假。最终,学校认为该学生长时间地向其他学生进行了不良的欺凌展示,并且对老师产生了实际的伤害,将其开除。法院也宣判该学生由于侵犯老师肖像权而由其家庭进行赔偿。在这一事件里面,网络欺凌提出了新的管理问题:学生建立网站的行为没有发生在学校内,是否归学校管?学生的网络言论是否真的构成违法行为?网络欺凌挑战了现实身份及权威关系,这种伤害的威力不可小觑,应该如何调节这种网络时代的关系?
最后,网络欺凌复制了现实中的权力失衡和不平等,还导致了自杀行为的发生。研究发现,美国中学生最容易被欺凌的内容包括:外表、性征、种族、文化和智力。反复张贴这类内容会让被害者内化这些信息,从而在心理上受到伤害[4]。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青少年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阿斯兰关于土耳其中学生的调查发现,父亲失业的孩子无论是成为网络欺凌的施害者还是被害者的几率都是非失业父亲孩子的两倍。网络让欺凌行为得以传播的同时,还对某些群体造成刻板印象,使人们对施害者和被害者以及网络欺凌本身做出过于简单的判断,由此无法认识到该行为的社会背景因素。网络欺凌导致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自杀,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并不鲜见,这足以引起我们思考网络欺凌作用于青少年心理之后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四、网络欺凌的应对办法:各方合力提升媒介素养
网络发展对青少年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将是持续的,原有“围墙”的消失在所难免,新的电子“边界”又还未被清楚地认知。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网络化环境中,如何防范网络欺凌的发生,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父母、学校、行业以及政府应该协作,共同提升各方对于网络化社会的认识,对青少年使用网络进行全面的评估,营造一个相互理解、互动顺畅的共同体,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不同场景、观众和身份糅杂的网络环境,增强网络媒介素养,努力提升在网络中管理和掌控自我行为的能力。
1.父母与学校的正确教导
父母与学校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网络欺凌,同时应通过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来教导青少年如何正确使用网络以及通过网络进行社交。首先,父母与学校要成为网络“中”人,而不是游离于网外,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青少年在“网中”是如何生存的。要使青少年明确无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都会在现实世界引起伤害、带来伤痛,是不可取的,网络中的不当行为同样会受到处罚。其次,学校应开设有关网络安全教育的课程,通过传授相关知识来提高青少年的意识,让他们学会如何在网络交往中阻止和回应网络中同辈的侵扰,做到既能恪守网络交往中的道德又能巧妙地进行社交。最后,父母与学校应进行有序的互动,在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的前提下共同关爱青少年的成长,让他们的隐私不被侵犯的同时合理地监督他们对网络的使用。
2.公益组织的积极引导
建立专门针对青少年成长的公益组织是治理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积极引导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规范,有效规避网络欺凌:一方面,可由与网络相关的企业成立专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公益组织,通过举办相关的讲座、活动和巡展来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或通过设计可防范欺凌的软件来进行技术防控。如CyberPatrol和LookBothWays两家公司就研制推出了一个警报工具,帮助孩子们在遭遇网上欺负或骚扰时可以即刻通知监护人。网络欺凌警报工具还可以在孩子的电脑屏幕上自行进行拍摄,然后将拍摄到的孩子触发恐吓邮件的截屏图片保存到一个文件中。此外,近来很火的大数据监控也可以被公益组织用来监控网络欺凌的状况,针对不同年龄、形式采取不同手段进行治理。另一方面,与青少年利益相关的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一些更贴近青少年的方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如新加坡一家名为“父母网络顾问组”的公益组织,该组织旨在教育公众和父母如何安全使用网络,使网络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从而引导孩子恰当和理性地使用网络,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使用环境[5]。再如美国的MTV频道就设置过“A Thin Line”这样一个节目,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网络欺凌案件,邀请青少年参与讨论,让他们自己思考哪些行为属于越界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或者通过虚拟学习,真实地再现网络欺凌的场景,让青少年自己选择应对的方法。这样的教导方式更有效,更能使青少年意识到网络欺凌的严重危害。
3.政府立法的有力保障
任何措施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因此面对网络欺凌问题,政府支持与法律保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政府官员应提高媒介素养,这样才能够提高辨别网络欺凌行为的能力,从而有效打击和治理网络欺凌行为。其次,政府职能部门应积极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支持公益组织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同时政府还应指导学校加强对学生的保护,并且督促学校开设媒介素养的相关课程。最后,政府应大力打击网络不法行为,通过制定网络欺凌的相关法律对网络欺凌进行治理和预防,从而净化青少年的网络使用环境。此外,还应完善相关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披露、转载相关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综合有效地治理网络欺凌。
[1]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2]Hinduja, S. and Patchin, J., Cyberbullying: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http://www.cyberbullying.us/cyberbullying_legal_issues.pdf
[3]Vandebosch, H. and van Cleemput, K., Defining cyberbully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o the perceptions of youngster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ur, 2008(4).
[4]Mishna, F., Cook, C., Gadalla, T., Daciuk, J., & Solomon, S. , Cyber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0(3).
[5]王国珍:《新加坡公益组织在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载《新闻大学》,2013年第1期。
2015-04-20
黄 佩,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网络文化与新媒体、传播与社会发展; 王 琳,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网络文化与新媒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移动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传播研究”(课题编号:13CXW018)、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基金项目“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课题编号:NSNC-2014 A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