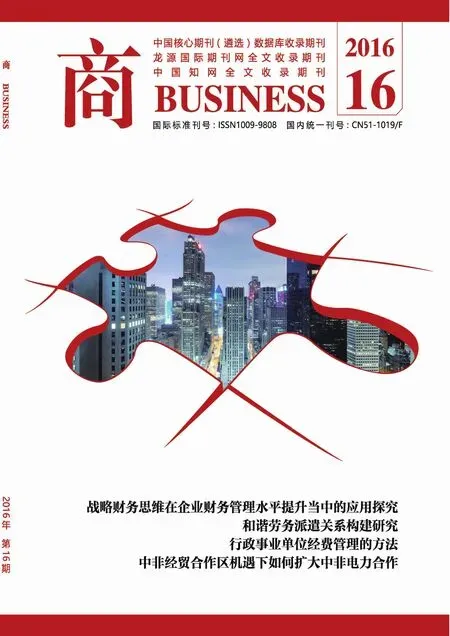全球视野下媒介素养的实践差异与概念辨析
2015-01-28范晓晨
范晓晨
全球视野下媒介素养的实践差异与概念辨析
范晓晨
摘要:在当今媒介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媒介素养”在处理媒介、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已为世界各国所认知。但是“媒介素养”在世界各地所推崇的理论概念和现实社会实践的方向既具有相似性也存在很大差异,若世界各地关于“媒介素养”概念体系的认知及其内涵界定的不统一会妨碍“媒介素养”的学科理论建设和长足发展。因此,本文一方面从横向全球视野来环视不同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从纵向脉络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实践的“媒介素养”相关概念之间的内涵与关系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关键词:媒介素养;实践;差异;概念;辨析
一、“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与背后逻辑
现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关于“媒介素养”概念提出的起源是英国的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及其学生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ampson),他们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文中主张通过教育来使得青少年能够辨别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那么,为什么利维斯关于文化批评的观点会被公认为是“媒介素养”概念提出的开端呢?“媒介素养”概念的思维逻辑是什么?从哲学上讲,唯物辩证法指出: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即,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①由此,欲探讨“媒介素养”概念的思维逻辑,需先结合英国的社会根源与现实状况。
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由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报业基于竞争的需要,开始迎合普通群体的需求,以“后院篱笆”即通俗娱乐化为原则尽可能的生产拥有“最大公分母”的报纸内容,以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而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界、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共同认为媒介的内容能够对人尤其是青少年产生“魔弹论”似的巨大影响。在自古希腊以来就拥有“批判精神”和“公共利益”概念的欧洲,尤其是英国,为了拯救陷入精神危机的国民,部分学者倡导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一立场和现实背景下,利维斯和汤普森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倡导以系统化的课程和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以抗拒大众媒介中“低水平的满足”。
由此可看出,在人们意识到“大众媒介的负面内容”能够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提出了“媒介素养”,并试图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抵抗媒介内容对受众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对所谓“大众媒介负面内容”的判定标准则是:“不符合当时当地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即“不符合当时当地社会所认为的人的精神发展方向和社会整体进步方向”。这也就是说,“媒介素养”概念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但是,也不免疑问“当时当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封建社会或专制化社会,政府牢牢把控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普通平民较少参与。而在现代化社会,“政治合法性”以国民价值认同为前提,此时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一个由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中上阶层人士与普通平民的共同协商与权力争夺的动态过程,即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社会,当普通人有了社会话语权和个人权利意识才开始产生关于“媒介素养”概念的讨论。因此,我们要辩证的看“媒介素养”概念的价值论体系,一方面,“媒介素养”概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权力阶层和中下平民阶层,具有个人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另一方面,“媒介素养”概念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传播活动不应被视为是一个线性的驯化过程而应是一个有机的协商过程。综上,“媒介素养”概念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扩充的概念体系,一方面“媒介素养” 概念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表现在不同的国家和时间维度下,“媒介素养”概念的内涵和侧重点会发生新的演变。另一方面“媒介素养”概念是经过有机协商之后的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其理论概念及相应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社会文化性。
二、“媒介素养”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差异
“媒介素养”概念发展至今已经有80多年,从英国开始逐渐扩展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媒介素养”属于人文社会学科体系,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断形成中的概念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和民主体制及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媒介素养”的理论概念与社会实践可能也要因地而易。但是对一个学科建立来说,如果世界各地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社会实践的侧重点差异较大的话会影响该学科的本体理论架构,从而破坏学科的长足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全球视野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素养”的实践做一个梳理。
首先从“媒介素养”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欧洲来看,目前欧洲已经接纳了一种关于指导信息社会的愿景,即采用系统的学校教育的方法来使得公民具备适当的“技能和能力”,而关于这些“技能和能力”的调查与评估指标的建立占据了欧洲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地位。尽管欧洲国家在地理上邻近,但是内部关于媒介素养概念的界定和实践方法则存在差异。
1.在欧洲大陆西北面的英国,虽然“媒介教育”概念的使用自1930年代之后一直在英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具体的媒介教育实践中,“媒介素养”被认为是媒介教育的核心目标,并且越来越被纳入政治领域的探讨活动中。虽然英国在媒介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强调个人技能和能力,但是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英国非常注重关于媒介的研究,强调公民对媒介整体的理解,其主要内容包括:媒介经济、媒介技术、媒介法律、媒介运行机制、媒介政治、媒介文化和美学。其中着力探讨媒体机构的属性、产业运作和生产机制以及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即便是与英国媒介教育合作的媒介机构也被纳入媒介批判研究范围,如英国电影协会和英语和媒介中心教育协会。
2.在中欧的德国,关于媒介教育所广泛讨论的概念不是“媒介素养”而是”媒介能力”,尤其是1971年由德国社会家哈贝马斯根据自己创立的“交往理性”理论所主张的提高人的“交流的能力”,这种关于“交流的能力”概念之后被Baacke引入媒介教育之中,具体指理解人类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象征能力。自1980年代之后,以“技能和能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概念也进入德国的部分公共讨论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及其与“媒介能力”之间的关系。此时,关于“媒介能力”的学术讨论则集中在理论建构的问题上。
3.在南欧的伊利比亚半岛,自1960年代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渐进入现代化,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开始寻求建立完善的教育系统,力求通过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随着计算机等新媒介展示出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葡萄牙于1970年代引入“ICT”素养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关的基础设施。西班牙自1985年开始在学术和政治领域讨论“ICT”素养教育,在这里西班牙政府主要是想要通过ICT素养教育实现建立信息社会的国家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欧盟关于“信息素养”的各种计划和项目。
其次,从北美地区来看,加拿大和美国都积极开展推广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活动,但是加拿大和美国虽然是相邻的两个国家,在媒介素养的发展历程上却有很大不同。美国的“媒介素养”相关研究开始较晚,1978年美国教育部举办研讨会强调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媒介素养在美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领域话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作了一个转换,即把“媒介素养”从欧洲国家的社会研究领域转移到教育领域,从“媒介素养”研究的社会文化性批判视角转变为不涉及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争辩的“能力”视角。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媒介素养”被划分为五个方面:“赋权”,“批判性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视觉素养”和“健康素养”。其中主要关注点“赋权”即属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范畴。
而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其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讨论开始较早,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中学就广泛开设了电影教育课程。1989年底,安大略省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7—13年纪的课程中,是北美地区第一个在中小学校开设媒介素养相关课程的国家。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John Pungente提出的“八大理念”为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框架。由于加拿大的“媒介教育”发展历程较为长久,因此新兴的“数字素养”也被纳入媒介教育概念的范畴里,认为“数字素养”只是“媒介素养”其中的一个方面或部分。
综上可以看出,在欧洲地区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较为深厚的英国和德国偏向于把“媒介素养”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公共讨论,不仅强调个人对媒介使用的技能层面,还主张批判性的看待媒介、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较晚的后起之秀中如芬兰、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则偏向于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媒介素养”,由政府主导致力于通过新兴的数字技术来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主要集中于全民的“数字素养”教育。而在北美地区,一向在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美国则把“媒介素养”纳入教育领域进行讨论,着力培养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和参与媒介社会的能力。其邻国加拿大的媒介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应对美国文化入侵,保护本民族文化为目的,发展轨迹仿照英国,更倾向于教授学生关于媒介的整体知识,侧重于对媒介信息的内容及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三、“媒介素养”的内在概念辨析
根据以上对世界范围内“媒介素养”社会实践的梳理和概括,从宏观横向角度可以得出“媒介素养”概念在一国所强调的侧重点和实践方向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国家有选择的进行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社会文化性的特征。那么,各国所强调的“媒介素养”相关概念的本体内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只有将这些梳理清楚才能从内在整体上系统把握“媒介素养”的概念体系,进而为“媒介素养”的学科理论建构和课程设置提供基础。因此,从微观纵向视角来看,有必要再从概念辨析的角度来界定“媒介素养相关概念的内涵”以及梳理“媒介素养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媒介素养”与“媒介能力”概念的内涵及关系界定
1.媒介素养:“media”在中国被翻译为“媒介”、“媒体”和“传媒”,但是这三个词语的侧重点不同,“媒介”在狭义上指一切大众媒介、如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指的是专业化的传播机构或组织,如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新闻网站等。“传媒”更倾向于指的是新闻传播这一新型专业或行业领域。由于媒体的范围过窄而传媒的概念又过于抽象,因此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媒介”一词,“媒介”是一个集合概念。“literacy”在英语中的本义为“识字”、“有文化”、“阅读和写作能力”,国内有“素养”、“认知”、“识读”等几种译法,其中“认知”、“识读”的范围过窄,“素养”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更多的指的是通过学习、训练和实践而逐渐积累获得的知识、技巧、能力和修养。“媒介素养”被作为“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界定在上世纪八十年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最终在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合并不同学者意见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Robb于2004年指出“媒介素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包括不同的阶段:“媒介意识、接触媒介、分析与评价内容、参与媒介活动与创作。”总的来说,鲁宾将“媒介素养”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知识模式、理解模式和能力模式。”
2.媒介能力(Media Competency):在英文中“competency”与“skill”都是指的技巧与能力,但是二者又有不同。“competence”:指能胜任某方面专长的能力,除却一些基础的技能,指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度的素质和能力;“skill”在英文中指的是技巧、技能、本领、技术,指通过学习、训练和实践能够拥有某一方面技艺来做某事。通过比较可发现“competence”更侧重于综合能力和胜任力。在德国,自哈贝马斯1971年提出“交往理性”,倡议提高人们的交流能力以来,德国一直在广泛讨论“Media Competence”。德国所讨论的“Media Competence”一直是将多元化的媒介及交往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之下,在此基础上来理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不局限于单纯分析个人与个人之间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和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一个伞状的概念体系,注重整体性。既包括基本的媒介使用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也包括更高层次的媒介创作与利用媒介参与社会能力。此外,还包括更抽象的关于媒体知识的理解和对个人与媒介社会之间关系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而“媒介能力”(Media Competence)强调个人与媒介和社会的融合所展现出来的更高层次和更具有综合性的能力体系。因此,“媒介素养”自身内涵之中包括“媒介能力”,“媒介能力”是“媒介素养”内涵中的一个高级层次,
(二)“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与“媒介素养”概念的内涵与关系界定
1.信息素养:早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i在给美国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中首次提出“信息素养”这一概念,以此指个人运用信息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后,信息素养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围绕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培养途径及测量评价等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目前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信息素养指标体系都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PL)制定的标准为参照,即认识信息、检索信息、评价信息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可以看出“信息素养”侧重于强调个人如何有效和高效的寻找、获取、判断有价值信息和构建自身信息知识框架的能力,即着力于人们如何在现有的信息提供机制下提高自身的信息筛选能力。不牵涉关于如何使用媒介技术进行制作与创造的能力,也不涉及关于媒介生产机制和文本分析方面的内容。
2.数字素养/能力:“数字素养”这一概念最早在1994年由以色列学者Yoram Eshet-Alkalai提出。1998年Paul Gilster在《Digital Literacy》一书中将数字素养定义为“检索获取网络资源,并加以应用的能力。”后来在2010年正式发布的欧盟八大核心素养里面,将“Digital literacy”一词改为“Digital Competence”,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在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地能力”。2011年欧盟实施的数字素养项目还建立了“Digital Competency”的内容框架,该框架包括信息、交流、内容创新、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5个“素养域”。相对于“Digital Literacy”,对“Digital Competence”的理解,从个人层面看,除了强调个人对数字技术的基础使用能力之外,还强化技术素养、技术设计、技术思维等高级技能;从社会层面看,不仅包括强调个人利用数字技术从事社会实践和交往的能力,还包括建立社会道德、法律等外部环境对个人数字技术使用的规范作用的责任意识等综合性能力。但总的来说,数字素养相较于媒介素养更偏向于对数字技术的功能性应用层面,缺少对媒介内容的批判性解读和对媒介产业运作的分析。
综上,首先“信息素养”包括对传统媒介信息和数字媒介信息的筛选和使用能力,而“数字素养”指的是对数字化媒介信息的使用和分析能力。因此“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延伸部分。此外,在数字素养内部,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用“数字能力”来代替“数字素养”)。
其次就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关系进行探讨,“媒介素养”注重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对大众传媒的理解和掌握,而“信息素养”更强调与信息处理相关的技能和学习能力。②相比于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立足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计算机网络等数字化新媒介,不仅包括对其特定媒介及其信息的接触和使用能力,还包括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媒介产业的内部运作和生产机制以及媒介文本的批判性分析,其涵盖面比信息素养更为广泛。而信息素养强调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有效信息的筛选和分类,侧重于学生关于基本媒介技术的动手实践能力。邵瑞教授也曾指出:“信息素养关注的是培养‘获取、传输、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所不同的是信息素养更关注‘技术和应用层面’,而媒介素养侧重的是‘技术背后的实质和理解层面’。信息素养只是多种媒介信息的一种,而媒介素养关注的是我们社会现存的各种媒介。” 因此,“媒介素养”包含“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属概念,“信息素养”是“媒介素养”的种概念。(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②宫淑红,张洁.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7),p25-26.
作者简介:范晓晨,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