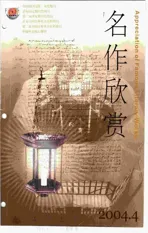左手“主义”,右手“问题”
——“天涯”体与韩少功创作关系初探
2015-01-28海南廖述务单正平
海南 廖述务 单正平
左手“主义”,右手“问题”
——“天涯”体与韩少功创作关系初探
海南 廖述务 单正平
《天涯》杂志的改版常为出版界、思想界所称道。这一事件对韩少功创作的影响则较少有人论及。应当说,“天涯”体与韩少功自身文体意识的强化,两者有互为生成的关系。“左手主义,右手问题”是“天涯”体的理念形态。“问题”须以“主义”为前提与立场,而“主义”则因问题意识有效去除了偏执的成分。20世纪90年代的韩少功,与道德理想主义有深切联系,因此被外界目为文学圈的“左派”。然而,问题意识常使韩少功非“左”非“右”,成为一个离队的异类。新世纪韩少功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新的视野。问题意识的强烈,使得这一道德关怀包含有更多制度创生的诉求。道德与制度的汇合,营构了有关公共正义的诗意空间。显然,道德与制度是“主义”与“问题”在新世纪的又一变体。
《天涯》 主义 问题 道德 制度
韩少功的文学观念与思想立场历来引人注目。这一方面因为其文学影响的巨大,再有就是其思想意义的含混与深广,往往招致阐释者争讼不已。有人批评他是写作的“追风少年”①,有人宣扬他是精神的“圣战者”②,也有人认定他瞻前顾后,太过保守③,抑或于新近更趋圆熟,规避问题④。这些评判都是基于特定前提做出的,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韩少功是一个实践型知识分子,完全撇开其“事功”去谈论所谓思想观念,盲视与误读可能难以避免。《天涯》杂志的改版是韩少功最为卓著的“事功”之一,其间的行为实践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不可轻估。分析这样的“事功”,有利于全面把握其思想的起伏与嬗递。应当说,“天涯”体与韩少功自身文体意识的强化,两者有互为生成的关系。“左手主义,右手问题”是“天涯”体的理念形态。“问题”须以“主义”为前提与立场,而“主义”则因问题意识有效去除了偏执的成分。
一
《天涯》这份刊物的独特性在于,它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同时有着强烈的介入意识。
它产生于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时发展主义甚嚣尘上,一种物质现代化的迷梦不只是笼罩着普通民众,许多知识分子也真诚地与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甜蜜的共谋关系。左翼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崩解与溃败,俨然昭示着“历史的终结”。《天涯》的创办人韩少功、蒋子丹等与其他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他们有意识地与市场化、发展主义的普遍价值观保持必要的距离,因为在这一意识形态背后依旧有着压抑性结构的存在。如何破除这一压抑性结构,成为《天涯》持之以恒的办刊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涯》确实秉持着一种理性的泛左翼立场。我们将其称作“左手主义”。《天涯》从来不学究,它将这一立场具体化为对市场化、大众文化、道德与人文精神、农村与贫困、集权腐败等中国问题的关注。这一问题意识可以称之为“右手问题”。左右开弓,才造就了《天涯》当时为人称道的标高与尺度。
形式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互为表里。《天涯》从一份偏于通俗的文学刊物演化为一个具有强烈介入意识的思想阵地,离不开形式上的彻底革新。当年,韩少功就坚决反对把《天涯》“办成一般的学报”,也就是说“不要搞‘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据他判断,凭依90年代新的再启蒙的大好语境,作家完全可以释放“挑战感觉和思维定规的巨大能量”。实际的操作表明,在形式方面这类文章于“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⑤。这一混合品种,在传统理论范畴中面临具体归类的难度,说成是理论小品、评论或学者散文似乎都可以,但又都不足以完全地概括它的特征。这些散文是文学和理论的完美结合,而不是侧重于某一方。我们不妨称其为“天涯”体。这一文体形式是沟通《天涯》与韩少功创作的桥梁。《遥远的自然》《货殖有道》《第二级历史》《文革为何结束》等颇具思想冲击力的散文,无疑与这一文体要求甚为契合。“左手主义,右手问题”作为“天涯”体的理念形态,自然也体现在韩少功自身的创作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韩少功有关社会、历史的问题意识并不强烈。这在其散文创作中最易窥见。80年代前期,韩少功的散文侧重于对自身创作的认识与总结,题材基本限于文学范围,如《学生腔》《留给茅草地的思索》《难在不诱于时利》《文学的“根”》等。访美的经历加上寻根的历练,促其视野渐趋宏阔,笔触也愈益老辣。作品《胡思乱想》可以看成这一时段的代表作。之后直到90年代初,韩少功与思想、理论展开了全面“遭遇战”,如《仍有人仰望星空》《米兰·昆德拉之轻》《海念》《灵魂的声音》等作品就呈现了这一特质。这一时段的韩少功与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人共享了许多逻辑前提,并且在观念上互为呼应,尽管前者对后现代主义投去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在此意义上,将韩少功目为道德理想主义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改版《天涯》前后,韩少功的问题意识日益凸显,“主义”依旧,但落到了实处,理想主义的执念无疑在淡化。他是《天涯》的编者,亦是作者,如发表其上的《完美的假定》《遥远的自然》《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等文,就对革命、环保、身份、民族等广受关注的问题有深入探讨。韩少功还曾为“特别报道”栏目写过一篇名为“观察亚洲金融风暴”的“示范文章”,目的在于抛砖引玉。遗憾的是,这一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⑥由此可见,当初韩少功的倡导有些曲高和寡。但于他个人而言,“天涯”体与自身文体意识的强化,两者间互为生成的关系相当鲜明,并对其后续创作影响至深。
二
当下思想文化界的“左”派,人员众多、声势浩大,已蔚为大观。这一群体鱼龙混杂,具体派系殊难区分。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刚告别极“左”思潮,其间与主流意识形态分分合合。当中多“右”的声音,而“左”的观念是几近于无的。90年代,市场、资本的兴起,最先在部分学者与作家那里引起了回响。其时,“二张一韩”(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的创作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相互呼应,影响甚广。于是,“二张一韩”几乎成了道德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并隐约地成为最早的一批文化“左”派。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深广的历史实践,对它的认知往往成为当下区分“左”与“右”的衡量标准之一。韩少功对“革命”的辩证反思在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写于1987年的《仍有人仰望星空》一文,对“红卫兵”“文革”有独到的看法。这些极“左”的东西,在当时的美国被千夫所指。韩少功依旧力图向他们阐明“文革”的复杂性,如红卫兵在何处迷失和在何处觉醒、红卫兵复杂的组织成分和复杂的分化过程、当时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响等。那时,仍有一些极“左”派在美国活动,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女孩在影院门口向韩少功他们散发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传单。女孩不理解“文革”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依旧对它满怀憧憬。传单上的“文革”式话语,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都有着滑稽的味道。但韩少功笑不起来,因为“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在举国一致声讨极“左”的时代,韩少功却毫不犹豫地为寒风中的理想辩护,随后被戴上“左”的帽子,似乎难以避免。
尽管如此,将“二张一韩”并置,仍旧是思想上的简单草率。这三人都对“理想”满怀敬意,但韩少功对待理想的方式与“二张”相差甚远。“二张”以笔为旗,发出灵魂之声,以坚决捍卫精神尊严,容不下任何犹疑与退却;相比而言,韩少功有一种参悟佛心的通透。⑦他曾言,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⑧这种看透与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就演化为一种理性的怀疑精神。或者说,没有任何先天的立场可以为主体提供永恒的精神庇护。因此,有评论家指出,韩少功所肯定的东西远不如他的否定对象那么明晰。在他的文本中也偶尔出现“圣战”这样的字眼,但即便是这样,更多的依旧是出击,而不是坚守。⑨难怪张承志批评韩少功滥用宽容,思想“灰色”,以至于恨不得在他屁股上踢上一脚,从而让他冲到更前面一些。⑩
韩少功热衷的“天涯”体使得他与“二张”之区分更加鲜明。针对道德理想主义,郜元宝曾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在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许多文章中,除了抽象地抨击人类千古皆然的道德缺陷外,实在读不出别的什么,看不出某种道德理想状况和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之道的因果联系,看不出由过去农业组织体系构型的意识形态向现今商业组织体系构型的意识形态转换过程中,人们切实的道德的迷惘与理想的挣扎,也看不到在这过程中重建道德理想体系时必须面对的资源与误区。他们的批评不可谓不激烈,却总显得不着边际,而当他们正面阐述自己的道德理想时,又含混其辞,不知所云,除了空洞的叫喊,委实听不出叫喊的实在内容。”⑪这一批评略显愤激,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指出了道德理想主义所存在的部分缺陷,即回归抽象德性,而相对漠视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
韩少功在亲近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对刺心的社会问题投注了莫大的阐释热情。这时,“问题”对于狂躁易热的“主义”具有解毒的作用。比如《完美的假定》一文,是韩少功发表于改版后《天涯》的一篇最早的长篇随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这是韩少功唯一一篇直接谈论“理想”的文章。它直接切入的正是当代社会历史核心的话题——革命。缅怀革命者,在此最期待韩少功引吭高歌,以彰显义无反顾的“理想”姿态。遗憾的是,他笔下的“理想”典型竟是两个在具体政治选择上迥然相异的人:一个是激进的“左”派格瓦拉,一个是决绝的右派吉拉斯。他认为,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无疑,只有返归历史,以革命为“问题”对象,并直面具体的人,才能对“理想”有较为深邃的辩证理解。
三
新世纪的韩少功,又开始重提“道德”这个频遭流放的词汇。⑫人们已经惯于将他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当这个词汇再次出现时,并不感到离奇和诧异,因此关注者很少。至于“道德”与他新近的创作有何关系,更成了批评话语中的语义空缺。如前所述,郝庆军等热心的批评者就认为,韩少功热衷于隐者的诗意以及圆熟的技巧,反倒渐渐遗忘了锥心的社会问题。韩少功是不是真成了不问世事的“闲达”呢?这还是得从“道德”潜含的语义谈起。
“道德”在新世纪的韩少功那里,有点近似于奉行的“主义”。如果“问题”缺失,诚难避免成为郜元宝所说的新世纪“道德理想主义者”。所幸,韩少功对政治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均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与戒惧。他认为,人类社会也许永远是带病运转,动态平衡,有限浮动。人们努力的意义,不在于争取理想中最好的,而在于争取现实中最不坏的——这就是现实的理想、行动者的梦。⑬“争取现实中最不坏的”表明要立足当下,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想的观念着手。这就可以预防理念带动的运动/暴力式结构大错动。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好办法,不能代替制度建设和管理发育。暴民的动乱与暴政的乱动,无一不是祸端。⑭因此,新世纪的韩少功重提道德,最终意图还是在于社会的改善,即正义社会的建构才是他这个“行动者的梦”。如罗尔斯、桑德尔等人一样,韩少功笔下的正义社会是道德与制度双向建构的社会,两者融汇,才有真正的“正义”可言。社会的改善、制度的创生,正是韩少功在新世纪关注的核心“问题”,它与道德一起,成为“天涯”体“问题”与“主义”的又一变体。
当下道德危机有目共睹。在韩少功看来,要改观这一现状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社会精英要有更多担当。这一阶层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因此更应该克己节欲、先忧后乐。这种道德责任等级制可以构筑一个屏障,延缓危机到来。⑮其二就是走相反的路,礼失求诸野。这一诉求在韩少功新世纪创作的部分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怒目金刚》中的吴玉和就是乡间仁者形象,他所誓死捍卫的正是最起码的人伦规范:不能背天理,不能仗势欺人,官再大也要尊贤敬长等。小说呈现了一个略带理想色彩的礼俗道德自足系统——它既经受住了商业化的考验,也从容应对了现代官僚系统的胁迫,并在关键时刻有效击溃权贵。在《赶马的老三》中,何老三对何子善的袒护,对两个没大没小的警察的惩戒,均表明对人情伦理的捍卫甚至超过对法理的遵从,尤其在后者往往偏袒于强者的时候。
在乡村,礼俗、人情往往比现代性规章制度更能规训与约束具体个体。或者说,当制度阙如的时候,礼俗道德往往会起到替代性的治理功能。卢梭的话依旧富有意义:在乡间,血缘、人情织成了一张网,乡民之间的生活相对透明,这就构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范与监控。礼俗社会较之于法理社会显然更符合卢梭的理想。现代法理包含了更多的身份异化,因缺乏血缘、人情的沟通,其中的个体必须通过名望和财富等扭曲方式来表现自己。中国乡村也近似于此。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凡事讲血缘亲情,而不是组建理性冰冷的契约关系。于是,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通常成为自然的文化选择。⑯《白麂子》中,因果报应的情景剧也许有点装神弄鬼,抑或有点过于戏剧化,但它并非空洞无凭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地有着乡土社会观念的基础。其中,最有趣味的当是李长子在医院院长面前的一通“牢骚”:“这科学好是好,就是不分忠奸善恶,这一条不好。以前有雷公当家,儿女们一听打雷,就还知道要给爹娘老子砍点肉吃,现在可好,戳了根什么避雷针,好多老家伙连肉都吃不上了。”这一抱怨从反面说明,传统的礼俗道德有着强大的整饬人伦的力量。科学,正如卢梭所言,正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西江月》中的流浪汉龅牙仔,地位卑微,形同乞丐,但他绝不做坑人害人的勾当,而且对这类行为深恶痛绝。为了替姐姐报仇,他经历了无数劫难,最终与仇人(一个为富不仁者)同归于尽。这里也见出了法理社会的深层局限,龅牙仔显然连一个律师也请不起,只能在反法理的暴力行为中完成道德人的悲怆涅槃。
那么,韩少功是不是和卢梭式的反启蒙主义者或道德理想主义者一样,意图在礼俗道德与制度之间确立一种对立关系呢?显然,他更青睐罗尔斯式的论断:“离开制度来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使本人真诚相信和努力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的牧师而已。”⑰在韩少功看来,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除了量化管理与加强制度建设以外,还须强化道德担当。因为,即便有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权力的管理量与支配度永远不可能降为零,这就需要道德的规约来进一步化解权力风险。这就有了一个权力制约公式:管理量×支配度系数×道德系数=危险权力。⑱要节制危权量,就须从管理量、支配度系数、道德系数等三方面着手。显然,在其他众多制度设计者那里,鲜有将“道德系数”列为重要的权衡变量的。
显然,道德与制度之融合是“左手主义,右手问题”在新世纪的又一变体。有论者曾批评韩少功在政治上过于保守,在对劳动和资本之关系的思考上、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拿不出自己坚定的信念。⑲这一批评显然以误读韩少功之“主义”为前提,将他当成了激进的“左”派。“主义”与“问题”并举使韩少功看似既“保守”又“激进”:貌似“保守”,因他信赖制度创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倡导一种威权性质的道德(礼俗)社会;近似“激进”,则因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疑虑重重,并对道德理想满怀敬意。在他这里,做一个“资”或“社”的强制性站队,顶多是智力上的偷懒行为。
①萧三郎:《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新京报》2005年10月21日。
②孟繁华:《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韩少功90年代论要》,《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③鲁枢元、王春煜的《韩少功小说的精神存在》(《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与李光龙、饶晓明的《试论“寻根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表现》(《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两文,均认为韩少功的创作有着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周展安在《翻过这沉重的一页——阅读作为政治寓言的〈第四十三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韩少功新世纪的创作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与其“左”派的身份完全不符。
④参见郝庆军提交海南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的论文:《韩少功晚近小说创作的新成就和新挑战》。
⑤⑥⑩韩少功:《我与〈天涯〉》。
⑦廖述务:《德性生存:韩少功新世纪创作的重要面向》,《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⑧韩少功:《看透与宽容》。
⑨南帆:《诗意的中断》,见《敞开与囚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⑪郜元宝:《容易失去的智慧:关于“道德理想主义”》,《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⑫⑮韩少功:《重说道德》。
⑬⑭⑱韩少功与笔者通信内容。
⑯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读书》2001年第12期。
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⑲周展安:《翻过这沉重的一页——阅读作为政治寓言的〈第四十三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本文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思想与中国镜像——《天涯》(1996—2010)话语分析”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NSK11-45
作 者:廖述务,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单正平,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