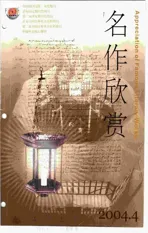哈姆雷特:“延宕”,还是“等待”,问题所在(下)
2015-01-28北京
北京
傅光明
哈姆雷特:“延宕”,还是“等待”,问题所在(下)
北京
傅光明
本文是《哈姆雷特:“延宕”,还是“等待”,问题所在》的下半部分,从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出发,直指人性深处的弱点。此外,文章还对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时代背景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对一些问题做了较为有趣的解答。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延宕 等待
“我”:一千分之一个“哈姆雷特”
“有一千个读者(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照这句话,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千分之一个“哈姆雷特”。这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躲藏在灵魂深处的自己。如法国史学家丹纳所说:“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不仅感受到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还感受到许多我们所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他具有不可思议的观察力,可以在刹那间看到一个人完整的性格、体态、心灵、过去与现在,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与深度以及剧情所需要的准确的姿态与表情。”简单说来,就是因为莎士比亚看透了我们,无论是他那个时代的“我们”,还是今天的以及未来不断延续着的“我们”。不是吗?从人性上看,莎士比亚所挖掘的伊丽莎白时代人性上的龌龊、卑劣、邪恶,并不比“我们”现在更坏,而今天“我们”在人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尊严、悲悯,也不见得比那个时代好了多少。
德国作家歌德(Goethe,1749—1832)曾说:“当我读到莎士比亚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首次读完他的一部作品, 竟觉得自己好像原来是一个先天的盲人,而在此一瞬间双目才被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视力。莎士比亚对人性从一切方向上、在一切深度和高度上,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极为深切地体会到我的生活被无限扩大了。对于后起的作家来说,基本上再无事可做了。只要认真欣赏莎士比亚所描述的这些,并意识到这些不可测、不可及的美善的存在,谁还有胆量提笔写作呢?”
包括歌德在内,没有作家会因此放弃写作。然而,歌德简单地认为,莎士比亚是要在《哈姆雷特》一剧中“表现一桩大事放在了一个不堪重任的人身上”。哈姆雷特是一位可爱、纯真、高贵、道德高尚的青年,却缺乏英雄气概。
是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哈姆雷特。歌德认为他软弱,在英国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眼里,哈姆雷特则是一个耽于冥想的人,有伟大的目标,却在从不付诸行动的“延宕”中幻灭了。英国著名莎学家安德鲁·布拉德雷(Andrew Bradley,1851—1935)认为,是哈姆雷特的忧郁害得他最终一事无成,也就是说,忧郁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核心。哈姆雷特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思考加重心理的忧郁,忧郁加深对行动的剖析,而反复思考、剖析之后又不付诸行动,再次加重、加深了忧郁。因此,他只能用装疯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同时也可以自我保护,并求得暂时释放心理重负。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无论莎士比亚还是他的哈姆雷特,以及“我们”的哈姆雷特,都是那个历史与时代的产物。
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历史:1558年11月17日,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她已经是一个新教徒。但在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执政时,她不得不使自己像一个天主教徒。当玛丽病重时问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发誓说,如果自己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就叫她天诛地灭。刚即位时,她一方面再次申明了新教观点,同时似乎也还显示出是一个天主教徒。但首先,政治家的头脑已使她在会见丹麦国王和信奉新教的德国使节时,明确表示自己是新教徒。她无疑更倾向于新教,而对玛丽女王时期的天主教会深恶痛绝,但作为一国之君,她当然希望能够代表国家以一种稳妥的方式解决分裂、对立的宗教问题,并要竭力避免国家因宗教而走向分裂。于是,当时的国家利益以及整体混乱的宗教状况,便将一种两难的处境天然地、无可选择地降临在了女王头上:玛丽在位时,她曾明确地表示要尊奉天主教礼仪;支持她继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是一位强硬的天主教徒。可是又再也不能让刚刚过去的“血腥玛丽”一幕重演,当然,她更不能允许罗马教皇的神权大于王权。她深知,她绝不能背叛长期支持她的新教徒,但她又必须在坚持让英格兰教会独立的同时,不能让新教改革走向极端。那同样是可怕的,一是因为当时英格兰还是天主教徒占多数,而且势力强大,后曾多次与西班牙国王联手,试图推翻她的统治;二是她并不喜欢“血腥玛丽”时那些义无反顾接受火刑的新教徒。她通过王权的力量将前文提到的中和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安立甘教派”确定为英格兰国教,这是她为自己树立的新形象,同时也是英格兰的新形象。她要让臣民明白,宗教是要给人民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
在那样的一个宗教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代,无论位于权力之巅的女王,还是在女王治下写戏的莎士比亚,以及无数普通的,尤其以前信奉天主教的平民百姓,都存在着一个基督徒身份的转换与认同问题。或许当女王和莎士比亚面对矛盾与纠结的两难选择时,在本质上与哈姆雷特的“延宕”“迟疑”是一样的。
关于莎士比亚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清教徒,莎学家们的看法似乎从来没有统一过。在此,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从当时的清教徒瞧不起写戏这个职业本身来看,基本可以推定一生都在写戏的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清教徒。但在伊丽莎白时代,慑于王权的威严,至少他不能是一个公开的罗马天主教徒,而必须是一个信奉圣公会国教的新教徒。而对他的宗教背景势必产生深刻影响的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一个是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1531—1601),一个是他在文法学院读书时的老师西蒙·亨特(Simon Hunter)。另外,同时代比莎士比亚年长的威尔士主教,同时也是学者的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1505—1581),也认为在年轻的莎士比亚身上沾染了“可恶的天主教徒习气”。因此,他应该是一个仍然在心底存有天主教信仰而在宗教观念上已经被马丁·路德化了的英格兰圣公会新教基督徒,这跟他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模一样——哈姆雷特在心底应该还相信有炼狱,但他的宗教观已明显经受了马丁·路德母校威登堡大学的洗礼。从这点来看,莎士比亚写的哈姆雷特,当然不是中世纪的丹麦作家、史学家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1150—1220)《丹麦人的业绩》(H istoriae Danicae,英文为Danish H istory,译为《丹麦人的历史》)一书中那个从时间上看肯定是12世纪以前的丹麦英雄,也不是任何一个流行于当时的“原型《哈姆雷特》”旧剧里的复仇王子,而是一个在政治上王权更迭(从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女王到伊丽莎白女王),宗教上变革、分裂、整合(从罗马天主教、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到英格兰圣公会),军事上开始成为欧洲第一强国(1588年7月,英格兰海军以弱胜强,打败了号称世界第一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莎士比亚开始写作最早的十四行诗)的英格兰的历史大时代之下,外在看似“复仇”,而内心却在沉思和叩问生命意义到底为何的孤独者。
他软弱吗?在该行动的时候,他犹豫不决吗?似乎是的,因为“我不知是出于畜类的健忘,还是由此而导致了顾虑重重、怯懦畏缩,因为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也有方法立刻动手,却还只是空喊着‘要做这件事’”。
但当他决心利用偷偷修改后的国书借英格兰国王之手,处死那两个令他讨厌的谄媚者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坦恩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残忍,至少在形式上并不亚于他的叔叔,那个邪恶的克劳迪斯。如他对霍拉旭所说:“我以国王的名义给英格兰王写了一封言辞极为恳切的信,说既然英格兰甘愿向我丹麦称臣纳贡,既然两国情谊如枝繁叶茂的棕榈,既然和平女神永远戴着她那顶麦穗的花冠,将两国的和睦友好紧紧相连,总之,诸如‘既然’如何如何的重大理由我写了好多,然后恳请他读完此信,不容迟疑,立即将两个递交国书者处死,连忏悔的时间也不许给。”
这仅仅是哈姆雷特的矛盾吗?似乎不是。当然,这也是一些学者经常提到的剧中的“哈姆雷特问题”之一:他何以不对克劳迪斯立刻复仇,却对这两个小人物毫不手软地痛下杀手,而且“连忏悔的时间也不许给”,即意味着要让他们遭受炼狱的煎熬?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哈姆雷特显然是要在复仇的瞬间,让克劳迪斯直接堕入地狱的无底深渊。从这一层来看,他对那两个昔日的同窗、今日国王的宠臣,虽然是立刻要他们死,但让他们先进入炼狱,已经算是厚道了。
他忧郁吗?在该惊醒的时刻,他畏首畏尾吗?当他把一切,包括他的装疯和复仇的誓愿向母亲和盘托出以后,对母亲毫不留情地说出了像带刺的钢鞭一样抽打灵魂的斥责:“我当然管不住那个肥胖的国王再把您引到床上去,然后放荡地拧您的脸,管您叫他的小耗子;我也管不住您因得了他一两个脏兮兮的臭吻,或者被他那该下地狱的手在脖子上抚弄,就把您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告诉他我并没有真疯,而只是装疯。您最好还是告诉他;因为有哪一个美貌、清醒、聪明的王后,会把这么紧急的大事故意瞒着,不去告诉一只癞蛤蟆、一只蝙蝠?谁会这么做?”这时,他似乎不再犹豫,更不再忧郁。
马丁·路德以为,忧郁和“所有侵扰人类的弊病”都是魔鬼制造出来的,魔鬼“不愿看到任何一片草或叶子成长”。魔鬼只热衷于破坏,使人遭受痛苦,挑唆争斗,“恶毒到沉醉在别人终日的饥渴、痛苦和不足中,以别人的不幸为乐,以犯下杀戮与背叛的罪恶,尤其以对那些对任何人都无伤害的生命为乐,这就是邪恶的魔鬼最极端的暴怒。人类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的”。毫无疑问,莎士比亚要通过哈姆雷特表明,是魔鬼造成了哈姆雷特的忧郁。哈姆雷特对此也十分清醒,就像他在与雷欧提斯比剑之前所说:“要是我做过什么伤害了你感情和荣誉的事,激起了你强烈的反感,我在此声明,这都是由我的疯狂所造成的。哈姆雷特会做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吗?哈姆雷特永远不会。假如哈姆雷特在精神失常时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那不能算在哈姆雷特的头上;哈姆雷特概不承认。那是谁干的呢?是他的疯狂。既然如此,哈姆雷特也是受伤害的一方,疯狂成了可怜的哈姆雷特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只能是魔鬼撒旦。
他觉得自己有着完美的品德,在行为举止上无可挑剔吗?在第三幕第一场中,他对奥菲莉亚说:“我虽自认并不算一个本性很坏的人,可我也还是做过些该诅咒的坏事,既然如此,母亲最好没有生我。我很自傲,报复心强,有野心,随时可以做出许多叫不上名字、想不出样子或没有时间实施的坏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匍匐于天地之间,能有什么用?”当他亲眼看到血气方刚的福丁布拉斯所率领的挪威军队,敢以血肉之躯“去迎接命运、死亡和危险的挑战”,他深刻认识到,“不到危急关头不轻举妄动,的确是一种伟大;但当荣誉攸关之时,寸土不让,寸利必争,也是一种伟大。可是我呢,父亲遭残害,母亲受污辱,却要让理性和血性激起的复仇的亢奋呼呼大睡吗?再来看看这两万视死如归的战士,为了那一点点虚幻、骗人的名誉,走向坟墓,就像是要去就寝安眠;他们只是为了那一小块土地誓死而战,那块土地小得都不够用来做交兵的战场,甚至不够做坟墓来埋葬他们的忠骨,我能不感到羞愧吗?啊!从这一刻开始,让我的思想充满嗜血的残忍,否则我就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废物”。他是要让那“不轻举妄动”的伟大,变为一种在行动上真正的、实际的伟大。
然而,他十分清楚,这样的伟大,一定要在上帝的名义下来完成。就像克劳迪斯试图强迫自己祷告时所说:“如果一个人的手里还留着通过罪恶攫取来的东西,他可能被赦免吗?在这个充斥腐败的世界里,镀了金的邪恶之手可以一下子将正义推开;因为那份罪恶的利益,常常可以贿赂法律,使之形同虚设。但天庭并非如此,到了那里,任何事情都甭想蒙混过关,一切所作所为的本相都被显现,我们甚至必须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作证。”
这显示出,伊丽莎白时代秘密的天主教徒们,对不经忏悔的突然死亡仍然充满了恐惧,因为在尘世留下的每一个污点,死后都要在炼狱里烧净。因此,也就能够理解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曾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在耶稣会于信徒们中间传阅的《心灵的遗嘱》上签字,这份遗嘱正是为了消除这样的恐惧。他的父亲期冀亲朋好友能通过神圣的弥撒帮助他死去的灵魂在炼狱的磨难中超生。而在伊丽莎白时代,任何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仪式,都是绝对禁止的。
所以,关键的问题,又回到了生与死。莎士比亚在第五幕第一场所增加的“原型《哈姆雷特》”所没有的发生在墓地的新戏,堪称精彩的神来之笔,也是诠释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生命孤独者思考生与死的点睛之笔。当他看到掘墓人手里的一个骷髅,说:“现在这蠢驴手里摆弄的也许是个政客的脑袋;这家伙生前可能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政客。”“从这命运的无常变幻,我们该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了。难道生命的成长只为变成这些枯骨,让人像木块游戏一样地抛着玩儿?”
现在,再回头看哈姆雷特在第二幕第二场时,面对着受克劳迪斯委派前来刺探他内心隐秘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坦恩,他坦诚地表示自己百无聊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心绪是如此的郁结,以至于在我眼里,这承载万物的美好大地,不过是一处贫瘠荒芜的海角。”接着,他说了那段著名的独白:“人类,多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啊!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无穷的能力!仪容举止是多么的文雅、端庄!在行为上,是那么的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又是那么的像一尊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不错,他极力赞美了人类自身。但他思考、反问的是:“这个尘埃里的精华算得了什么呢?”今天,一个生命的孤独者,同样会做这样的思考,同样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宇宙和万物的无限时空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粒尘埃。或者,换句话说,人类中的思想者一定是孤独的。哈姆雷特并不孤独,我们会时时与他相伴。
几个谜语一样的小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轻松地来说说莎士比亚留下的几个谜语一样的小问题。
有人问,莎士比亚写了不少故事发生地在国外的戏,他出过国吗?终其一生,他从未出国旅行。不过,以《哈姆雷特》为例,里边只有两个戏剧人物取了丹麦名字——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坦恩,他并未想过要再现丹麦宫廷。剧中的宫廷和大臣,全是英格兰的。莎士比亚剧团多次进宫演出,他也结识了许多朝中大臣,包括埃塞克斯伯爵、南安普顿伯爵,他对如何写宫廷,自然不陌生。
“哈姆雷特问题”困扰着众多的莎学家和不计其数的读者,不过,其中的许多问题却也不是莎士比亚故意留下来的。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以及剧情的一些矛盾,是由于版本的修改自然产生的。因为莎士比亚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一份手稿,或他自己认可的版本。
哈姆雷特的年龄多大才合理?霍拉旭是哈姆雷特最亲密的朋友,为什么到丹麦参加已故国王的葬礼,几乎是一个月后两人才见面?如果霍拉旭并不了解哈姆雷特所揶揄的丹麦宫廷的狂歌纵酒,那他仅仅是哈姆雷特威登堡大学的同学吗?第一幕中几个人共同目睹的幽灵,到了第三幕,为什么只有哈姆雷特能看见,而王后看不见?
这些同“哈姆雷特为什么不立刻复仇”这样的核心问题相比并不十分重要的小问题,应都是因莎士比亚自己“改编”造成的。从版本上来看,《哈姆雷特》有两个四开本,一个是1603年印行的“第一四开本”,一个是1604年印行的“第二四开本”。前者可能更接近最初演出时的演员脚本,但因它是未经莎士比亚认可的“盗印版”,莎士比亚对此十分不满,便大加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许多昭示人物心理特征的大段独白。正像梁实秋在《哈姆雷特问题之研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假如莎士比亚从没有改编第一版为第二版,则哈姆雷特问题根本不致发生,即使发生亦不致若是之复杂。”“哈姆雷特问题是随着莎士比亚的改编剧本而起来的。”“所谓哈姆雷特问题者,所谓哈姆雷特之谜者,不过是起源于莎士比亚编剧时之疏误而已。”
庆幸的是,尽管莎士比亚来不及对由改编而自然产生的诸多矛盾做统一的调整、梳理,但多亏他的这一修改,才使哈姆雷特成为了哈姆雷特。假如此时已在写作《麦克白》的莎士比亚对修改《哈姆雷特》稍有疏懒,不愿分心,而是默认了那个第一四开本,“哈姆雷特问题”或许不存在了,却会给后世带来一个永远的缺失,即哈姆雷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哈姆雷特。或许,他也就得不到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1811—1848)那样至高的赞誉,他把《哈姆雷特》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人类所加冕的戏剧诗人之王的灿烂王冠上一颗最辉煌的宝石”。
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位叫威廉·莎士比亚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连他的基本生平都难以说清楚。我们知道,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生意的杂货商,1565年任斯特拉福德镇的民政官,三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少年时在当地的文法学院读书,十三岁时家道中落,此后辍学经商,二十二岁前往伦敦,在剧院工作,后来成为演员和剧作家。由于他没有大学学历,更非名校出身,在他写作之初,也曾受到当时把持剧坛的出身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的贬低,甚至嘲讽,他们瞧不起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难怪剑桥大学出身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 ilton,1608—1674)会在1632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二对开本所附的颂诗中,写下这样的赞誉:
他,一个平民的儿子
登上了艺术的巅峰,
创造并统治着这个世界。
……
他善于用神圣的火焰,
把我们重新塑造得更好。
作 者:傅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