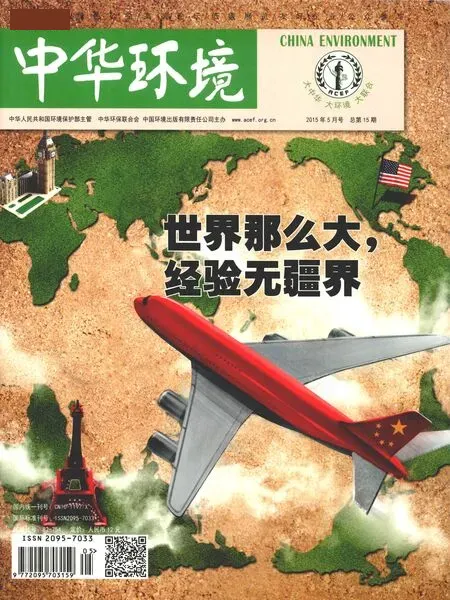“天人感应”没有国界
2015-01-27张华强
张华强
“天人感应”没有国界
张华强
面对大自然对人类超越分野的惩戒,我们虽然不必纠结于将责任归结于某一个人身上,但绝非表明无人对此负责。
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近日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然意味着中华生态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文中所列举的生存智慧之一“天人合一”背后,有一种天人感应说就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联系到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臭氧层耗损与破坏等等全球环境问题,可以找到对应的现代版。当然,这需要以超越国界的视角,予以唯物主义的解读才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超越“分野”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可以将其理解成人与大自然要和平共处。作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键在于“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孔子《春秋》中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其说固然奇伟怪谲,但决非无中生有。汉代董仲舒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吉凶祸福,虽说是一种迷信,但他也力图给予物质的解释,认为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
由于历史的局限,诸子的天人感应说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则告诉我们,由人类活动作用于环境而引发的、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变暖等问题不容忽视。这则是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新版天人感应:如果人类藐视生态规律,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在我们今天看来,天人感应有一个软肋在于分野说。古人依据二十八宿的天文观察把天分为二十八个天区,分别与各州郡邦国对应,特定天区所发生的天象变化预示着地上特定区域的吉凶,与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的执政状况相关联。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国就是“天下”。比如心宿是当时宋国的分野,在宋景公三十六年,火星迫近心宿,即“荧惑在心”。这被解释成是宋国君主要遭受灾祸的预兆,因而使宋景公感到害怕。而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则告诉我们,环境恶化超越国界,比如多瑙河的跨国污染、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所导致的欧洲环境问题等,其影响范围均超越了本国的“分野”。而上天对人类惩戒的感应更是全方位的,比如臭氧层的被破坏。
臭氧层的被破坏所带来的地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等,作为大自然对人类滥用制冷剂氟利昂的感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氟利昂分子被紫外线打开化合键释放出氯离子的一个原子,足以催化破坏10万个臭氧分子。英国气象学家法曼等人在1985年8月布拉格会议上展示的第一张南极臭氧空洞卫星图像表明,其“塌陷”面积超过了美国领土。面对大自然的这种对人类超越分野的惩戒,我们虽然不必纠结于将责任归结于某一个人身上,但绝非表明无人对此负责;恰恰相反,“天人感应”,人人有责。
约束“任性”
天人感应理论的提出,最早是出于政治思维。在大一统的封建专
制体制中,皇帝在人间的权威至高无上。然而,既然皇帝以“天子”自居,那么他至少应当对“天”心怀敬畏。当时的学者作为体制内外的臣民,针对严重的社会弊端,提出拨乱反正主张的相对稳妥的办法就是把老天爷抬出来,以约束最高统治者的“任性”,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和推行变革主张。在古人看来,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子违背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孔子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除了改弦更张,没有捷径可走。董仲舒从墨子的天罚理念出发,提出了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那是在倒逼“天子”反思。反思体制者的行为方式、所推行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对人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等等。
约束最高统治者的“任性”,也有规律可寻。古时候以农业立国,对天气的依赖性比较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需要按照生态规律办事,比如不违农时等等。这就在客观上强化了环境意识,有助于人与环境之间进行和谐共振式的感应。如同荀子所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相反,如果国君不能“正刑与德,以事上天”,就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大自然的“谴告”就难以避免。
应当看到,天人感应说所虚构出来的天的至高无上权威,最终还是为了用来强化人间皇权。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对法制建设不以为然,还对科学技术的争鸣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如果说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说的完善在客观上构成了生态文化的一个基础,那恰恰是从体制外看到了皇权“任性”的弊端。汉武帝最终采纳董仲舒的一些诉求,说明体制外的呼声不可小觑。在当代的全球环境保护中,这种超越体制的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中非政府组织(NGO)的活跃,要比像董仲舒那样以个人的学识来约束体制内的“任性”要有力的多。
健康“承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大自然对人胡作非为的谴告不像君主对臣民的斥责那样明显,是潜在的,而且有滞后性:“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无声,潜而无形也。”这种情况叫做“承负”。承负是前辈后辈之间的关系,即“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前辈行善,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等等。今人承担先人善恶所带来之后果为之承;今人善恶后果对后世之影响为之负。从天人感应的意义上讲,这不仅超越国界,而且跨越代际。解决超越国界的环境问题,不能只顾眼前过得去,必须考虑给子孙留下什么,把更美好的地球“还给”子孙后代变得刻不容缓。
按照天人感应说中的积极意义,在大自然的谴告面前,解除环境“承负”之厄的出路在于担当。既不能以邻为壑,又不能听任绥靖主义蔓延;只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就能得到“上天”的积极回应。上面提到的宋景公在“荧惑在心”的谴告面前勇于承担的“三善言”,就将“上天”感动。当宋景公正在为上天显示国君当亡之兆而忧愁之际,有位大臣表示可以“作法”将灾祸转到宰相身上,宋景公以“宰相为手足股肱”为由拒绝。大臣则说可以“作法”将灾祸转到百姓身上,宋景公则强调“国君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大臣又表示可以“作法”用一年的灾荒代替对国君的惩罚,遭到宋景公的痛斥。这种凛然正气使得“在心”的荧惑移动三度,为宋景公延寿21年。
当代人健康的“承负”当然绝非像宋景公有几句善言就可以搞定那样简单,需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偿还前一代人的环境欠账,努力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链条;另一方面,不仅不能再形成新的环境欠账,而且要致力于造福子孙的生态保护工程。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面前,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今天的环境污染有不少是他们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追求工业化留下的隐患,作为“原始积累”的继承者,理应为此买单。如果说今天的环境问题与昨天发展的不平衡有关,那就应当解决好今天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即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跨越式发展,不能再重复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环境问题的超越国界不能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否则那就会在天人感应的“谴告”泥淖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