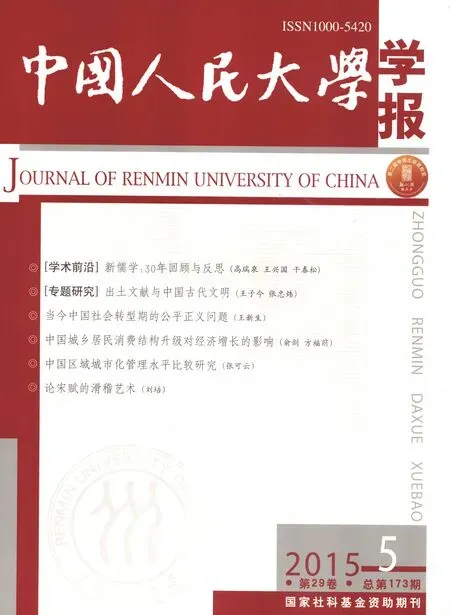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
2015-01-23王新生
王新生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
王新生
我们对当今中国公平正义问题的考察,总是习惯于将西方以稳态的现代社会为基准而建构的正义理论作为参照。这种考察方式没有充分考虑转型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特殊性。合理的伦理论辩不仅要考察支撑正义原则的社会条件,而且要考察正义原则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仅仅对正义原则进行道德论辩。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根源于平等价值取向与公平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这一冲突和张力不可能被消除,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在公平与平等之间达至某种平衡。为此,不仅需要保障公平正义的国家制度的建构,而且需要社会自我救治机制的生长与完善。
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伦理论辩
如今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转轨,而是复杂的社会转型。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但这种经济体制转轨只是社会转型的始发环节,整体的社会转型远未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会继续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经济的发展也将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但却不会自动消除这些问题。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交往体系的形成,即依赖于一个能够为公平正义提供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未来中国是否能够形成这样的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到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因而决定着改革开放是否能够取得全面成功。
一、社会转型期:一般正义理论的盲区
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是高度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与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考察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不仅需要诉诸正义原则的道德论辩,而且需要将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重要的变量予以关照。如果说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的持续性变化,那么,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是指具有质的差异的两种社会模式之间的转化。因此,社会转型期是社会变迁的特殊时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两种社会模式的交错点,是新旧两种社会结构的重叠区,它本身不属于任何一种具有稳定结构的社会类型。
然而,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正义理论却是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分析之上的,它以具有稳定结构的“稳态社会”为考察对象,因而无法把握变动不居的“转型期社会”,无法对其公平正义状况进行分析和刻画。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罗尔斯,哲学家们建构的正义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致力于根据特定的交往关系模式论证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在这里,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具有稳定结构的稳态社会即是具有稳定交往关系模式的社会,而特定的公平正义原则正是用以规范特定模式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因此,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必将导致公平正义原则的相应改变。这意味着,旧有的交往关系模式已经失去效能而新的交往关系模式尚未形成的社会转型期是一般正义理论的盲区。
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对应于不同的政体自然就有了不同的社会基本结构和与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虽然他所列出的政体有好坏之分,也有常态的变形,但它们均有自己实现公平正义的独特方式。至于这六种政体之外的公平正义问题,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讲的虽然是“政体”,但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希腊城邦,不同的政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类型,意味着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稳定模式,即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些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类型各有其适应于自身的正义原则。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86~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可见,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所关心的只是具有稳定结构的稳态社会范围内的事情。罗尔斯在说明他的正义理论的适用范围时一再强调,“为一个暂时同其他社会隔绝的封闭社会的基本结构,概括出一种合理的正义观来”,并且,“主要考察那些调节着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正义原则”。[1](P6)罗尔斯所谓“暂时同其他社会隔绝的封闭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组织良好的社会”,就是指具有稳定社会结构的稳态社会。他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正义理论只应关注稳态社会,而不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变化着的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虽然一般正义理论往往从稳态社会的社会结构出发讨论正义问题,并由此建构正义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不重要,或者可以将其归并于稳态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序列。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转型期社会往往存在更为复杂的公平正义问题,其形成的原因也往往不同于稳态社会。社会转型期是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它是一个社会系统维持其均衡的基本条件被打破,原有社会的机能障碍集聚到临界点而不能再发挥整合作用,因而需要以新的社会系统取代旧的社会系统的非常时期。对于社会转型的成败而言,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塑造固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价值指向问题,即新的社会结构将支持怎样的交往关系模式、维护怎样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因此,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不仅会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左右未来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走向和形态。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当然是未来的目标,而这样一种社会是否能够形成,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未来,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当今中国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曾在许多地方发生,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失败的,其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且在于这一社会结构是否是在现代公平正义原则的规范下形成的。因此,要想对特定转型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获得清晰的认识,就应当更加关注社会交往关系的流动变化和发展趋向,而不是仅仅关注固化的交往关系模式所形成的固化社会结构;应当更加关注导致社会转型的具体原因,而不是仅仅关注社会变迁的一般动因。
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正义理论形成于西方,既包含着对普遍道义原则的理性反思,也包含着西方的特殊经验和特殊观念。那些关于普遍道义原则的理性反思无疑为我们考察各种类型社会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理性的依据,而那些依据于特定经验形成的特殊观念却不是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在这些正义理论的盲区里,当然无法洞悉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这也正是为什么最近三十年间,我们虽然一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正义理论,却又总是感到它们并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现实的重要原因。考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当然需要依据于普遍的理性原则对一般道义规范进行辨析,但更需要从稳态社会与转型期社会的区别出发,对两种社会状态下的公平正义问题进行辨析,尤其需要从当前中国的具体现实出发,建构能够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理论。这种公平正义理论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要为正义的直觉信念提供理论论证,而是要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具体现实,因此,它既应包含一般的道德论辩,也应包含社会的、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伦理学的,也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是在规范性和描述性的交叉点上和它们的相互补充中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把握。
二、公平正义问题的道德论辩与伦理论辩
罗尔斯所谓的“组织良好的社会”,既可以比对于混乱无序的社会,也可以比对于尚未建立起稳定社会结构的转型期社会。混乱无序的社会是未来发展方向不明的社会状态,人们无法把握在其中将会形成怎样的稳定社会交往关系模式。转型期社会则是从一种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向另一种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转化,虽然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但却有着确定的发展方向,因而不同于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不过,无论相较于哪一种情况,“组织良好的社会”都是指具有稳定社会结构,即具有稳定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稳态社会。因此,转型期社会可以在与稳态社会所构成的对子关系中加以考察。
罗尔斯之所以将正义理论限定于对“组织良好的社会”的考察,首先是出于一种康德主义的考虑:“一种对应于基本结构的正义观是值得为自身的缘故而拥有的,不应当因为它的原则不能到处适用就放弃它。”[2](P7)据此,他认为,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我们不应当被那些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紧迫的问题”所干扰,而是应当专注于理想的社会状态,从社会基本结构出发,把握最基本的应然原则。罗尔斯承认“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概念”[3](P36),但是他又说:“我相信,我们从理想的理论开始的理由是,这种理论能为我们系统地把握那些紧迫的问题提供唯一的基础。”[4](P7)一旦我们从“组织良好的社会”出发把握到了这个“唯一的基础”,也就确立了正义的“绝对命令”,从而也就为非稳态社会(包括转型期社会)立了法,进而也就可以根据这一普遍法令审视非稳态社会中出现的公平正义问题。根据罗尔斯的这一理解,从一个假设的稳态社会出发获得的“绝对命令”确立了一个普适的正义原则,它既是稳态社会必须遵循的正义准则,也是衡量战争、非暴力反抗、好斗的抵制、革命等等非稳态社会状态下正义原则的“唯一的基础”,因而也就自然可以充当转型期社会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唯一基础”。
从理想的社会状态出发推论出一般正义原则,并用这一原则衡量一切社会结构的正义性质,以其规范人们行为,这确实是清晰的道德论辩方式,因为它清晰地呈现了善恶的标准。但是,这种道德论辩却是有问题的,它往往只能停留于道德应当的领域,而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却是在各种现实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是依据绝对的道德原则建构的。正如黑格尔在批评康德时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应当’里,总是包含有一种软弱性,即某种事情,虽然已被承认为正当的,但自己却不能使它实现出来。”[5](P212)只有被高度“理想化”的稳态社会,才可能大致符合罗尔斯所谓“秩序良好社会”的标准,因而才有可能符合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行条件。现实社会总是存在着“偏差”的,对于转型期社会和其他非稳态社会来说,这种“偏差”将会非常显著。就像罗尔斯承认的那样,在战争、抵抗和革命等非稳态社会状态下,人们必须用“战争正义论”、“革命正义论”等正义原则而不是用理想的正义原则来考虑公平正义问题。可见,在变动不居的转型期社会中,人们也只能用特殊的正义理论来考虑公平正义问题。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考察特定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时,是否舍弃了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道德要求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是有冲突的,而这种冲突体现在理论上就是规范性与事实性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康德力图在思维中排除掉这种紧张和矛盾,但在黑格尔看来却必须正视矛盾的存在,而说明它们就需要采用与道德论辩不同的伦理论辩方式。他认为,伦理论辩立足于道义规范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发展,而不是立足于抽象的道义推论,因而优于抽象的道德论辩。他指出:“无论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因为法欠缺主观性的环节,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所以法和道德都缺乏现实性。”[6](P162-163)黑格尔认为,伦理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为人们“普遍行为方式”的“风尚”和“习惯”,“伦理性的东西就表现为这些个人的普遍行为方式,即表现为风尚”。[7](P170)因此,与驻足于抽象善观念的道德论辩不同,伦理论辩是从现实的伦理实体出发考察问题的,不是将抽象的善观念与现实隔离开来,而是通过对体现特定“风尚”和“习惯”的“伦理实体”的考察来把握善。他说:“如果我们从客观方面来观察伦理,那末可以说,人们在其中不自觉具有伦理观念。”[8](P165)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黑格尔和康德一样将“法”看做是“自由的实现”,但他却反对对法进行抽象理解,而是区分“道德”与“伦理”,将“道德”归于人心,将“伦理”归于现实,并从现实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出发考察现实的伦理关系及其演进逻辑的原因。*其实,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原理》阐释的就是这样一个伦理关系的演进逻辑。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在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将道德比作上层建筑,认为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而是必须透过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原因。
从现实的伦理论辩出发考察公平正义问题,就需要将问题聚焦于价值与事实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聚焦于价值规范本身,需要从现实的社会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化的社会出发考察价值规范的承载基础。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考察什么是应当的正义原则,而且需要考察怎样的社会条件能够支撑这样的正义原则,甚至需要考察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对应的正义原则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仅仅注目于正义原则的道德基础;这同时也意味着,考察公平正义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哲学任务,而是需要哲学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联合才能完成的任务。考察变动不居的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更是如此,不仅需要诉诸多学科的联合,而且需要诉诸现代社会转型的学术视野。
三、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近代以来发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包含着多种层面和维度,受不同逻辑的支配。无论是较早的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还是后来的韦伯、哈贝马斯等人,都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逻辑,揭示了它不同的方面。当代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尼丝·赫勒在综合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归结为现代性的展开和实现过程,并据此阐释了它的发展逻辑。她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三种逻辑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一是技术的逻辑,即科学成为支配性世界观的发展逻辑;二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即现代社会在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上形成的迥异于传统社会的发展逻辑;三是政治权力的逻辑,即在政治统治方面形成的迥异于传统社会权力格局的发展逻辑。在她看来,这三种逻辑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她说:“在一个本质的方面,现代社会的第二种逻辑是所有前现代社会格局与现代社会格局之间的本质差异的载体,因为社会等级制度构成的主要制度坐落于此。”[9](P117-118)与前述伟大思想家相比,虽然很难说赫勒的这一说法有多么大的创新,但她对问题的这一现代表述确实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开辟了说明问题的新思路。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来说,赫勒所揭示的这个逻辑无疑具有一般性意义,在总体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可能超越这个逻辑。这意味着,当我们考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时,也应当从标志着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本质差异的“市民社会的逻辑”出发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真正根源,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需要从这一“坐落着”“社会等级制度构成的主要制度”的发展逻辑中获得本质性的理解。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发展恰恰贯穿于现代社会在“社会地位、功能、财富划分”上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支配逻辑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凸显的公平正义问题的总根源和总原因。马克思说:“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10](P345)传统社会是一种将个人固定于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之中的社会。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个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既不是独立的经济个体,也不是独立的政治个体,而只是依附于地缘和血缘共同体的“成员”。“成员”之不同于“个体”,从根本上说在于他的非独立性和非自足性,他是共同体的一个“构成成分”或“构成部件”,而不是作为独立自足的个人而存在的。作为机器的部件,一个离开了整架机器的齿轮是没有独立自足意义的;作为共同体的部件,一个离开了共同体的个人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滕尼斯说:“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占有和享受的意志就是保护和捍卫的意志。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祸害;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敌人。”[11](P76)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个人的价值要靠他在共同体中的作用定义,他的生命归属、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功能定位、他的财富分配,均取决于他作为共同体“部件”的价值。在这种关系里,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各安其位便是最大的社会公平。这是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中人们对公平正义进行评价的基本依据。柏拉图从社会功能论出发,将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不同的品性赋予不同的公民,并将他们划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的根据就在于此;儒家从维护等级名分制度、恢复礼制的要求出发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据也在于此。
与此相反,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自主的个人构成的。缺少了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便不可能存在和延续,因而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必须是独立自足的个体。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个人的过程,是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关系和财富分配制度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个将个人与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撕裂开来,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孤立的社会原子的过程。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以及为了维护这种交往关系模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本质性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原则因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改变而改变,它将为市民社会提供道义辩护,这是市民社会必然要求它这么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12](P154)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塑造了现代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只有通过对这一逻辑的理论再现,才能把握现代正义原则的实质。
无论是根据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种自足的市场交往体系,还是根据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种契约式的现代社会关系模式,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都是一个重新塑造公平正义原则的过程。这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新旧正义原则交织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发生于传统制度框架崩解和现代制度框架尚未形成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这一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难以用一般正义理论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加以解释。黑格尔试图以思辨哲学的方式,将问题归于伦理精神的异化与异化的克服,并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所各自代表的伦理精神的逻辑演进,说明市民社会所代表的正义原则的历史合理性和超越它的路径。[13](第三篇)马克思则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途径。这些伦理论辩为我们理解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
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既是一种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又是一种在特殊社会基础上、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这一社会转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既具有一般社会转型的特征,又与其存在重大区别。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既然是一种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不遵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般规律;以稳态社会为基础的道德论辩,其意义在于辨明善恶,因而也必然是我们确定公平正义原则的观念基石。但是,仅仅诉诸一般的道义原则和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转型理论,是无法解释当今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的。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当今中国公平正义问题的考察,大多是建立在西方以稳态的现代社会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之上的,既缺乏对转型期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考虑,也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关注。
应当肯定,作为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当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大批农民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转向城市,从传统的农业劳动转向现代工业生产,从稳定的血缘和地缘依赖关系转向临时性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所有这些曾经发生于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都在当今中国发生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极其相似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正是这种相似性,激发了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高度关注。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解释模式遭到放逐之后,这种理论转向是自然而合理的。在考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时,这种理论转向不仅不应否定,而且应当继续深化。但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情境,这种理论转向并没有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为构建新理论提供了外部脚手架。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仍然需要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
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一样,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首先经历了一个市场体系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呈现出一般社会现代化转型共有的特征。这种共有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上述理论转向的重要方向。在这个重要方向上,重要的理论任务即是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亦即赫勒所谓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般逻辑”。这一逻辑表明,市民社会是与市场体系相伴而生的,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的。在人类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社会交往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而这一变革又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在谈到欧洲社会近代的发展史时说:“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14](P2)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交换体系从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生产体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才导致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的形成,并由此导致规范这些“社会结合形式”的各种现代制度的形成,从而塑造了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也因而形成了以强调个人权利为基本内容的一般现代正义理论。当今中国的公平正义理论,无疑应当以此现代社会结构为基础,构建一种理论解释和道义辩护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不仅一般的正义理论,而且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转型理论,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于生存于前市场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将“市场体系”或“经济体系”与“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分离恰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经济体系本来是“嵌入”于整个社会之中的,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却力图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从社会肌体中剥离出来,以使其独立运转,并反过来使整个社会服从和依赖于它的运转逻辑。卡尔·波兰尼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经济对社会的“脱嵌”,因而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看做是“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过程。[15](P19)波兰尼的这一理解是正确而深刻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一经展开,经济“脱嵌”于社会便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行进过程,并且将会导致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之为“转型期效应”的社会后果。一方面,这种“脱嵌”过程既表现为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形成过程,也表现为韦伯所谓“合理化”的制度建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身处这一过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一“脱嵌”过程撕裂了人们之间原有的社会联系,摧毁了社会的原有结构,将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变成怀旧的乡愁,将人们陌生的生活方式变成坚固的囚笼,从而导致各个阶层对社会公平问题的高度敏感。波兰尼认为,由于“脱嵌”的不可避免性和它给人们带来痛苦体验的双重效应,所有的转型社会都必然发生“脱嵌”和“反脱嵌”的“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另一方面是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这种“双重运动”构成了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运动之两极。在阶级解释模式下,我们将这种体验和认知仅仅归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无产阶级,因而也就将社会变化的动因仅仅看做是由这个特殊的阶级提供的。但是,波兰尼认为,并不是只有无产阶级会参与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而是所有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可能参与到这一抵制之中。例如,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资本家也有可能倾向于中央银行加强调控。[16](P18-19)从宏大历史叙事的角度看,波兰尼的这一观点和他所提供的例证或许并没有超出阶级解释模式的理论视野,但从反思20世纪历史的角度看,却可以说他提出了超出阶级视角的新问题。在社会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如果受影响的只是无产阶级,阶级理论便要求我们从阶级分析出发,将激烈的阶级冲突看做转型的必然结果,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从根本上超越这个进程;如果受影响的是所有的人,我们便需要从伦理论辩出发,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正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出路。
在后一种视域下,问题最终归结为怎样在“市场”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即怎样将市场的驱动力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尽可能稳定在既能够较好维护社会公平而又不至于破坏发展驱动力的平衡点上。实际上,西方社会现代化变迁的钟摆始终围绕着这一平衡点摆动。在阐释公平正义理论时,西方政治哲学也因此不断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博弈和互鉴中寻求理论平衡点。市场与社会的平衡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中介,因此,市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便成为理解和解决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问题的最基本场域。这个基本场域包含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多重逻辑之间的交错关系,因而隐藏着现代社会变迁的多重秘密。从这一基本场域出发,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条件、特殊动因和发展目标,从而通过市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把握与其相关联的公平正义问题,无疑是考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只有在这一基本场域与中国特殊情境的交错点上,我们才能在充分汲取西方社会理论和经典正义理论合理观念的基础上摆脱对它的依赖,真实而深刻地把握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避免陷入抽象观念的陷阱。
首先,依据西方的历史与理论,人们往往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考察现代社会转型的前提性假设,但这种假设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当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并不具有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它的社会转型既是一个市场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业基础逐步积累的过程,因此,它的这个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然而,当今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却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工业积累基础之上的,虽然转型前的中国尚未形成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农业生产仍然占据很大比重,但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现代化工业已初具规模。因此,与西方国家早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相比,中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的社会很难被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传统社会”,而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已经迈入现代社会门槛的“非市场社会”。这意味着,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公平正义问题,是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转型起点上发生的。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而不是像早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果说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公平问题是由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财富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那么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只是放大了这一问题,而问题的初始原因和早期发展却并不是由市场化转型导致的。
其次,总体而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自由放任到更多国家干预的历史过程;同时,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始终是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调节者。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开启的,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不是自发发生的。以前文所述赫勒所提供的观点看,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遵循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赫勒所谓现代性的第三种逻辑)。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改变国家对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过多的干预,因而是一个国家向社会放权和社会增强自主性的改革过程。一方面,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一过程恰好与西方相反,即主动性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国家,改革的“行动者”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另一方面,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一过程虽然也同样表现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运动,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的,这种“脱嵌”实质上是市场从国家计划控制之下脱离出来,而不表现为经济脱嵌于社会。这一特殊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得国家成为一切矛盾的“承担者”,而不是市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调节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自身的制度改革就将对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建构发挥关键性作用,因而也将对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向社会的放权将会释放市场的活力,获得改革的红利;另一方面,国家向社会放权也必须着眼于社会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着眼于推动新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形成,否则市场机制的加速增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脱嵌”,加剧社会不公平。
第三,西方市场经济是从冲破封建等级制开始的,因此,它所着力改变的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它所着力建构的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制度。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从一种平等主义制度模式向公平主义制度模式的转变,它所着力建构的虽然也是公平主义的社会结构,但它所着力改变的却是平均主义取向的平等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要在充分发展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的制度体系,虽然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所难免,但它所建构的平均分配体系无疑具有高度的平等特征。平等与公平之间本来就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模式,以及当前立足于公平对这一模式的制度改革,使平均与平等、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更为复杂的面相。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社会公平问题无不与这种复杂局面相关。如何处理好平等与公平的关系,对于解决当前的公平正义问题,对于未来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还是经典正义理论,都无法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根源于平等的价值取向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冲突一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机制。因此,这一冲突不可能完全被消除,只能随着社会的成熟和发展而得到缓解,在公平与平等之间达至某种平衡。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经验看,这种平衡最终依赖于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的形成。因此,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的制度建构,而且需要社会自我救治机制的生长和完善。只有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我救治机制有效结合,共同筑起保卫社会的防线,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转型才能顺利进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市场对社会的“脱嵌”才能被限制在不危害社会基本公平的底线之内。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取向是平等主义的,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建构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必然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提出更多的平等主义要求。平等→公平→以公平为基础的平等,这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公平正义问题发展和解决的基本路径。
[1][2][4] 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 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7][8][1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9]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16]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Problem of Transitional Period of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NG Xin-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It seems that we often focus on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problem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theory of Justice,which is constructed on the western stable society.The approach disregards the dual specificity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general and Chinese transitional society and it is undoubtedly flawed.In fact,a reasonable ethical argument rather than a moral one needs to focus not only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back up the justice principle,but also on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justice principle.Based on this,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problem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finally rooted in the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the equality orientation and fairness.The tension of the two values would not be removed,but only be alleviat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until they reaches a balanced state.Thus,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rrangement is insufficient to promote fairness and justice,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lf-treatment mechanism of the society is also vital.
transitional period of society;fairness and justice;ethical argument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14JZD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10ZX017)
王新生: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