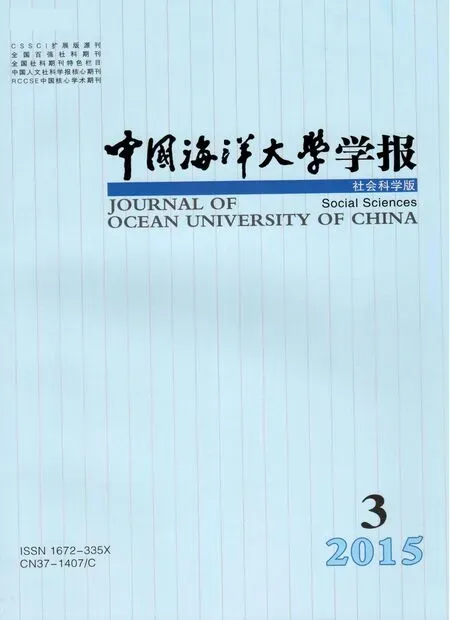关于中国传统文论哲学核心组合式及其历史主线的发现 ——从解析魏晋文艺美学方法论出发 *
2015-01-22杨继勇,田培春
关于中国传统文论哲学核心组合式及其历史主线的发现
——从解析魏晋文艺美学方法论出发*
杨继勇田培春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发现在中国传统文论及其审美思想中持续潜含着显-隐同构律,即文论诗性智慧的纵深可析出的哲学内核组成式,属二元同构而非单一的;从魏晋始探其源、追其流可见,中国文艺理论史始终潜含着这种哲学内核的运行主线,此乃文脉所系。其方法论启示人们不为表象所限而扩展审美视域、索隐启蔽、关注本源;当代文论建设基于这一主线所呈规律,才能继承传统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关键词:文艺理论;方法论;显隐同构律;文赋;文心雕龙;审美视域
收稿日期:*2014-10-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12&ZD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继勇(1968-),男,山东莒县人,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3-0118-07
Abstract: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metaphorical excellence in expressions withi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aesthetic thought; it is a combin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re summarized from the poetic wisdom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hich is dual but not unitar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n Wei-Jin period, it is clearly to see that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lways follows the clue of philosophical core. The methodology suggest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be limited by its appearance, but goes deep into its orig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should follow the main clue, inherit the tradition and demonstr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因中国文论现代性建设只有基于传统文论的运行趋向和规律,才能避免与古代文论脱节、失序,从而在发展中彰显中国特色的魅力。又因经学科反思和学术自省,使文论历史线索本身成为反思对象,这才是学科自觉的标志之一,以索隐而启蔽而昭示文论建设的未来向度和价值。这就须深入研究传统文论及审美的基本范畴、逻辑起点、方法论等,进而寻找归纳其持续运行中所潜含的逻辑主线,所以,中国文论其以一贯之的文脉是否可以凸显、归纳?所含最根本的哲学主线是什么、如何存在?此乃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使命诉求着理论彻底性。
本研究发现并求证:中国传统文论基本范畴概念的基本构成关系及其演进史之中都存在着“显-隐同构律”,“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1](P39)预设这组合式概念以便于考察、求证其是否存在、存在特性及其持续运演状态,是否构成传统文论及其审美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的潜在主因。
一、析《文赋》《文心雕龙》等潜含的哲学特质
若说传统文论的哲学核心是天人合一等未免浩瀚无际,秦汉及其以前文论及审美思想是丰富的但体系化奠基当属魏晋,故有必要将其作为考察切入点。
(一)显-隐同构之理从魏晋奠基之作《文赋》之中可析出。其开端即强调“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说创作或鉴赏也属面临虚无,即文艺活动要立足于有、进而解除“遮蔽”,才可能悟及似“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诗性之“显”;这前后关系已构成了“显-隐”反差。后句貌似各说其一,实参乎成文、内在之理一也:创造性地将关于自然美的哲学观纳入了创作论鉴赏论;借韫玉-山辉、怀珠-川媚的生态化审美图式折射着宇间造化之因缘、彰显了“显-隐”共在属性,“美必伏于广大,故石蕴玉而山尽含辉,水怀珠而川悉献媚,珠玉不独处也”。[2]整体考察贯于《文赋》通篇的潜方法论也是“显-隐”同构方式;因为其开篇玄览、叹逝、“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即通篇思想平台之背景是“隐”、旨在彰“诗性之显”皆凭“索隐”,“凡有皆始于无”、“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老子注》)。创作、审美也是立足于“万有”而面向“无”、隐寂、遮蔽……进而达乎诗性文采“显”化的过程,其间玄机乃隐-显同构而演进;再如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罄澄心以凝思”即强调为文机制存乎显—隐之际,即强调审美经验的纵深效果、其“澄心”所获必基于诸多关系、折射宇宙自然造化之内-外、遮蔽-澄明等至理;或曰怀珠-川媚的显-隐二元同构性,折射出了宇间“隐匿与生成的共在性”。据此可见所谓《文赋》之奠基,不仅是强调将文艺使命从表达显性的“诗言志”转向强调内隐化的“诗缘情”,且强调应将审美的内心之隐对应于存在之隐、重索隐而启蔽,将寻觅彰显那易被忽略的“被遮”作为文艺哲学之基,以诗性方式强调艺术特质所由本源,也旨在突出未出场之“隐”,以之补救专于表面之“有”的“镂金错采”式文风之弊。
据上可证,在其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框架上,在诗性智慧覆盖下所折射出的哲学核心组合式,可窥及一对哲学范畴显-隐,“显-隐属性共时二元同构”,系二元而非单一这是成立的。再需求证这属性于其他文论思想上是否存在及是否具普适性。
(二)显-隐属性共时二元同构特性存于《文心雕龙》之中并可析出。刘勰将《文赋》思想精髓及审美图式、内在之理多向度扩展进而演化为隐秀说;“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者;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隐秀》),考其“隐之为体”,这和《文赋》开端的“玄览”所寄相似,是面向本源究文艺至理的本体意识,即陆机所论显-隐同构思想的奠基,这使得刘勰及其后文艺观更看重无限、本源,强调索“隐”而启蔽。显现在两者所论都借用“珠-水”图示而折射着相应的二元范畴:文-情、内-外、上-下、远-近、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珠玉潜水-澜表方圆……上述所含诗性智慧覆盖的艺术关系,可进一步用审美范畴“隐-秀”概之,若取其内涵、关系的哲学“纯粹性”皆可谓之“显-隐属性同构”。且可证该同构性不限于《隐秀》残篇而贯于《文心雕龙》,如:“沿隐以至显, 因内而符外”(《体性》),“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张戒引《隐秀》轶文)……综上可证:《隐秀》所寓这显-隐属性与其全书相应,且《文赋》与《文心雕龙》所含“显-隐属性同构”也全息相应。三者哲学核心概念及其诗性关系构成式和方法论为:显-隐属性共时二元同构。
魏晋上述所论内涵繁杂而又交互,若分为若干层次有其必要性、也有难度。《文赋》《隐秀》借自然生态的图示统摄了珠玉崇拜、以水喻道等意向,寓文-道关系宏旨,其立意重在文艺,但其文艺观是在囊括天地人的审美系统之中阐发的,而这文艺美学观又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所以, 阐释隐、秀及珠-水的二元内涵,应分生态自然→文艺→美学→哲学等层级,但诸项之间却无时不在全息相应而意义纠合,抽刀断水水更流、致清晰界定的难度; 若无视上述多层次性与显-隐二元同构性这两者相交叉的逻辑坐标,而试图严格界定,则必因剥离某项与其相邻意义的关联而陷入窄化甚至抽象,如关于隐秀、意境及其子项的研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盖因于此。
可证“秀”的本根性摄于“显”。因所谓秀,动词,会意。石鼓文上为“禾”、下象禾穗摇曳,本义谷物抽穗扬花。指人的容貌姿态或景物美好秀丽,重于内在的气韵(《高级汉语词典》);如“采三秀兮于山间”(《山鬼》)。秀,用于品评人物如“五行之秀气也”(《礼记》)。可见秀还可释为人生及作品等的精华光彩,即以“显”性存在为前提的。不同语境中“秀”应有自然生态、人物外貌、文法修辞,以至文论、美学及哲学等层面的内涵。但其间辩证性是依于“隐之为体”,隐待秀而明、秀凭隐而显。
(三)还可从《诗品》析出其显-隐同构属性。设《文赋》《文心雕龙》上述观点构成了文论思想史上的线段,那么可证至钟嵘所论乃至其后显隐同构属性的哲学主线在中国传统文论之中持续运行不已。第一,《诗品》开端“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乃至“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珠泽-邓林,内-外,及处于幽微遮蔽-诗性动感澄明……这和隐-秀的审美属性同质、可互代。再者,同样是强调:自然造化隐而不彰的存在-文艺思想精华秀美,属性关系对应同构。上述若干对诗性范畴共同折射出的哲学潜质即显-隐同构性。相形之下潜质之外的那些其他规定性则似模糊不清的轮廓而已。第二,《诗品》的显-隐同构性,还现于强调若实现“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的“显”效,则离不开“直寻”,即凭诗性智慧“不涉理路”透过表面现象物理空间而直觉其后诗意空间所潜含的艺术真实的可能性。凭“直寻”,即王弼所倡“得意忘言”在诗学领域的运用,即“索隐”,直寻“万有”背后“无形无名者”之“隐”而非逻辑推理式。这与《隐秀》强调“文外重旨”、与海德格尔所论梵高画作《鞋》所用的在场-不在场[3](P27)之显-隐,其致思意向相似。“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直观开始,从那里进到概念,而以理念结束”。[4](P544)即可证《诗品》诗性智慧覆盖的哲学核心概念及逻辑关系属:显-隐同构属性,这与上述所论两者相较而抽象统一。
二、显-隐同构律哲学属性的析出和确认
关于中国传统文论及美感经验之中若干诗性范畴的再分析。
(一)据上而析出的显-隐属性,其主要理论背景是据玄佛哲学。可拍案称奇的是上述魏晋三者所论都使用了珠-水同构的审美图式即以符号隐喻表达显-隐同构之理,且二元共时共在。任一理论观都是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生成,三者有据于“上善若水”(《老子》,有据于“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的“不可……”,有据于玄学凭有-无、本-末来探讨本体与实在的关系;即据于万有之“显”和无形无名的万物所宗之“隐”的二元相依之理。如《诗品》开篇从遮蔽之“无”进而显化“自然英旨”诗性;所论怀珠-川媚之“秀”不过是人的一种感悟,秀所示为去蔽澄明的诗性、以在场可感的世界显性为前提,秀和显基于无限之隐,审美的隐-秀折射着哲学的显-隐。诸关系如海上冰山、大部“隐”于水下,不在场之“隐”即无限而意味着本源;其更大部分是“隐之为体”、不在场的无限;其理在解释学即“诗并不描述或意指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5](P601)纵观天下文章刘勰遗憾有的“虽奥非隐”而隐秀兼备之文“希若凤麟”(《隐秀》),强调篇中是否存“隐”是评价优劣的标准而并非指晦涩乃是蕴籍有余。生活中那些士人避开显赫生活而谈玄归隐其理与此同归。“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6](P23)这显然合乎“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7](P195)即珠-水同构所示与当时关于有-无、本-末的哲思相关。还可证显-隐同构性主线的形成也不单是道家哲学的显现,如“逝者如斯夫”也映现着儒家对显-隐同构之理的感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即显现于唐的佛法兴盛等的隐秀之致,也属《文心雕龙》之时代背景。
(二)魏晋三者所论美感经验之中,其水下之“珠”处玄隐、貌似无,示无限、体、终极之道,于自然景观及诗意具统摄力;珠-水共在构成了概念范畴运动的逻辑系统,及真理发生的场所,启示着索隐以启蔽。析三者所论水下之“珠”,是与其“水上”秀美景观相应、共时的决定因,实喻“万有”本源及文艺审美属性之“隐”;其人文智慧覆盖的哲学本质是形而上和形而下共在。“珠”之“隐”“遮蔽”实即存在者的“存在”,“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这在通常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或复又反过来沦入遮蔽的东西,或仅仅以伪装显现的东西,却不是这种或那种,而是像前面的考察所指出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可被遮蔽的如此之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8](P41)据此,怀珠-川媚示其隐匿与生成共在,启示神思超越物理空间面向诗性空间而索“隐”而启蔽,以叩问文艺之“显”所基“真理发生的场所”、“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
联系刘勰《原道》篇可见其所论文艺之“秀”,又从属于“万有”的外在特质广义之“文”; 广义之“文”是人感悟“万有”所获表象;表象基于本源,悟本原需悟“隐之为体”,此即文艺系于始基“终极之道”。“珠”隐,这和“水上”万千气象共在,是万有、秩序等的决定因,但人永远难以直观那水下富有生机的“珠”本身,这似乎永难见到艺术、美本身……“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韩非子·主道》), 诗性空间超越于物理空间其隐喻性只存在于超验性之中、感其真气而遂通,若借佛理而言即“一本万殊”。通常只能欣赏到无限的艺术品等审美对象之“秀”,而哲理中“隐”、“珠”又对应着隐秘的心、意。概《隐秀》《文赋》《诗品》立意所含两点哲学核心的布局,是“隐之为体”为基、同构于万有之“显”而展开。若无视“隐之为体”而偏执“显”性追求,似难以索隐、启蔽而所向通达。秀、有、明显和隐、无、玄暗同构,因为珠-水所示系统之中“隐”待“秀”而澄明、同时“秀”依“隐”而根深。所以上述诸多成对的诗性审美范畴,与此显-隐哲学关系、辩证性同质。
(三)溯其源,考以怀珠-川媚之“珠”喻示、慧解道的历史观。还原到历史长河可见“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5](P347)如黄帝过赤水登昆仑所遗玄珠惟有象罔得之,玄珠、象罔都是显-隐属性交互的幻化,玄珠乃“道之真”的典型隐喻(《庄子·天地》);佛道借玄珠喻道之实体真谛,如“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大戴礼记·劝学》);如“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凡蚌孕珠,乃无质而生质……凡蚌孕珠,即千仞水底,一逢圆月中天,即开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中秋月明,则老蚌犹喜甚。若彻晓无云,则随月东升西没,转侧其身而映照之。他海滨无珠者,潮汐震撼,蚌无安身静存之地也”(《天工开物》下篇第十八珠玉)。归纳其方法论可发现以上述三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论体系建构,其哲学概念的核心属性上,是将不在场、未出场设为理论本质的源点、事物根据及审美原则出发点,所以静处于隐之“珠”所蕴,反而示现实之中艺术之“真”的思想向度;据《原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即应据道之基本精神的精妙特性来从事文艺诗性的阐释,那诗性空间不限于物理空间,既折射出人生亲在方式的诉求,也具面向哲学之“无”、“体”的理论勇气。天人合一之下的诗论,二元的显-隐同构强调着形而上和形而下共在,这横向而较于西方强调模仿、反映、再现等的文论视域更玄远。
(四)“文外之重旨”强调着索隐而启蔽、具诗性空间的超越特性。溯“文外之重旨”其原初性属“道动于反”之理化入了上述珠-水所示图式中。如“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隐以复意为工”,且“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原道》),其“复隐”也即“隐”不限于“水下”,又可在那玄远不明之处,刘勰强调“秀”意实现之后所化“文外之重旨”复归于“玄”,从珠玉潜水的隐之为体始,至其上“澜表方圆”之扩展、再至“若远山之浮烟霭”,在空间极致上一切“秀”复归为“境玄”;且认为隐→秀、秀→隐过程“有似变爻”。玄,亦即去蔽后的澄明诗性反归于玄远,或胸臆之“隐”,此即人类超越之艰。其理具哲学、文论及人文精神的诸层启示,其一,强调“文外之重旨”即情在词外曰隐,即强调了突破人审美经验的有限性,而不将怀珠-川媚等因果的合理性限于经验及认识客体物质性;所涉思维空间存在胸罗宇宙的彼-此、近-远、显-隐的往复。融主-客界限为一。第二,强调“文外之重旨”,可证这化为后来“象外之象,景外之境”、“味外之旨”等诗论原则。第三,借此可发现其“远山之浮烟霭”、“境玄”……表明隐秀说已将“境”自觉用于审美空间、纳入文艺批评的端倪,可证此乃传统文艺美学最高境界“象外之象”的奠基、主潮“意境说”的萌发。第四,从“隐之为体”,到“远山所浮烟霭”再到文论史上非“目击可图”的象外之……词外之……言外之……文外之……画外之……等境界、原则的创设,诗性空间同构了形而上和形而下共生的显-隐之质,使得老庄玄“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等哲理植入了文论智慧。这以及显-隐二元同构等艺术原则的奠基,至今仍是中国文论具鲜明特色的主因和极致。第五,上述图式为意义的多层特质与同构性间相互交叉的逻辑坐标,从秩序、神思、形式特征上又折射着动态性、开放性和不完满性的生命力;也佐证了“真理,就其本性而言,即非真理”[3](P53)的哲学观在文论的适用性。第六,这也是审美心理结构方式的显现,也潜含了君子健动、超越有限而生生不息的哲学品格。总之诗性的“文外之重旨”本质上即显-隐二元同构哲学属性的动态性、交互性显现;亦即从三者所论之中可随机析出显-隐二元同构的思维路径。
(五)对传统文论史显-隐二元同构律的确认。综上,若透过各家诗论表面的具体性、丰富性和超越诗话的芜杂,可发现并析出所论诗性现象、审美经验背后潜在的概念范畴运动的逻辑系统,包含着普适的逻辑统一性,取其较纯粹的哲学属性命名为:显-隐同构律,其诗性空间是隐匿与生成共在的特性,其诗性的表达式因时代不同而可有多种方式,隐-秀、意-境仅是其二。据“特殊的个体是不完全的精神,是一种具体的形态,统治着一个具体形态的整个存在的总是一种规定性,至于其中的其他规定性则只还留有模糊不清的轮廓而已。因在比较高一级的精神里,较为低级的存在就降低而成为一种隐约不显的环节;从前曾是事实自身的那种东西现在只还是一种遗迹,它的形态已经被蒙蔽起来成了一片简单的阴影。过去的陈迹已都成了普遍精神的一批获得的财产,而普遍精神既构成着个体的实体……”[1](P18),因此,显-隐同构律如具普遍性,那么它应存于魏晋以降“具体形态”的文论中,且可从中析出其“普遍精神”。
可见在唐宋以降理论表达中果真是“它的形态已经被蒙蔽起来成了一片简单的阴影”,即较少用“珠”及水珠-川媚、秀-隐等表达,但其显-隐同构之理已被转述为更多的范畴,但仍可从文论之中析出。再据“真理的如此发生是作为澄明和双重遮蔽的对立”,[3](P62)所谓中国传统文论的显-隐同构律,即其理论的逻辑基点不是单一元素(范畴)的而是二元:即强调形而上和形而下共生的显-隐共在、同构,彼此渗透、贯通、依存联结,据一定条件向其相反方面发生影响,但隐的一方无形无象而处遮蔽状态难以被认识和反映。所以,其方法论、审美原则超越了单纯反映客观、强调逻辑分析的理论所限,启发人们注重诗性时空的索隐启蔽,在基于显性的同时关注潜在、感悟未出场的本源。显-隐二元共在具同构性、共时性、普适性、稳固性、动态性、交互性等生命力特征,是精英与通俗诸家展开文论及审美思想所基的哲理框架。尽管万有皆是“末”,但一切诗性观照无不立足显性现实而出发,故将“显”前置而名为显-隐同构律。
三、验证显-隐同构律的普遍性作为反思传统文论的逻辑中介
文论作为文艺本质特性的集中阐述,“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9](P295)若文论和“真理之创建”关系密切、显-隐同构律的概括是成立的,那么就应可证显-隐同构律的“真理之创建”不限于魏晋而其生命力应贯于文论史。本研究发现整个传统文论及其审美思想史之中确可析出其运行主线,但在魏晋后的经典阐述字面表达之中宏大无限的思想平台“隐”这一元往往被转述为其他范畴,所以其二元组合式只能通过分析而间接得出。
(一)溯《文赋》之前所论相似美感经验之中的哲理。如魏晋《典论·论文》,其通篇的立论平台也基于显-隐同构属性律。其开篇叹时间是一切现象的必然基础、有限人生之“显”属五行之“秀”的呈示,遗憾的是在生卒年的线段之外那属无限之“隐”:“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之隐,所以追求以文章立言而“显”为“千载之功”;“年寿有时而尽”乃无限“隐”无,故应“显”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再溯魏晋之前,典籍中文史哲一也、似难找到纯粹文论,《淮南子》有“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其《坠形训》有“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其《说山》曰“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析之可见其显-隐同构属性同质。
(二)下探显-隐同构律的普适性,在魏晋钟嵘后的文论演进史可见其整体运行。以下可见其在经典思想中皆可析出、在历史演进中二元同构律之质未变。如画论“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神;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谢赫《古画品录》),其体物-象外即折射着虚-实、显-隐之质;至王昌龄“张之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诗格》),其真、神对应“隐”意,且呈意-境范畴同构;尹璠评诗“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创作论上“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奉和至舍人》)……透视其本根性合于水珠-川媚意向,且可断定其境中含秀、已植入意-境关系。可谓实质相同。
显-隐同构这种诗性的哲学特质,在唐宋之后潜行的另一表征,是诸家学说这个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摄于显-隐二元同构的必然性。即不仅是此前隐-秀、珠-水等成对范畴在表达上少用,且同构中的“隐”这一元被慧解成为:珠、体、玄、无、真宰、真、冥……转述为胸、心、意、题……所示,乃至兴趣、神韵、意境……虽表述不一,但同构性实为其与普遍性原则结合起来的中项,异彩纷呈的背后仍可析出统摄功能的显-隐二元同构律即其哲学本质,相形之下本质之外所获规定性则似模糊不清的轮廓。再如:皎然“诗之至”为“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盖诣道之极也”,“情在言外……旨冥句中”(《诗式》);张璪论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图画见闻志》);司空图倡“‘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与极浦书》),此处之玉-烟、环中-象外……祥和之间属性同构。荆浩曰“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笔法记》);梅尧臣、欧阳修强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苏轼重“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黄庭坚“有万里之势……得古人道者以为逃入空虚无人之境,见此似者而喜”(《跋画山水图》);张怀所论“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豪,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山水纯全集》);张戒强调“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岁寒堂诗话》);陆游“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儿》)的诗之质与“诗外”;严羽“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需避免迷失的是在其演进中不仅所用概念变换了,且仅在简短的话语中难以析出其二元、需联系其整篇才可析得。“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其造物者之“隐”,这和苏子“共适”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万有之显,较之“隐之为体”、“源奥而派生”、“深文隐蔚”、“远山之浮烟霭”所含显-隐同质。金王若虚评“论妙在形似之外……而要不失其题”(《南诗话》);明高濂“故求神似在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燕闲清赏笺》);至叶燮“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崇“晨钟云外湿”(《原诗》);至王国维意-境仍存和水-珠所喻隐-秀之缘,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于第一流”(《人间词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所谓兴趣, 阮亭所谓神韵, 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0](P143)再至黄侃依然“言含余意,则谓之隐,意资要言,则谓之秀”(《文心雕龙札记》)。去其表面而取其本根特质,精灵、深得、诗之至、旨、珠、源、环中。诸图式的潜核心仍对应“隐”之属性,且折射着内-外、形-神、内-外、简约-丰富。其互动关系皆通过在场有限性而悟尚未出场之隐、据于物理空间进而悟诗性空间的意向。
考上述唐宋以降皆含显-隐之质,呈于诗论、画论的所用概念范畴发生了变换,较少直接用上述魏晋的范畴,同构律之主线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其美感经验之质已被折射从而述为了具同构特性的:文-道、内-外、意-境、意-象、有-无、心-物、形-神、风-骨、言-意、文-质、情-理、情-采、情-景、言-意、形-神、虚-实、一-多、真-幻、俯-仰、动-静、虚-静、通-变、奇-正……万有之象均在各环节显现着必然性,其索隐启蔽之致,可谓“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诗),即幻化为诸多体现着既感悟物理空间,同时反思诗性空间、个体心性所悟-外在世界秩序相融的范畴同构格式,而对应着同构律。经典皆可析出,乃是因为“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8](P179)所谓“进入这个循环”即在历史演进中二元同构律之质未变。
黑格尔曾认为真理就是全体所呈示的与各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综上诸历史阶段可见显-隐同构律乃中国传统文论及美学文脉之所系,直至近代其中依然映现着相似的基本范畴、逻辑起点及组合式与方法论。
四、基于显-隐同构律的历史趋向与反思
上述间接证明了隐秀说融入意境说的踪迹,亦即催生了后者的萌发;因较为公认的是意境说于唐宋后渐为传统文论及审美主潮,及“刘勰隐秀之说实为于文学意境美学特征阐述之最早滥觞”;[11](P343)又因“可证《隐秀》虽系残篇但该学说乃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重要学说,隐秀同构的要义潜在的贯于中国美学思想主潮”,[12]所以,可证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结论:文论及文艺美学史上虽有不同指称、学说表达的自由万象,都基于一条历史上持续潜在、运行不息的显-隐同构律哲学主线,诗学上也可述为遮蔽与澄明同构等,直至现代,其特征、要义仍相贯而同源,这也佐证着中西审美心理结构方式、文论及文化的本质差别,这确是成立的。反思陆机、刘勰之始的审美理论实为强调人文要循自然之道,遗憾的是个体的人被纳入了天地人的整体系统之中,这虽可避开社会群体纲常思想的辖制,但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又被统摄于自然而淹没,即其身心于自然之美的诉求和遵循是以无奈被动为代价的——这乏力度美的缺憾性特质,也存在于显隐同构思想主线之中。
乏主线的研究可能为史实的罗列、忽视底蕴普遍性易导致片面芜杂甚至失序,“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1](P11)具备上述称谓不一的通变,传统文艺理论才汇为滔滔而不腐,真理在具体进程的各种现象之中往往自己否定自己而又呈为诸多新的可通约性,这易遮蔽应予彰显的历史主线是潜在的但是客观实存的,而研究的许多自我迷失往往是因划地为牢。因此需参考“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各个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能可能”。[13](P56)
若“真理就是全体”所呈示的,那么显-隐二元属性同构其价值又可呈现于多领域:逻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包容着逻辑的直觉经验性的洞察力也不可或缺。重索隐启蔽方法论,可益于启示人们不限于物理空间表面之有而拓展审美思维的诗性视域,关注本源;益于反思文艺反映论是否具片面性、显化被遮已久的文脉价值,尽管文化断层或理论译介等易致文论疏离哲学本根性、思想主线长期被遮,但文脉所趋应是文论面向未来建设、彰显中国特色及与国际接轨所应承继的必然。若忽视“隐”则易默认“显”性的专断,或将致学科研究限于万有的知识论性质、学术浮躁和繁荣式贫困。无视“潜在”即忽视“隐之为体”,那么所谓文论研究的体用结合、中体西用就可能以偏概全、拘于热点、无缘通达;或把学问及其他现实生活实践引向功利、从光环到光环甚至物欲横流之途。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陆机.文赋[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76.
[3] (德)海德格尔著.诗·语言·思[M].北京:文艺出版社,1991.
[4] (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楼宇烈.王弼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
[9] (德)海德格尔著.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
[10]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卷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11] 张少康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教程: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2] 杨继勇,杨献捷.关于中西方两种美学观的比较论纲[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09.
[13] (德)黑格尔著.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The Philosophical Cor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Discovery of Its Historical Clue
Yang JiyongTian Peichun
(School of Art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Key word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methodology; metaphorical excellence in expressions;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 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 aesthetic perspective; historical clue
责任编辑: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