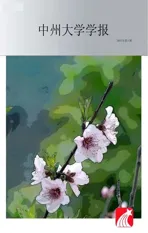别尔嘉耶夫论托尔斯泰
2015-01-21耿海英
耿海英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别尔嘉耶夫论托尔斯泰
耿海英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摘要:在我们接受托尔斯泰的百余年中,由于不断的阐释、想象、转化,我们越来越远离其思想中的“善、道德、恶”等的原初内涵。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揭示了托尔斯泰思想的根源及其内涵,为我们开启了认识托尔斯泰的另一路径。
关键词:别尔嘉耶夫;托尔斯泰;宗教哲学阐释
一
列· 托尔斯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百年有余,且已形成了可观的“托学”。在接受中,虽具体的切入点不同,但人们关注的焦点要么是思想家托尔斯泰,要么是艺术家托尔斯泰,也有通过诗学打通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努力。在对思想家托尔斯泰进行研究时,集中在了“托尔斯泰主义”上。对这一主义的具体内容基本界定为“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全人类普遍的爱”。可是,在不断变迁的具体历史境遇中,我们要么就思想论思想、就主义论主义,要么实用主义地利用他或批判他。对于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也各有说辞,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多是将其思想移植到我国的社会背景上,以我们对这些词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进行评说,缺乏从更深的层面把握托尔斯泰思想的实质所在。也许,在我们这个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度里,我们很难真切地触及到这位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的精神人物的精神深处。
我们对托尔斯泰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相关。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最早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1]162。我们知道,值此前后,鉴于中国当时变法图强的政治需要,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等一系列主张,并发表有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强调其小说在政治上之“不可思议之力”。自此开始,就定下了接受托尔斯泰的基调,虽然以后也研究其艺术特征,不过更偏重于他的思想价值。但对于其思想价值中的宗教思想,虽在寒泉子的《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1904)中有重点评价,但“文章所涉及的关于托尔斯泰宗教思想领域,后来长时间少有人涉足”[1]163。即便有之,多为否定。鲁迅就指出过其不抗恶思想中包含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1]164在此后几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的激烈动荡中,都是从政治斗争出发,纠缠于托尔斯泰是进步还是反动,对其或崇拜或贬抑,没有也不可能从宗教根源的角度阐发其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有了从宗教角度对其思想的探讨,但依然脱不掉实证功利与世俗化(该文中“世俗”与“宗教”相对)的思维惯性。
首先,关于托尔斯泰主义是否源于基督教教义,在我国学者中就有分歧。有人认为,“托尔斯泰不相信基督及其教义”,而其“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全人类普遍的爱” 这三条原则实际上也都背离了基督教的原意。研究者认为,“勿以暴力抗恶”,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来自耶稣“不可与恶人作对”的教诲,但耶稣教诲人“不可与恶人作对”,是以上帝对人的最后审判为前提的。托尔斯泰则是在暴力与生命的对立中提出“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而“道德自我完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托尔斯泰对人的趋善性的认同上。托尔斯泰不相信“原罪说”,也不相信末日审判,他相信人的良心。“全人类普遍的爱”的“人类之爱”也较少宗教成分,而更富伦理色彩。因此,研究者总结说,这三条原则“是托尔斯泰为人生努力寻找的精神路标,根本不是基督教教义的翻版”[2]。这一“重新认识”完全褪去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宗教色彩,将其世俗化了,视其为一种“为人生”的理论。
另有人则提出相反的观点,指出:“托尔斯泰认为,人生的意义,人类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信奉并遵守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亦即以爱心待人,不仅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且要爱一切人,包括宽恕和爱自己的敌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道德,纯洁自己的灵魂。托尔斯泰还认为,宗教探索的归宿不只是要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而是要消除人间的罪恶。他认为,俄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现存的一切罪恶,用暴力的途径是不能消除的。暴力压制或暴力斗争只能使恶增加,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隔阂。改造社会的唯一正确途径是个人道德的完善,是人们在基督教精神基础上的友爱团结。”[3]还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否定暴力是托尔斯泰乌托邦思想的基石,正是在反对暴力、消灭暴力的前提下,他从《福音书》耶稣的教义中提取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旨。在这看似消极、被动的教义里,其实隐含着强烈的为理想而战斗的动因。因为基督的最高律法是爱人、不抗恶,他把前者视为‘要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互相服务的律法’,把后者称为‘不抵抗主义’,视此为彻底根除暴力的惟一途径。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4]
这些评述虽然承认三原则是以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原始教义为基础的,但却夹杂着对这一精神的世俗解释。也有人认为,“‘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宗教哲学的综合体”。但对其具体内涵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人生下来是完善的。小孩是天真、无邪、善良和美的,只是进入人世间以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沾染上不良习气,逐渐堕落。……托尔斯泰希望修复童心实现‘道德自我完善’,希望靠自我牺牲的道德信念保持人性的纯洁。……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勿以暴力抗恶’,来自《圣经》的《马太福音》。……他对邪恶只是反对、谴责,而不是抵抗、想办法消灭之。托尔斯泰的良方是退让、仁爱、道德自我完善、自我修养。”[5]
无论是否认为“托尔斯泰主义”源于基督教教义,这些解释似乎浮于字词的表面意义,有人甚至说:“‘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道德的自我修养’。其所追求的就是人人平等、和睦和友爱。”[6]这确实是太“简单”了!而且我们从中体会到,这里的“道德、自我修养、人人平等、和睦、友爱”这些字眼完全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具有的是特定的中国语境中的世俗的修辞色彩,极富中国味道。还有人讲:“托尔斯泰作为老子学说最忠诚最天才的倡导者和传通者,他深得老子学说的精髓……托氏的‘勿以暴力抗恶’决非同暴力妥协,而是‘以柔克刚,对统治者施行一次柔弱胜刚强的中国功夫’。”[7]这种遣词用语的解释就更为中国化了。
我们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转化能力,一种思想在我们这里都会极端地“为我所用”,有人这样讲:“托尔斯泰一生‘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的思考,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的关注。”[8]还有人讲:“‘暴力’在托尔斯泰那里也是一种‘恶’,它威胁人类生命,破坏人类和平,而人类却有珍视和保护自身及他人生命的义务,在这种思索下,托尔斯泰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托尔斯泰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治人,追求个人道德升华和全人类道德进步。”[5]就这样,托尔斯泰的“道德”也好,“完善”也好,都具有了我们现阶段的特定含义。对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也有人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并作了引申,认为“这一原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郑重告诫人们,暴力是恶。它有巨大的危害,因而要拒绝它。我们在充分考虑人的现实世界的状况后,可以把他的警告延伸为‘对于暴力,要尽量不使用,要谨慎使用。如果非得使用暴力不可,也要以达到目的为限,在达到目的时要即刻停止使用……’”[9]如果托尔斯泰知道后人对他的思想作这样的解释,会作何感想?
事实上,接受中的不断阐释、想象、转化……使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个远处的托尔斯泰,其“善、道德、恶”等的原初内涵究竟为何?我们倒恍惚起来,我们没有也无力作出阐释。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角度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探讨,打破了我们看待托尔斯泰的路径依赖。
二
别尔嘉耶夫曾坦然承认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托尔斯泰对世界的谎言性的揭露。别尔嘉耶夫说:“我最初对周围的恶和非正义的反抗,最初的对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义的向往是与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的。”[10]112在另一处他又讲:“我的一个很早的信念就是,文明的基础是谎言,在历史中有原罪,整个周围社会就建立在谎言和不公正上,这个信念就与列夫·托尔斯泰有关。”[11]430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最大的功绩就是,揭示了世界与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与不公正的基础上的。他说:“我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甚至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托尔斯泰起来反抗历史上的假伟大、假神圣,反抗所有社会关系中人的虚伪,渗透到了我的本质中。就是现在(即写作《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时的1939年——笔者注),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我还能在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初评价……还能辨认出对暴力、‘左派’‘右派’的反感。我把这看作是我身上的精神的革命性,它可以产生对周围环境的各种反应。”[11]430-431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质地中,渗透着托尔斯泰的某种情绪,托尔斯泰对历史与文明的谎言的揭露,像疫苗一样植入了别尔嘉耶夫的血液中。不过,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搞明白别尔嘉耶夫所使用的“谎言”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才能理解托尔斯泰提出的谎言问题在什么层面上影响了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又是在什么层面上理解托尔斯泰的。
在《论人的使命》中,别尔嘉耶夫指出自己所指的“谎言不是被认为是恶的那种谎言,而是那种为了善的目的而被肯定的谎言”“不是表面的谎言,……而是内在的隐秘的谎言,对自己和上帝的谎言。它是人的意识所不及的,在人的意识里,它能获得善的特征”[12]237。他认为,谎言的社会积累会变成社会规范,程式化的谎言是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自我保护的方式;为了自我保护的目的,这些社会组织认为谎言比真理更有用。别尔嘉耶夫认为,谎言有自己的标志,当谎言获得某种社会标志时,它总是被当作善;谎言在积累中获得某种被认为是善的规范性的特征;谎言被认为有益于支持和组织人类社会生活,并具有社会功能。谎言问题的悲剧就在这里。这种谎言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道德上所证明并变成了善。谎言以道德和善为特征。在政治生活中,有最大限度的谎言,它形成了生活的虚假的外围,这个伪善已经不被认为是恶,而被认为是义务。整个灾难不在于被认为是恶的谎言,而在于被认为是善的谎言,被认为是善的谎言已经充满了社会日常生活。别尔嘉耶夫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发现的正是人们面对谎言的、非真实的文明生活的分裂,“托尔斯泰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他总在描写人的这种双重生活:一种是外在的、相对的、充满谎言的、不真实的生活,人靠它来面对社会、国家和文明;另一种是内在的、真正的生活,人在其中面对的是原初现实,面对的是生命深处。当安德烈公爵仰望星空时,这是一种比他在彼得堡沙龙高谈阔论时更真实的生活。人表面的‘我’被过分地社会化、理性化和文明化了,它不是人身上的个性”[11]443。“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主要情节就是,客体化的‘我’与内在的‘我’的不同。”[13]87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创作魅力的秘密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人的客体化是别尔嘉耶夫哲学思考中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人的双重性获得了符合文明条件的规范化的特征,双重性是文明条件下作为自我保护的谎言的必要性引起的,客体化正是人对文明社会的谎言的适应。托尔斯泰对谎言的揭露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人的客体化的批判,正是别尔嘉耶夫对个性的捍卫。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正确出路”[12]237。他借以反抗谎言的途径是回归“自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自我完善”。而托尔斯泰的这个“自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自然”?托尔斯泰要回归“自然”的思想,其实反映着他深刻的宗教意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伦理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实际上,“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没有被充分深入地研究,很少有人从本质上、而非从功利主义的观点上对其加以评价。一些人带着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赞赏托尔斯泰,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另一些人带着同样的战术上实用的目的诅咒他,认为他是反基督的仆人。在这些情况下,托尔斯泰是被作为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工具而加以利用。这样,人们就侮辱了这位天才人物。在其死后对他的纪念尤其受到了玷污,他的死本身被转化为实用的工具。托尔斯泰的一生,他的追寻,他反抗式的批判——是伟大的、世界性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在永恒的价值、而非在短暂的利益之中加以评价”[10]119。因此,别尔嘉耶夫专门撰文《托尔斯泰意识中的新约与旧约》[10],从宗教意识的深层分析了托尔斯泰的“自然”观的根基。在该文中,别尔嘉耶夫从人们通常所利用的托尔斯泰的基督徒身份切入,提出问题:托尔斯泰是否是一位基督徒?他怎样对待基督?其宗教意识的性质是什么?由此出发,对托尔斯泰进行考察。他认为,不能因托尔斯泰被圣公会开除教籍就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同样不能因他被圣公会开除教籍,就仅仅看到他是恶魔的仆人,这些教权主义的实用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同样妨碍理解和评价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别尔嘉耶夫发现,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在他一生中的所有时期,都是前基督教的世界观,而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
对托尔斯泰持有此观点的不只别尔嘉耶夫一人。舍斯托夫在《列·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一文中说:“尽管托尔斯泰伯爵总是喜欢援引福音书,可他的学说里基督教成分很少。如果把他的学说与《圣经》放在一起比较,倒不如说他和他的学说与先知和《旧约》更相像。”[14]353同样,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整个处在《旧约》中,在圣父之中。这是基督之前的宗教。在基督之前,深刻的宗教意义上的个性还不存在,个性最终的形成只是到了基督的宗教。托尔斯泰像前基督教时代的人那样,与个性的意识格格不入。他感觉不到基督教的个性问题,感觉不到每一个人的唯一性与不可重复性及人永恒的命运,他没有看到个性,在他那里不存在个性,他生活在“类”的自发力量之中。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渴望完成的是圣父的意志,这是他根本的主要的东西。他继承并宣扬“山上圣训”的宗教,即旧约的宗教。新约的宗教于他是异己的和陌生的。在他看来,旧约的宗教比基督-上帝之子的宗教要好,因为旧约的宗教是教给人怎样生活,给出律法、戒律和圣训。别尔嘉耶夫强调,托尔斯泰更多地接近佛教,而不是基督教。佛教是同情的宗教,而不是爱的宗教。同情的宗教,要求人的是顺从与听从;爱的宗教,是个性的、给予自由的宗教。在托尔斯泰身上的旧约的律法宗教反对新约的拯救宗教,反对赎罪的秘密。而且,从来没有谁像托尔斯泰这样,相信人本身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轻易地完成圣父的意志,这一完成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平安。当人们承认只有通过圣子、赎罪者和拯救者才可以完成圣父的意志时,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他极其厌恶地对待赎罪和拯救的思想。他整个处于《旧约》之中,而不知道《新约》。
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摆脱文明的谎言要回到的“自然”,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主观的”自然,是自我实现与完成了圣父意志的“自然”状态。自我完成与实现了圣父意志,即是“善”的状态,即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之所以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圣父意志,达到善的自然的状态,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罪和恶,不懂得非理性的恶的自发力量,因此他不需要赎罪,也不想知道救赎者。托尔斯泰理性地苏格拉底式地看待恶,在恶中他只看到了无知,只看到了理性意识的缺陷;而不知道与非理性的自由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恶的秘密,即个性的秘密。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只要认识了善的律法,单凭这一意识,人就已经希望实现善的律法;只有失去了意识才会产生恶,恶不是根植于非理性的自由,而是由于理性意识的缺乏,是由于无知;如果知道了什么是善,就不会产生恶了;人的本性独具善的无罪的一面,之所以做出恶事来,只是因为不知道善的律法,善是明理。托尔斯泰尤其强调这一点:只有愚蠢才生出恶来,没有谁故意算计要作恶的。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看待善与恶,是理性地看待它们,把善与明理等同,恶与不明理视为同一。他认为,对圣父给予的律法的理性意识将带来善的彻底胜利和恶的灭亡。这一切将轻而易举地愉快地发生,人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
别尔嘉耶夫指出,没有谁像托尔斯泰这样抨击生活的恶与谎言,并倡导道德的极端完善,要求刻不容缓地彻底地在一切领域实现善,但是,他相信的道德完善正是与对恶的无知联系在一起。他天真地(其中却包含着天才的感召力)不想知道恶的力量、克服恶的难度以及与恶联系在一起的非理性的悲剧。他只看到,人们没有完成圣父的意志,人们在黑暗中行走,是因为他们按照世界的法则而不是按照圣父的律法生活,是人们还没有领悟他——圣父,是人们的无知和疯狂。但是,别尔嘉耶夫指出,无论如何托尔斯泰没有看到恶。如果他看到了恶并洞悉恶的秘密,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人靠自己天生的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地完成圣父的意志;更不会说,善,可以不通过赎罪赎恶就能取胜。托尔斯泰不知道罪孽为何,罪孽对他来说只是无知,只是理性的圣父律法意识的虚弱。别尔嘉耶夫再次指出,托尔斯泰不懂得恶与罪孽,是因为他看不到个性。因为恶与罪孽意识与个性意识联系在一起。人的个性被意识到,是因为意识到恶与罪孽,是因为个性与自发力量相矛盾,是因为有界限。在托尔斯泰身上,个人自我意识的缺乏也正是由于他缺乏恶与罪孽的意识。他不懂得个性的悲剧就是恶与罪孽的悲剧。意识、理智都不可能战胜恶,因为恶深埋于人身上无限之深处。人的本性不是善,而是堕落的本性;人的理智已经是堕落的理智。在托尔斯泰那里是某种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
同时,别尔嘉耶夫注意到,托尔斯泰的“自然”,一方面在宗教意识上是处于《旧约》的圣父的意志之下的“自然”,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这个“自然”又与大地、庄稼人联系在一起,与使用简单工具的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的“自然”具有了原始化和蒙昧主义的特征,具有了作为现象的自然界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主张,不应该用某种野蛮状态来对抗文明,不应该用某种无个性的自然人或托尔斯泰所认为的本性善良的野蛮人来对抗文明。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提问方式,早已过时了。文明的恶和奴役不能用善良和自然界来对抗。自然界不能对文明进行审判,这个审判只能由精神来进行。对抗文明人及其所具有的缺点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精神的人。不是单纯地使物质生活简单化、愚昧化,使人重新走回自然界来消灭文明的恶。文明处在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对抗文明的问题,不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然界,而在于要从文明走向自由。“被技术文明伤害的人盼望回归到有机的自然生活的状态,人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天堂。这是意识的错觉之一。向这个天堂返回的路是不存在的。从技术组织的生活向自然有机的生活的复归是不可能的。”[15]542“不是用‘自然界’来对抗‘文明’的谎言、社会和历史的谎言,应该用精神、精神性、本体世界来与之对抗,它们可以改变意识,并可以作为具有改造作用的力量进入这个世界。”[15]443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考察托尔斯泰是否是基督徒出发,发现托尔斯泰所要回归的“自然”是接近多神教、佛教,甚至是蒙昧主义的“自然”,他借以对抗文明的“自然”是无个性、无精神自由的“自然”。这种对抗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对抗。最可怕的是,这是对人的个性生活、创造性的精神生活的取消,因此是必须抛弃的。别尔嘉耶夫从个性、自由、精神的角度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以本体的精神的创造性介入世界以克服文明的谎言。
关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们通常都有误解,至少理解得不够深刻。批评或推翻“勿以暴力抗恶”学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任何人都明白,在勿抗恶的情况下得胜的总是恶和恶人。但是,常常人们没有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如果把人们经常忘记的忽略的那种力量的作用考虑在内,那么,“勿以暴力抗恶”学说就具有了意义——人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就会妨碍神性的作用,阻碍上帝干预人的命运。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一点托尔斯泰或许表述得不够清楚,但他坚信,在勿以暴力对抗的情况下,上帝就会亲自干预,就会以一种有效的力量介入。当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时,要么按照世界的法则,要么按照上帝的法则;世界法则是对抗和暴力,是斗争和战争。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深刻得多。这一深刻性在于,如果人不再用暴力抵抗恶,即不再按照世界的法则,那么上帝将自行干预,上帝的“自然”将行使自己的权利;只有在上帝本身起作用的条件下,善才可以获得胜利。
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学说里有大胆的真理。托尔斯泰相信,上帝自己会在世界上实现善,只是需要不违抗他的意志。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善的。别尔嘉耶夫认为,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接近卢梭和十八世纪关于自然的学说;他认为,不抗恶,善自己就会在没有你的意志参与下实现,就会出现自然的状态,在其中神的意志、生活最高的律法亦即上帝就会直接实现。不过,别尔嘉耶夫进一步分析指出,正如托尔斯泰相信自然状态的善和通过自然的力量可以实现善,在其中神性的力量会自己起作用一样,他也相信自然理性的无罪性、无误性。他不知道自然理性是已经从上帝的理性中堕落的理性。托尔斯泰坚持天真的自然的纯理性主义。在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中,总是显示着对善的自然状态的信仰,对本性与自然的东西的善的信仰。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无力解释人总是具有摆脱理性和自然状态的冲动与倾向,即非理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充满了人类生活,正是它们导致托尔斯泰产生了如此强力,抨击生活的恶和谎言。
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托尔斯泰奉行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的思想源于对生命的原始本性的信仰,托尔斯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宗教道德学说中,这一原始信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扭曲了,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基本矛盾。在托尔斯泰的学说中,自然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真理,服从于托尔斯泰的理性,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一理性完全产生于文明。别尔嘉耶夫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性”与伏尔泰的“理性”没有多大差别,也是文明对自然的暴力。于是就出现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对天然本性的善的信仰与对理性和意识的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托尔斯泰教导,不以暴力抗恶,具有神性的自然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并取胜;另一方面,他又教导,应当在自身的意识中揭示理性的法则,用它来改变整个生活、整个世界。托尔斯泰用这样一种假设来摆脱困境:意识所揭示的生活的理性法则即是善的法则本身,神性法则本身。但这也是他的理性主义的困境。托尔斯泰相信,只要认识到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真正法则就足够了。恶对于他来说是虚假的意识,善是正确的意识。他不相信恶的强有力的非理性根源。别尔嘉耶夫认为,他的本性接近佛教,他不仅不懂赎罪的秘密,还被“天性善”的学说搞得激动不已。别尔嘉耶夫发现,他对于拯救者基督的个性麻木得没有任何感觉。而别尔嘉耶夫的宗教则是以基督的个性的自由的创造实现拯救的宗教,这正是别尔嘉耶夫的超越性所在。
别尔嘉耶夫还指出,尽管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问题很重要,但其错误在于,似乎他太少关注暴力和强力的受害者。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在恶存在的条件下,在人的暴力意志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应该来保卫自由和权利,这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但别尔嘉耶夫强调,任何形式的国家绝对化,都是极大的恶。国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职能,但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意识:国家是人的公仆,而不是最高价值。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常常出现的情况却与此背道而驰。正是善在斗争中沾染了恶,并且开始采用恶的手段,这是一个魔圈。别尔嘉耶夫认为,走出这一魔圈的出路在于:上帝只能在自由中对自由并通过自由起作用,上帝在必然中对必然并通过必然就不起作用。上帝就是崇高的自由。然而托尔斯泰不明白自由问题和个性问题,因此,他走向了寂静主义即无为。这是他的无力。
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地阐释出“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本原所在。这一阐释为我们廓清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原貌及其精神实质。只有彻底地抛开功利主义的阐释,才会回到精神的本原。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M].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
[2]潘新华.对托尔斯泰宗教思想的重新认识[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5).
[3]许海燕.托尔斯泰的宗教探索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 2001(6).
[4]赵宁.托尔斯泰的乌托邦思想[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5]周振美.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宗教思想[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6]周亚明.再论“托尔斯泰主义”[J].平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7]谢南斗.老庄学说与托尔斯泰[J].俄罗斯文艺,2000(4).
[8]林学锦.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善”的重新评价[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1).
[9]雷永生.重评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4(6).
[10]Бердяев Н А.Л.Толстой[M]//Типы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и.[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III]Париж,1989.
[11]Бердяев Н А.О рабстве и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а[M]//Опыт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й этики.Москва,2003.
[12]Бердяев Н А.О назнач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M]//Опыт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й этики.Москва,2003.
[13]Бердяев Н А.Я и мир объектов[M]//Дух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осква,2003.
[14]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M].张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5]Бердяев Н А.Опыт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етафизики[M]//Дух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осква,2003.
(责任编辑刘海燕)
N. Berdyaev on Tolstoy
GENG Hai-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During our acceptance of Tolstoy over a hundred years, the more we explain, imagine and transform, the further we are from his original thinking like “kindness, morality and evilness”, etc. Berdyaev reveals the sourc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olstoy’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and explores a new way for us to know Tolstoy.
Key words:Berdyaev; Tolstoy; explanation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I106;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3-0038-06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3.008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市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宗教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近30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别尔嘉耶夫文学思想研究”(08BWW017)
收稿日期:201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