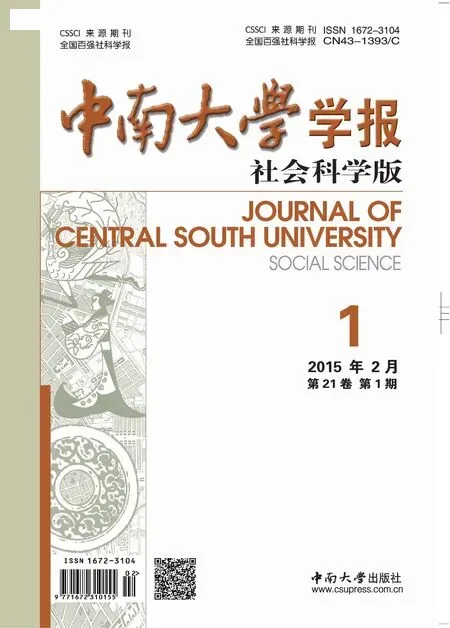论《失乐园》中亚当的正当理性与选择
2015-01-21崔梦田
崔梦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论《失乐园》中亚当的正当理性与选择
崔梦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在《失乐园》中,亚当的正当理性与选择涉及弥尔顿的古典资源与神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区分自然法与实在法,可以说明正当理性与选择之间并无抵牾。上帝赋予亚当自然法,使其可以遵从正当理性。但是有关知识树果子的命令属于实在法,与正当理性不自动相合,因此亚当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失乐园》中自由选择(free choice)与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之间实有差异:前者对应亚当自由选择的能力,后者则是他遵从正当理性的结果。亚当在吃知识树的果子时,行使了自由选择,但他选择的是夏娃,而非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一事件的后果之一便是正当理性被蒙蔽,亚当从此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弥尔顿;《失乐园》;正当理性;自由选择;真正的自由
弥尔顿在使用理性一词时,有时指正当理性,有时指选择。弥氏古典思想资源丰富,且具备深厚的神学知识,他可以使二者并行不悖地统一在一起。但批评家们对于这两方面,向来各有侧重。关于弥尔顿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正当理性与选择之间潜在的矛盾反而越来越难以调和,持不同看法的评论者甚至失去彼此讨论的余地。在《失乐园》中,由于亚当趋于理性的认知方式,正当理性与选择之间的矛盾毫无保留地集中在他身上,二者间的张力于亚当在知识树下的激烈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将仔细分析文本,并结合17世纪的思想语境,探讨弥尔顿如何处理正当理性与选择之间的矛盾,使之共存于他的诗歌之中。
一
在第十二卷中,米迦勒提醒亚当时,非常明确地将正当理性与自由联系起来,他如此解释道:
自由总是和正当理性
孪生,并不能离理性而独立存在。
人身上理性晦暗了,或没有遵守,
没有节制的欲望和一时冲动的激情
马上就抢走理性的统治
权力,并把到那时还自由的人
降为奴隶。①
(True liberty) always with right reason dwells
Twinned, and from her hath no dividual being:
Reason in man obscured, or not obeyed,
Immediately inordinate desires
And upstart passions catch the government
From reason, and to servitude reduce
Man till then free. (XII. 83-90)②
在上述引文中,理性,或曰,正当理性被置于极高的地位,人若不服从理性,容易沦为各种欲望与激情的奴隶。这段话常被早期思想史或观念史学者引用,作为弥尔顿对正当理性的定义。尼科尔森便据此将弥尔顿的正当理性总结为,“一种内在天赋,乃人类与上帝共有,可绝对可靠地判断正误(an infallible judge of right and wrong),并指挥命令意志、本能与欲望。”[1]如果仅仅根据十二卷的引文,尼科尔森的概括没有问题。但笔者的关注点在于亚当如何看待正当理性。《失乐园》的第九卷里,当夏娃提出劳动分工的建议时,亚当如此告诫道,
上帝让意志自由;因为服从
理性是自由,而理性他造得正确。
但嘱咐她千万当心,永远要警惕,
不然,受金玉其外的东西的袭击,
她就信口雌黄,并唆使意志
干上帝显然禁止的事情。
……
因为理性不是不可能碰到
敌人虚构的似是而非的事物,
只要不听从警告,不提高警惕,
一不小心那就会上当受骗。
But God left free the will, for what obeys
Reason, is free, and reason he made right,
But bid her well beware, and still erect,
Lest by some fair appearing good surprised
She dictate false, and misinform the will
To do what God expressly hath forbid.
…
Since reason not impossibly may meet
Some specious object by the foe suborned,
And fall into deception unaware,
Not keeping strictest watch, as she was warned.
(IX. 351-63)
也就是说,此时,在亚当的眼里,上帝使得理性正确,意志若服从理性便可自由(这与米迦勒所说相似)。但理性并非无懈可击,她亦可能遭遇伪装,做出错误指挥,从而使得意志违背上帝的禁令。亚当认为理性可能犯错,米迦勒并未谈及此话题,尼科尔森所概括的正当理性“绝对可靠”(infallible)之特点与亚当的观点出入更大。那么,问题出现了:这一出入的形成是因为亚当的认知有偏差,还是弥尔顿对正当理性态度模糊所致,或者是尼科尔森以偏概全?
另外,弥尔顿多次将理性与选择联系。例如,在《论出版自由》中,他直接断言,“上帝赋予人理性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性就是选择。”[2]他后来在《失乐园》的第三卷重复了这一说法,再次强调“理性也是选择”(III. 108)。尼科尔森当然注意到了这些诗句,基于对正当理性的如上理解,她认为, 对于弥尔顿来说,理性即是选择,“事物本身有好有坏;理性控制着激情,它透过事物的表面洞察内在的真实”(419)。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如尼氏所说,正当理性“绝对可靠”,那亚当只需完全服从其引导即可,选择与自由又何从谈起呢?尼科尔森是著名观念史研究者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的学生,她是较早关注弥尔顿与17世纪思想史联系的学者,她的观点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受她影响的学者对于正当理性之强调近乎绝对③。此外,与剑桥柏拉图学派一样,尼科尔森认为,即使上帝也必须遵从正当理性,不能做违背自然法(law of nature)之事(433)。她讨论弥尔顿、霍布斯以及剑桥柏拉图学派的文章写于1926年,前面提的几个问题在她那里似乎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正当理性”与“选择”是弥尔顿对于理性的两种阐释。但现在看来,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毫无保留地集中在亚当身上:按照尼科尔森的说法,知识树下的他若遵从正当理性,便不会吃果子,但如此一来,他的选择与自由表现在何处?尼科尔森将选择理解为对理性、意志、激情以及欲望进行排序,并最终遵从正当理性,但她又认为,正当理性绝对可靠,可以指导意志、激情与欲望,这样一来,整个选择过程是不是形同虚设?韦利(Basil Willey)以及后来的很多学者均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在《17世纪的背景》一书里,韦利将正当理性与自然法概念(law of nature)联系起来,并引用《论基督教教义》中的话解释道,“自然法本身可以很好地指示人们做那些与正当理性符合的事情。”但他紧接着又引入“实在律”(positive law)概念,并指出,在弥尔顿看来,上帝禁止亚当吃知识树的果子以及关于婚姻之命令均属于实在律的范畴,不受自然法的制约。[3]韦利强调的正是尼科尔森忽略的方面,关于这一面,弥尔顿在《论基督教教义》中有过清楚的论述。在他看来,人以上帝的形象被造,被赋予整个自然法,此法内在于他,因此他并不需要其它指令来遵守。但关于知识树上的果子以及婚姻的律令属于实在律,本质上与正当理性无关,否则的话,自然法本来可以告知亚当如何行事。因此,上述两条律令并不包含在自然法的范畴内。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两条律令于上帝而言,是任意(arbitrary)的。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弥尔顿坚持认为这两条律令的任意性是必要的,如若不然,对于自然法下的命令,人会自动遵守。基于此,弥尔顿认为,作为顺从标准存在的命令,只因上帝的命令或禁止生效。如果上帝没有命令或禁止,这些律令就其自身而言,不管怎样,原本既非善亦非恶,本不对任何人具有约束性。[4]韦利等学者的论述,基于《论基督教教义》,很有说服力。在2005年出版的《弥尔顿与堕落的观念》一书中,普尔(William Poole)在该问题的讨论中仍然沿袭了韦利的看法。[5]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自然法与实在律不仅涉及神学,也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杰斯(John Rogers)将此一问题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区分了弥尔顿在政治哲学与神学领域对于自然法的不同阐释:在政治领域,他反对实在法,倡导人遵从自然法,一个理想国度中的法律也不可违背自然法;但在神学领域,他强调,上帝关于知识树果子的命令属于实在律,具有任意性特征,惟其如此,人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6]由此可知,弥尔顿在政治与神学上的看法往往彼此关联却又各有差异,极易引起误解,因此在关键问题上确实应该像罗杰斯那样,谨慎地对二者进行区分,以免造成混乱。
韦利、普尔、罗杰斯等学者对自然法与实在律的区分,从神学的维度进行讨论,对一向侧重弥尔顿古典思想资源的批评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疑问也很有帮助。首先,在第九卷中,亚当之所以提到,正当理性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原因并非其本身不完善,而在于他记挂于心的“上帝明确禁止的事情”并非自然法的范畴,因此无法自动与正当理性相合。另外,恰恰是在无法与正当理性相合的实在律这里,选择的意义才真正得以凸显,而且这一选择极其重要,它实际上是亚当对上帝顺从的唯一纪念(memorial),⑤这样的理解才符合弥尔顿对选择的一贯看法。如我们所知,在《论出版自由》中,他曾说道,“上帝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a perpetual childhood of prescription),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性来选择(trust him with the gift of reason to be his own chooser)。”⑥可见,选择于弥尔顿的意义,恰在于它不是规定好的,虽具有极大风险,但是上帝仍信任亚当,将之视为礼物赐予他。这个意义上的选择极易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选择的讨论。斯图尔特(J. A. Stewart)在对该书的注释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能力,它“使一个人在所面临的危险中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意味着在当下显得令我们愉悦然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与本身就有益于善的目的的事物之间做出决定。在这种概念下,选择常常是一种困难的决定,它包含着对当下的快乐的一个判定和处理:如果它总体上有害,就放弃它”。[7]可见,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选择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样,弥尔顿使亚当面临的选择更不轻松,甚至正当理性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甚至不无危险的局面,这种困难或危险在第八卷中开始略显端倪。
第八卷的末尾,亚当向拉斐尔倾吐了自己的矛盾:许多感官乐趣都不能令他心动,但夏娃不同。他理智上明明知道相较自己,夏娃在内在天赋与头脑上都略逊一筹,但一旦靠近这位可爱的伴侣,她“看来竟那么完美/本身就完备无缺”。(VIII. 547-548)于是,亚当承认道:
一切高等的知识在她面前都相形
见绌;“智慧”跟她说话都惊惶
失措,羞惭满面,显得象“愚蠢”;
“权威”和“理性”只配给她当侍从。
All higher knowledge in her presence falls
Degraded, wisdom in discourse with her
Looses discount’nanced, and like folly shows;
Authority and reason on her wait, …(VIII. 551-554)
这便是亚当的困境了,他的认知在可爱、完美的夏娃面前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有的知识、智慧、权威、理性似乎都派不上用场。面对亚当的困惑,拉斐尔十分谨慎地强调了爱(love)与情欲(passion)的区分,告诫亚当要使爱居于理性之中,并为他指出清晰的方向:应当遵守上帝“伟大的命令(His great command)”,不可为“激情(passion)左右判断”(VIII. 635-636)。联系前面亚里士多德对选择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亚当即将面临的选择正是在于“当下显得令他愉悦然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激情或情欲)与“本身就有益于善的目的的事物”(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两者之间。这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如前文所论述,上帝的这一命令是任意的,与亚当的正当理性不自动相合,而情欲却通过那可爱的伴侣——夏娃具体呈现出来。这样艰难的选择,亚当将何去何从?
二
《失乐园》第九卷是全诗的高潮,但知识树下的亚当只说了两段话。在第一段独白(IX. 896-916)中,他在哀叹夏娃违反禁令后,迅即坚定了与夏娃同死的决心:“我也跟你遭了殃;因为,我的 / 决定当然是跟你生死与共。”(906-907)其后,他的独白以及对夏娃说的话则是在这一决心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论证,主要论据如下:首先,夏娃若遭遇不测,他无法接受另外一个夏娃;其次,自然的联系(the link of nature)(914)——或曰自然的纽带(the bond of nature) (956)——已将他们二人紧紧连结在一起,他们应同赴患难;第三,或许夏娃不一定会死(因为蛇吃了果子后仍然活着), 甚至还可能获得相应的高升(proportional ascent);第四,或许上帝并不会真令他们死亡,因为这将招致敌人的嘲笑。最后,他再次表示自己心意已决,如果夏娃遭遇死亡,他将义无反顾地一同赴死。亚当虽然具有优秀的推理能力,然而,不难发现的是:此处,他的推理都基于自己已下的决心展开,观念先行的论证再严谨,可供参考的价值终究有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亚当的选择,学者们向来众说纷纭,看法不一。这里大概回顾一下批评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几种看法。
汉福德(James Holly Hanford)在1926年首次出版的《弥尔顿手册》中说明,弥尔顿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学派等古典学者的影响。同先哲们一样,弥氏认为,人的灵魂中存在着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因此亚当的堕落在于情欲战胜了理性。[8]在1942年首版的《简论〈失乐园〉》中,路易斯试图用另外一个词解释亚当的犯罪原因——溺爱妻子(uxoriousness)。另外,他认为亚当的堕落原因相对崇高些,因为他选择的是较易被读者理解的价值。但作为一个有柏拉图主义倾向的基督教思想家,路易斯十分谨慎地提醒道,“如果在亚当的世界里,婚姻之爱是最高价值,那么他的决心无可厚非。但如果某些存在对人有更高一层的价值要求,如果宇宙被想像为另外一个图景——在那里,当紧要时刻来临(即那更高要求必须被兑现时),人应该为之放弃妻子、母亲、甚至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下,如果亚当成为夏娃的同谋,便不是在帮她了。”⑦路易斯洞察力极强,他继续指出,亚当的困难还在于他无法确知:如果他不选择与夏娃一同赴死,整个事件是否存在其它可能性。其实,这也是弥尔顿本人的困境,因此他在第九卷919行说道,这事“看来已经无法弥补”( seemed remediless),以此表达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疑惑。[9]路易斯的评论一波三折、发人深省,这确实是一个无确定答案(因而必然导致多种解读)的问题。1968年,福勒(Alastair Fowler)在为《失乐园》做的注释中,对第九卷914-915行进行了极其敏锐的评价。他指出,亚当此处暗示的仅仅是肉体(flesh)以及情感(heart)上的联合,与此前第八卷499行中所说的“同一体,同一心,同一灵”(one flesh, one heart, one soul)形成微妙对比,暗示此时亚当与夏娃已不再具有同一个灵。[10]相较之下,福勒注释里提到的伯登(Dennis Burden)要绝对得多,他引用霍尔(Joseph Hall)的话,对于亚当所说的“自然的联系”如此批评道,“对于不承认自然之上还有其它力量的人,自然或许是个好托词,但这不应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借口。”[11]这一立场诉诸高于自然的存在,与路易斯的看法有些相近。相较之下,达姆罗施(Leopold Damrosch, Jr.)对亚当则更加同情:在《上帝的情节与人的故事》一书中,他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作为参照,后者在思考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历时发现,这个故事的宗教意义超越了其伦理或美学意义。达姆罗施冷静地评论道:一方面,在弥尔顿看来,毫无保留地爱另一个人,哪怕对方完美如夏娃,也是一种自爱的表现,因为只有上帝配得上人全部的爱;而另一方面,那些声称亚当本来可与夏娃离婚,不与之一同犯罪的说法在神学上正确无误,但在观念上难以接受,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想像另外一种可能。[12]以上几位评论家的看法使得亚当选择的复杂性得以更全面、具体地呈现:批评者多采取同情之理解,即便绝对者如路易斯、伯登,言语间依然留有余地,采取了信仰与世俗两分的讨论方式。对于亚当来说,上帝的禁令极其明确,他当然深谙其中之厉害关系,但夏娃对他来说绝非可轻易放弃之人。更何况,他无法确知如果他不吃果子,整个事件是否会有其它可能。可以说,亚当现在面临的选择与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的困境并无二致:在这样紧张与艰难的选择面前,基督教传统中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义与古典资源中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互相撕扯,产生巨大的张力,深化了史诗的主题。
三
再看第九卷末尾:经历极其沉重的斗争后,亚当选择了夏娃。他接着做的便是在自己列的第三、四个论据里将那唯一的禁令相对化——或许上帝不一定让他们死,并进一步表达了愿与夏娃同死的愿望。夏娃十分感动,她赞美起那果子的功效,认为它“提供了有关亚当爱情的这幸福的考验,否则/决不能得到如此卓越的认识”,并由此感叹说:“善仍由善而生, 不论直接或间接。”(IX. 973-976)对比本卷752行中夏娃所说的“知识树,不但能知善而且能识恶”,我们可以发现,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夏娃将果子关于恶的功能完全略去了。感动之余,她拥抱了亚当,喜极而泣,丈夫为了她,宁可选择触犯上帝甚至死亡(IX. 992-993),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于是她伸手摘下果子,给亚当也吃了。992行中的“选择”(choice)一词直接、明确地昭示了亚当的动机。惟恐说得不够清楚,诗人又在997-999行引用《圣经》的话解释道,“(亚当)违背他更好的知识,并非受欺骗,/而是愚蠢地拜倒于女性的魅力(female charm)。”因此,同前文分析的那样,亚当是在对夏娃的情欲与顺从上帝的命令之间选择了前者,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亚当对夏娃的爱情确实令人动容,我们虽然不愿承认,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当下显得令人愉悦然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与本身就有益于善的目的的事物之间,亚当选择了前者。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在至善(supreme good)与其它性质的善之间,亚当选择了后者。
回到论文一开始讨论的正当理性与选择的冲突,如前文论述,韦利等学者通过区分自然法与实在律,肯定了“理性也是选择”的实际意义,使选择不像尼科尔森阐释的那样形同虚设。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亚当违反禁令后便清晰地暴露出来。韦利不无尖锐地指出,在弥尔顿这里,当亚当服从或顺从正当理性时,他是自由(free)的;而当他行使不加限制的自由选择时,他离开了上帝,自动地失去了自由(automatically ceases to be free)。更可怕的是,在韦利看来,弥尔顿在诗歌中需要将作为概念的正当理性替换为上帝这一具体形象(picture-God)。如此一来,上述逻辑便演变为:亚当顺从上帝时,他是自由的;而当他行使自由选择时,离开了上帝,从而失去了自由。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亚当行使的自由选择和他之前顺从上帝时的自由有什么不同?正当理性与选择是弥尔顿对理性做出的两个不同阐释,但是不是这两个概念无法共存于诗歌中呢?亚当面临的处境是一个自由的悖论吗?这些都是笔者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 而回答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回溯到17世纪的思想语境。
17世纪中后期的许多思想争论都集中于学者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自由选择。例如,神学兼容论者(theological compatibilists)承认自由选择,但同时他们又在其思想体系中融入必然性因素。在《弥尔顿的良善的上帝》中,丹尼尔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弥尔顿与神学兼容论者的观点差异巨大。许多批评弥尔顿自由选择论自相矛盾的学者,都忽略了诗人一直坚持的非兼容论立场,并且混淆了可以从善恶间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free will)与正当理性所对应的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之间的微妙差异。丹尼尔森认为自由意志论者所说的自由(libertarian notion of freedom)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 前者指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后者则涉及与正当理性一致的选择。⑨其实,韦利的问题也集中在这个地方:亚当行使的自由选择和他之前顺从上帝时的自由是相同的吗?如果不同,差异何在?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韦利提出的质疑进行回答。
首先,弥尔顿不是神学兼容论者,他在《论基督教教义》中曾经明确说过,“在自由的概念中,……所有必然性的想法必须被排除出去。”⑩另外,在《失乐园》第三章,弥尔顿通过上帝之口说道,“意志与理性(理性也是选择)/ 备而不用,两者就贬损自由,/ 使两者都显得被动,这服从了必然(necessity),不是我。”(III.108-111) 可见,弥尔顿关于自由的思想无法与必然性兼容。在这一点上,弥尔顿与霍布斯(典型的神学兼容论者)存在着根本差异:霍布斯认为自由(liberty)与必然(necessity)可以融合。在霍氏那里,人必然会选择他选择的东西,自由(liberty)仅意味着摆脱外在的阻碍遵循这必然的选择。只有理解了弥尔顿与霍布斯等兼容论者在自由观上的巨大差异,才能在接下来讨论问题时不至陷入混乱。
其次,回到韦利提出的问题:亚当行使的自由选择和他之前顺从上帝时的自由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弥尔顿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异,米迦勒在第十二卷83行中论及遵从正当理性方能享有真正自由时,他用的词是true liberty。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意志自然是free will(IX. 351),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道,“上帝给人自由来选择(freedom to choose)。”[13]看来,弥尔顿在使用“freedom to choose”与“true liberty”这两个表述时,十分谨慎,颇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实际上,这一区分并非是弥尔顿独树一帜之处,因为在奥古斯丁那里,这两个表达就代表不同的意思。吉尔松(Gilson)对奥古斯丁关于上述两词的区别概括为:“使用自由选择(free choice; liberum arbitium)的能力来选择善的目的才是自由(liberty; libertas)。能够作恶是自由选择(free choice)的证据;能够不作恶也是自由选择(free choice)的证据;但是当通过神恩得到确认,到达无法作恶的境界是最大程度的自由(liberty;libertas)。”[14]
这个区分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弥尔顿的意思:亚当遵从正当理性是以选择遵守上帝的命令为前提的。当亚当自由地选择遵守上帝的命令时,他才可能遵从正当理性,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 而当他自由地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时,罪的后果之一即是正当理性被蒙蔽⑪,他因此失去了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所以,米迦勒在第十二卷中这样说,“自从你原先一失足,真正的自由已丧失。”(Since thy original lapse, true liberty/Is lost.) (XII. 83-84) 可见,失去与正当理性对应的真正的自由,是亚当自由地选择违背上帝命令的后果之一。韦利没有意识到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认为弥尔顿给出了一个“freedom from freedom”的悖论。实际上,正当理性与自由选择在弥尔顿那里并不冲突,但常有学者认为它们矛盾的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与奥古斯丁以及弥尔顿理解的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实在是相去甚远。对于奥古斯丁与弥尔顿来说,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是合理运用自由选择(free choice)产生的结果。因此,法伦认为,从现代的角度看,相比较自由(freedom),它(true liberty)实际上更接近于必然(necessity)。⑫
第三,韦利还质询道,如果用上帝代替正当理性,结果更加可怕。但之前的讨论说明,在弥尔顿这里,不能自动将上帝等同于正当理性,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剑桥柏拉图学派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即使上帝也必须遵从正当理性。但对弥尔顿来说并非如此。按照法伦的论证,一旦决定创造世界与人,上帝受“有条件的必然性”(conditional necessity)的制约,创造活动必须是完美的。但在创造之前,他可以自由选择创造还是不创造。[15]因此,在弥尔顿这里,不能像尼科尔森阐释的那样,想当然地将上帝置于正当理性的支配之下,认为上帝必须做符合自然法的事情。在《失乐园》第七卷的171-173行,上帝明确说过,“践行与否,任凭自由,偶然/和必然,与我无缘,我的意志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依此逻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在正当理性与上帝之间划等号。
四
在以上讨论中,笔者不惜笔墨论证正当理性与选择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如果这两个概念中有一个不能存在与成立,那么亚当在知识树下经历的斗争便变得虚假、无意义。弥尔顿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沦为机械般的存在,服从于必然性,他在《论出版自由》中强调过,如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亚当就会变成一个虚假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he had bin else a mere artificial Adam, such an Adam as he is in the motions)。”(CPW, Vol. II, 527)而事实上,首先,亚当本来有可能自由地选择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样的话,他便可以遵从正当理性行事,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其次,亚当自由地选择了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导致犯罪。罪的后果之一便是正当理性的匮乏或蒙蔽,他因此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尽管如此,选择的能力与权利仍是上帝赋予亚当的极其珍贵的礼物,反映出他对亚当能动性的充分尊重。这一点是理解弥尔顿之神学及哲学思想至为重要的钥匙,也是他晚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综上所述,正当理性与选择之间的张力赋予《失乐园》极其丰富的内涵,也使得亚当在知识树下的斗争得到更丰满的呈现。
注释:
① 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参考该史诗其他译本:刘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朱维之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注:本论文中关于《失乐园》的译文均出自金发燊的译本,一些地方根据原文及另外两个译本有所改动,下文只标明卷数与行数,不再另行加注。
② William Kerrigan, John Rumrich, and Stephen M. Fallon (eds.),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7), p.197. 参考其他版本:Alastair Fowler (ed.),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1)。本文中关于《失乐园》的引文均出自以上两个版本,下文只标明卷数与行数,不再另行加注。
③ 法伦(Stephen Fallon)认为: 相比较自己的老师洛夫乔伊,尼科尔森对弥尔顿的思想更为同情,但她认定弥尔顿的思想类似于柏拉图学派,忽略了弥氏与后者的差异。参见Stephen M. Fallon, Milton among the Philosoph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p. 13. 受尼科尔森影响的学者有布什(Douglas Bush)、胡普斯(Robert Hoopes)、明茨(Samuel I. Mintz)等。
④ 这一点显然与尼科尔森的观点有差异,因为在尼氏的看法中,弥尔顿认为“自然法是一切之根源,是一切行为之准则”,参见Marjorie Hope Nicolson, “Milton and Hobbes,”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23, No.4 (Oct., 1926), p. 433。
⑤ 福勒在对《失乐园》第三卷94及95行做的注释中,引用《论基督教教义》中的话解释说,“善恶树不是一个圣物(sacrament),…… 因为圣物是被使用、而不是被禁止的东西,它实际上如同一个信物(pledge),是对顺从的纪念(memorial)。”福勒认为弥尔顿的这一看法符合基督教传统,与圣奥古斯丁的观点相近。参见Fowler, p. 148。
⑥ 斜体与黑体乃笔者所加。英文原文引自Earnest Sirluck, ed.,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514。
⑦ 路易斯的评论与奥古斯丁的观点相近。在《上帝之城》第12卷第8章中,奥古斯丁如此说道, “(The defection of the will) is a turning away from that which has supreme being and towards that which has less. . . . Hence, he who perversely loves the good of any nature whatsoever is made evil through this very good even as he attains it, and is made wretched because deprived of a greater good.” 也就是说,意志的变节是从至高的存在转向较低的存在,……因此,若有人离弃至善,执迷于任何其它性质的善,即便最终获得它们,他也会因这不完美的善而变为恶,而且会由于失去至善而变得不幸。以上英文引自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 and trans. R.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pp.508-509。
⑧ 斜体与黑体乃笔者所加。参见Basil Willey,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3rd ed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6), p. 228。
⑨ 在148页提出这一解释后,丹尼尔森在254页注释的第37条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看法。参见Danielson, p.148;p. 254。
⑩ 参见Danielson, p. 139。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论基督教教义》的英语翻译,各个版本之间有时会有差异,正文中这句话的翻译出自耶鲁版散文全集。牛津全集版与之基本一致,英文译文为:“all necessity must be removed from our freedom.”拉丁文原文为: “Omnis igitur a libertate necessitas removenda est.” (De Doctrina Christiana, Part I, pp. 60-61)。但休斯的版本则不同( M. Y. 休斯:《约翰·弥尔顿诗歌全集和主要散文》,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第914页):“the liberty of man must be considered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necessity.” 笔者认为这里用“liberty”并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解。需要说明的是,休斯编的全集中,《论基督教教义》选自萨姆纳(Bishop R. Sumner)1825年的译本,该译本质量如何,笔者无从置喙。但丹尼尔森在《弥尔顿的良善的上帝》143页中直言,尼科尔森论霍布斯与弥尔顿的文章中,将弥尔顿与神学兼容论者的观点混淆,正是由于她是根据萨姆纳糟糕的翻译(bad translation)进行推断的。
⑪ 在《论基督教教义》中论及罪的惩罚时,弥尔顿提到四种程度的死亡,第二种乃灵性死亡(spiritual death)。这一死亡的表现之一即是正当理性之匮乏,或者至少可以说,正当理性处于严重麻木状态。([spiritual] death is located, first, in the privation, or at least the serious dulling, of right reason)。参见De Doctrina Christiana, Part I, p. 433。
⑫ 参见Stephen M. Fallon, “ ‘To Act or Not’: Milton’s Concept of Divine Freedo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9, No. 3 (Jul.-Sep., 1988), p. 427。
参考文献:
[1] Marjorie Hope Nicolson. Milton and Hobbes [J]. Studies in Philology, 1926, (4): 419.
[2] 约翰·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 [M]. 吴之椿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7.
[3] Basil Willey.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3rd ed [M].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6: 224−225.
[4] John K. Hale, J. Donald Cullingt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ume VIII: De Doctrina Christiana, Part I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59−361.
[5] William Poole. Milton and the Idea of the Fall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3.
[6] John Rogers.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Milton’s heaven [C]// The New Milton Criticism. Eds. Peter C. Herman and Elizabeth Sau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7−78.
[7]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xxix.
[8] James Holly Hanford. A Milton Handbook, 4th ed [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6: 233.
[9] C. S. Lewis. 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127.
[10] Alastair Fowler.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68: 491−492.
[11] Dennis H. Burden. The Logical Epic: A Study of the Argument of Paradise Lost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67.
[12] Leopold Damrosch, Jr. God’s Plot & Man’s Storie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10−111.
[13] Earnest Sirluck, ed.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II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527.
[14] Etienne Gil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5: 79.
[15] Stephen M. Fallon. “To act or not”: Milton’s concept of divine freedom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8(3): 438.
On Adam’s right reason and choosing in Paradise Lost
CUI Meng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In Paradise Lost, Adam’s right reason and choosing involves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Milton’s classical thoughts and theological ideas. The article, by distinguishing positive law from the law of nature, contends that right reason and choosing are not contradictory. God implants the law of nature in Adam to teach him things agreeable to right reason, while God’s command about the Tree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the positive law which is not intrins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right reason. Thus, Adam can make a choice in the real sense. Moreover, the free choice (or freedom to choos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rue liberty in the epic.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free choosing, whereas the latter denotes the outcome of choosing in accordance with right reason. In tasting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Adam exercises his freedom to choose, yet what he has chosen is Eve rather than obeying God’s command.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event is the privation of the right reason and Adam henceforth loses his true liberty.
Milton; Paradise Lost; the right reason; free choice (freedom to choose); true liberty
I059.9
A
1672-3104(2015)01−0204−07
[编辑: 胡兴华]
2014−09−25;
2014−12−20
崔梦田(1983−),女,山西永济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17世纪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