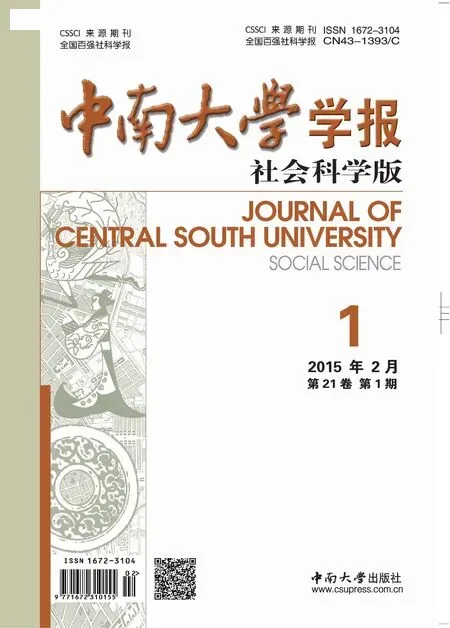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
——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2015-01-21武良军
武良军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
——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武良军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缓解当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时所面临的尴尬。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主要通过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来实现。习惯法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具有较大运行空间,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构成要件解释时,其他要素或要件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由于违法的判断是实质的、具体的,故习惯法在此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分析。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用很小,更合适的路径应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然目前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制定法;习惯法;教义学;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的理路
应当说,不论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是在我国法制发展相对发达地区,习惯法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真实存在着。[1](54)由于制定法与习惯法各自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的巨大差异,对同一行为之评价常有抵牾与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常有某行为在习惯法上被认为是正当但制定法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反之,某行为被习惯法认为是“犯罪”而制定法不作评价的情形亦有之。对于后一情形,因依1997年刑法典确立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在制定法上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自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实践中也罕有异议。然而,对于前一情形,究竟是要舍习惯法于不顾还是应弃制定法于一旁,司法人员时常倍感困惑。让我们先看下面三则事案。
(一) 案例与问题
[案例1] 地处云南的哈尼族有一习俗,如果几个小伙子看到长得好的姑娘就会一同上去用手乱摸,在当地看来这并不是对姑娘的凌辱,反而表示姑娘很受欢迎,俗称“然民干”习俗。一天,几个汉族男子在乘车时看到两个哈尼族小姑娘坐在路边,便商量好去摸,把这两个小姑娘弄得乱叫,内衣也被扯掉了。该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对于行为人是否因习俗不成立犯罪,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存在激烈分歧。[2](323)
[案例2] 家住重庆市某区长期在工地守夜的丈夫张某发现,妻子李某与佃租户中一工程师王某有暧昧关系,但一直没有抓住两人奸情的证据。后,张某于某夜悄悄溜入家中,将李某与王某捉奸在床。于是,张某提出要王某拿几十万来“了事”,否则便不客气和要报案。经过“协商”,王某答应拿出4万元作为补偿。然半年后,王某向警方报案称被敲诈勒索。后,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3]
[案例3] 每当稻田里的谷子渐渐饱满成熟之际,便会有成群的麻雀来抢食,有时成群地在同一片地里啄谷子,若不加以制止,很快便会颗粒无收。庄稼汉陈某想了诸多办法驱赶均不能奏效,出于无奈用粘网捕杀,不出几天便粘到上百只麻雀。因陈某听说麻雀可卖钱,便将捕捉的麻雀卖给了收购麻雀的商贩。后此事被民警知晓,以涉嫌非法狩猎罪将陈某刑事拘留。听说陈某被抓,乡民十分不解,认为不构成犯罪。
显然,以上事案向我们直观展现了实践中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对于类似事案的处理,既有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过去实践中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做法,即司法人员常以“刑转民调解”“不立案”等方式将案件堵截在正式司法程序的入口,从而将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冲突遏制在萌芽状态,避免案件进入正当司法程序之后的正面冲突,即使案件最终进入司法程序,也会以各种方式避免制定法的直接适用。[1](124−126)案例2的捉奸事案即如此。[4]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在我们过去的刑事司法语境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及传媒方式发展带来法律知识的普及,刑事司法语境已有较大改观,这一做法也正渐显尴尬。因为,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和转型深入导致习惯规则对当事人约束力的式微,当事人因对利益之追求而在司法人员主导下就案例处理的合意已越发难以达成,进入正式司法程序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此时,当司法人员再像既往那样依习惯法努力给当事人讲“情理”时,却发现当事人却在努力给法官讲“法律”。[5]质言之,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正面冲突增多,而过去那种对于处理两者之间幕后冲突颇为有效的做法,已然不能再有效应对这些逐渐走向台前的冲突。
(二) 分析的理路:法教义学路径的提倡
对于这种冲突正面化的增多,或许有见解想到了习惯法的制定法化。且不说这一路径是否会使习惯“失去其作为习惯的活力”[4],至少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在目前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97刑法第90条的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权在实践中虚置就是例证。况且,对于司法人员来说,追求立法的方式过于“遥远”,他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目前该如何具体面对这些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事案?如何使这些事案的处理既能考虑习惯法的特殊性,又不与制定法发生抵牾,同时还能经得起刑法学理的深层检验?
在笔者看来,要想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回到法教义学路径上。所谓法教义学的路径,在部门法刑法中又称刑法教义学路径,主要是指以现行有效的刑法规范为基础和界限,通过对法条的概念性内容和构造的阐释来解决具体个案,并尽可能使裁判知识体系化的进路。[6](53)重视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提出解决个案的建议和对裁判知识体系化的研究是法教义学三个最为核心的内容。根据教义学的要求,犯罪的成立与否必须合于现有刑法规范及根据现有规范发展出来的概念、体系和判断规则。对于具体事案中涉及的习惯法因素,我们既不能在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时全然忽视,也不能直接作为成立或者否定犯罪的理由,而须将其判断“能够融入既有的刑法体系,并关涉犯罪成立各项条件中的某个要素,才能对刑事责任成立或排除发挥影响力,否则仍然仅是外于犯罪结构的文化或族群感情问题”[7]。换言之,对于事案中习惯法的判断,必须要在体系化的犯罪构成下探讨。
目前,大陆刑法学界就犯罪构成体系有“四要件说”与“三阶层说”的争论,孰优孰劣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也不影响事案分析的结论。然而,体系的选取无疑会影响本文的论述方式与进路,故有必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在笔者看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通说采取的是耦合式的、平面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尽管其存在有其合理之处,但难以反映犯罪构成的层次性与位阶性[8](94),在方法论上较之于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递进式的、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欠缺科学性;此外,在行为出罪与入罪问题的判断上,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较四要件体系更为明晰与合理。鉴于此,下文拟以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分析结构阐述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在刑事制定法中的运行逻辑,并结合前述事案详细分析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即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性的判断与有责性的判断中习惯法的判断路径和作用空间。
二、构成要件解释中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根据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犯罪的成立要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三个层次的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无疑是犯罪成立判断的首要要件,若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规定,即使行为具有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将其作为犯罪论处。
(一) 路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开放的构成要件
在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初期,其始倡者贝林格主张构成要件乃是一种“纯粹记述的”“完全不包含价值判断”的要件。[9](112)对于构成要件即使认为存在解释,也无需进行价值判断,只要进行事实判断、知觉的、认识的活动即可确立。[10](110)所以,富含价值判断的习惯法在构成要件解释中难有存在的余地。然而,随着人们对构成要件理论的不断认识,理论上普遍主张除记述构成要件要素以外,还存在一些在解释时需要法官的规范评价、补充价值判断才可确立的要素,即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就“猥亵”的概念来说,尽管判例与学说将其定义为“引起性的兴奋或刺激性欲,危害普通人的性的羞耻心并违反善良的性的道德观念”,“但是单凭此定义并不能认定猥亵,还必须经过一般的社会文化的评价才能予以认定。”[11](112)由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依赖于法官价值上的评判,而且这种价值的评判又依赖于“一般人的社会文化的评价”,所以这也给习惯法的判断在此要素的解释中提供了空间。诚如有见解所言,“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生活共识的重要载体,习惯规则在法官的这种评价与解释中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价值。”[1](202)
是故,对于案例1中的几位被告是否该当《刑法》第237条“猥亵”的判断,就需依“社会文化的评价”,即要“参照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与习惯规则而加以确定”。[1](202)对于哈尼族来说,由于存在“然民干”习俗,哈尼族男子对看上的哈尼族女子进行乱摸并不被认为是对健康性风俗和习惯的违反,反而会认为这姑娘漂亮而受到更多人喜爱。因此,族人之间,男子对心仪女子的乱摸并不违反哈尼族一般人对性的羞耻心和善良的性道德观念,进而也就不能将类似行为认定为“猥亵”。但习惯法规则有地域属性和时间属性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习惯可能会发生变化。如“然民干”这一习俗在哈尼族的接受程度就在发生变化,有些地域聚集的哈尼族人慢慢对这一习俗开始抵触,并渐被视为“陋习”,所以对是否该当“猥亵”需结合变化了的情势而定。此外,部分习惯法还具有社会属性的特点,如“然民干”的习俗是存在于哈尼族熟人或恋人之间的,对于哈尼族以外的人是不适用的。[2](323)是故,对于案例1中的汉族男子来说,就不能以哈尼族人之间的“然民干”习俗来否定其行为的猥亵性。
尽管上述分析展现了习惯法在构成要件解释中的作用方向是“出罪性”的,但习惯法在构成要件解释上也有“入罪性”的功能。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出罪”因为有利于被告就与罪刑法定主义不相违背,而“入罪”因为不利于被告而就与罪刑法定主义相冲突。这里主张习惯法“入罪性”功能并不是指单纯以习惯法为由直接将行为人定罪,而是指习惯法可与制定法一并起作用,从而进行“入罪性”的判断。例如,尽管在大多数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难以将公然接吻和拥抱视为刑法上的“猥亵”行为,但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基于风俗的原因,类似行为就可能被视为猥亵。譬如在藏族地区,公然接吻“便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伤害风化的猥亵行为”,故“猥亵”的判断较之其他地区有差异。[1](202)当然,鉴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缘故,习惯法“入罪”方向的判断应当严格要求,否则容易造成对人权的践踏。
此外,除了可通过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实现制定法中习惯法的评价以外,通过对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解释,也可实现。苏永生教授就认为,“民族习惯法上的犯罪就完全有可能通过开放的构成要件要素被解释为刑法上的犯罪;同样,民族习惯法不认为是犯罪而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开放的构成要件将其解释为非罪。”[12](58)当然,这不仅限于民族习惯法。所谓开放的构成要件,是“指刑罚法规的构成要件规定上仅仅记载着犯罪要素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当其适用时预期由法官予以补充的构成要件”[9](127),其中最典型的是不真正不作为犯与过失犯。例如,对于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的理解,日本判例认为“不只限违反各个法规上明确规定的义务,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按照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未采取社会一般的共同观点上理应采取的一定措施……”[13](47)。此外,对于过失犯之注意义务的判断,有见解认为,“除由法令规定的注意义务之外,还承认基于习惯或条理的注意义务。这样的注意义务,必须根据具体案件,一方面考虑社会的现实的要求,一方面由法官适当地论定。”[9](258)
(二) 误解澄清:“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的曲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开放构成要件的解释中习惯法均有较大的运行空间,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大体仍是一种抽象的、定型的判断,除本需价值补充判断的要素以外,其他要件或要素的解释应尽可能采取相同的标准予以认定,以保证要件的客观定型意义,避免“因人设事或处罚范围的游移不定”,从而“维持法域内在的一致性”。[7]所以,对于除这两个构成要件要素之外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不能因习惯法而过分曲解刑法中部分构成要件要素或构成要件的内涵。遗憾的是,理论与实务对此并非全然清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曲解。
例如,针对类似案例2的事案,有见解提出,丈夫的索赔行为表面上似乎是“以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索取,但实质上这并不是纯粹基于直接故意的非法占有,“勒索者”勒索财物的目的并非完全是非法、无故占有他人财物。[14]换言之,由于丈夫在习惯法上有请求赔偿的理由,所以其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对于部分未进入审判的捉奸事案,也有公安或检察机关以不具非法占有目的而不立案或不起诉的。问题是,能否因行为人的行为是在基于对习惯法规则认同下进行的,从而就能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在笔者看来,要阐明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中“非法”的涵义。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为虽然对某物享有所有权,但如果对方具有合法的占有权利时,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该财物的,侵犯了诈骗罪的保护法益,行为人的占有目的也具有非法性。”[15](304)也有人从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角度来理解非法性,认为“从实体法角度看,‘非法’应该是指没有法律依据;从程序法角度理解,‘非法’则是指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采用了法律不允许的手段”[16](289)。由此看来,“非法占有目的”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行为手段不被现行法规范所允许即可,不论是实体规范还是程序规范,即使行为人认为具有习惯法上的实体权利,但只要认识到行为为法规范所不允许就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亦如学者许恒达所言,“财产犯罪的不法所有意图,只要求行为人知悉他将违反民事法律秩序而侵夺他人财产的终局利益即足。”[7]对于案例2来说,张某显然知晓法律不允许以胁迫手段从他人处取得财产,即使主观上认为行为具有习惯上的正当理由,但也应知晓需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张某以胁迫手段迫使王某答应交付财物,已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是故,以张某主观上认为自己权利遭受损害而有权从他人处获得赔偿这一理由,进而否定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否定案例2中构成要件解释时习惯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对案例2及类似事案就一定要以犯罪论处。理由是,犯罪的成立除需要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以外,尚需进一步判断行为的违法与有责。所以,即使在构成要件解释阶段,习惯法在类似事案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判断路径。
三、违法性判断中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前已述及,按照阶层犯罪论体系,犯罪的成立除了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以外,尚需满足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判断。由于构成要件是对法益侵害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具备了违法性,故违法性的判断事实上通常表现为一种消极的判断,即主要判断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属于一种类型性的、抽象性的和形式的判断不同,违法性的判断属于非类型性的、具体性的和实质的判断。[17](160)因此,尽管违法性判断在实务中一般表现为判断是否有违法阻却事由的存在,具有形式性的特点,但事实上,判断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则必须做实质、具体的判断,否则无法确认”[17](160)。
(一) 路径:社会相当性理论
对于违法性的判断,显然不意味着违反一种法律上的禁令即足,尚需实质上的理由。尽管基于学者们学说立场的差异,就实质违法性之内涵有规范违反说和法益侵害说等学说的激烈争论,然理论上的通说和实务上一贯的立场都采取的是一种二元的立场,即“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18](215)。据此,违法阻却事由的根据也可被认为是符合社会伦理规范,亦即具有“社会的相当性”,进而违法阻却事由判断的根本落脚点也就在于社会伦理规范的判断。但是社会伦理规范的判断,“常常很困难……只有以人性为基础的、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一般观念为基准,才能发现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伦理。”[18](215)这正好给违法性判断中对习惯法的考量提供了巨大的运行空间。杜宇博士就提出习惯法是可以作为一种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习惯法规则与社会相当性具有紧密的内在勾连”;在违法性之社会相当性的判断中引入习惯法,将深化和拓展我们对社会相当性之“社会”这一范畴的横向理解和空间理解。[1](208−210)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相当性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域外理论表述,我国现行刑法中也有其规范基础。例如,《刑法》第13条的“但书”就蕴含了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内核。苏永生教授就认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为第13条“但书”规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依据,有利于克服形式合理性弊端,“但书”规定为法官依习惯法出罪提供了规范上的依据。[12](56−59)
(二) 维度:习惯法考量的具体化
然而,以上仅是从抽象意义上就习惯法在违法性判断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及路径的简单说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对于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情势,并不能抽象和简单地认为“行为符合习惯法规则,就是应合了这个社会的生活秩序,就是该当了这个社会的生活伦理,就是一种具备社会相当性的行为”[1](208)。质言之,违法性判断中是否该考量习惯法以及习惯法究竟是出罪还是仅降低行为的违法性,要视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定。有些事案尽管存在习惯法上的理由,但并不影响违法性的判断,有些事案中习惯法的存在仅是对行为违法性程度的降低。不妨让我们回到案例2的讨论。
不论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抑或是法制相对发达地区,类似案例2的事案时有发生。尽管目前诸多判决几乎无视丈夫习惯法上的赔偿请求理由不值得认可,但那种认为“丈夫有习惯法上的依据,不存在违法性,故不能作为犯罪的处理”的观点也不能全然赞同。事实上,“违法性乃实质的、具体的判断”本身决定了,对于类似“捉奸敲诈勒索案”不可能提供一个“统一”的阻却违法还是降低违法的结论,需要根据个案情形的仔细辨别来进行具体判断。然而虽说无法为类似事案提供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较为简单、可操作的判断规则。在笔者看来,对于类似“捉奸敲诈勒索案”中能否因习惯法阻却行为人之违法,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
第一,案发地区民众对习惯法的所持态度。虽说在制定法上,丈夫对与妻子通奸的“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并无法律上的依据,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惯习已将事案中的丈夫视为事实上的受害者,习惯上也默认丈夫有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然而其惯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受地域性影响。在法制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与国家法尚未深入渗透的民族聚居地区,这一习惯法的内涵和约束程度是不同的,人们对其认可程度也存在差异。如瑶族的习惯法对于与有夫之妇通奸的,可以捉到后剥光通奸者的衣服游街并摇铃招众观看,捆缚两三天后释放,并罚款;而在景颇族,丈夫抓住奸夫奸妇可当场杀死无罪也不用赔偿,只需用一头牛“洗寨子”,丈夫抓住与妻子与人通奸的证据,可到姘夫家论理,并可索赔十几头牛。[19](179)此外,在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村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于丈夫可以向奸夫提出赔偿请求的习惯法的认同程度也是有差异的。这说明,当案件发生于不同地区时,由于辖区内民众对这一习惯法认同度的不同,自然对因遵循这一习惯法而形式上触犯敲诈勒索罪之行为违法阻却的程度也会大不相同。当案件发生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有可能将这一因遵循习惯法而形式上触犯刑法规定的行为视为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而当案件发生于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可能认为只是对违法性程度有影响,但不完全阻却违法。或许有见解会对因地域差异而导致违法性判断的不一产生质疑,但违法性本身就是非类型的、具体的和实质的判断,因不同地域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伦理规范内容的不一,社会相当性的认定也自然会不一致,这并不奇怪。
第二,行为人所采取手段的方式与程度。尽管习惯法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捉奸”丈夫对第三者的惩罚措施和赔偿请求权,但是权利的行使从来不是漫无边界的。所以,习惯法赋予的权利,其行使的手段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应符合社会相当性的要求。当权利行使的手段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时,自然不能全然阻却违法。如丈夫用对奸夫生命权的夺取或对其身体健康的重大伤害以胁迫并提出显然不当的“赔偿数额”,就超出了绝大多数公众所能接受的程度,不能阻却违法。当然,在违法性程度的判断上,应将其与一般故意伤害和敲诈勒索案件相区别,量刑上还是存有差异。
在此,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丈夫索取的“数额”能否成为手段相当性判断的重要标准?质言之,能否认为案例2中张某索取4万元的数额没有超出社会相当性,而类似事案的甲某索取16万元的数额就超出了社会相当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需面对的问题。理论上,如果肯认丈夫的夫权受到了侵害,丈夫提出多大“数额”都属权利行使的范畴。实践中,我们也难以就“合理的数额”划定一个明晰的界限,所以无法以数额来决定是否超出了相当性。但这并不否定数额在违法判断中的意义。首先,索赔数额可与手段相结合判断行为是否超过相当性,若丈夫反复以此事为由威胁从第三者处获取财产,就可能超出相当性的范畴,但每次数额均不大的也可认为没有超出相当性,而手段极为严厉,即使数额不大也可能超出相当性。此外,当丈夫索取的数额明显与第三者的承受能力不相当时,民众基于通常的伦理规范也可能会认为超出了相当性的范畴。是故,数额在实践中并非是毫不考虑的因素,只不过不是作为单独因素而影响相当性的判断,而是结合了手段严厉性和第三者可能承受程度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案例2的张某来说,由于案发地区尚属法制发展程度化较高的地区,所以不能完全阻却其行为违法,但违法程度较一般敲诈勒索行为显然要低。就案例3中陈某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来说,尽管陈某对麻雀进行捕杀具有部分正当性,然从实质法益衡量来看,陈某财产的受损程度与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相比,所保护法益要低,故也不能完全阻却行为的违法。当然,陈某毕竟存在部分权利行使的正当理由,无疑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行为的违法。
四、有责性判断中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很多情形下,符合习惯法的行为既不能否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也不能完全阻却行为违法,但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判断并未终结。按照阶层犯罪论体系,犯罪的成立除了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以外,还需具备有责性。“并非所有该当于构成要件之违法行为皆能成立犯罪,必须能将责任归属或归责于行为人时,犯罪始得成立。”[17](213)
(一) 路径一:违法性认识的判断及局限
对于有责性判断中习惯法有无作用的空间,杜宇博士给予了肯定回答,“当我们就此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之时,我们却可能发现,习惯法上的规定已成为行为人责任上的一种宽恕事由,使我们难以对行为人予以主观的、伦理性的非难。”[1](218)更准确地说,“当行为人本着习惯法上的合理确信而行事,从而陷入违法性认识的错误时,此种错误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而可以考虑阻却行为人的责任。”[1](223)显然,杜博士认为违法性认识是习惯法阻却责任的一条重要路径。将违法性认识作为习惯法阻却责任的路径,是源于现代刑法之“责任”,“以行为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并且如果意识到的话,就能够期待其形成反对动机,决意实施合法行为为根据的。”[18](308)行为人仅有故意与过失,尚难以加以责任非难,必须要求行为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或者是有意识的可能性。换言之,只要行为人“意识到自己之行为乃不被法所允许之可能性”即足[17](213),当行为人对违法性意识的欠缺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可阻却责任,行为人不成立犯罪。
虽然说,在违法性认识的判断中考虑习惯法因素,于理论上来说似乎可以有效排除部分因遵循习惯法规则而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之行为的有责性。然而,因这一路径而阻却责任之情形在实践中极为少见,故其实际功用很小。理由是,阻却责任之违法性认识错误需对违法性认识的欠缺是出于不可避免之情形,但事实上,今日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的欠缺仍存在不可避免之情形甚为少见,即使在国家法渗透尚不足的少数民族地区亦是如此。像杜宇所举铁匠杨某欠缺对非法制造枪支罪的违法性认识的事案将越来越少见。[1](218−219)①
问题是,当我们对行为被现行法规范所不允许已有知晓时,能否认为因遵循习惯法比遵守制定法优越,从而就否定行为人存在违法性认识?在笔者看来,只要行为人清楚认知或可能认知其行为违反现有实证法规范,即可认定具有违法性认识,而行为人是否最终考虑认同其他伦理或文化规范,不影响违法性认识的满足与否。亦如有见解所言,“一个明知违反实证法,却因试图遵守其他规范而仍实行犯行的行为人,他其实已然拒绝遵守实证法行为规则,如果任何拒绝服从刑法诫命者都能基于‘我信仰比实证法更优越的其他规范’而成立禁止错误,这毋宁必然导出刑法不具任何效力的结论,刑法指陈的行为规范与法益保护机能也必然成为空谈。”[7]
对于案例1中几位汉族青年,显然他们可能认识实证法规范禁止对妇女进行猥亵,只不过考虑哈尼族习惯可能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实际存在违法性的认识,故不能阻却责任。同样,对于案例2来说,行为人无疑知道任何人通过胁迫手段获取他人财物是不法的,即也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当然,如果这一类似事案发生在极为偏远和封闭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法根本未能进入该地区,或由于特殊之原因本地区生活的人不可能知晓国家法的内容,有存在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但可预见的是,这种情形已极少存在。对于案例3,由于今日大陆地区绝大多数村落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知晓捕杀麻雀为国家法禁止,就以本案来说,事实上陈某也承认知晓国家禁止捕杀麻雀,但因出于无奈才捕杀。所以,本案中陈某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只是迫于现实之压力而无强烈的遵法意识。
(二) 路径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与重构
尽管违法性认识这一路径事实上并不能很好地将因遵守习惯法而与制定法发生冲突的行为人阻却责任,然而这不意味着在有责性的判断中就没有其他可循路径。根据今日已被理论与实务广为认可的“规范责任论”,有责性的成立,“除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故意与过失、违法性意识或意识可能性外,尚以行为人具有合法行为之期待可能性为必要。”[17](248)尽管期待可能性肇始于德日刑法理论,但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诸多规定也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20]例如,《刑法》第241 条第6 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也规定,对于家庭成员或近亲属之间偷盗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也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目前,期待可能性作为一般超法规的排除责任事由在理论上逐渐被认可,有学者也意识到在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中有习惯法判断的存在空间。[1](223−225)但是,以欠缺期待可能性阻却遵循习惯法之行为人的责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尽管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已不陌生,但由于这一理论的抽象性,我国刑法理论对其认同的程度尚属不高,司法实务中明确肯定该理论的案例很少。所以,目前习惯法想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法教义学框架下作用于具体事案还有一定的困难。
第二,理论上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解过于偏狭。通说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具体情势下,有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18](321)只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当时行为人的意志自由遭受了强制状态,才能认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从这一概念来看,在具体情势下,只有当行为人在实施合法行为与实施违法行为无从选择之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免责。而在意志自由论来看,这一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就前述事案来看,案例1由于不存在实施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选择之情势,所以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案例2、案例3可能存在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倘若按照目前我们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解,并无对案例2中的张某和案例3中的陈某绝对心理强制的事由,故两被告均有实施适法行为的可能,进而也都不能阻却责任,只可部分减轻被告的责任。
然而,期待可能性作为规范责任论的基础与核心概念,我们对其如此加以限定性的理解,显然过于偏狭,事实上也不利于发挥这一概念创设的本来功能。况且我们对其解释赖以的意志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受限制的意志自由,绝对的意志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杜宇博士所言,“对基层民众而言,习惯法的力量是真实而强大的。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牢固地树立起对它的信赖和尊重。在此种具体情况下,当行为人基于对习惯法的确信而行事时,习惯法是如此有力地控制和笼罩着行为人的认识和观念,以至于行为人完全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种合法且正当的行为。此情此景下,我们很难再去期待行为人会对另一种规则保持足够的警惕,再去考虑自己的行为在另一种制度和规则中的实际意义和性质,更何况此种制度和规则,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陌生和难以理解。”[1](224−225)因此,对于期待可能性理应重新加以理解。如果行为人“已经被他固有的背景意识强制去违反法律,刑罚在这个意义下,基本上几乎等同于一个违反人性尊严的国家行为,必须考量行为人欠缺期待可能性的特点,而认定为阻却罪责事由,排除刑责”②。这才是期待可能性的应有之意。必须承认,期待可能性是抽象的,亦因此导致期待可能性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对低下。但是这不是我们摒弃这一理论的理由,反而是应该不断开拓期待可能性在个案中的判断规则,增强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
对此,台湾学者许恒达就良心犯的认定标准或许可为我们利用,即①系争习惯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善恶标准,而善的行为标准将构成违法犯罪;②行为人决定优先遵守上述习惯法而放弃遵守现行法之规定,必须有不得已之情势的存在;③行善却违法的行为须被承认多元文化的一个可能选项。[7]是故,对于案例2来说,尽管张某具有习惯法之理由,但难以认为具有不得已之情事的存在,故而不能以欠缺期待性阻却张某的责任。但对于案例3中的陈某来说,由于陈某面临稻谷将被麻雀吃完之不得已情势,并且其固有背景不能期待陈某舍其可能赖以生存之稻谷而保护更为抽象的生态环境,在不主动损害其他利益之前提下,行为人以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与倡导多元文化之理念不相违背,所以应当认为陈某捕捉麻雀之行为欠缺期待可能性,从而不成立犯罪。
五、结语
以上本文围绕三则事案详细阐述了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在刑事制定法中的运行逻辑。由此可知,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在刑事制定法中的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犯罪成立的各个要件的判断来实现的,即在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性的判断和有责性的判断中通过具体要素的判断来考察是否有习惯法判断存在的空间。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构成要件解释中,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通过两个需要价值补充判断的构成要件要素或构成要件来实现,即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开放的构成要件。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对于构成要件其他要素的解释应尽量排除习惯法的影响。理论和实务常以具有习惯法上的正当性为由进而否定行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和做法,是错误的。
第二,在违法性判断中,习惯法作用的空间较之于在构成要件解释阶段要大得多,并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的。由于个案发生的社会结构背景存在差异,其违法性之判断也存有不同,故习惯法在此阶段的判断应努力结合个案具体判断。
第三,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进行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能很小,更多阻却责任或减轻责任的重任应落在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上。目前理论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从而使部分遵循习惯法之行为能够顺利阻却责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法教义学的路径是目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最宜采取的路径,但对于二者冲突的解决,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从长远来看,从多方面促进制定法与习惯法背后依赖的不同文化的交融,并在制定法中内化习惯法,或许才是根本的解决之路。
注释:
① 有学者统计,台湾地区刑法实施七十余年来,只有寥寥一则判例以违法性意识错误而否认行为成立犯罪的。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上)》(第10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注释(26)。
② Rudolphi, Hans-Joachim. Bedeutung eines Gewissenentscheides fűr das Strafrecht, in: Hans Welzel-FS,1974,S.633.转引自许恒达:《国家规范、部落传统与文化冲突——从刑法理论反思原住民犯罪的刑责问题》,《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杜宇. 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方慧. 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以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案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 邱旭. 丈夫捉奸 索要补偿被判刑[N]. 重庆商报, 2006-7-9(4).
[4] 苏力. 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法——从司法个案透视[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3): 124−135.
[5] 王国龙. 从难办案件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权的运行逻辑[J]. 法学, 2013(7): 83−94.
[6]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 徐久生,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7] 许恒达. 国家规范、部落传统与文化冲突——从刑法理论反思原住民犯罪的刑责问题[J]. 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2013(2): 33−82.
[8] 陈兴良, 陈子平. 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 马克昌. 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学刑法总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0] 张明楷. 刑法学(第三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1] 野村稔. 刑法总论[M]. 全理其, 何力, 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12] 苏永生. 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3] 日高义博. 不作为犯的理论[M]. 王树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14] 庄绪龙. 敲诈勒索罪的理论反思与区别性认定[J].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10(5): 21−26.
[15] 张明楷. 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16] 黄冬生. 行使财产权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C]//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九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17] 陈子平. 刑法总论(2008年增修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8] 大谷实. 刑法讲义总论[M]. 黎宏,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9] 高其才.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20] 张小虎. 论期待可能性的阻却事由及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J].比较法研究, 2014(1): 65−75.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customary law: The operation logic for customar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gmatics
WU Liangjun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The path of dogmatics can alleviate the judicial personnel’s discomfiture in the fac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customar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gmatics, the operation logic of customary law is mainly realized by the judgment of crime constituents. The customary law has large operation space in regulating normative constituents and their open recognition. Bu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haping elements of these constituents, other elemen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stomary law. In judging criminal illegality, the judgment of customary law is mainly realized by social considerable theory. Because judging illegality is real and concrete, judgment of the customary law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ase. In judging culpability, even though illegality cognition is, in theory, a path of crime for the customary law, the actual effect is very small. A more suitable path should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ossibility of judgment, which is, however, very limited. Therefore, the theory should be properly 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rmative theory of culpability.
statute law; customary law; dogmatics; constituents; illegality; culpability
D914
A
1672-3104(2015)01−0051−08
[编辑: 苏慧]
2014−07−14;
2014−09−18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09YJC820024);海南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2014HDY0042)
武良军(1988−),男,安徽宣城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刑法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