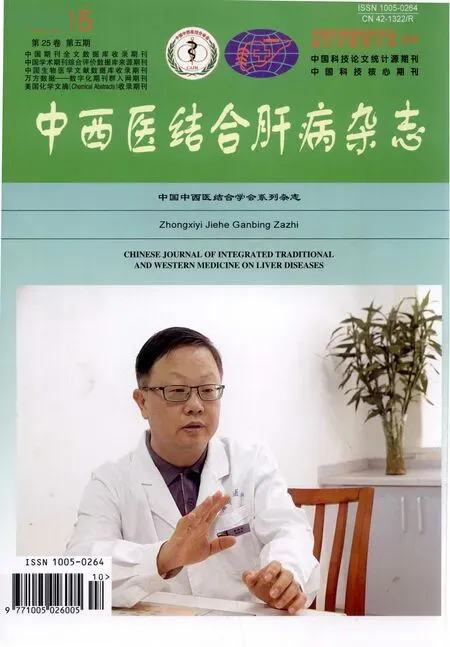肝癌证候要素理论探讨*
2015-01-20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中医院)中医肝病研究所(湖北 武汉,430061)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高,严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中医药防治肝癌具有明显优势,但肝癌证型较多,证候演变复杂,各家对证候要素的认识各异,给临床辨治带来一定的困难,亦影响了中医药防治肝癌的实验与临床研究的成效。因此,阐明肝癌的证候要素,对规范临床辨证行为、提高实验与临床研究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在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反复交融结合的过程中,湖北省中医院中医肝病研究所中医药辨治肝癌经历了从“毒”到“毒痰瘀”再到“毒痰瘀虚”的不同认知阶段,提出了“毒痰瘀虚”为原发性肝癌的证素特点。现对其科学性进行理论探讨。
1 毒
毒之涵义,在中医学中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指药物之毒性或偏性,一是指疾病,一是指病因。所谓毒邪,则专指病因之毒,是对人体明显有伤害的、较六淫病邪损害更强的一类病邪。癌毒亦属于毒邪之一,其概念的提出来源于中医毒邪致病学说。中医界自古以来一直认为恶性肿瘤的发生与毒邪有一定的关系。如《灵枢·刺节真邪》云:“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着……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溜……肠溜……肉疽。”意指邪气在不同部位停留是导致恶性肿瘤产生的根本原因。华佗《中藏经》言,癌肿的发生非独气血壅滞,更有五脏六腑蓄毒不流,意为只有体内气血痰食等聚结,没有“毒”的参与,则不会发生恶性肿瘤。
癌毒是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是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子,属于有形之邪,其“多少”和“盛衰”可以定量描述,即可以用单位体积内的癌细胞数量或癌细胞在身体局部形成肿块的大小来直接描述,也可以通过确实能反映其多少和盛衰的某些生化指标,如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间接描述。如此定义癌毒,是对中医“毒邪”概念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发展[1]。
毒有外来与内生之分。外来之毒主要是指由六淫邪气过甚转化为毒或外邪内侵蕴久成毒。如湿邪郁于体内,影响气血运行,气血阻滞可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更加助长了湿邪,化而为毒,酿为痰毒结肿。内生之毒主要是由于脏腑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造成机体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体外,蕴积体内而化生。内伤七情、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均可为内毒产生的诱因。内毒与外毒虽然来源不同,但都能造成对机体的损害,并且外毒可造成机体功能紊乱而产生内毒,内毒之生能加重病情,耗伤正气,使外毒易于入侵[2]。
导致肝癌的毒邪包括外毒和内毒两方面。在我国外毒主要指肝炎病毒、黄曲霉素及亚硝胺类物质。内毒是因外毒入侵导致机体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失调所产生的对机体有特殊而强烈损伤作用的病理产物,可能涉及到T 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性“毒”、细胞因子“毒”、炎性因子“毒”、内毒素“毒”、脂质过氧化“毒”等[3]。
2 瘀
肝血瘀阻是肝癌的主要证候要素之一,这一证候要素特点不但是由“血瘀”的致病特点决定的,而且是由肝脏的基本生理病理特点决定的。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明确提出了瘀的致病特点:“无论何处,皆有气血……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肝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肝主疏泄,若肝失疏泄,肝气郁滞,气滞则血瘀,瘀久则成癌。
肝癌普遍存在着血液高凝状态,大多数癌细胞可以诱发血小板聚集,血小板的聚集以及癌细胞释放的高凝血因子通过抗纤溶、促血小板聚集等途径导致血液凝固性增强,使肝癌患者处于血液高凝状态。肝癌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检验指标也常有较明显的变化,如红细胞聚集性明显增高、血液屈服应力、全血低切粘度、沉降率等反映红细胞之间聚集性的指标均有上升,而红细胞变形指数降低、电泳时间延长[4]。
3 痰
百病皆生于痰。《杂病源流犀烛》曰:“《内经》论痰饮,皆因湿土,以故人自初生,以至临死,皆有痰。而其为物则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说明痰邪为病贯穿人的各个部位。《证治汇补》曰:“凡人身中有块,不痒不痛,或作麻木,乃败痰失道,宜随处用药消之”。
痰未由正常通道排出,所产生的肿块多无疼痛、瘙痒,如影响血液运行则有麻木之感,根据病位用不同的化痰药进行消散。朱丹溪对痰证深有研究,认为百病中多兼有痰,曾云:“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说明体内肿块的形成多与痰有关,并认为痰饮为病在肝脏病中亦较为普遍,他在《脉因证治·胁痛》中指出:“痰积流注厥阴,亦使胁下痛,痛则咳嗽。”
痰在肝内表现为肝纤维化,是细胞外基质(ECM)合成与降解失衡而引起的病理改变,它是许多慢性肝病向肝硬化、肝癌发展的必经病理过程。随着ECM 的增多病情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肝脏血管扭曲变形,血供异常,肝细胞缺血缺氧,功能下降,代谢产物及毒物增多,加重肝细胞损伤和纤维化[5]。
4 虚
4.1 脾气虚《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又云:“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
中医认为肝癌发生主要与内伤劳倦,饮食不节及寒温失宜有关,积聚的形成主要与脾虚有关。《灵柩·百病始生篇》曰:“ 壮人无积,虚者有之。”中晚期肝癌虽然多数表现虚实夹杂,但是核心在于脾气虚亏,脾虚则湿滞,湿阻成痰,痰聚成积。董秀丽等认为脾虚乃原发性肝癌基本病机[6]。方肇勤领衔的科研团队在临床调查中发现,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证候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占87.1%[7]。说明脾气虚是肝癌的基本证候。
4.2 肾阴虚《内经》曰:“阴成形”。阴性寒,性静,性凝敛,阴精是物质之基础,所以阴可以凝聚而成形。肝癌的发生导致肝脏形态发生了变化,按照《内经》的观点,必然会存在阴虚。肾阴虚证是肝癌患者常见的证候。
李瀚旻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深入研究“肝肾阴虚证”的生物学基础后发现,肝损伤与肝再生平衡失调,即肝再生过程紊乱致肝脏“形质毁坏”(组织损伤)、甚或整体“形质毁坏”(全身与肝病相关的脏器组织功能损伤、减退或衰竭)是其重要的本质特征,通过“补肾生髓成肝”治疗在“肝肾阴虚证”改善的同时,肝脏的“形质毁坏”得以改善或恢复[8]。
4.3 肾阳虚《内经》曰:“寒伤形”。寒为阴邪,伤人精液,阴精为物质之基础,阴精亏损,人之器官形体必然发生改变,而肝癌的表现就是肝脏形态发生了变化,按照《内经》的观点,必然是寒邪所致。阴盛则阳衰,阴盛则寒,是外在表现,阳虚才是内在根本,故肾阳虚证是肝癌患者的主要证候要素之一。
根据《内经》“阳化气,阴成形”,认为阳虚、寒积是肿瘤发病的重要因素,肿瘤是阴盛表现出来的病理产物,阳虚是导致阴盛的病理基础。阳虚既是发病的内在因素,又是疾病过程的一种病理表现,贯穿于恶性肿瘤病变的始终。《内经》“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成为温阳法治疗肿瘤的理论依据。
陈群伟等[9]应用肝癌基本证候定性诊断标准和量化分析模型,探讨了原发性肝癌阳虚证患者血清代谢组特征,为肝癌阳虚证诊断的客观化、规范化提供依据。该研究认为,肝癌阳虚证与非阳虚证代谢谱的差异提示阳虚证特征性代谢网络的失调,主要表现为脂类代谢、糖代谢、能量代谢等多种代谢的紊乱或衰减,VLDL/LDL、异亮氨酸、乳酸、脂类、胆碱、葡萄糖/糖类等代谢物浓度的下降可能是肝癌阳虚证特征性的代谢物改变,是潜在的肝癌阳虚证生物标志物。
5 基础研究
我们以“毒痰瘀虚”理论为指导,通过基础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肝癌“毒痰瘀虚”的证素特点。从“毒”、“痰”、“瘀”、“虚”不同方向着手,系列探讨了中医药辨治肝癌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从“毒”着手,探讨叶下珠药物血清对人肝癌细胞株的诱导分化作用,结果表明,叶下珠药物血清能诱导人肝癌细胞株Bel-7402向正常方向分化[10]。从“痰”着手,探讨中药皂荚提取物对肝癌细胞TGF-1 mRNA 信号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皂荚提取物可通过对肝癌细胞TGF-1 mRNA 信号高表达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11]。从“瘀”着手,探讨膈下逐瘀汤对人肝癌细胞Bax、Bcl-2、P53 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结果表明,膈下逐瘀汤能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12]。从“毒痰瘀”着手,运用血清药理学方法探讨中药博癌丸对人肝癌细胞株HepG2 细胞凋亡及相关调控基因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博癌丸对HepG2 细胞具有抑制增殖及诱导凋亡的作用,其机理可能是通过上调Bax 和P53 的表达而发挥其促凋亡的作用[13]。从“毒痰瘀虚”着手,探讨了黄白抑瘤方对Colo320 细胞增殖与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的影响,以明确黄白抑瘤方治疗结直肠癌的生物学基础,结果显示黄白抑瘤方能抑制人直肠癌Colo320 细胞增殖,从而达到抗肿瘤的作用[14]。
肝癌的证候要素是毒痰瘀虚,但在肝癌发生发展的不同时期,毒痰瘀虚四大证候要素的表现轻重不一。肝癌的发生发展多由于正气内虚、阴阳失调,复因感受邪毒、情志郁结、饮食损伤、宿有旧疾等因素日渐损伤人体正气,使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产生气滞、血瘀、痰浊、热毒等病理变化,蕴结于肝脏,相互搏结,日久积渐成块如岩,形成肝癌。初期邪盛而正虚不显,故以气滞、血瘀、痰浊、热毒等实邪为主要表现,中晚期由于实邪逐渐耗伤人体气血津液,气血阴阳失调逐渐突显,邪愈盛而正愈虚,正愈虚而邪愈盛,两者互相影响,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
[1]凌昌全.“癌毒”是恶性肿瘤之根本[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8,6(2):111-114.
[2]戴小军,朱雅敏,孙鹏.“从毒论治”肿瘤病理药理基础与临床应用浅释[J].中医药学刊,2002,20(1):67-69.
[3]毛德文.肝衰竭毒邪病因学说辨析[J].中医药导报,2007,13(1):8-11.
[4]李彬先,李瑞昆.恶性肿瘤病人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的临床价值[J].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2005,15(4):596-597.
[5]王振常,黄晶晶,夏兰,等.从痰毒瘀损肝体探讨肝炎后肝纤维化发病机制渊薮[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12(12):48-49.
[6]董秀丽,李长华,李炜.原发性肝癌从脾虚论治探讨[J].山东中医药杂志,2001,20(8):459-461.
[7]任艳红,方肇勤.方肇勤治疗原发性肝癌撷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4,20(1):83-86.
[8]李瀚旻.论“补肾生髓成肝”治疗法则[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5):937-940.
[9]陈群伟,黄雪强,凌昌全.原发性肝癌阳虚证患者血清代谢组学特征初步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3):526-529.
[10]张建军,黄育华,晏雪生,等.叶下珠药物血清对人肝癌细胞株的诱导分化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2,9(5):289-291.
[11]彭望君,陆定波.中药皂荚提取物对肝癌细胞TGF-1 mRNA 信号表达的影响[J].湖北中医杂志,2010,32(5):6-7.
[12]黄廷荣,周虹,费新应,等.膈下逐瘀汤加减方对人肝癌细胞Bax、Bcl-2、P53 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8,18(6):355-356.
[13]刘坚,谢红东,李瀚旻,等.肝癌细胞株HepG-2 细胞凋亡及相关调控基因的影响[J].循环医学杂志,2007,17(4):152-154.
[14]李天望.黄白抑瘤方对人直肠癌Colo320 细胞凋亡与Caspase3 及聚ADP 核糖聚合酶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09,17(6):35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