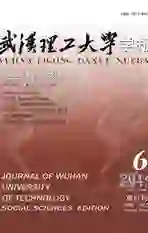“年代剧”中的时间叙事与文化症候
2015-01-15申朝晖
申朝晖
摘要:年代剧中的时间叙事极富特色,其故事时间具有双重性,虚构的故事时间与真实的历史时间之间形成互文照应关系,而且年代剧大多偏爱以民族主义精神强调或省略特定的历史时刻。另外,通过苍凉的想像式怀旧感伤,年代剧还表现个体生命内在时间的绵延特质。
关键词:年代剧;故事时间;叙事时间;文化症候
中图分类号:J905;J902文献标识码:A
俄国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认为,在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中,电影是人类首度发现“留取时间印象”的方法,人们通过电影能够获得“真实时间的铸型”,并可将之长久保存[1]63。从观影的角度而言,“一般人看电影(电视)是为了时间:为了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他去看电影(电视)是为了获取人生经验。”[1]64在影视艺术的发展史中,时间元素可能受制于不同时代、不同题材或不同哲学思潮流派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电视剧因其不受时间篇幅的限制,在展现人类延绵的历史与记忆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国内几度火爆的“年代剧”热播潮无论在影视收视率还是观众口碑上,都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年代剧”多以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传奇笔法”,以史诗般的笔触叙写近代中国急剧变迁中个人、家族及整个民族悲壮不屈的家国奋斗史。正如“年代剧”之“年代”二字暗示我们,时间要素在“年代剧”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关乎表层的故事营构、画面构图、灯光、服装等等,也涉及深层的表意空间及所形成的美学风格。当然,这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手法,也含混着当代人关于那段逝去不久的历史的心理想象,契合了当下人类自我正遭遇的处于急遽变革时代的精神诉求。因而,从时间的叙事功能切入“年代剧”的文化分析,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故事时间的双重性及其史诗品格
任何叙事都涉及两种时间: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故事时间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则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前者是由我们在接受过程中根据日常生活的逻辑重构起来的,后者是作者经过对故事的加工改造提供给我们的现实的文本秩序。故事时间的内涵包括以人物性格逻辑推演的有一定长度的情节链,也指涉虚构故事所置于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这个常被称之为“故事背景”的坐标定位往往约束或限定着叙述的表意空间,是故事获得理解与阐释的必要条件。
“年代剧”的故事时间与真实的历史时间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在以《大宅门》、《闯关东》为代表的年代大戏中,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和作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故事时间的或明或暗的时间坐标。在年代剧中,表现历史事件与历史时间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有些直接生成为故事的情节,如“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京”在《大宅门》中就演化为情节:义和团运动洋教堂受到冲击,黄春被白景琦转移到白家花园。白景琦和白颖宇留守京城,但二者对外国入侵者具有不同的态度,白颖宇借机而报私仇,带兵烧抢詹关两府,反致自己的妹妹白雅萍被一群德兵强奸;白景琦为报师仇,杀了德国兵,在被当作“酒吧”的百草园,结交了反战的日本兵。而有些历史事件则以画外音或字幕等外在于故事的叙事话语进行交代,如辛亥革命到1921年,只是通过白景琦剪鞭子的两个特写镜头,直接跳跃到以字幕出现的1921年白景琦自立门户的“大宅门”的情节链上来。
历史时间与情节线的交相辉映,使得“年代剧”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剧在表意上具备了主题深化的空间,并获得史诗的品格。现在许多年代剧自觉意识到“史诗”之于年代剧的重要意义,有些也自称“大型传奇史诗”。如何厘清史诗叙事中故事虚构与历史叙述、英雄传奇与集体意识表达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后来一些年代剧在类型化创作中只硬搬形式外壳、不计精神内涵诉求的简单模仿,以求突破年代剧创作的瓶颈。史诗叙述与历史有着特殊的关联性,著名的古希腊史诗多是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叙述英雄传说,在结构类型上亦延伸出两种基本的叙事原型:一是《伊里亚特》式的“场景—空间型”,其中时间因素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横向展开的宏大场面及众多英雄之活动;另一种是《奥德修记》式的“历险—时间型”,其中纵向时间因素成为主要的结构/叙述要素。[2]年代剧里对历史的表现多从历时的方向展开,在家族宅门戏里,通常以与家族命运共存亡的主要人物的传奇经历为主线,有些贯穿一生,有些涵盖了人物最具传奇的生命黄金时期,如《大宅门》的白景琦、《大染坊》的陈寿亭、《乔家大院》的乔致庸、《闯关东》的朱开山。而《大宅门》的故事叙述以白景琦的年龄编年为经,以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时间为纬,谱写了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以白景琦为中心所辐射下的大宅门里的众生脸谱及其生命历程。下表列举了自2001年以来有代表意义的一些年代剧的故事时间:
在大跨度的史诗书写之内,细读年代剧中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挑选与表达中,我们能轻易发现,无论是老北京的故事,还是走西口、闯关东,他们对历史的把握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在外型上表征为明晰的历史时刻的标定,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和作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清晰可辨,这些历史事件本身的恢宏,极大地丰富了年代剧里对平民、草根阶层的命运表现。从深层里挖掘年代剧对近代历史事件的省略与强调,不难看出人们对这段历史接受的集体潜意识,即对民族保卫战争的讴歌及对国内军阀或不同党派混战的集体沉默。
从图1可见,年代剧对历史时刻的选择和强调注重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将个体、家族的命运置于民族存亡的端口,从而使故事演绎的不只是家族历史,更关乎民族英勇抗争的沧桑史。在《大宅门》与《闯关东》中,为了更好地将民族抗争融入到家族历史当中,在叙事时间线上,二者均采用了类似中国传统小说“草蛇灰线”的叙事策略。《大宅门》在叙述“八国联军”一节中,讲述白景琦结识了一个反战的日本军人作为朋友,抗日战争中,这个日本军人的儿子田木也来到了中国,从而将大宅门的抗日纳入家族的故事当中。同样,《闯关东》前期讲述秀救下了一个日本孩子一郎,后来日本入侵东三省,一郎来了,从而也将朱家的抗日内化为家族内部具体的故事情节之中。《大染坊》因为当时纺织业的洋布多来自东洋,中日角色的对立由商战中的买卖双方构成,内化到情节链中,自然天成。在《乔家大院》和《走西口》两剧中,没有正面的战争接触,但两剧仍着意要表现民族大义的书写。《乔家大院》叙述了乔家为清政府提供抗击八国联军所需要的军费、山西晋商联手从洋人手里买回矿产事件。同时还有一组写意镜头,乔致庸要画师替其画身着官服、左手拿枪、右手持望远镜的画像,以表达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渴慕与向往,极为传神。然而,《走西口》对民族精神的书写流于概念的图解,剧中讲述田青要去北京参加游行,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其次,徐木匠借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来游说土匪刘一刀不要打劫诺颜王子为革命党筹备经费的驼队等,但都是通过声音来叙事的。然而影视语言中,说什么并不可靠,做什么才更为真实 (戴锦华语)。《走西口》虽在叙事框架上力仿《大宅门》和《乔家大院》,叙述宅院文化、童年经历、“仁义理智信”的传统经义,个体家族命运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的突显,然而,这些因素由于没有很好地内化演绎为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人物个性,上述诸多观念虽杂陈俱现,却难免有失生硬而流于概念的图解。
三、苍凉的生命时间的书写
清晰的历史时间坐标,是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生命体认。生于乱世,人之命运受制于年代,如《闯关东》中的夏元璋一家妻儿全死于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旅顺的大屠杀,没有直接的因果,就是你赶上了。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你是否赶上了也是当代人最真切的时代体认,这就是个体生命与所处时代的关联,生命时间的一种外在限定。然而,艺术对生命的把握更包含通过记忆生成的作为一种精神概念而存在的生命时间的内在特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是孔子发自肺腑的对时间的诗语感叹;普鲁斯特在一个巨大的小说记忆架构里“追忆似水流年”;塔可夫斯基用一种“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的电影语言雕塑生命,烙印时光,他甚至认为雕刻时间才是导演工作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所在,而且这种雕刻还须指向个体独特而内在的生命价值体验。[1]64
年代剧作为类型化的系列电视连续剧,在影像的打磨上相对高成本投入的大片自然难免粗糙,但相比同期其他电视剧剧种,在艺术的创作旨趣上无疑最接近“雕刻时光”这一美学命题。其实,如果不是吹毛求疵,至少在年代剧的代表作《大宅门》、《乔家大院》和《闯关东》中,这种生命咏叹的主题显而易见。
首先,年代剧借鉴了中国传统叙事中“以人带史”的创作手法,对历史时间的把握通过典型的生命个体形象的塑造来呈现,而且在叙事模式上都不约而同地追求传奇人物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的书写,从生到死,悲与壮、离与散、热闹与冷寂的边缘,年代剧让故事的传奇演绎成生命的悲歌。《大宅门》从白景琦出生开始,写他顽劣的童年往事,独闯济南研创黑七胶、自立大宅门门户的青年时代,及其与家国命运共存亡、誓死保卫秘方的中年,到疲于儿孙争家夺产的暮年,一生叱咤风云,但对这种热闹的讲述却悲壮而哀婉。《大宅门》的大结局写到白景琦自己进棺材、立遗嘱,回首一生,虽百折不屈,却最终也只能分家,散财,蹲坐在宅门口矮矮的石门槛上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大宅门》里类似这样的生命挽歌极为普遍,如杨九红、白玉婷等形象的塑造都氤氲着悲剧色彩。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对生命的咏叹主要是通过梦来抒发。梦醒后,乔致庸对镜自语:追问自己这辈子过得值吗?却发现自己过去的生命都葬送在一些琐事上,最终成了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只有银子和院子的老地主,一生的热情、智慧、才学和勇气,犹如阳光落在深渊。英雄迟暮,时间于生命的悲凉在此展示得如梦如痴。
其次,年代剧中的生命咏叹主题还表征为一种挽歌式的怀旧。通过影像烙印时光,记录生命,以一种文学式的怀旧,来反抗时间的川流不息。而怀旧,不同于回忆或记忆,“怀旧根本就是把过去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当下重新现实化。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其‘看到的过去也未必完整或真实,怀旧是一种有选择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当怀旧指向自然、民族共同体、精神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怀旧则完全是形而上的,它靠想象支撑起对过去的重构。”[4]年代剧的想像性怀旧首先体现在对“家族”观念的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观念被当作阻碍青年自由发展的禁锢而屡遭批判。如果说《红楼梦》对家族之大厦将倾充满了无比的眷顾与惋惜,那么,到张爱玲、张恨水和巴金这一辈人的笔下,家多成了爱情不自由、个性受压抑、家庭里到处充斥着礼教的残忍及长者绝对权威和卫道士的无耻。这类小说中塑造的家长多是无能腐朽者。然而,在新世纪人们自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当现代化城市将人隔离在没有故乡,没有童年,没有邻居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丛林里时,人们开始以一种想象式的怀旧重构传统的家族文化。年代剧多以家族叙事,宅院文化为载体,在探索个体与家庭命运时也多借鉴《红楼梦》、《家》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小说文本中“家国同构”的手法,但这里的家族重新被认定为亲情、力量、民族大义等正能量内涵,家长形象也大为改观,如《闯关东》中的朱开山,《大染坊》中的陈寿亭,《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大宅门》中的白文氏和白景琦,即便是《走西口》中被预设为赌徒和败家子的田耀祖,也因其舐犊情深而使总体形象得到温润。当然,这只是一种意向性的重构,是断裂的传统文化与急剧变革时代下无处安放记忆的经验个体的一次造梦,犹如影像中的老宅,幽暗成了神秘。正因为这种想象性怀旧的作用力,清末民初,在当代历史评价里被认定为最黑暗混乱与民族耻辱的年代,在年代剧里演绎成英雄辈出的传奇。当然,这种英雄的传奇“半是挽歌”,故事里渗满了苍凉的生命底蕴。
综上所述,年代剧通过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互文映照,大跨度书写真实而有力的人物生命历程,显现在历史、时代、民族等宏大命题约定下个体生命的鲜活烙印,从人物的童年遭遇、青年的血气方刚、中年的中流砥柱,一直到晚年的英雄迟暮,表现他们为生存、为尊严、为爱情、为家国的不屈挣扎与抗争。因而,时间才是年代剧要表现的深层主题,正是在这种真实历史时间背景下,年代剧对时间的烙印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和主题深化的可能,并达到了影像之雅俗共赏的艺术旨归。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间[M].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张清华. 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J]. 文艺研究,2006(7):416,158.
[3]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96.
[4]赵静蓉. 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457.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Time narrative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period series”,in which story time shows its duel nature,fictional time corresponding to the true historical time.But most of the “period series” show preference to the historical time,especially to evoke patriotism,or direct at no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In addition,they also incline to express the continuality of time that internalized in some characters through bleak reminiscence.
Key words:period series;story time;time narrative;cultural symptom
三、苍凉的生命时间的书写
清晰的历史时间坐标,是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生命体认。生于乱世,人之命运受制于年代,如《闯关东》中的夏元璋一家妻儿全死于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旅顺的大屠杀,没有直接的因果,就是你赶上了。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你是否赶上了也是当代人最真切的时代体认,这就是个体生命与所处时代的关联,生命时间的一种外在限定。然而,艺术对生命的把握更包含通过记忆生成的作为一种精神概念而存在的生命时间的内在特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是孔子发自肺腑的对时间的诗语感叹;普鲁斯特在一个巨大的小说记忆架构里“追忆似水流年”;塔可夫斯基用一种“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的电影语言雕塑生命,烙印时光,他甚至认为雕刻时间才是导演工作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所在,而且这种雕刻还须指向个体独特而内在的生命价值体验。[1]64
年代剧作为类型化的系列电视连续剧,在影像的打磨上相对高成本投入的大片自然难免粗糙,但相比同期其他电视剧剧种,在艺术的创作旨趣上无疑最接近“雕刻时光”这一美学命题。其实,如果不是吹毛求疵,至少在年代剧的代表作《大宅门》、《乔家大院》和《闯关东》中,这种生命咏叹的主题显而易见。
首先,年代剧借鉴了中国传统叙事中“以人带史”的创作手法,对历史时间的把握通过典型的生命个体形象的塑造来呈现,而且在叙事模式上都不约而同地追求传奇人物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的书写,从生到死,悲与壮、离与散、热闹与冷寂的边缘,年代剧让故事的传奇演绎成生命的悲歌。《大宅门》从白景琦出生开始,写他顽劣的童年往事,独闯济南研创黑七胶、自立大宅门门户的青年时代,及其与家国命运共存亡、誓死保卫秘方的中年,到疲于儿孙争家夺产的暮年,一生叱咤风云,但对这种热闹的讲述却悲壮而哀婉。《大宅门》的大结局写到白景琦自己进棺材、立遗嘱,回首一生,虽百折不屈,却最终也只能分家,散财,蹲坐在宅门口矮矮的石门槛上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大宅门》里类似这样的生命挽歌极为普遍,如杨九红、白玉婷等形象的塑造都氤氲着悲剧色彩。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对生命的咏叹主要是通过梦来抒发。梦醒后,乔致庸对镜自语:追问自己这辈子过得值吗?却发现自己过去的生命都葬送在一些琐事上,最终成了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只有银子和院子的老地主,一生的热情、智慧、才学和勇气,犹如阳光落在深渊。英雄迟暮,时间于生命的悲凉在此展示得如梦如痴。
其次,年代剧中的生命咏叹主题还表征为一种挽歌式的怀旧。通过影像烙印时光,记录生命,以一种文学式的怀旧,来反抗时间的川流不息。而怀旧,不同于回忆或记忆,“怀旧根本就是把过去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当下重新现实化。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其‘看到的过去也未必完整或真实,怀旧是一种有选择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当怀旧指向自然、民族共同体、精神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怀旧则完全是形而上的,它靠想象支撑起对过去的重构。”[4]年代剧的想像性怀旧首先体现在对“家族”观念的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观念被当作阻碍青年自由发展的禁锢而屡遭批判。如果说《红楼梦》对家族之大厦将倾充满了无比的眷顾与惋惜,那么,到张爱玲、张恨水和巴金这一辈人的笔下,家多成了爱情不自由、个性受压抑、家庭里到处充斥着礼教的残忍及长者绝对权威和卫道士的无耻。这类小说中塑造的家长多是无能腐朽者。然而,在新世纪人们自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当现代化城市将人隔离在没有故乡,没有童年,没有邻居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丛林里时,人们开始以一种想象式的怀旧重构传统的家族文化。年代剧多以家族叙事,宅院文化为载体,在探索个体与家庭命运时也多借鉴《红楼梦》、《家》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小说文本中“家国同构”的手法,但这里的家族重新被认定为亲情、力量、民族大义等正能量内涵,家长形象也大为改观,如《闯关东》中的朱开山,《大染坊》中的陈寿亭,《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大宅门》中的白文氏和白景琦,即便是《走西口》中被预设为赌徒和败家子的田耀祖,也因其舐犊情深而使总体形象得到温润。当然,这只是一种意向性的重构,是断裂的传统文化与急剧变革时代下无处安放记忆的经验个体的一次造梦,犹如影像中的老宅,幽暗成了神秘。正因为这种想象性怀旧的作用力,清末民初,在当代历史评价里被认定为最黑暗混乱与民族耻辱的年代,在年代剧里演绎成英雄辈出的传奇。当然,这种英雄的传奇“半是挽歌”,故事里渗满了苍凉的生命底蕴。
综上所述,年代剧通过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互文映照,大跨度书写真实而有力的人物生命历程,显现在历史、时代、民族等宏大命题约定下个体生命的鲜活烙印,从人物的童年遭遇、青年的血气方刚、中年的中流砥柱,一直到晚年的英雄迟暮,表现他们为生存、为尊严、为爱情、为家国的不屈挣扎与抗争。因而,时间才是年代剧要表现的深层主题,正是在这种真实历史时间背景下,年代剧对时间的烙印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和主题深化的可能,并达到了影像之雅俗共赏的艺术旨归。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间[M].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张清华. 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J]. 文艺研究,2006(7):416,158.
[3]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96.
[4]赵静蓉. 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457.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Time narrative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period series”,in which story time shows its duel nature,fictional time corresponding to the true historical time.But most of the “period series” show preference to the historical time,especially to evoke patriotism,or direct at no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In addition,they also incline to express the continuality of time that internalized in some characters through bleak reminiscence.
Key words:period series;story time;time narrative;cultural symptom
三、苍凉的生命时间的书写
清晰的历史时间坐标,是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生命体认。生于乱世,人之命运受制于年代,如《闯关东》中的夏元璋一家妻儿全死于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旅顺的大屠杀,没有直接的因果,就是你赶上了。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你是否赶上了也是当代人最真切的时代体认,这就是个体生命与所处时代的关联,生命时间的一种外在限定。然而,艺术对生命的把握更包含通过记忆生成的作为一种精神概念而存在的生命时间的内在特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是孔子发自肺腑的对时间的诗语感叹;普鲁斯特在一个巨大的小说记忆架构里“追忆似水流年”;塔可夫斯基用一种“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的电影语言雕塑生命,烙印时光,他甚至认为雕刻时间才是导演工作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所在,而且这种雕刻还须指向个体独特而内在的生命价值体验。[1]64
年代剧作为类型化的系列电视连续剧,在影像的打磨上相对高成本投入的大片自然难免粗糙,但相比同期其他电视剧剧种,在艺术的创作旨趣上无疑最接近“雕刻时光”这一美学命题。其实,如果不是吹毛求疵,至少在年代剧的代表作《大宅门》、《乔家大院》和《闯关东》中,这种生命咏叹的主题显而易见。
首先,年代剧借鉴了中国传统叙事中“以人带史”的创作手法,对历史时间的把握通过典型的生命个体形象的塑造来呈现,而且在叙事模式上都不约而同地追求传奇人物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的书写,从生到死,悲与壮、离与散、热闹与冷寂的边缘,年代剧让故事的传奇演绎成生命的悲歌。《大宅门》从白景琦出生开始,写他顽劣的童年往事,独闯济南研创黑七胶、自立大宅门门户的青年时代,及其与家国命运共存亡、誓死保卫秘方的中年,到疲于儿孙争家夺产的暮年,一生叱咤风云,但对这种热闹的讲述却悲壮而哀婉。《大宅门》的大结局写到白景琦自己进棺材、立遗嘱,回首一生,虽百折不屈,却最终也只能分家,散财,蹲坐在宅门口矮矮的石门槛上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大宅门》里类似这样的生命挽歌极为普遍,如杨九红、白玉婷等形象的塑造都氤氲着悲剧色彩。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对生命的咏叹主要是通过梦来抒发。梦醒后,乔致庸对镜自语:追问自己这辈子过得值吗?却发现自己过去的生命都葬送在一些琐事上,最终成了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只有银子和院子的老地主,一生的热情、智慧、才学和勇气,犹如阳光落在深渊。英雄迟暮,时间于生命的悲凉在此展示得如梦如痴。
其次,年代剧中的生命咏叹主题还表征为一种挽歌式的怀旧。通过影像烙印时光,记录生命,以一种文学式的怀旧,来反抗时间的川流不息。而怀旧,不同于回忆或记忆,“怀旧根本就是把过去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当下重新现实化。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其‘看到的过去也未必完整或真实,怀旧是一种有选择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当怀旧指向自然、民族共同体、精神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怀旧则完全是形而上的,它靠想象支撑起对过去的重构。”[4]年代剧的想像性怀旧首先体现在对“家族”观念的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观念被当作阻碍青年自由发展的禁锢而屡遭批判。如果说《红楼梦》对家族之大厦将倾充满了无比的眷顾与惋惜,那么,到张爱玲、张恨水和巴金这一辈人的笔下,家多成了爱情不自由、个性受压抑、家庭里到处充斥着礼教的残忍及长者绝对权威和卫道士的无耻。这类小说中塑造的家长多是无能腐朽者。然而,在新世纪人们自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当现代化城市将人隔离在没有故乡,没有童年,没有邻居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丛林里时,人们开始以一种想象式的怀旧重构传统的家族文化。年代剧多以家族叙事,宅院文化为载体,在探索个体与家庭命运时也多借鉴《红楼梦》、《家》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小说文本中“家国同构”的手法,但这里的家族重新被认定为亲情、力量、民族大义等正能量内涵,家长形象也大为改观,如《闯关东》中的朱开山,《大染坊》中的陈寿亭,《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大宅门》中的白文氏和白景琦,即便是《走西口》中被预设为赌徒和败家子的田耀祖,也因其舐犊情深而使总体形象得到温润。当然,这只是一种意向性的重构,是断裂的传统文化与急剧变革时代下无处安放记忆的经验个体的一次造梦,犹如影像中的老宅,幽暗成了神秘。正因为这种想象性怀旧的作用力,清末民初,在当代历史评价里被认定为最黑暗混乱与民族耻辱的年代,在年代剧里演绎成英雄辈出的传奇。当然,这种英雄的传奇“半是挽歌”,故事里渗满了苍凉的生命底蕴。
综上所述,年代剧通过故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互文映照,大跨度书写真实而有力的人物生命历程,显现在历史、时代、民族等宏大命题约定下个体生命的鲜活烙印,从人物的童年遭遇、青年的血气方刚、中年的中流砥柱,一直到晚年的英雄迟暮,表现他们为生存、为尊严、为爱情、为家国的不屈挣扎与抗争。因而,时间才是年代剧要表现的深层主题,正是在这种真实历史时间背景下,年代剧对时间的烙印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和主题深化的可能,并达到了影像之雅俗共赏的艺术旨归。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间[M].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张清华. 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J]. 文艺研究,2006(7):416,158.
[3]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96.
[4]赵静蓉. 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457.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Time narrative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period series”,in which story time shows its duel nature,fictional time corresponding to the true historical time.But most of the “period series” show preference to the historical time,especially to evoke patriotism,or direct at no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In addition,they also incline to express the continuality of time that internalized in some characters through bleak reminiscence.
Key words:period series;story time;time narrative;cultural symp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