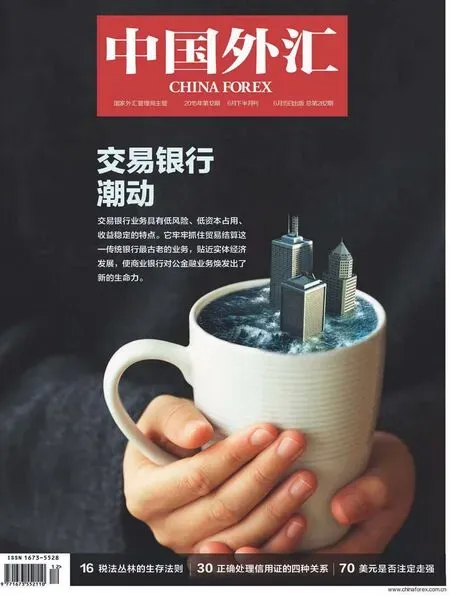“税法丛林”的生存法则
2015-01-02向延建编辑蔡原江
文/向延建 编辑/蔡原江
“税法丛林”的生存法则
文/向延建 编辑/蔡原江
通过不断学习、适应巴西的税务法律制度,华为公司逐渐找到了在巴西“税法丛林”中的生存之路。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在法律上先行一步。这是对外贸易投资的基础,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公司”)进入巴西市场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学习、适应巴西税务法律制度的过程。
联邦税务案:起死回生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对网络发展有巨大需求。华为公司从1996年起开拓巴西市场,1999年在巴西正式注册公司。经过20年发展,华为公司已成为目前巴西第一大综合网络设备供应商,2014年合同销售额达15亿美元。但巴西经营环境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税务制度高度复杂、管理严格、遵从性要求高、法律实体及程序繁多等。中国企业初来乍到,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适应巴西的经营环境。华为公司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适应过程。
联邦税务案件是华为公司在巴西经历的最大一起税务案件。2007年1月,巴西联邦税务局以2002~2006年期间华为公司违规进口为由,开出了约2亿美元的罚单(该处罚在之后长达8年的行政审理期间累积了接近4亿美元的风险总金额)。华为公司对此不服,向巴西联邦收入局裁决委员会(下称CARF)提出行政二审。同年8月,该案件第一次进入行政二审阶段。四年之后,CARF第二次开庭,法庭形势对华为公司有利,但当地税务局任命的一位法庭审理员却节外生枝,提出要把另一家第三方公司一并纳入处罚对象,导致案件没有进入表决程序,而是被发回税局重新处理。事实上,税局已经对该第三方公司另案处理,该官员如此不合常理的提议,就是为了阻止案件顺利结案。
华为公司此前的一切努力化作泡影,该案重回原点。当地税务局一直在寻找华为破绽,希望在对它有利的情况下迅速结案进入执行程序。2012年12月,当地税务局做出了维持原处罚的一审裁决。按既定路径,华为公司再次就一审裁决提出行政二审到CARF。由于税局采用了内部网站送达方式,华为公司在程序上错过了一个月的有效上诉期限。2013年初,当地税务局启动了案件执行程序,华为公司数亿美元的罚金将被强行划走。
对此,华为公司立即由其南美地区部总裁牵头,成立了由巴西代表处主管、地区部CFO、地区部法务部长、巴西法务经理等组成的最高级别的6人应对小组,继续与时间赛跑、与政府执行局(PDFG)斗智斗勇的诉讼大战。首先,华为公司根据巴西法律直接向法院申请了临时禁令,暂停了执行局的行动。执行局立刻反击,启动了对临时强制令的上诉,要求撤销强制令。华为针对执行局的上诉也迅即提出了抗辩。其次,华为向法院申请裁决书送达无效,认为税局新的送达方式存在瑕疵,未尽到对拟处罚企业充分明示的义务。最后,华为公司抢先启动行政二审立案申请。这是因为执行局就临时强制令的上诉和华为就裁决书送达效力的起诉两个官司同步进行着,按巴西法律规定,谁先出结果就对谁有利。为抢得先机,华为公司打破常规,启动了在CARF的行政二审立案申请,执行局再次陷入被动。2013年10月,案件终结,华为公司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企业的预期目标。
这起案件极具典型性。对中国企业来说,国际税收通常相当复杂,一旦产生争议,流程往往相当冗长。以巴西为例,其税务体系与税务申报系统均非常复杂。巴西联邦、州与地市层面有超过60多个不同的税种,并且税务机关对于进出口属地和数据、会计记录及税务申报的电子化要求相当高,若不事先做好税务研究,则很容易出现因无法满足当地税务合规性的要求而面临税务争议与罚款。鉴此,中国企业在税务筹划或面临税法案件时,如果企业无法以最优的税务架构实现自己的效益目标,就需要对多方面的因素权衡考虑,在研究并“吃透”当地的税务法律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一套次优架构,以尽可能使税法执行的各方都能够接受;在税法诉讼中,则应据理力争、灵活处置,在法律制度范围内和可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护企业自身的利益。
圣保罗州税案:挽回近3亿美元
2012年3月中旬,巴西圣保罗州裁决委员会(以下简称TIT)重新表决,确认华为公司圣保罗州税务案件的抗辩理由成立,华为公司无需承担纳税义务,累积风险金额超过2.7亿美金的两个处罚遂被撤销。这起案件起因于当地税务局对华为公司2003~2006年期间进口模式的质疑。圣保罗州税务局认为,巴西华为注册地在圣保罗,应该直接从圣保罗州进口,在圣保罗州缴税,而不应该从别的州进口并纳税,华为公司的进口模式属于虚假交易。据此,2008年该局对华为公司先后进行了两次处罚,总金额高达1.8亿美元。
这一案例实质上是华为公司设备进口州和华为巴西公司注册州这两个州之间的税款争夺。从2008年到2010年,该案一直僵持不下。2010年,负责行政二审的TIT做出了维持税局处罚裁决,意味着案件的正常行政程序已经结束。华为公司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主动交纳罚款和迟延罚息;要么将案件起诉到法院,而这需要提供巨额银行保函。此时,加上高额利息,该案累积的风险金额已经达到2.4亿美元。无论哪种情况,华为公司都要承担巨大的损失。
能否打破常规,寻找第三种选择?华为公司在巴西的合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Abel律师提出“特别上诉”建议,即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行政阶段特别上诉。但以往的经验表明,除非申请人能够证明此前同样的案件获得了与申请人现在不一样的裁决,否则获准立案的机会比较小。而经过查询,以往案件中并没有已裁决的同类案件。这也启发了华为人的思路:没有同类案件借鉴,可以是特别上诉不被立案的原因,但也可以是申请人要求立案的原因。而一旦“特别上诉”获准立案,就可以为华为公司争取1~2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外部局势变化或可为企业带来转机。
果然,华为公司提出“特别上诉”一年之后,巴西26个州联署了一份缓和税务战争的州际协议,对不同州的合法贸易公司进口再转售模式下的巴西境内买方的以往处罚案件一律豁免。华为公司立即召集律师和其他诉讼团队人员一起研究州际协议文本。然而,协议说明文本中规定:对于认定为诈骗或者虚假交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协议。华为案件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恰恰是虚假交易。如果能够推翻这个结论,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经各部门主管讨论之后,华为公司认为,该案件的关键在于对虚假交易认定标准的定义,不能依靠过去抗辩中单纯从字面上的解释,需要进行突破。为此,华为公司从已有的案例分析入手,找出以往不同机构、不同时期认定或者不认定虚假交易的判例来,从中归纳出对虚假交易的认定标准。几周后,华为公司的代理律师在抗辩书中提出了新的虚假交易的认定标准:仅有书面文档没有实质交易发生;或者采取阴阳合同、虚构合同等手段隐瞒真实交易。显然,华为的案情不符合这两条标准。抗辩书附件还列举了华为在巴西发展的事实:累计投资已达5.5亿多美元,在巴西网络设备市场所占份额平均达40%以上,公司员工90%以上是本地人,直接带动本地就业20000人,并创造了大量的间接就业岗位,仅在2010~2012年间已累计向巴西政府缴纳了7亿美元的税。
特别上诉和华为公司提出的对虚假交易新的认定标准成为两件“重武器”。TIT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半年多后终于做出了撤销对华为处罚的决定。2012年8月,这个持续了五年的税案终于正式关闭,华为公司最终避免了近3亿美元(根据结案时汇率计算)的损失。在巴西,只要认真研究当地各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化经营,企业经营就能够取得成功,获得收益。
从无知无畏到谨小慎微,再到沉着自信,华为公司在巴西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2013年,华为公司在巴西第一次实现了利润和现金流“双正”。华为公司巴西法务工作已经伸出了新的业务触角:税务筹划、劳工风险治理、黑名单清理、关税节省、子公司合并等。税案官司、节税筹划两手都要抓,不输大官司,也不付冤枉税。入乡随俗,华为公司逐渐找到了在巴西税法丛林中的生存之路,同时也说明,在巴西,只要认真研究当地各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化经营,企业经营就能够取得成功,获得收益。
作者单位:华为公司法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