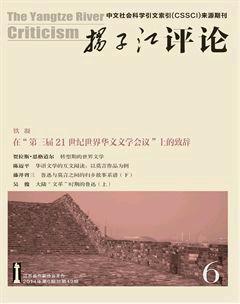视像之“变”与视点之“常”
——丁玲散文集《欧行散记》《访美散记》综论
2014-12-31秦林芳
秦林芳
视像之“变”与视点之“常”
——丁玲散文集《欧行散记》《访美散记》综论
秦林芳
丁玲的《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在性质上均属国外记游散文。其中,前者出版于建国之初的1951年,后者则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4年问世,前后间隔了三十三年,时间跨度相当之大。虽然它们成文于两个不同的年代,虽然它们叙说的对象也明显有异,但是,丁玲贯注其中的政治心理和意识倾向却是一脉相通的。二者相比,变化的只是表面的视像,而在其政治心理支配下形成的深层次的价值视点则一以贯之。事实上,在这两个集子出版的间隔期里,丁玲的人生运程和政治生活曾出现过巨大的波折。具体来说,在《欧行散记》出版四年后、在《访美散记》问世五年前,在这段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反右派”斗争以及接踵而至的改造流放,使丁玲饱受了左倾政治的迫害,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丁玲自左联时期起形成的政治心理。因此,将这两部性质相同、时间跨度很大的散文集作一综合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晰、也更加集中地看出丁玲这种政治心理的恒常性和贯通性。
一、视像:“明天”与“昨天”
这两部散文集分别记述的是作者三次“欧行”(以“访苏”为其主要内容)与一次“访美”的经历与感受。那么,丁玲亲临现场、亲手触摸到的“苏联”和“美国”给她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她的这两部散文集又以怎样的视像呈现了她的这些记忆呢?
总的说来,她所呈现出来的“苏联”视像和“美国”视像分别代表着的是“明天”与“昨天”。在1955年所作的一篇散文里,丁玲曾对自己心目中的“苏联”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这里有很多是我们今天的事,但在苏联昨天曾有过;而我们向往着的明天,却又有很多就是苏联的今天。”①虽然这段文字作于《欧行散记》出版四年后,但其中所表达出的将“苏联”视为“我们向往着的明天”的思路却贯通了整部《欧行散记》,它事实上也成了《欧行散记》描绘“苏联”视像的精神总纲。《访美散记》对“美国”视像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那就是“昨天”。其开篇之作即被她命名为《向昨天的飞行》。文中,她借同机的一个华裔美国人的议论(美国“许许多多人生活不错,可是空虚,一片空虚”)和自己的感悟(“生活可能是美国方便”,但“人情是中国好”),为整部《访美散记》定下了书写基调。其中所谓的“昨天”,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时差问题;从她的书写内容来看,它更隐喻着美中两国在文明层次上所具有的“昨天”与“今天”的落差。
在《欧行散记》中,丁玲怀着“一个美好的感情,一个爱”②,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到“苏联人”,全面神化了具有“明天”性质的“苏联”视像。她将作为苏联象征的“莫斯科”比作是她“心中的诗”,将自己说成是“不会说苏联话的莫斯科人”,以不能抑制的激情,向作为苏联象征的“莫斯科”发出了“我爱你!……因为你太伟大了,你太丰富了,你太理想了,你太崇高了,你太庄严了,你给人的启示太多了”的热烈歌吟(《莫斯科——我心中的诗》)。她还将“苏联”比作“故乡”,将自己对苏联的感情比作是“人们对故乡的感情”,以“充满了幸福”的心情,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爱苏联”的情感(《苏联人》)。
从整部集子来看,她之所以如此“爱苏联”,首先在于苏联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吸引了她。如《苏联的三个女英雄》描写了在斯达哈诺夫运动中出现的三个女英雄的光辉事迹。其用意既在讴歌苏联的“新人”,也在借此讴歌苏联的经济建设成就(物质文明),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制度文明)。在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晚会上,丁玲又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女工。她由此感悟到,一个劳动模范能够享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度里才有可能。于是,她将对“一个英雄在社会主义社会上的地位”的如此描写,导向了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赞许。《列宁格勒和保卫列宁格勒博物馆》则侧重揭示苏联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尽所有力量教育人、提高人的理想和品质”,能够使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变得更伟大一些”。因自己的特定身份,丁玲在《欧行散记》中予以更多关注的是苏联的文学艺术。在写作《欧行散记》的过程中,丁玲在天津发表过一个讲话。她将“中国文艺”与“苏联文艺”作了一个对比,称前者“今天还是‘课本’阶段”,而后者“今天是把人提高一步”③。她对“苏联文艺”的这种理性认识,在收入《欧行散记》的《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苏联美术印象记》《塔娜莎娃的〈安娜·卡列尼娜〉》《乌兰诺娃的〈青铜骑士〉》等较多篇什中一再外化了出来。在这些作品中,她赞赏苏联产生了“那样完美的艺术”,其中有“特别能为我们所喜爱”的俄罗斯文学、令人“永远敬重”和“无限的留恋”的“苏联的美术”以及给人们带来“高级的艺术享受”的塔娜莎娃、乌兰诺娃的表演艺术等。
其次,丁玲“爱苏联”,还在于“伟大的、热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公民”感动了她。在她的笔下,“苏联人”是世界上使她“景仰”、“留恋”的最完美的人:他们“使人类的生活提高,保卫世界的和平和增进人类的幸福”,“充满了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的自信和乐观”,其人生观高尚而充实;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又真正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具有“为人类事业乐于牺牲的品质”;他们每个人都很勤恳,“又极有趣味、各有风趣”,“人与人的关系是极友好的,单纯的,正直的”,其人格自然也健全而高贵(《苏联人》)。除此之外,“苏联人”还有着“崇高的思想”(《苏联的三个女英雄》)和很高的“文化修养”(《塔娜莎娃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们是历史的保卫者,他们的辛勤,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列宁格勒和保卫列宁格勒博物馆》),因而其精神境界也显得美好而高远……
总之,在《欧行散记》中,丁玲以澎湃的激情,对苏联的一切(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所有这些文明的创造者——“苏联人”)作出了全面的认同和热切的赞美。她以“凡苏联一切皆好”的求同思维方式,将苏联描画成了一个只能用“‘天堂’、‘乐园’、‘神仙世界’等等字眼”来形容的神话般的存在(《儿童的天堂——保育院》),从而呈现出了一个纯然的“明天”视像。而即便如此,她《〈欧行散记〉序》中还声言自己远远“没有写完我对苏联的爱”,其所写还“没有表现出百分之一的感情”。可见,“苏联”在其心目中该有何等的神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三十多年后所作的《访美散记》中,她则以求异思维方式,将美国当作“昨天”之视像,通过对比和转折,倾尽全力地描绘了“美国的影子”——那些“笼罩着我”、“压迫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的“浓重的阴影”④。自然,丁玲不能否认高度发达的美国现代物质文明。《访美散记》中的《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五月花公寓》《芝加哥夜谭》《曼哈顿街头夜景》等篇,确也从其生活的富足、科技的发达、交通的便捷、环境的优美整洁等方面,写出了美国的“繁华、现代化”。但是,她的这些描写,却没有其自足之价值。不仅如此,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倒适成其没落的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之反证。她在美期间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的科技是好的,生活是好的,但文化是低的……什么理想也没有”⑤。这段话和盘托出了她对美国的认知。在这种认知的作用下,在创作《访美散记》时,她不但在整体运思上,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往往顿起转折,以“蓝天之下,也有乌云”(《约翰·迪尔》)式的极其尖锐的(有时也是不合常理的)对比,揭出了美国视像所具有的“昨天”之性质。
《访美散记》对美国作为“昨天”视像的描绘,是借助于揭露和剖析美国社会尤其是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种种弊端而完成的。其锋芒所至,主要涉及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商业文明和精神危机等。在揭露美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纽约的住房》《汽车与计程车》。它们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是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介绍了纽约的住房和计程车,在介绍中甚至还突出了住房的种类繁多、管理严格和计程车的“实在也方便”,但在结尾处,却又分别借“人们告诉我”的美国有“流浪汉”和自己所见计程车内的安保设施这两个细节展开了缺少关联度的联想,陡然转折,曲终奏雅,将立意升华到揭露美国贫富不均和批判“有过可怕的戏剧性的危险发生”之“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宏大主题上去了。
《超级市场》是批判美国商业文明的代表之作。该文在手法上与上述两篇文章一样,也使用了欲扬先抑之法。它以很大的篇幅分别介绍了爱荷华等城市卖食品和卖衣服的超级市场的“方便”,甚至由此也说到“美国的工厂、商人为消费者设想是非常细致和周到的”,但最后一段却又陡起转折,并从下列两个方面对美国商业文明展开了批评:首先,它批评美国本身是个“大的超级市场”,其本性就是惟利是图:“凡是好的,有用的,美国都不遗余力地去挖掘、搜集、网罗、购买,不惜血本。但一旦被认为过时了,陈旧了,无利可图了,便都无情地扔掉,毫不可惜”。这就把她在同期一个公开演讲中所指陈的“资本主义社会看重钱”⑥的命题具体化了。其次,它由如此处理商品货物的方式联想到美国“使用人力”问题,说“这样对待商品货物,还可以无足厚非,但对待人才,使用人力,也是这样,那就未免过于残酷了”。如果说她所作第一个层次上的批评虽显严苛(因为讲究成本、追求利润本是市场经济之规则),但在文本上总算还有所依凭的话,那么,第二个层次上的批评则是建立在毫无关联度的联想基础上的,因而,其中所包孕的不但有其对美国商业文明理性上的批评、更有情感上的憎恶。
在美国社会诸多问题中,丁玲最为关注的是其精神层面的问题。《二十九日又一页》《电影〈锡鼓〉及其它》等篇,一再写到美国的精神病象:“缺乏信仰,精神空虚”;“不关心他人”,“人与人之间冷漠”;“精神生活”腐朽,“艺术创造”也“萎靡不振”等等。在揭示其精神堕落表征的同时,丁玲在《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等文中还具体分析了原因。说到底,其精神危机形成的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的冷漠,利害竞争,弱肉强食,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既以“金钱”和“个人”为中心,因而它给人们脑子里塞进去的只能“是意大利烤饼,法兰西香水,或者就是空虚,无信仰,‘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具体到美国出版业,“审查官”是由商人充任的,其衡量作品的标准就是利润原则;商人和“金钱”的支配,导致了“向读者传播自私,引诱青年放荡、犯罪”之“黄色无聊的作品”的泛滥。总之,在她看来,这种危机的形成,是这种制度因素所导致的,而危机的出现又进而加剧了这种制度性问题。
二、视点:两种文化立场与同一政治心理
综上,在两部“散记”中,丁玲所呈现出来的“苏联”视像和“美国”视像各自代表着“明天”与“昨天”。因为性质不同,所以,这两个视像之间出现了巨大反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它们的问世间隔了三十多年,也虽然它们所呈现的视像本身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隐含在其视像之后的视点(即主体的政治心理)却是恒常如一的。这正构成了其“变”中之“常”。
应该看到,丁玲笔下这两个视像之间巨大反差的出现,是与其双重文化立场互为因果的。在全球化时代到来、各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为了求得自己的发展,既必须坚决摒弃本土文化虚无主义,去努力发掘本土文化的合法性,以建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又必须坚决摒弃以本土文化为中心去排斥异元文化的文化中心主义,去积极学习和借鉴异元文化,以弥补本土文化之不足。对丁玲而言,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它们客观上都属异元文化。因此,面对着它们,丁玲本应以我为本,而兼取他者之长。但事实上,她却走上了一条与之完全背反的道路。
首先,在对“苏联”视像的呈示中,丁玲灭失了自我文化的主体性,表现出了将本土文化虚无化的倾向。如前所述,丁玲对“苏联”是全方位肯定的,其中所隐含的是“凡苏联一切皆好”的文化立场。固然,当时的苏联确实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先进文化,因而,以向苏联学习、借鉴苏联成功经验的方法来改变我国落后的文化现状,也符合我国文化发展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丁玲说苏联和中国“像一对哥哥和弟弟……一个在前一点,一个在后一点”⑦,是基本符合实际的;说“你们各方面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你们好好学习”⑧,也是不应一概否定的。但是,毋庸置疑,丁玲却在对“苏联”文化无条件的认同中,灭失了对之进行自主审视的理性。二战以后出现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使丁玲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找到了“同志”、“自己人”的感觉。对此,丁玲在《〈旗帜〉杂志编辑部给我的鼓励》作了这样的描述:编辑把她“当成他们自己人”,而她也体会到了“同志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感觉的作用下,丁玲发现了“我们”,却又在对“我们”的认同中忘却了“我”,忘却了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她以“我们”“在一条路上前进”的认知,灭失了文化上的他我之别,由此,她自然就不用分辨地将他者文化的“今天”视为自我文化“明天”的方向。这种文化逻辑所导致的只能是对自我文化主体地位的消解。
其次,在对“美国”视像的呈示中,丁玲却以文化中心主义的张扬,表现出了以异斥异、盲目排外的倾向。与《欧游散记》对“苏联”视像的勾画相比,丁玲的《访美散记》在勾画“美国”视像时倒是始终保持了应有的警醒和批判的态度。较之于前者中那种肤浅的赞美,应该说,它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并因此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不但如此,它对于异元文化的如此态度,对于建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异元文化持必要的理性的批判的态度,其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对之作出辨析,以择取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从而在融合借鉴中实现本土文化的自强。这也就是说,批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否则,对于一种曾经辉煌而现实中落的民族文化来说,就极易跨过“批判”的桥梁,而在观念上走向本土文化中心主义、在行动上走向保守和排外。
丁玲赴美作实地考察,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主动打开国门、自觉向异元文化学习的年代。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当她置身于美国这一异元文化环境里时,她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发现者”和“学习者”,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身暂在此而心永在彼的“偶然的,匆忙的过客”。这个“彼”,显然就是她一再称颂的“中华精神文明”。1983年5月,在刚作完《欧游散记》所有单篇时,丁玲在一个演讲中对此说得就很明白:“尽管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平不高,物质条件比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比人家丰富得多。因此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最光明的地方。”⑨这段话时可以说是对《欧游散记》立意的一个注释。这种对自我“过客”身份的认知,导致了其在情绪上的疏离和对抗(“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并进而使之形成了其观看“他者”的特定角度——她虽徜徉在热闹的、灿烂似锦的街头,却不但“看不出它的美丽”⑩,倒反而随处看到“许多浓重的阴影”。上述丁玲对美国社会制度、商业文明和精神危机这些“浓重的阴影”的揭露批判,无疑是丁玲在中华精神文明这个参照系中展开的,是其以异斥异(即以不同文化排斥不同文化)的结果。丁玲这种“以我观他”的文化立场,有很强的先入为主的色彩。它显然既影响了对“他者”的客观全面评价,最终也不利于本土文化在交流互补中的自强。
总之,对于“苏联”、“美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丁玲所持是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所显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这一方面导致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显然,这两种文化立场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它们却又均根源于丁玲本人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同一种政治心理。1930年代初,丁玲因胡也频牺牲的强烈刺激,思想急剧“左转”,并投身到了革命和集体的行列。此期所作《田家冲》《水》等作品,以“集体”、“政治”和“为革命”为其思想立足点,也鲜明地传达出了丁玲的“革命意识”。此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丁玲思想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革面洗心”⑪式的改变,更是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⑫。丁玲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构建起的这种以“革命”为核心、以“党的立场”为自己立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政治态度、情感等政治心理的形成。她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受压迫者”和“压迫者”这两个阶级阵营,以政治化的二分法思维断定“艺术不可能守中立”(它“不是替大多数受压迫者说话……便是替少数压迫者说话”)⑬,并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国内题材的创作中,通过描写贫苦农民和地主阶级两大阵营的对垒和斗争,鲜明地表现出了她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
丁玲的这种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由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心理定势,自然也会在《欧游散记》《访美散记》等国外题材创作中外化出来。与上述国内题材作品相比,这两部国外题材散文集只是将“阶级阵营”的外延作了扩展,将之放大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这样,她的阶级意识就随之演变成了“阵营意识”,她的阶级斗争思维也随之演变成了“冷战思维”。如前所述,她把“苏联人”视为“自己人”、把自己在“苏联”视为“在家里一样”(《法捷耶夫告诉了我些什么》),而说自己在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正是这种“阵营意识”和“冷战思维”的极好喻示。在这种政治心理的观照下,既然“苏联”和“美国”对于“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意义,那么,为了呈显它们不同的政治价值,丁玲必然会从“我们”的政治需要出发,选择这两种不同的乃至矛盾的文化立场:对于前者,“他”就是“我”,因而,“我”就是“他”;而对于后者,“他”不是“我”,因而,“我”必斥“他”。所以,丁玲对两种不同文化立场的择取,其实倒是出于同一种政治需要和同一种政治心理。
丁玲是抱着这种政治心理去触摸“苏联”和“美国”的。在奉命去东欧参会途中,丁玲就意识到此行承担着“国家的任务”,因而“要努力和别人(指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者)接近”,“要合作得好”⑭;在去美国前,她也宣称自己“不是去写作的,而是想为中国去做一点工作”⑮。这种政治心理自然既决定了她在异邦怎么看,又决定了她后来对异邦怎么写。反过来,在她怎么写中,我们自然也能够看出其隐藏其中的政治心理。我们看到,在《欧行散记》中,丁玲不但客观地描写了两大阵营的对垒,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主观倾向。一方面,她讴歌代表“民主、自由”、“和平”和“前进力量”的东方阵营“必然受到欢迎拥护,必然日渐壮大”(《保卫和平,争取和平——旅捷散记》),另一方面,则抨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罪恶,勾画了“美帝的狰狞面目”(《十万火炬》)和“很可笑地生活着”的“美国人生活的本质”(《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揭露了它们“企图独霸世界,挑起新的战争”的阴谋(《通过〈保卫和平宣言〉》)。丁玲写作《访美散记》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虽未结束,但在此之前,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此时,丁玲对“美国”的态度虽然不再像写作《欧行散记》时那样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而是淡化了不少敌意,但是,她在文化立场上仍然以本土文化中心主义排斥美国文化,仍然流露出了其意识形态上的许多偏见。不难看出,丁玲的这些偏见仍然是冷战时代里的“阵营意识”和“冷战思维”所致。虽然她在《访美散记》中多次说过:“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相信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彼此友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⑯;“应该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认真克服自己弱点,我们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⑰。但是,它们仅止于抽象的观念表达层面。如上所述,丁玲通过许多具体描写,特别是通过那些缺乏关联度的联想对比,彻底颠覆了这些观念,而将之倒转为对其“弱点”的呈显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访美散记》是丁玲从文化上描绘“美帝的狰狞面目”和“美国人生活的本质”的续篇。
综上所述,《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分别将“苏联”和“美国”作为“明天”视像和“昨天”视像进行了呈示。在对这两个视像的呈示中,丁玲表现出了将本土文化虚无化和中心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虽然这两类视像和其中蕴含的两种文化立场不同,但是,它们却又均根源于创作主体的同一种政治心理。这显现出了丁玲的“变”中之“常”。正是这种具有恒常性和贯通性的政治心理的作用,使丁玲选择了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立场、并对这两种对象作出了如此的呈示和评价。
【注释】
①丁玲:《春日纪事——我们是兄弟》,《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下引《丁玲全集》其他各卷,版本均同此。
②丁玲:《〈欧行散记〉序》,《丁玲全集》第9卷,第81页。
③见王端阳编录:《王拉日记·文艺十七年》中的1949年12月25日日记,《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
④丁玲:《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丁玲全集》第6卷,第145页。
⑤丁玲:《致蒋祖林》(1981年11月2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14页。
⑥丁玲:《谈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456页。
⑦丁玲:《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丁玲全集》第5卷,第358页。
⑧丁玲:《〈旗帜〉杂志编辑部给我的鼓励》,《丁玲全集》第5卷,第376页。
⑨丁玲:《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丁玲全集》第8卷,第329—330页。
⑩丁玲:《曼哈顿街头夜景》,《丁玲全集》第6卷,第203页。
⑪陈明回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她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封面的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见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⑫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全集》第7卷,第65页。
⑬丁玲:《作家与大众》,《丁玲全集》第7卷,第43页。
⑭丁玲:《致陈明》(1949年4月2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81、82页。
⑮丁玲:《致周良沛》(1981年3月18日),《丁玲全集》第12卷,第169页。
⑯丁玲:《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丁玲全集》第6卷,第246页。
⑰丁玲:《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丁玲全集》第6卷,第263—264页。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种文学传统’视野下的丁玲文学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5105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