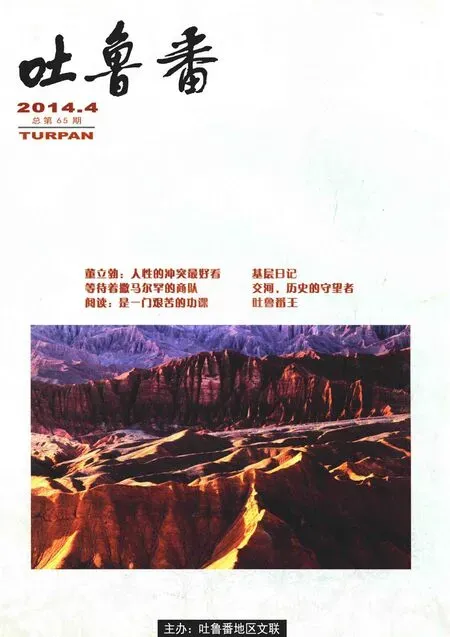喂马站
2014-12-25王爽
王 爽

喂马站,是大帮哄年代农村生产队的队部,也是生产队车马集中的场所,门前有一个巨大的粪堆。同时还是用来开社员大会和下地干活之前集合的地方。
昔日的喂马站,一般都是一个三合或四合的宽敞大院。正房至少有五间,中间大多是烀饲料的灶屋兼磨房,一边的两间带有与住户一样的通连大炕,可以兼作会议室,另一边的两间则是粮种和小农具仓库。东西厢房如果一侧是大农具仓库,另一侧就是马厩和草料库了。院角还应该有一口水井,井旁有一个饮牲口的大水槽,由粗大的圆木抠成,夏天我们在喂马站里玩儿,热了常到水槽子那里洗脸。嫌牲口饮过的水脏,就拔去槽子底下的木塞子,让水流出去。再重新打上来一柳罐兜子净水,倒入水槽里。
由于牛粪不好收拾,所以牛棚一般设在院外的大粪堆附近。院外还有草垛,是给牲口备用的饲料,用墙围着,附近还有场院、更房子和碾坊。
由于拉车耕地等粗重活儿离不开畜力,因此每个生产队差不多要养二十左右匹大马和二十左右头耕牛。老年人习惯把喂马站叫“社底儿”,这个称呼应该是从农村生产合作社年代延续下来的,我们则习惯称喂马站或简称马站。由此可见,当农村尚未普及机械化之前,以马为代表的牲畜,在农业生产劳动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设在喂马站偏房的马厩,乡下人称它马圈,一般是两三间大小,前脸有矮墙但没有窗子,地面铺着木板。马是站着睡觉的,它们在圈里头朝外并排站着,胸前是支架起来的马槽,吃的是营养更丰富一些的谷草,里边拌上泡过的高粱。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饲养员夜里要起来一次,往马槽里加一次草料。
老牛的待遇,相对差多了,牛棚简陋,草料里也没有粮食。农忙时,它们白天拉车或拉犁,中午由牛倌把它们赶到壕沟帮子或草甸子上吃青草。晚上收工后,再把它们赶出去吃半宿野草,然后赶回牛棚,慢慢倒嚼。到了没有青草的冬季,由牛倌负责喂他们一些干草料,饮大井的水。如果时逢冬闲没有什么活儿,就一天晚上喂它们一顿,白天解开缰绳,让它们自己到野地里找干玉米秸或柴禾叶子吃。
夏季每逢雨后,大地一片泥泞,牛马就可以放松休息一天半天的,由车老板负责在草甸子里放马,牛倌放牛。此时如果突然来雨了,马就会拼命地往喂马站跑,而老牛则不怕雨淋,跟没事儿似的。如果下得太大,就慢悠悠地往回走。
生产队的马圈旁,还有两间房子是草料库,里边堆着草料。门旁放着一把加工牲口饲料的铡刀,铡刀的刀片有一米多长,约十五公分宽,前端有个穿铡刀钉的圆孔儿,后端有个安装木把儿刀裤,铡刀的刀床一般是个整块方木抠制而成,前端有横孔儿,与刀片上的孔儿对齐,穿上铡刀钉便可以用来工作了。
将喂牲口的草,铡成寸八长的小段儿,既便于消化,又容易与高梁或豆饼这些精饲料搅拌到一起。铡草时,由一个人续草,另一个人手握刀把向下用力。由于铡草是个力气活儿,常常要在刀把上再装个横木长把儿,用于两个人同时用力按压铡刀。铡草的人和续草的人相互配合,续草的人把草向前移动近一寸,铡刀便“嚓”的一声铡过去,动作敏捷,循环往复,肌肤节奏感。但铡草时切忌疏忽大意伤到续草的人,我们到这里的秃爪子周二,就是当年在铡草时续草不慎,被铡刀切掉了两个手指头。
那时乡下没有机械车辆,一年里见不到几次过往的汽车。寂静的村落偶尔路过一辆拉货的汽车,会远远就能听到马达声。小孩子们从不同方向蜂拥到路边,好奇地看这个怪物,常常还要跟随着碾起的灰尘追赶一段。
有自行车的人家也极少,人们出行,哪怕三五十里都是步行,因此大马车便成了乡下最奢侈豪华的交通工具。生产队的马车平时忙于生产,除非本屯子的姑娘出嫁需要送亲,才能给出一天车。再就是赶年集时出一次车,还得早早去生产队等着,去晚了就有可能没了座位。
平时赶路遇到后边赶上来的顺路大车,要先跟车老板打招呼,请求搭车捎上一段,这叫做“捎脚”,在那个年月是常有的事。我上中学时,有一次放学路上,大队分销店的毛驴车从后面上来了,我想他们也都认识我,就不用客气了,一蹿就上车了。结果“咔擦”一声,有一块大镜子让我给碰碎了。我尴尬地下了车,心里十分沮丧。
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主动去赔。分销店的经理说:“算了,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已经打入损耗了。”
当年小伙伴们发生争执或打闹时,常常用一句童谣来戏谑地劝架:“别打别打,二十八甲,要骡子给骡子,要马给马。”简简单单的童谣,却从侧面反映出大骡子大马在那个时代的价值所在。
有一次,四姥爷问我,拖拉机上标着的“二十八马力”是啥意思。我信口开河地说,是二十八匹马的力气。其实我在回答时,心里一点儿底气也没有。但四姥爷已经点头,还夸我聪明,说我说的差不离。
那年秋天,生产队买回来一匹枣红马,队长想试一试它的力气,就从车上解下一副马套,套在枣红马身上,他又把马套接长,让七八个壮劳力拔河一样地拉住。喜欢好奇的我此时刚好放学赶到,便马上加入其中,在最后面凑热闹。队长扬鞭赶马喊“驾!”,那马四蹄蹬地开始发力,我们与枣红马仅僵持了几秒,便跟头把式地摔得满地爬。那一刻,我真正见识了一匹马的力气。
正在哺乳期的牲口,饲养员就给弄“小灶”吃,在拌料时添加一些豆饼。我们在喂马站玩儿的时候,如果赶上饲养员切豆饼,就拿几块吃,挺香的。饲养员肯定会吆喝我们,不让吃,但那吆喝是象征性,表示他在维护公家利益。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置若罔闻,照吃不误。
公马又叫儿马,母马又叫骒马。儿马成熟后,脾气较大,性情暴烈,一旦见到发情的骒马,就会难以操控。如果到兽医站将儿马骟了,它性情就稳定温顺了,且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地出力做活。刚骟的儿马,要歇几天,但不能静养,得由专人遛它,以防刀口肿胀或有粘连。尾巴也要缠上,免得它乱甩弄脏弄裂伤口。
乡下没有专门的牲畜配种站,都是车老板观察母马有发情迹象后,在喂马站院子里用固定的种马与其交配。我们火烧泡子的马圈里,有一头高大的黑驴,专门用来配种。驴配马生出来的应该是骡子,骡子虽然不再生育了,但高大有力。在生产队的院里玩耍时,我们偶尔会见到配马的场面,但在那个年代,十二三的孩子都特别单纯,看到配马、配牛或是狗连裆,只当是看个热闹,竟然没有产生与人的联想。
分田到户后,养马的就少了,铃铛山响神气十足的大马车也不见了,养牛的农户曾一度剧增。印象中,当时在村委会的后院,曾有个给母牛做人工授精的配种站。
后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普及,养牛户也渐渐地少了。听老农讲,现在已经找不到可以放牛的地方,田埂越来越窄,防虫除草都要喷洒农药,牛在乡下已经难以生存,以后想看到牛马,恐怕就得去城里的动物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