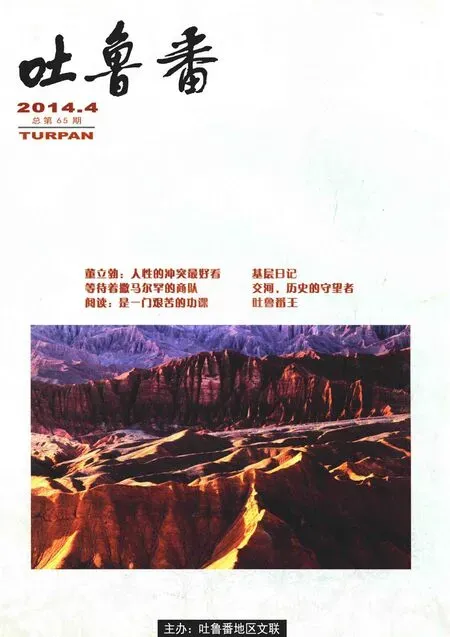交河历史的守望者
2014-12-25碧小家
碧小家

一
“交河故城”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书·西域传》中:“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城下,故号交河。”汉书的解释无疑是准确的,伫立在吐鲁番高高土冈的交河故城南北狭长达1700余米,中腰最宽处达300余米,像一个柳叶船舰一般呈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原河水至此向南分流城下的遗迹依然历历在目。
交河故城和其他故城相比,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一没有高大的城墙,二是一座从台地上深掘出来的天然土城。迄今为止,如此罕见独特的土城,在世界上还是独一无二。
每年入冬以后,凛冽的寒风一阵阵从火焰山与盐山之间扑泻而下,然后掠过吐鲁番大地。天长地久,啸啸厉风将平展而坚实的黄土撕裂成一道又一道的沟壑,将交河大地造就成片片土冈。如削的土冈峭壁高达30余米,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要想攀登如此陡峭高耸的土壁,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车师前王庭坐落于厉风长啸的交河土冈上?
为什么唐王朝统一吐鲁番地区后,曾一度将控制西域大局的安西都护府设在了交河城头?
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一种解释:为了战争。
交河故城应该属于战争的,它诞生于战争,最终又毁于战争。
人类的残酷、血腥、贪婪,在动荡不安的交河城头的旗帜变幻中,在交河千年的荣衰中一幕幕地升起,又一幕幕地沉落下去!
向台地下挖,比垒墙艰难十倍的筑城方式,隐隐透出古人对战争、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情。正是这些不安的阴影笼罩在交河人的心头,迫使他们构想和筑造出如此奇特的土城。
这座曾经威震中亚的赫赫名城,由于四面的悬崖峭壁而直接制约了其发展前景——它只有城而没有势。它犹如一只古老的沉船,由显赫一时的安西大都护府渐渐沦落为小小的交河郡,最终沉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变得沉默而苍凉。原来,曾经壁垒森严的城郭外表下,蕴藏着的却是一个孱弱的灵魂。
二
如若从公元前三世纪算起,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交河城毁灭,这之间足足有1600多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交河古城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风雨的剥蚀和战争的击打?这座名声赫赫的大城曾经以刀剑寒光的威猛姿态高高地蹲踞在吐鲁番大地上,它曾经牵动过无数人的神经、思绪和感情,它使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显赫过,同时也悲伤过;它使许多王权之梦升腾过,同时也破灭过;它是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发生在吐鲁番大地的纷繁往事的见证者……最终,它沉入了历史的长河中,留给了大地现实一只干枯僵死的大手,留给了今人一片没有生命的枯叶,它在无尽的岁月中变得沉默寡言,满目苍凉。
两千多年又过去了,交河城头曾经猎猎飘动的战旗、河谷中咴咴嘶鸣的战马啸叫声随着王城的毁灭,早已飘然而逝,它渐渐变成了飘动在人心灵深处的一段陈年旧梦。值得当今人赞美的往往不再是大城的历史,而成了大城本身千年不衰的顽强与坚韧。二十多个世纪过去了,大城容颜依旧傲立于土冈,默默蹲踞成一种柳叶状姿态,苍凉而悲壮地坚守在吐鲁番大地上。
其实,沉卧于吐鲁番大地的交河故城并不显得有多么寂寞。它不像柏孜克里克佛窟那样深隐于世人难以涉足的荒寂之山中,除了每日如云的游人外,交河古城的台地下,沿着一道道深深切入大地深处的沟谷伸展,谷中泉水淙淙,绿树成荫,环境清幽宜人,村庄的鸡鸣狗吠声不时地穿越浓荫,在河谷与台地的上空缓缓地飘荡着。于是,几千年来,大城不急于消亡和沉没,它愿意以永久的沉默姿态安详地占据着台地,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现实苍生。
三
西汉时期,交河古城是车师前部王国的首都。那时,匈奴人与西汉王朝对立抗衡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交河城头。粗略计算一下,从公元前108年开始,到公元前60年匈奴人归降汉王朝为止,前后50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人在交河曾经有过5次大的角逐,历史学家称其为“五争车师”。
交河城,作为车师前王国的都城,经历了七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在交河城头,才最后一次永远地降下车师前王国那面呼呼飘响了700年的王旗。
车师前王在失去自己的国土时,竟在交河城头苦苦坚守了八年!足见,作为一个王权者,对失去自己的国土、自由、乐园、天堂和梦想,是多么的不情愿拱手相让啊!
车师国灭亡后,便进入了麴氏高昌王国。公元640年,唐王朝控制高昌、统一西域后,交河城成了王朝设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这期间,有许多诗人墨客随军来到西域,为西域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最初踏上交河大地的唐代诗人李颀目睹了戍边将士的勇武和笼罩在交河城头的战争风云,写出了雄奇而悲壮的动人诗篇: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万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古军行》
同时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两度来到西域,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6年。天宝年间,他随节度使高仙芝到安西,后又随封常清到北庭。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他曾不断地往返于西州与北庭之间。这当儿,他来去交河境驿馆,留下了一笔又一笔的马科支用账。这些账册,在交河大地下沉睡了一千多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年代中期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
岑参保留至今的大量边塞诗中,吟咏交河的也不少,如《火山云歌送别》、《夜宿交河有感》、《交河》等,现摘录一首以飨今人:
浑躯大宛马,击取楼兰玉
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
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骷髅,皆是古战场。
——《交河》
有了诗人李颀和岑参的诗为证,唐时交河的干旱、炎热和多厉风的恶劣环境,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悲怆和痛苦,都一一跃然纸上,历历可感。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瓦解,后来,短时期的安西都护府又迁到了龟兹。公元九世纪中叶后,回鹘人自漠北草原大规模地西迁,交河又成了回鹘王朝的军事重镇。高昌回鹘王朝以西州为都城,以天山北麓的北庭故城为夏都,交河城成了王公贵族们来去天山南北的驻节地。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响于高昌大地时,这里的回鹘人毫不迟疑地投在了蒙古汗大王的麾下。直到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初,蒙古人对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徒发动了一次圣战后,交河城在这次惨烈的圣战中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此后的许多年,它像一艘失去了大海的远洋战舰,永远地搁浅在了吐鲁番大地,成了后人不断瞻仰,不断叩问的历史纪念品。
四
生存于吐鲁番大地最早的居民遗迹是从交河城西南的台地上发现的。最初,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留下来的打制石器。后来,考古学家又在阿斯塔那村北戈壁、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吐峪沟、鲁克沁附近的荒漠之地,发现了大量的细石核、细石片、小石镞、锯齿型刮削器等细石器。用来切割羊肉的小石叶,尤其是那小小的刮削器,形状如指甲盖,直径只有7毫米,其工艺的精湛、完善,是当代人为之惊叹!
车师人,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出现在吐鲁番大地的居民。2500年前的车师人已经知道使用金属工具。在交河台地,在现代吐鲁番绿洲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车师人曾经生活过的足迹。那时的入土者已有了衣服和鞋帽,有了食品和各种生活器具。男子头戴毡盔,女子头戴各式尖帽,他们在漫长的劳动岁月中创造了毛纺织品、皮革品、陶器、木器,他们钻木取火,蓄养牲畜,他们还种麦子、谷粟、黑豆和葡萄等,他们还能对病人的胸部操刀一割,留下了毛线缝合的医术痕迹……
丰富的新石器告诉了人们,两千多年前的吐鲁番大地已是树影婆娑,一片繁荣景象。汲水的少女曾经在交河边的清清碧水中投下过婀娜的身姿,河边的庄稼地里满目禾苗曾经随风摇曳过,在吐鲁番大地,在交河河畔,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响彻过丰收的歌声……
五
当代人,对于交河城曾经发生过的事总是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渴望和叩问的心情,他们期望弄清古人的经历,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就这样,每日的远游者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奔至交河城下,他们的脚步声永不停息地回荡在交河城的街头巷尾……
走在交河故城的深深巷道里,被两边高大的城墙迫压着,总让人感觉在那些壁垒森严的土墙后面,好像隐蔽着一双双警惕而敌视的眼睛。走进故城的东北部,可以看到保存相当完好的古代民居。这些民居大多是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的。巷道路面,也都是挖地取土而形成的路沟。这种建筑风格,是车师人的一大创造,显露的是车师人的智慧。仔细想一想,在两千多年前,面对着土质坚硬的土冈,在缺水少木的境况下,还有比这种生土、夯土、土坯和版筑建筑物更实用、更切合实际的建筑方式吗?两千年来,交河古城依然能屹立于吐鲁番大地,这就是历史对这一朴素无华的建筑作出的最高评价。
在众多的民居小院墙角,古人挖了许多深井。井深40多米,清冽冽的井水,在黯淡幽深的井底一闪一闪的,犹如一只只沉默的眼睛注视着你。粗略数了一下,这种古井在交河城共有40多眼。
随着佛教文化传入西域,交河古城城成了一个时期的佛教文化重地。如今,那些保留完整的、用版筑的众多塔林寺院建筑成了当时佛教文化兴盛的见证者。在塔柱四面的小龛中依稀留存的残破佛像,由于长时间经受厉风剥蚀,使他当年的光彩和魅力早已荡然无存。泥塑佛像暴露在外的草束骨架、黄土身躯呈现出一种无限的凄凉。
这些宏大的寺院和100座舍利塔很可能是建筑于回鹘高昌王朝时期,它伴随着回鹘高昌王朝走完了最后的岁月。随着蒙古人的铁蹄踏响于吐鲁番大地时,这些佛家寺院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曾经被烧得通红的寺院向今人证明着那灰飞烟灭的历史一瞬。
六
夜间仰望那肃穆的繁星吧!
那亘古至今依旧旋转的天体——
即使最了不起的权威和最崇高的盛名,
在他们面前也显得坐井观天!
还要想到,所有人不分贫富,
也不论聪慧和痴顽,
在此后千秋万代的绵绵岁月里,
都同样进入无尽的长眠。
——惠特曼《抱负》
几千年来,在交河城头疯狂地争夺过和贪婪地强占过的人;为了王权、金钱和美女操矛执戈,在胜利中被拥戴为王的人;在交河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变成一位人人尊崇的大英雄的人;在辉煌中接受过欢呼和荣耀的人;在战乱中死里逃生,或一箭未发已被对手击倒的人;为了自由、正义,为了饥饿和被奴役的地位而奋起抗争的人;为了活命出卖过弟兄的人;被胜利者赶出交河城门、惴惴不安左顾右盼地奔跑在逃亡之路上的人;重整旗鼓,又卷土重来的人……如今,都静静地躺在了交河台地上!
一睡万事休。一切贪婪和狂妄,一切不可化解的矛盾在岁月老人面前,都会变成一丝烟云,飘然而逝。在交河故城官署区同一台地上有一处墓葬区,一个个被掘开的墓穴在正午的阳光下,犹如一只空茫的眼睛,望着沉寂的天空,一言不发。无论是带着丰厚殉葬品的贵族墓,还是一无所有的“婴儿墓”,如今都平静地躺在台地上,不再喧闹,不再炫耀,不再悲伤,不再痛苦。
往事如一阵阵云烟飘散了,唯有土城犹在,它表现出的耐力无与伦比。也许,有关土城繁纷错综的史话大多有人为的虚假和揣测中的不真实,然而,伫立在交河千年的土城是真实的,它成了吐鲁番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它成了历史撤退时留在吐鲁番大地的最后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