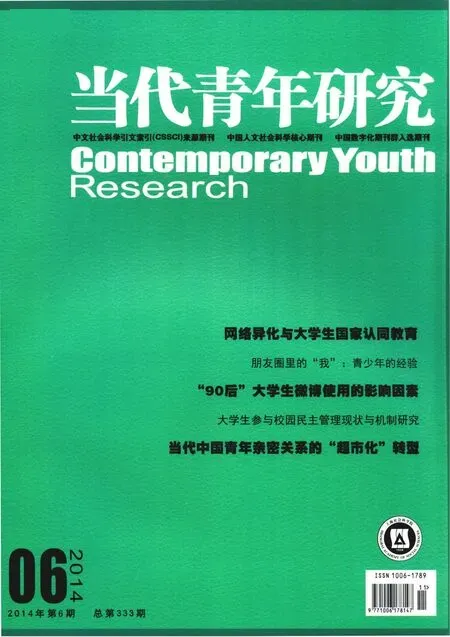论大学生同学关系疏离的普遍性
2014-12-23邓雅丹吴建平
邓雅丹 吴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
近来,围绕复旦大学投毒案及相关的高校恶性事件所展开的一系列报道,引起了人们对高校大学生同学关系的普遍关注,人们在对类似的极端事件表示同情、忧虑的同时,也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归因。比如:有人将这类事件归因于个人心理问题, 并将这种心理问题的形成归结到个人成长经历或家庭背景等特殊因素;有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现代年轻人的独特个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同学间交往障碍,并往往会给他们贴上诸如“80 后”、“90 后”等标签;也有观点宽泛地将之归为教育问题,认为国内的教育只注重智育或才育而失之于德育,造成学生之间的关系冷漠;还有观点认为是社会风气使然,等等。 这些归因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合理性,毕竟任何社会现象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单一性的,而是由诸多复杂因素综合而成。 但是,就像矛盾论所指出的那样,矛盾存在主次之分,那么,对于当前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关系疏离,甚至一些极端现象,其中的根本原因或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针对这一主要矛盾,我们是否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呢?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之间出现的疏离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的疏离现象不过是社会急剧转型必然引发的社会失范现象的一种表现。 针对这一问题,教育仍是基本的解决办法之一,但在具体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本文认为,通识教育或许迫在眉睫。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针对大学生同学关系的疏离现象,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者予以了积极关注,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彭少军指出,目前大学生同学交往存在不和谐,表现为同学交往理念有偏差、缺乏正确的交往技巧和交往主动性不高、缺乏正确的异性交往理念和方法。 对此,他从外部原因和个人原因两方面作出了解释,并从大学生自身和学校等外部环境提出建立和谐关系的路径。[1]刘学伶等人描述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不理想不和谐的现状,认为这种不和谐会导致个人心理疾病;并从社会上人际关系淡化趋势、大学生个性特征、对自我成才的片面理解三方面剖析了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原因。[2]景庆虹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总体人际关系、宿舍人际关系、学校人际交往能力、课程开设情况、恋爱关系、与父母老师的沟通频率六个方面对北京市30 所高校实施样本调查,得出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乐观的结论。[3]陈锐和黄生学在研究中将大学生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不适当的交往观念、缺乏交往的主动性、缺乏同学交往的正确方法和策略、异性交往的困惑与烦恼等类型,并从个人心理层面提出了调适策略和方法。[4]
对既往研究的整理发现,研究者基本认同大学生同学关系存在疏离问题,并大多将缺乏交往技巧、理念偏差等个人特征视作原因。但这种对个人内部原因的归因解释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缺陷。因为,如果归因于个人原因,那么个人特质千差万别,同学关系的疏离应该是小范围的个别现象,或者说是纷繁多样的同学关系中的一种而已,并且这种现象应该伴随着同学关系的产生早已有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大。 但我们的直观感受是,社会并非一直是用淡漠、功利等这些表示疏离的词汇来评论大学生的同学关系,相反这些字眼都是近些年才被采用的,在这一过程中,还往往会伴有对过去同学关系较为亲近的对比和眷恋。 可见,仅在个人层面上理解和解释同学关系不和谐的现象是不充分的。
建立同学关系看似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当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时间里存在的“同学关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时,“这个整体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的总和,也不是一个聚合性的整体,而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它的统一性和特性,因而有它特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主要是社会性质”。[5]因此,自然需要将社会层面纳入考虑,即寻求这种现象深刻的社会根源。 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的疏离,实质上是急剧社会转型处境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 涂尔干曾指出,急剧社会变迁必然引发社会失范。 在急剧变迁的处境下,“大批的人突然无法适应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切既定的标准被打乱了,对许多人来说不可能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原本形成的某些关系被搅乱了,由此产生一种混乱意识”。[6]“‘混乱’是指正常状态的丧失和解体。 ”[7]急剧社会变迁时,外部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目不暇接的发展,传统经过一代一代地稀释,渐渐失去了权威感,渐渐被怀疑式地拷问,渐渐被疏远,急迫地渴望着新鲜事物。 然而当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节各种需要的尺度也就不可能再维持原来的样子。 原来的社会标准被打乱,但新的标准尚未建立起来,因为失控的各种社会力量尚未建立起新的平衡,各种价值观还处于未定状态。 此时,“社会生活并非由习惯所支配;个人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中;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要求很多,因此,他们经常感到欲望和满足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痛苦”。[8]当一切制约机制都在混乱中失效了,人心也就此迷失了。 我们怎么能期盼在标准混乱的社会中个人的内心却保持良好的秩序呢,怎么能期盼个人会以除了恼怒和反感之外的情感来面对整个社会团体呢,怎么能期盼人与人际关系能够和睦友好呢?
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危机的症结在于社会的失范,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变迁来说,也难以避免出现社会失范问题。 事实上,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失范”一词,并指出当前我国“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 在对社会失范概念的具体解析方面,国内学者渠敬东指出,社会失范的表现之一便是“关系的断裂”(另两个表现是制度的变迁和意义的缺失)[9],因此,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下滑、人与人关系冷漠淡薄就是普遍社会失范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 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即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表现出来的种种疏离现象是社会转型处境下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现象必然具有普遍性特点;极端事件的出现,则是在关系的普遍性疏离的处境下,加上一些个人因素而引发的结果。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对于同学关系疏离普遍化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同学关系由交往而建立,因此“疏离”首先体现在交往过程当中,即关系过程中的疏离程度;其二,也许大家的交往比较频繁,似乎在关系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疏离,但这并不表示大家对这种频繁交往的结果感到满意,因此,还需要分析关系结果中的疏离程度。
在本研究中,分别用六个指标制成两个李克特量表,对“关系过程的疏离”和“关系结果的疏离”两个变量进行测量。 前者的指标包括如下陈述:“很多同学的交往主要在网上进行”,“多数同学间的交往是以宿舍为单位”,“除了上课,我与一些同学的见面机会很少”,“我与好些同学基本没有什么交往”,“平时我们班里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多”,“我们很少去别的宿舍串门聊天”。 后者的指标包括如下陈述:“同学之间关系很疏离”,“同学之间彼此信任度不高,防范心理强”,“同学之间交往功利化严重”,“班干与同学的关系比较差”,“同学有困难,很少有同学真正关心”,“我甚至一时半会说不出某个同学的名字”。 计分以满意为正方向,得分越低,说明被调查者对关系过程和关系结果的满意度或认同度越低,关系过程和关系结果中的疏离越高。
本次研究的问卷调查于2011 年初在北京市某普通本科院校进行,在抽样方案上,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以年级为标准进行分层。本次调查总共发放了600 份问卷,最后回收有效问卷573 份,有效回收率是95.5%。调查对象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男生261 人(45.5%), 女生312 人(54.5%);18 岁及以下69 人(12.1%),19 岁99 人(17.4%),20 岁158 人(27.8%),21 岁141 人(24.8%),22 岁及以上102 人(17.9%);一年级136 人(23.7%),二年级163 人(28.5%),三年级156 人(27.2%),四年级118 人(20.6%);来自发达地区学生116 人(20.2%),来自中等发达地区252 人(44.0%),来自不发达地区198 人(34.6%),不明7 人(1.2%)。 为了能更深入地掌握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的疏离现状,本次调查还于2010—2011 年期间进行了实地访谈,对不同年级的19 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
(二)研究假设的细化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存在普遍性的疏离,提出两个分假设:分假设1(H1):当前大学生在关系过程中存在普遍的疏离;分假设2(H2):当前大学生在关系结果上存在普遍的疏离。
在本研究中,引入性别、年龄、年级和生源地四个因素,最终需要检验的假设如下:H1—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关系过程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1—2: 不同年龄的大学生在关系过程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1—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关系过程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1—4: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关系过程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2—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关系结果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2—2:不同年龄的大学生在关系结果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2—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关系结果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H2—4: 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关系结果的疏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调查结果与发现
(一)各指标基本情况分析
测量关系过程中的疏离的指标统计结果显示:56.2%的学生同意(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很多同学的交往主要在网上进行”;66.7%的学生同意“多数同学间的交往是以宿舍为单位”;57.6%的学生同意“除了上课,我与一些同学的见面机会很少”;44.3%的学生同意“与好些同学基本没有什么交往”。 由数据得到的直观感受是现今大学生的同学交往过程并不乐观,交往频率较低。 访谈对象对此也提供了验证:“大学都很散,上课的位置想怎么坐就怎么坐,大家很有那种小团体意识……班上不搞什么集体活动,我们基本就都不会有交际,就不会在一块说话交流。”(访谈对象3,男,大一)“根本一点集体意识没有,如果没有老师组织,比如开班会之类的,大家就很难聚在一起。 ”(访谈对象6,女,大四)“有的同学整个学期都见不到几次,都认不全哪个人是哪个人,我也只能够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但是你说要有所了解就不可能了,甚至可能进校两年,我和对方说话合起来都没有10 句……也没什么活动制造大家互动的机会,甚至时间久了大家都很淡漠,即便组织活动也没几个人参加。 ”(访谈对象7,女,大二)
测量关系结果中的疏离的指标统计结果显示:43.3%的学生同意 “同学之间关系很疏离”;45.4%的学生同意“同学之间彼此信任度不高,防范心理强”;41.8%的学生认为“同学之间交往功利化严重”。 上述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同学关系的信任、亲近认同度不够高。同样地,访谈调查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彼此共同语言和交流都很少,彼此感情表面化”(访谈对象3,男,大一);“就像浮萍漂在水面,看似亲密无间,实际水下的根相分相离”(访谈对象2,男,大四);“只是局限于宿舍或同乡的小圈子交往,整体上缺乏凝聚力”(访谈对象5,女,大四);“甚至宿舍也分出小群体,或者干脆就是碎片化的孤立状态”(访谈对象7,女,大二);“而且彼此防范心理严重,关系日趋目的化和功利化”(访谈对象9,女,大三;访谈对象5,女,大四)。
对上述两个李克特量累加得分结果进行百分制处理发现,被调查对象对关系过程和关系结果的满意度评分的平均值都偏低(见表1),换言之,被调查对象对关系过程和关系结果中的疏离感都较高。 90%的被调查者的关系过程量表的得分在26.01—53.81 分范围内;90%的被调查者的关系结果量表的得分在33.845—65.055 分范围内。 由此可见,目前大学生同学关系的确存在较为严重的疏离问题。

表1 对关系过程与关系结果的满意度的统计结果
(二)各研究假设的检验
针对前文提出的8 个分假设,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检验,统计结果见表3。
对分假设H1—1 至H1—4 的检验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得知,在α=0.01 的显著水平上,年级、生源地和年龄组,在对关系过程中的疏离的主观评价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唯独性别具有显著性影响,相比而言,在对关系过程的满意度评分上,男生要高于女生,换言之,在对关系过程中的疏离感上,女生要高于男生。 可见, 除了H1—1 外,H1—2、H1—3 和H1—4 这三个假设都不能拒绝。 对分假设H2—1 至H2—4 的检验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得知,在α=0.01 的显著水平上,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年龄组这四个因素都不对关系结果中的疏离具有显著性影响,因此,H2—1、H2—2、H2—3 和H2—4 都不能拒绝。
综合而言,分假设H2(即当前大学生在关系结果上存在普遍的疏离)获得了通过,而分假设H1(即当前大学生在关系过程中存在普遍的疏离)只在性别因素上未获得通过(不过这个差距只有3.3 分),在其余三个因素上也都获得了通过,因此大体可以认为,H1 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通过。 结合H1 和H2,基本可以断定,当前大学生的同学关系的确存在普遍性的疏离问题。

表2 各影响因素与关系过程、关系结果的方差分析表
四、结论与讨论
调查数据确实表明,当前大学生同学关系存在普遍性疏离问题。 前面指出,反映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这种普遍性疏离,不过是整个社会普遍性的关系断裂的一个表现而已,而后者正是社会急剧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失范的一个层面。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类似于一种“社会潮流”,普遍弥散在社会当中,就像“流感”一样包围着我们;同样,就像不同个体在面对“流感”时因个体体质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一样,不同的个体、人群或组织,在面对这种“疏离潮流”时,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有些表现得不那么强烈,而有些表现得极为剧烈,就比如文章开篇所指出的极端事件。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面对这种带有必然性意义的普遍性的“疏离潮流”时,并非是无可奈何的,而是有予以弥补或改善的可能的。
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问题时,涂尔干曾强调过“集体意识”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尝试从建构“集体意识”的角度,来思考目前高校存在的普遍性疏离的危机问题。 对于大学而言,“集体意识”具体是由什么代表或支撑的呢?存在于校园里和大学师生之间的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和文化语言就是一种“集体意识”。因此,本研究认为“通识教育”不失为值得一试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曾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所有不同科系、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所有不同科系、不同专业的人应该在大学内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这就是他提出的‘通识教育’主张,所谓‘通识教育’就是对所有人的‘共同教育’。 在哈钦斯看来,如果现代大学没有这样一种‘共同教育’,那么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各个不相同的系科和专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性,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只有这种通识教育才能沟通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人,从而建立大学所有师生的共同文化语言。”[10]更为重要的是,通识教育让大学生能够一同去思考具有共同性、永恒性的经典论题,在该过程中,逐渐在学生内心中搭起一种对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共同感。 因此,本研究认为,化解普遍性疏离乃至社会失范,通识教育提供了一种重要且可能的渠道。
[1]彭少军.大学生和谐同学关系建立策略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3(9):196-197.
[2]刘学伶、白仲航、张慧敏、田丽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调试与改善[J].中国成人教育,2010(17):77-78.
[3]景庆虹.大学生人际关系危机的调查分析及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97-98.
[4]陈锐、黄生学.大学生同学关系的调适[J].柳州师专学报,2006(2):107-109.
[5][6]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274.
[7][8]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09,317.
[9]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