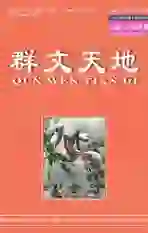昆剧何以缺少地方戏特征
2014-12-23杨瑞庆
杨瑞庆
昆剧诞生在元末明初的江苏昆山,属于地方戏范畴。顾名思义,地方戏就是由特定的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戏剧,应该具有本地区的民风底蕴,为本地区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存在差异,曾先后涌现过300多种戏剧。在漫长的繁衍和流变中,相互借鉴吸收,取长补短,然后优胜劣汰,强留弱退,直至今日,只有数十个剧种还延留在剧坛上,并且,有的勉强维持、有的每况愈下、有的甚至奄奄一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今各地方戏的发源地已呈开放态势,由于人员流动,大多“移民”已难以适应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地方戏了,因为只有大多数人能看得懂、听得懂的戏剧,其生命力才能旺盛。相比较而言,北方的戏剧由于语韵接近要比南方的戏剧更容易被人接受,如京剧、评剧、豫剧的欣赏市场就比较活跃。由于昆剧存在着许多非地方戏的特征,所以也容易产生共鸣,虽然高雅,也吸引着不少天南地北的文人雅士。600多年来,昆剧生生不息,保存完好,因此被评为“世界级”的优秀文化遗产。
昆剧品位高、影响大,被公认为“百戏之祖”,其生旦净末丑的表演程式滋养了全国各地的地方戏,而唯有唱念部分的昆腔昆韵保持了“独领风骚”的纯正,因为这是昆剧中的精华,又与其他地方戏的常规特征格格不入,所以,保留着物稀为贵的唯一性而受到百戏敬重。
地方戏的最鲜明特征是唱念重用本地民言,腔调渗透本地民歌,剧情反映本地民生,表演富有本地民风,而这些地方戏的共性特点,昆曲偏偏回避。这好像有违地方戏的一般发展规律,现在看来却是昆山先人打造昆曲的聪明之举,因为只有不落俗套,才能独放异彩。
昆剧的非地方戏特征是在无意和有意中逐步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好多环节得益于本地人独辟蹊径的追求和外地人引进基因的融合。
昆山属吴语地区,其发声口音也具有吴侬软语的特点。昆山水网密布,一马平川,因此,话语是软绵绵的甜懦,歌调是水灵灵的委婉。但昆剧的唱念语音基本运用了中州韵的“北方官话”(除丑角重用方言外),唱腔素材基本是各种“经典曲牌”的变形设计。昆剧的这些特点好像都没有“昆山”的地方性特点,如要追根寻源,可以回首昆剧的发展过程,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据曲圣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说:“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待等魏良辅改良昆山腔一鸣惊人时,他把昆曲的雏形定格在“黄幡绰所传”的历史事件上。黄幡绰是唐玄宗时期的宫廷艺人,擅演“参军戏”、“木偶戏”,具有幽默的说表功力和高超的演唱技巧。安史之乱后,流落于江南信义(今昆山正仪)传播宫廷音乐,因此造就了这一带百姓能歌善舞的乡风民俗,也因此出现了如“傀儡湖”、“行头浜”等与戏曲有关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当然,黄幡绰那时传播的唱腔形态已不得而知,但它是西北人,一定跟江南音调大相径庭,一定带有粗犷、高亢的风格。那时,黄幡绰拍曲教唱,老百姓潜移默化,已经被动地接受了许多北腔北调。后来,黄幡绰寿终正寝,当地百姓感激他的教曲之恩,就把他厚葬在正仪的风水宝地绰墩山下。从唐宋一路传承下来,正仪地区的民歌已经“蜕化变质”了,已不知不觉地烙上了外来音调的印迹。
元末,正仪出了一位富商顾阿瑛,他精通书画,擅长诗文。由于从小受到当地音乐的熏陶,也酷爱编腔唱曲。为了吸引知音,广揽曲友,他投资营造了名闻遐迩的玉山佳处,并组建唱曲家班,终于引来了四方戏迷唱和昆山腔。其中,不乏北曲大家高朋满座、南戏大师云集一堂,为切磋戏腔而呕心沥血。由于南来北往的文人参与了昆山腔的改良,已经不自觉地将南腔北调熔于一炉,使早期的昆山腔就淡化了本地的“原生态”特点。
在玉山雅集的嘉宾中,有一位与顾阿瑛志同道合的朋友———昆山千墩(今千灯)的顾坚。如果说顾阿瑛把研磨昆山腔当作兴趣,那么,顾坚把研磨昆山腔当作了事业,所以,顾坚对于昆山腔的唱腔形态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当时,南戏四大声腔盛行,基本还带有各地坊曲俚调的乡土特点。为了能使昆山腔脱颖而出,顾坚赋予了昆山腔以高雅品格。一方面他“善作古赋”,吸收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格律,将唱词雅化;另一方面他“善发南曲之奥”,融会贯通了各南戏声腔中的精华,将昆山腔的旋律设计得更加妩媚、隽永。在玉山雅集同仁们的群策群力下,到了明初,昆山腔终于成为“鹤立鸡群”的“正声”。虽然,没有留下当时昆山腔的乐谱资料,可想而知,由于强调了高雅品味,唱腔难免会游离本土本色。
明嘉靖年间,江西南昌的魏良辅慧眼独识昆山腔的迷人魅力,深感昆山腔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同时又得悉昆山腔存在着“止行于吴中”的危机,于是,他背井离乡,为改良昆山腔而投奔昆山的怀抱。要知道魏良辅对身边的弋阳腔早已烂熟于心,和其他南戏声腔相比,弋阳腔的旋律和语言比较靠近北方风格,魏良辅在改腔过程中自然会渗透进一些外来音调。特别是他招北曲大家张野塘为婿后,与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了北曲的阳刚之美,当然会不自觉地运用到昆曲的创腔中去。所以,后人评介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为集南北曲之大成。
稍后的昆山曲家梁辰鱼,根据魏良辅的新编昆曲的格律进行填词,创编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奇《浣纱记》,使昆曲摆脱清唱形式而走向舞台演出的昆剧时代。由于梁辰鱼追求唱词的文采更华丽、更精美,树立起使昆曲更高雅的“昆山派”。典雅的“昆山派”影响了日后的昆剧创作。虽然,后来江西汤显祖追随“昆山派”的文采风格,与吴江沈璟提倡的“本色派”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但远离本土,弘扬高雅,仍然成为昆曲发展的主流方向。数百年来,昆曲我行我素地居雅独尊,为塑造戏曲舞台上的“阳春白雪”而前赴后继。
回首昆山的昆曲发展史,巧合的是几个关键人物接力移植了外来基因,如黄幡绰的“参军戏”、魏良辅的“弋阳腔”、张野塘的“北曲”等;又接力融合高雅元素,如顾阿瑛创立的“雅集”、顾坚创用的“古赋”,梁辰鱼创始的“昆山派”等,都为昆剧非地方戏特征的形成而推波助澜。由于外来戏曲精英的参与和本土高雅格调的追求,使昆剧产生了许多非地方戏特征的表现。
由于昆剧与本土风韵不够融合,所以远离了当地老百姓的审美爱好。当明初昆山腔声名大振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想分享昆山腔的优雅,他以为年纪大的人总会演唱,于是他召见了昆山百岁老人周寿谊进宫献唱。当皇帝开了金口:“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谁知老人直言不讳地说:“不能,但善吴歌”。害得皇上乘兴而邀,败兴而散。说明昆山当地也对昆曲敬而远之———因为腔词难懂、旋律难记、韵味难学而高不可攀,所以,昆曲只能成为文人雅士的附庸,凡人俗夫是难以成为知音的。学唱昆曲的人大多是学堂书生、闺阁才女,或者是科班拜师,世家传承,从而模仿经典,享受风雅。虽然薪火不断,但几回都是在“奄奄一息”中“死灰复燃”,传存得相当惊险。
昆曲作为昆山的家乡戏,理应扎根在昆山的民间并为百姓所热爱,但昆曲熔不进家乡调,演不了现代戏,只能被附近通俗的沪剧、锡剧、越剧所取代。由于没有演出市场,昆山从没成立过职业的昆剧团,只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堂名班子在勉强撑着门面。这在地方戏的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昆剧的这种孤芳自赏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圈内人自命清高,并蔑视其他剧种。如苏州的老郎庙中专演昆剧,其他剧种休想挤进。圈外人望曲兴叹,畏难高雅昆曲。当上个世纪20年代中由于滩簧戏平易近人,在“上海大世界”盛演不衰时,昆剧团却屡遭被驱逐的厄运。究其原因,昆剧缺乏地方戏特征,与苏南的乡风民俗格格不入,由于普通老百姓少感兴趣,使昆曲的传承危在旦夕。
昆剧少了地方戏特征,当然会少了本地知音。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昆山除了少数戏迷追捧昆剧外,大多百姓无动于衷。直至今日,每当各昆剧团“回娘家”演出时,即使敞门开放也难以满座。大家反映听不懂唱词,自然看不懂剧情。虽然都知道昆剧是昆山拥有的“国宝”级艺术,就是难以进入寻常百姓的欣赏领域,其制约昆剧普及的要害就是少了地方戏特征。
这种局面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当历史进入跨世纪时,昆剧迎来了被尊为世界级“非遗”的好运。究其原因,应该为昆剧存在的非地方戏特征而喝彩。正因为昆剧和一般地方戏不同流,才使昆剧一花独放,出类拔萃,成为顶级的艺术精品。现在看来,昆剧为中国的戏曲发展建立了令人瞩目的丰功伟绩:
一是唱词采用古赋,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高雅艺术。
二是唱念采用北韵,疏通了传播中的一些语言障碍。
三是旋律采用曲牌,诞生了少有的曲牌体结构体系。
由于昆剧中非地方戏特征的存在,而制约了昆剧在昆山民间的传播。昆曲确实委屈了昆山人,盛名之下的昆曲,只有自豪感,少有享受感。但是,昆山人又聪明绝顶,不走常规、不落俗套———避通俗,追高雅,可谓创新至上而成为独特。虽然昆曲被捧为“百戏之祖”,已经敞开胸怀,为兄弟剧种无私奉献,但“百戏”学去的只是一些表层的演技程式,幸运的是腔词方面的精髓由于太高雅而未被模仿,使昆剧既历史悠远又保存完好,才被评为世界首批中国首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其中,“高雅”是昆剧中非地方戏特征的主要特征,对于这种独特追求历来存在着争议。反对者认为只有将唱词本色化,将旋律本土化,才能使昆剧平易近人。但支持者始终占上风,认为昆剧就是高雅艺术,应该坚持高层次,打造高品位,才是传承昆曲的唯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