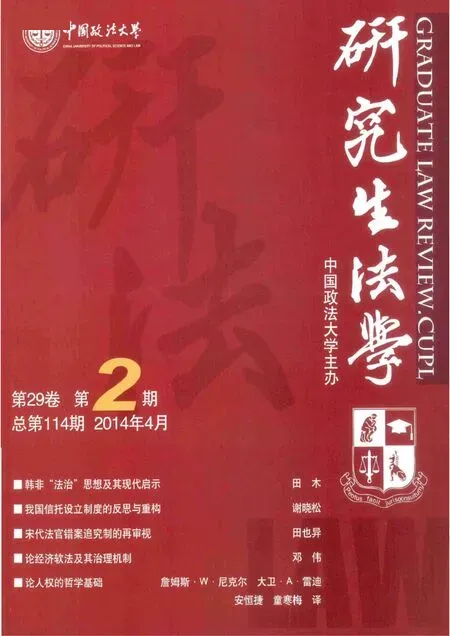我国信托设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的考察
2014-12-21谢晓松
谢晓松
引 言
衡平乃信托之母。发轫于英美衡平法的信托制度以其功能的多样性和结构的灵活性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获得了普遍的运用,它在英美法中之地位如此地重要,以至于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特兰这样称赞道:“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1〕See F.W.Maitland,Equ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10.但由于法系传统迥异,信托制度基于各种不同原因引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之后,与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多有扞格之处,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现象不容于传统民法所有权概念即是典型例证,我国学者致力于此问题之解决的学术贡献至巨。但是,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其不仅冲击了所有权观念,同时也给大陆法系之德国支系特有的法律行为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点不得不引起主要继受德国民法理论的我国学界同样的注意。信托设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大陆法系信托设立制度必须在法律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完成信托设立过程的再造,但我国《信托法》并没有完成这一理论任务。〔2〕笔者认为,这也是我国实践中信托仅应用于商事领域而民事信托几乎空白的原因之一。考诸《信托法》之具体规定,我国信托设立制度存在着立法表达逻辑混乱、理论阐释力不足等诸多弊病,原其根本,乃在于立法者未以法律行为理论检视信托设立过程。本文将以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为基本考察工具,着重探讨信托的涵义、信托行为的性质以及信托公示的效力等三个问题,期能为我国信托设立的制度重塑解开些许理论迷思,并为我国信托法理论的长远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信托”的涵义:法律行为抑或法律关系
(一)信托是一种法律关系
在英美信托法中,尽管学者们认为,考虑到信托功能的多样性和用途的广泛性,给信托下定义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3〕See Gary Watt,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7.但至少对信托特征进行描述的努力可以奏效。著名信托法学者Bogert教授这样描述信托,“信托乃一种信任关系。持有财产权者负有为他人利益管理处分该财产之衡平法上义务”,〔4〕原文为“A trust is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in which one person is the holder of the title to prop erty subject to equitable obligation to keep or use the property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See George T.Bogert,Trusts(West Publishing Co.1987)1.Halbach教授同样指出,“信托乃关于特定财产之一种信任关系。受托人系为他人之利益拥有该特定财产之法律上所有权;而此他人即为受益人,享有该特定财产衡平法上之所有权”,〔5〕原文为“A trust is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specific property,to which the trustee holds the legal title for the benefit of one or more persons,who hold equitable title as beneficiaries”。See Edward C.Halbach,Trust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eg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Inc.1990)1.这表明信托在本质上为信任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几为学者间共识。1987年英国《信托承认法》(Recognition of Trust Act)第2条则明确规定:“信托是指由委托人在生前或者死时创设的一种法律关系。委托人将一定财产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之下,而受托人则须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为此种控制。”〔6〕原文为“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vention(指 Hague Convention,即《海牙信托公约》——笔者注),the term‘trust’refers to the legal relationship created——inter vivos or on death——by a person,the settlor,when ass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a trustee for the benefit of a beneficiary or for a specified purpose”。See Nigel Stockwell& Richard Edwards,Trusts and Equity(Pearson Education Ltd.2005)10.此处进一步将信托(trust)确定为一种法律关系。
作为移植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直接以专条规定了“信托”的定义。2006年新《日本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特定人根据设立信托的契约、遗嘱或者特定的书面方式(包括电子记录)的规定,按照一定目的为实现财产管理或处分以及为实现该目的而实施的必要行为”,《韩国信托法》第1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以信托指定者(以下称信托人)与信托接收者(以下称受托人)间特别信任的关系为基础,信托人将特定财产转移经受托人,或经过其他手续,请受托者为指定者(以下称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管理和处理其财产的法律关系而言”,〔7〕霍玉芬:《信托法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本文涉及韩国《信托法》条文的,均引自本书“附录六”部分,为行文方便,以下不注明出处。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1条规定:“称信托者,谓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或为其他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8〕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本文涉及台湾地区“信托法”条文的,均引自本书“附录一”部分,为行文方便,以下不注明出处。由此,在日本,信托为一种法律行为;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信托则为一种法律关系。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因此我国立法对信托的定义与新《日本信托法》相同,均认信托为一种法律行为,“信托”与“信托行为”似为同义反复。笔者认为,就英美信托法以言,确定信托究为法律行为(Rechtsgesch?fte)还是法律关系(Legal Relationship)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英美法并不存在体系化的法律行为理论,也就不需要以信托行为这一概念完成信托法的理论建构,但对于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尤其是承认法律行为理论的国家(地区),确定信托属于法律行为还是法律关系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体系效应。如认信托为法律行为,则无引入“信托行为”之必要,所谓“信托”不过乃“信托行为”之简称,但无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大陆,其立法和学术界均并用“信托”与“信托行为”两概念,且对二者多有区分。如日本学者能见善久教授就明确指出:信托的设立就是使信托关系成立,而设立信托的行为被称为信托行为。〔9〕参见[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姜雪莲、高庆凯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8页。因此,信托行为既存,“信托”概念本身则只能界定为法律关系,否则便有叠床架屋之嫌。
(二)对区分信托成立与生效的质疑
我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了“信托成立”,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信托生效”,第十一条规定了“信托无效”,由此可见,《信托法》严格区分了信托的成立、生效和无效三种不同情形。与立法相应,我国大陆学者大多区分信托的成立和生效,并分别定其要件。如何宝玉先生认为,“信托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完成了设立信托的行为,真实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信托的生效,是指当事人设立的信托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体现了法律对信托效力的确认。信托的成立表明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信托的生效表明了当事人的意思符合法律的规定”,〔10〕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周小明博士则指出,“信托成立的条件与信托生效的条件的主要区别,在于信托财产是否已经有效地转移于受托人”,〔11〕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信托的生效和信托的效力不可等同视之,“在信托生效后,信托当事人或第三人仍然有可能对信托的效力产生疑问或者存在纠纷,需要对信托的效力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评价,以对信托效力进行确认,如主张信托的无效或者可撤销。这时对信托的评价主要是是否有效力的问题,而不是生效问题”。〔12〕同上注,第166页。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论述看似合理,实则大有值得推敲之处。首先,自英美法观之,其信托法中所谓“不完全设立信托”(Incompletely constituted trust)和“完全设立信托”(Completely constituted trust)之区分,固然意在明确信托成立与信托效力之不同,但由于英美法律制度多由判例建立,其发展也主要为因应实践的需要,较少关注理论的体系性,因此没有以“信托行为”这一中心概念贯穿整个信托法,信托成立与生效之区分当然可以直指“信托”概念本身,因为在这里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信托能否被强制执行,至于其能被强制执行的原因则无须过多的理论阐释。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经由法律行为理论的体系效应,立法引入“信托行为”概念,所谓“成立”与“生效”之区分自然合乎逻辑地指向了“信托行为”,而“信托”本身则被界定为由有效的信托行为所创设的法律关系。根据法理学常识,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13〕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合法性判断与效力评价均体现了法律对法律行为的价值判断,因此信托法律关系一经成立,即表明创设此种法律关系的信托行为合法有效,如再区分所谓信托的“成立”与“生效”,岂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其次,以财产转移至受托人为信托生效要件,则信托财产权利一旦完成移转,信托即行生效,其有效性如何会再次受到挑战?学者上述观点似对“生效”与“有效”之关系存有误读。信托行为的“有效”是指信托行为成立之后齐备了所有的有效要件,诸如主体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信托目的不违反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等,信托行为的“生效”是指有效的信托行为产生其效力,信托行为当事人开始受到信托行为的拘束,而这种拘束正是信托行为中当事人之效果意思的体现,因此,信托行为的“生效”是以其“有效”为前提的,有效的信托行为可能暂时不产生效力,如当事人通过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对信托行为的生效时间进行自治性控制,但已经生效的信托行为绝不可能在效力方面再次受到挑战,否则将颇有本末倒置之嫌。而产生“生效”在前、“有效”在后这样的有违逻辑之判断的原因,仍在于不当地区分了信托成立与生效,此点不得不察。
综上,我国《信托法》错将信托定为法律行为,并导致了信托成立与生效的不当区分,立法表达由此混乱不清,从而使信托法研究陷入理论误区。从《信托法》第十一条〔14〕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公共利益;(二)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四)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五)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具体规定来看,该条列举的“信托无效”的五种具体情形中,第二项与第五项应属于信托行为不成立之事由,〔15〕信托行为本身包括移转财产的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须以被处分财产的确定性为成立要件,故“信托财产不能确定”自然属于信托行为的不成立事由;“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应认为属于《信托法》规定的私益信托行为的特殊成立要件。第一、三、四项则是作为信托行为组成部分的信托合同或者遗嘱的无效事由,〔16〕“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公共利益”和“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分属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两种情形。“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应认为属于《信托法》规定的信托行为的特殊有效要件。由此可见,所谓“信托无效”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空有其名。反观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该法第1条明定信托为一种法律关系,同时以第5条〔17〕该条规定:“信托行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无效:一、其目的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者。二、其目的违反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者。三、以进行诉愿或者诉讼为主要目的者。四、以依法不得受让特定财产权之人为该财产权之受益人者。”、第6条第1项〔18〕该项规定:“信托行为有害于委托人之债权人权利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分别明定信托行为(而非信托)的无效事由以及可撤销事由,其立法用语之严谨,足堪我国《信托法》未来之修订学习、借鉴。
二、信托行为:单一构造还是复合构造
(一)信托行为与信托合同之区分
从制度发达史角度考察,信托制度在英国是先于合同法而产生的,英国信托法从来不属于契约法的范畴。因此,英美信托法中,明示信托的设立只需要满足“三确定”(The Three Certainties)原则即可,也即信托意图的确定性(Certainty of Intention)、信托财产的确定性(Certainty of Subject Matter)以及受益人的确定性(Certainty of Objects),〔19〕See Andrew Iwobi,Essential Trusts(影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4页。并不认为生前信托(Inter Vivos Trust)须通过合同方式才能设立。因此,英美信托法通常使用“信托文件”一词,并无“信托合同”这一概念,当然就更不存在作为法律行为的“信托行为”概念了。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移植信托制度时已经存在完备的合同法制度,且均承认法律行为理论,因此信托合同成为设立生前信托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抽象出了“信托行为”的概念。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信托行为不仅包括信托合同,还包括遗嘱行为以及其他设立信托的法律行为,据此可将其划分为契约信托行为、遗嘱信托行为以及其他信托行为,故信托行为可谓信托合同的上位概念。“一般而言,通过契约设立信托的情形很多,所以把信托行为和信托契约两个概念做同义理解也没有问题”,〔20〕[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姜雪莲、高庆凯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能见善久教授此处意在指出:在通过合同设立信托的场合,信托行为等同于信托契约。但笔者认为,即使在此种场合,信托行为与信托合同仍不可等而视之,〔21〕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探讨契约信托行为的法律构造时,经常混用“信托行为”与“信托契约”。笔者认为,概念的清晰界分是法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如此混用做法将使信托基础理论研究陷入误区。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实际上,此时信托合同不过为信托行为的组成部分,而此种判断之合理性与信托行为特殊的复合式构造密不可分。关于此点,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信托行为是一种复合行为
前已述及,信托行为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适用于信托法领域的产物,其作用在于媒介信托法和大陆法系民法,使信托制度这一“域外来客”投入到大陆法系固有民法的“慈母般的怀抱”中。尽管信托行为在大陆法系信托法中居于如此重要地位,但其在有关国家(地区)信托法中只被浮光掠影地提及,(如《日本信托法》第四条之规定〔22〕该条规定:“受托者须按信托行为的规定,进行信托财产的管理或处理。”参见霍玉芬:《信托法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3、5、6条等之规定,以及我国大陆《信托法》第一条之规定〔23〕也有学者指出,该条规定之“信托行为”含义相当广泛,包括信托由成立至终止过程中的全部行为,与作为创设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的、狭义的信托行为有异。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8页。),均未见其清晰定义。就信托法学界而言,能够达成共识的亦仅限于“信托行为是设立信托的行为”这一极简定义,而其法律构造的确定因为“信托”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变得极具挑战性,对此问题向来也是聚讼不休。关于信托行为的法律构造,日本学界概有二说。一为“复合行为说”,该说认为,信托行为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行为,即使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信托财产管理义务的负担行为或者债权行为,以及使财产权直接发生变动的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一为“单一行为说”,该说认为,信托行为是一种单一的法律行为,但其特殊性体现在同时发生债权和物权两方面效果。〔24〕参见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笔者认为,“单一行为说”强调信托行为作为一种单一法律行为具有能够同时发生债权和物权两方面效果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却着实让人费解,因为根据传统民法物债二分理论,债权行为产生债权,而物权行为则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单纯一种行为不可能同时发生债权和物权效果,否则物权行为理论几无存在之必要。“复合行为说”将相互独立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统一纳入信托行为的范畴之中,与物债二分理论并无冲突,相较而言更为可取。考虑到我国《信托法》中合同和遗嘱为设立信托的两种主要方式,以下区别合同信托与遗嘱信托两种不同场合,分别论证“复合行为说”的合理性。
1.合同信托场合
在通过合同设立信托的情形中,由于信托行为与信托合同相互交织,信托行为的法律构造问题因此与信托合同属否要物契约密切相关。英美信托法中,由于采纳了合同法中的对价(Consideration)理论和衡平法的无偿受让人理论,只有在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或者受益人为信托的设立支付了对价的情况下,信托才能生效。〔25〕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信托财产转移前,信托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与大陆法系债法中的要物契约的概念十分类似,因而信托制度引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之后,学界引发了信托合同究为要物契约抑或诺成契约的争论。就台湾地区“信托法”以言,徐国香教授认为:
依信托定义,信托关系之成立以具有管理或处分行为为必要,而此管理或处分之标的必然以‘物’之存在为必要。易词以言,契约信托行为除须具有委托人与受托人间之意思表示以外,尚须具有财产权之移转或设定以及财产之管理或处分行为,始能成立,故契约信托行为乃要物行为。〔26〕徐国香:《信托法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0页,转引自张淳:“信托合同论——来自信托法适用角度的审视”,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97页。
但也有学者反对将信托合同认定为要物契约。例如,赖源河教授即指出:
按“信托法”第1条的定义性规定,实可知信托契约系由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两者组合而成。亦即其除须有债权行为外,尚须有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且关键在于,信托法中并未有类似“民法”第475条有关消费借贷的规定条文,明定信托须因财产权的移转或交付而生效力,因此在解释上,似难认为信托契约系要物契约。……由此观之,在信托法下的信托契约,其法律构造乃系由二者可区分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所组成。
我国大陆学者张淳教授通过比较考察则认为,无论是《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其中既未规定信托合同自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时成立,也未规定委托人在信托合同签订后负有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因此应当认为这些国家(地区)的信托立法认信托合同为要物契约。而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由此可认为我国《信托法》认信托合同为诺成契约。〔27〕参见张淳:“信托合同论——来自信托法适用角度的审视”,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98页。
笔者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均有可商榷余地。首先,将信托合同认定为要物契约,则在信托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信托财产转移前,信托合同不成立,一方当事人难以强制对方当事人执行合同,势必损害信托合同当事人在签订信托合同时的基本预期,此种损害于受托人从事营业信托时更为巨大,甚至有可能使信托业陷入无序状态;其次,前引赖源河教授的观点,实际上主张信托合同为集相互独立之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为一体的诺成合同,但问题在于,在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将契约二分为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的情况下,信托合同同时包含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之属性殊难想象,且使得上述二元区分彻底崩塌;最后,没有规定“信托合同自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时成立”与“委托人在信托合同签订后负有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并不表明立法否认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故而前引张淳教授据此认定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信托立法认信托合同为要物合同的观点,似有论证不足之嫌。此外,我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是“信托成立”而非“信托合同成立”,据此款规定否认我国《信托法》中信托合同为要物合同,难谓有充足的说服力。笔者主张,信托合同属于不要物的债权契约,理由在于:首先,“复合行为说”下,承认信托合同仅为债权契约,同时与移转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一起构成信托行为,〔28〕由于信托行为由债权行为与处分行为共同构成,因此只有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均成立生效,信托行为方成立生效。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由于信托行为是由《信托法》直接规定的特殊法律行为,认其为由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复合构成的法律行为并不与物债二分理论相矛盾。“复合行为说”在遵循物债二分理论的基础上,恰当地处理了信托行为和信托合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释路径。其次,学者反对将信托合同认定为诺成契约的主要理由无非在于,如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则“信托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受合同约束,交付信托财产。但大陆法系民法的赠与合同,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一般地说,赠与人可随时撤销赠与。民事信托的受益人通常都是无偿取得信托利益的人,在性质上和受赠人相似,对这些信托的成立与生效如果采取和赠与不同的法律规则,在法理上难以贯通”。〔29〕周玉华:《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但是,且不说我国《合同法》已然认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30〕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赠与合同本身与信托合同也存在诸多差异,表现在:赠与合同中,作为无偿受让人的受赠人为合同当事人,而信托合同中,作为无偿受让人的受益人则并非合同当事人,尽管受益人也可根据信托合同向委托人与受托人主张权利,但受托人作为信托合同当事人的地位不可忽视,而受托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无偿受让人,因其不仅承担管理信托财产之义务,在营业信托场合,还享有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委托人收取报酬的法定权利。此外,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而根据《信托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信托合同为法定书面要式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已经为委托人设立他益信托提供了充足的考虑时间和斟酌机会,因此,不宜认为委托人在信托合同签订后、财产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总之,上述差异性决定了信托合同的性质认定不可简单类推适用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则。最后,从其发展史来看,要物契约在罗马法中产生的初衷在于使得未完成法定手续的交易行为同样获得执行力,〔31〕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但现代社会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古罗马当时的高度形式化的交易方式,因此要物契约不过为法制史上的残留物,其于当代契约法之意义已经微乎其微,王泽鉴教授即主张,“财产性的契约均应予以‘诺成化’,保留要物契约此种法制史上的残留物,实无必要。”〔32〕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因此,在我国《信托法》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径直认信托合同为要物契约,以免徒增设立信托之繁琐。
2.遗嘱信托场合
在英美信托法中,遗嘱信托(Testamentary Trust)与生前信托相对,是指委托人通过遗嘱行为设立的信托。在遗嘱信托场合,遗嘱行为与遗嘱信托行为关系密切,且极易混淆,而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遗嘱信托究竟自何时成立?对此,我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之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时,信托成立。据此规定,信托成立的时间应为受托人承诺时。同时,《信托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规定,似乎即使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受托人,信托也依然成立,只不过可依一系列规则重新确定受托人。因此,我国大陆许多学者认为,上述两款规定存在直接冲突,信托成立时间仍有待进一步探讨。〔33〕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笔者认为,《信托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乃是承袭英美遗嘱信托制度的产物,因而要明晰其与《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之间的关系,阐释两者发生冲突的原因,必须对英美遗嘱信托制度加以细致考察。英美信托法奉行“信托不因欠缺受托人而失败”(A trust will never fail for want of a trustee)这一衡平法格言,因此即使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受托人,甚至立遗嘱人并未在遗嘱中指定受托人,立遗嘱人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仍然负有向随后重新指定的受托人交付财产的义务。由此,遗嘱信托的成立并不以受托人的承诺为要件,大陆法系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则亦大体与此相同。但是,仍存争议的是,信托是否于遗嘱行为生效时即行成立?答案看似肯定,实则否定。实际上,英美信托法之所以有“信托不因欠缺受托人而失败”这一原则,与其建立的法院指定受托人制度不无关系,因为即使暂时欠缺受托人,最终都会由法院强制指定一人担任信托的受托人,不可能出现如我国《信托法》下受托人无法重新产生的情形,信托最终还是有成立的可能性,而上述衡平法格言反映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但由于其用语的修辞色彩远甚于其严谨性,大陆法系信托法学者才对其准确含义产生了误读。信托并非自遗嘱行为生效时成立,从英美信托法学者对遗嘱执行人(Executor)与受托人之区别的强调亦可得印证。如Penner教授即指出,尽管实践中,立遗嘱人(Testator)通常都会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为受托人,但在受托人由法院最终确定之前,遗嘱执行人的地位不可等同于受托人。受益人确定之前,潜在的受益人(Prospective Beneficiary)享有要求遗嘱执行人适当管理财产的权利,此种权利与信托受益人对受托人的权利类似(Like)。〔34〕See J.E.Penner,The Law of Trusts(LexisNexis UK 2004)52 -53.而此处之所以用“类似”而非“相同”(Same),是因为遗嘱执行人尚未被法院指定为受托人,尽管实践中法院通常都会指定遗嘱执行人为受托人。
由此可见,遗嘱信托场合,信托成立的时间并不是遗嘱生效之时。笔者认为,信托是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核心应是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控制信托财产,因此信托财产权利移转至受托人应为信托成立的时间点。此时,遗嘱信托行为由遗嘱行为和财产移转行为复合构成,其中遗嘱行为为负担行为,财产转移行为为为处分行为,而这正与“复合行为说”暗合。以财产权利转移为遗嘱信托的成立要件,须特别说明者有二:其一,遗嘱生效之后,财产权利移转之前,受托人可以根据生效遗嘱要求遗嘱执行人或者立遗嘱人的继承人移转信托财产权利,在受托人暂时欠缺而重新指定受托人之前,遗嘱中载明的受益人可要求遗嘱执行人承担适当管理财产的义务。其二,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遗嘱信托类似于遗赠,因此遗嘱生效时,信托财产已然发生转移,此时要求实际交付信托财产信托始为成立是否必要?实际上,本条规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物权瞬间变动的拟制,尽速确定物权的归属,避免出现财产无主状态,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例证之一便是《继承法》关于放弃继承的时间规定。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更是明确指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由此可见,我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实际上以遗产的处理为遗产所有权变动的时间点,因为如按照上述《物权法》之规定,继承权殆无放弃之可能。而移转信托财产权利的目的在于使信托财产处于受托人的实际控制当中,因此仍有必要以信托财产的实际交付为遗嘱信托行为成立生效之条件(即遗嘱信托的成立要件),此处当亦无《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适用。〔3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并未见类似于《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此遗赠时物权变动以遗产的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遗嘱信托时则以信托财产(权利)的实际移转为信托行为成立生效之条件(也即信托的成立要件)。参见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三、信托公示:成立要件还是对抗要件
(一)信托公示之不同立法例
信托公示,“系指于一般财产权变动等的一般公示外,再规定一套足以表明其为信托的特别公示而言”,〔36〕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是将信托法律关系展现于外部的过程,不同于信托财产的权利移转公示。从比较法角度考察,信托公示之立法例大体有三:
其一,无需公示。英美信托法中,“信托是隐蔽的”为一项基本原则,信托法注重对信托财产保密,而保护交易安全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信托设立后无需进行信托公示。采此立法例的除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外,还包括移植英美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瑞士。
其二,以公示为信托对抗要件。采此立法例的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如《日本信托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如不登记或注册,其信托不得对抗第三者”〔37〕此为1979年修订的日本旧《信托法》条文,由于该条在2006年修订时并无变化,因此此处径直引用旧法条文。参见霍玉芬:《信托法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韩国信托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关于需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其信托可因登记或注册而与第三人对抗”,台湾地区“信托法”第4条第1项规定:“以应登记或者注册之财产权为信托者,非经信托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其三,以公示为信托生效要件。〔38〕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由于信托是一种法律关系,因而此处信托生效要件应为信托成立要件。但为论述方便,此处仍采通说。从目前来看,采此立法例的国家只有我国。我国《信托法》第十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二)对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的检讨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十条之规定,如信托财产为须经登记之财产,则信托登记是信托的生效要件。周小明博士则将信托登记作为信托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39〕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54页。笔者认为,无论将信托登记作为信托的生效要件还是信托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做法均难谓允当。自大陆法系信托法以言,相较于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信义关系,信托法更注重通过维护第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因此我国信托立法建立信托公示制度实有必要。〔40〕实际上,美国法中也存在信托公示制度。如美国《统一遗嘱法典(Uniform Probate Code)》第7-101条规定受托人有在法院进行信托登记的义务;美国《统一信托法典(Uniform Trust Code)》第810c条同样规定,受托人具有标注(earmark)信托财产的义务。参见王涌:“论信托法和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0页。但是,我国《信托法》“对设立信托采取不登记不生效制度,似失之过严,也是对委托人设立信托意图的最大打击。以如此强烈的公权干预,挫败私人设立信托的自由意志,是否有必要,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效果看,都值得研究”。〔41〕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笔者认为,公示生效主义不仅否定了信托行为的外部效力,同时也否定了信托行为在信托当事人间的内部效力,不仅于交易安全之保护无益,更对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相较而言,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公示对抗主义,兼顾了交易安全和信托当事人之利益,更具有可采性。此处所谓对抗,“系指如信托财产的权利关系发生纠纷时,如信托具备公示要件,则信托关系人对于第三人得主张信托关系存在;相反地,如信托不具备公示要件,信托关系人就不得对第三人主张信托关系存在。”〔42〕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这里暗藏的逻辑是,作为一种法律行为,信托行为一经生效便产生信托法律关系,该信托法律关系约束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托人,信托关系人得依据信托法律关系相互主张权利或者要求他方承担义务,但信托尚未登记前,第三人无从知晓信托法律关系的存在,信托关系人直接援引信托法律关系使第三人受到约束有违保护交易安全之宗旨而难具正当性,由此而生信托登记制度。但无论信托登记与否,信托法律关系已然成立,惟能否使第三人同受约束不同而已,此理甚明。因此,我国信托立法应抛弃严格的信托公示生效主义,改采较为宽松的信托公示对抗主义。
结 论
早在一百多年前,霍菲尔德在对英国衡平法中的信托制度进行考察时就发现,用于讨论信托法的语言是具有误导性的。〔43〕See Wesley N.Hohfeld,“The Relations Between Equity and Law”,9Michigan L.Rev.537(1913).产生这种误导性的原因或许在于,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信托的功能是如此多样,以至于当人们谈起它时,总是会用充满修辞的语言来抒发内心的赞叹,却忽视了这种略带文学性的阐述很可能使得诸多基本概念丧失其应有的准确性。在大陆法系国家引入信托制度之后,这些带有误导性的语言加大了大陆法系学者研究信托法的难度,也使得相关基本概念的误读难以避免。
由上文分析可知,如以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考察我国现行信托设立制度(如图一所示),会发现该项制度尚存有三处主要缺陷:其一,误信托为法律行为,造成了信托成立与生效的不必要区分;其二,信托行为的法律构造不明,导致信托成立时间的确定出现偏差;其三,将信托公示不当地定为信托成立要件,不利于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利益。针对上述缺陷,参考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信托立法中的相关规定,笔者提出若干修法建议,以达重塑我国信托设立制度之目的(重塑后的信托设立过程如图二所示)。
首先,修改《信托法》第二条,明定信托为一种法律关系,纠正“信托是法律行为”这一误读。
其次,修改《信托法》第十一条,由对“信托无效”的规定改为对“信托行为无效”的规定,同时删除不属于信托行为无效事由的项目;〔44〕如“信托财产不能确定”和“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当为信托行为成立要件,应当予以删除。当然,也可以考虑以专条单独规定信托行为的成立要件。修改《信托法》第十二条,由对“撤销信托”的规定改为对“撤销信托行为”的规定;修改《信托法》第四十四条,将受益人享有信托受益权的时间由“信托生效”之时改为“信托成立之时”。
复次,修改《信托法》第八条,明定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实际转移至受托人时信托成立,同时以专条规定信托合同,遗嘱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法律行为的效力,条文表述为:“信托合同,遗嘱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法律行为生效后,受托人和受益人可要求委托人向受托人实际移转财产权利,委托人也可要求受托人接受财产权利。”此外,可考虑在《信托法》第十三条中作补充规定,建立法院最终确定受托人制度,〔45〕这里可参照指定监护人的程序设计,即被委托人、受益人或其监护人指定担任受托人的人对指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可比照民事诉讼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并根据情况作出维持或者撤销指定的判决,撤销原指定的,可以同时指定新的受托人。逾期起诉的,按变更受托人处理,法院将按民事诉讼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以避免受托人不确定而导致信托迟迟无法成立的情况发生。
最后,修改《信托法》第十条,对于不补办信托登记手续的后果,由“信托不产生效力”改为“信托不得对抗第三人”。

图一〔46〕 鉴于我国学界对《信托法》中遗嘱信托成立时间尚有争议,为方便计,此处径以合同信托为例。 我国现行《信托法》下的信托设立过程

图二 重构后的信托设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