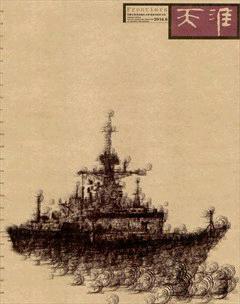集市买书记
2014-12-17唐棣
唐棣
一
集市就是乡间的盛会。我们马州人赴会时所用动词有两种。一种适用于物品交易者,他们不说去哪里,而说“上集”;另一种用于无物可买卖,仍出没在集市上的闲逛者身上。他们用行为反对“上集”的理由很直接:上集下市——下市就啥也买不到了。动词“赶”,特别适于呈现他们从小路向旷野进发,其中近乎小跑的姿态。在这部分人的观念里,作为一件和新鲜蔬菜抢时间,跟准备与你抢时间的人抢摊点的事,赶集又代表着一个你追我赶的进程。
马州村辐射出的范围有限。我的记忆由阴历初一初六的胥各庄集、初二初八的将坨集、周末两天的果园集拼凑而成。
在我有记忆之前,集市的背景是一片灰突突的旷野。当周围农民把沟沟坎坎填满,喧闹也随之而来。别以为旷野的面貌“倏”地一下就变温柔了。后来,我发现它始终没被打败过,比如野风埋伏在山丘后随时伺机行动。有一次我刚走到路口,就看见把阻拦它盘旋的摊位掀飞。然后,那个摊主一边大声骂娘,一边追着那个大遮阳伞奔跑出很远很远。
乡村集市撒得起这点野。而城市的大卖场太拘谨,不生动。形式上接近一点的,散布城中某条小巷里的简朴小摊,又太不成器。
二
卖书人是乡村集市上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在集市上贩卖与吃喝拉撒无关的东西。弥漫着生活味的场地反衬出他们孤单的身影。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人,不仅把集市当作一个交易场,还把很多交朋友的机会存放在这里。
在我与这些卖书人的交往中,我自然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我和赶集的农人们一同出现在集市的入口,却在人群中分道扬镳,他们去买蔬菜农具,我去找书看。这些卖书人戏称自己“书贩子”。每次见到我,就远远地跟我摆手。他们无数次抱怨过书卖得不好。可他们谁也解释不清,天底下那么多东西可贩,为什么偏偏贩这个?看来这也是冥冥中的选择。
他们在乡村集市上的地位也是最低的。最高的地位还要看时节和人们所需的急迫程度,如大白菜下来时,卖白菜的人就是最受拥护的。
我认识的一个人甚至负气做过学隔壁卖大白菜的人立木牌的事情。木牌上写:“大甩卖,十元四本,薄厚一样。”可想而知的结果也没有改变他的作风。下个集市,我远远看到同一块木牌上面的字变了:“不贱卖,最少给十块,可以不买。”两次的字组合起来,就像一副可爱兮兮的对联。
集市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卖书摊。南面是卖辅导书的老冬。西面是卖画册和字帖的豁子嘴。北面是卖旧书的尤头,他的书尤其贵,他懂书。所以,他的书摊在周围卖衣服和瓜果的人群中只能门可罗雀了。尤头脸上永远写有一种固执,从不向买主低头。我记得曾看到过一个书生穿着的人挤过两旁摊位淤出来的人群,走到他的摊前。然后,没多久又空手离开了。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没让我说话,就忙不迭拿起一本书,说:“这本书十元绝对不多,这个品相,这个中华书局版本,再加上沈从周的序……”尤头跟我描述那本旧书的价值时,我称之为“文人般的固执”又从苍老的脸上浮现了。
三
我逢集必到的摊子在东面,那是进入集市的必经之路,我听很多跟他聊天的人叫他老黄,我也就跟着叫了起来。
老黄卖的和别人不一样。他摊位的左边是卖白菜的摊位,右边是卖调味料的摊位。它夹在两边络绎不绝的顾客中间。其次是书也不一样。他说是他在北京开书店的儿子关门了,拉回家留着给他卖个酒钱。据说,老黄有四千本书,这四千本书里有过半的文学书。他按照薄厚和重量卖书。《博尔赫斯全集》《荷马史诗》等几本厚书一直被冷落在书摊的角落。他不止一次殷切盼着我把它们买走。它们太重了,来回搬运挺累的。我在旁边不失时机地还会填上几句贬这两本书的话——其实,我在等他处理给我。买书人与卖书人的关系除了精神性的沟通,也具有一般买卖的心理。我认为这种关系有时也反映着我与乡村记忆的关系。有时,钱的问题解决了,也还有一种较量。这次,我赢了,十元就把这两套书扳回了家。并且给他钱时,我还故意摆出一副恬不知耻的犹豫。
老黄到底不是个书贩子。卖书时,常常以奇怪的够不够玩一场牌为标准。
“多给两块吧。”他说,“都不够一场牌。”
老黄对赌博的了解比对书多。不过,后来不见他来集市了。集市上南面卖辅导书的老冬就说他:“瞎卖,破坏规矩。不来正好。”西面卖画册和字帖的豁子嘴没说这个,倒说他好像哪天下了集赌博输了,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死了。总之,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老黄。老黄不来摆摊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遇上了他希望中的大买家,一气把剩下的三千五百六十五本书都买走了。
在胥各庄集未迁到远处前,我从东门进入集时,必朝那个角落看一眼。那里已被一个鱼贩占据,铺书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花花绿绿的鱼肠、鱼鳞、鱼血。左边还是卖白菜的摊位,右边还是那个调味料的摊位。
这不足两平方米的喧嚣却已远远超出了两旁,大有震撼全胥各庄集的声势。望着那些提着剖好的鱼的人,我耳边是卖鱼人从铁水槽里抓出鱼往地上砸的声音,嘭——嘭——
四
将坨集搬到了我们村边的一块野地上。将坨集从粱屯街道里的小摊慢慢发展起来,在我小时候,已相当繁华。我人生中首次与人群接触就发生在这个集市上。母亲用自行车大摇大摆地把我带入谈价还价的热闹里。那是一个冬天,我被一阵热浪团团包围。胆小的自己被吓哭了,可哭声对外界毫无影响。
而现在昔日的街巷已被一条始终处于建设中的公路开膛破肚,长期搭着铁板,拉着铁丝。此刻的安静是不对的,我还是第一次视安静为莫大的耻辱。
现在,卖辅导书的老冬和我还有联系。关于尤头到底为何不来卖旧书,老冬给出的答案是:“那脾气!他被旁边卖猪血的气坏了。”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卖猪血的人拿他的书取笑说,一块猪血抵他一本书。尤头就生气了。尤头的脾气的确很大。老冬的生意只能和尤头的生意比。有几次,遇上卖画册和字帖的豁子嘴,他人也不在摊位上静候买主。三轮车里的画册只出几本,做做样子。如不认识这三轮车,恐怕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书摊。我倚在那里等很久,他才从一片卖白萝卜的人群里钻出来。
五
果园集离我们村最远。我去赶果园集主要是为了看它的花鸟市场。另外两个集市没有这么多动物贩卖。我认识的几个卖书人很少来这里。他们不来的原因与不去将坨集的理由不一样。这里靠近城里,有很多从城里来的卖书人,价格种类上都是老冬、豁子嘴、尤头难以匹敌的。于是,他们无视了这个战场的硝烟。据尤头说,果园集历史最久,大量退休老干部在书摊边聊天。遇上聊得好的买书人会中间拦下买家,说:“我家有这本,还买什么买,我送给你!”老头美滋滋地走后,卖书人一脸尴尬地杵在几个老头中间无所适从。
这些话从老冬、豁子嘴、尤头的嘴里说出来,像为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敌情一般。
遗憾的是我和果园集上的卖书人后来也没熟悉上来。他们往往都是一些业余的卖书人,退休了没事干,也不在乎卖不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过,这种陌生感倒让我抓住诸多时机。可以说,我在果园集上买的书不比在将坨和胥各庄集少。我记得有套茨威格正是连续观察三个集后跟一个喜欢张爱玲的老头买的。每周,我不买书,就蹲在边上,趁没顾客时跟他聊张爱玲。聊过一次,再见面就深入一点。由张爱玲的苍凉人生,聊及胡兰成。第三次,我看他生意不好,就蹲在旁边翻一本胡兰成。他主动把话头搭到老上海的爱情上。这才知道老头地震时被一个上海来的医生救活了,两人还产生了感情。不过后来,女孩回了上海。女孩临走给他留下了一本张爱玲小说。当他让我把那套张爱玲拿去看时,我反而有点愧疚。他甚至告诉我,这套书是他去外地出差十几年,一本一本凑的。当时就一本《倾城之恋》。他指了指那本书。我摇了摇头。他倒不依不饶,还说:“这个茨威格你也一块拿去吧。放在我这占地方。”
六
我所认识的几个卖书人年纪都不小。有时,我到集市先去跟他们打招呼。正午,掐时间,返回书摊。我想帮他们收收书。有几次,天气不好,等我赶回来,他们已离开了。而这时,我知道下个集市我们还能打招呼,并没有后来的伤感。
后来,胥各庄集的那块土地建起了楼房,将坨集那块土地建起了变电站……在被驱逐的路上,它们像丧家之犬。城市是它们的主人,一声呵斥,它们就夹起尾巴逃到另一处。再一声呵斥,它们又夹起尾巴换一处,直至主人命令它们死去为止。我可以说,这也是剿杀下的一生。
灾难殃及到了乡村。最近,果园集的小贩们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纸,上面写的是“集市取消”的消息。我问几个卖书人下集还来卖书么?他们说,既然这样,做人也得有个骨气吧?还有那些卖菜的,卖鱼肉的,每个人的表情在那刻都是相近的。
记忆一点点瓦解,那些夹杂在小贩中的朋友,或者说乡村记忆无一幸免。现实意义上的消失也令我申诉无门了。最后的风险是逼迫我成为诬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