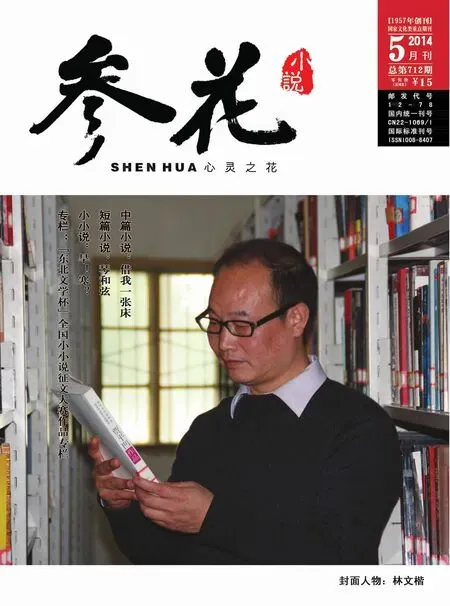论文艺的空灵美与充实美
2014-12-12刘德钊
◎刘德钊
论文艺的空灵美与充实美
◎刘德钊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以及古人、西方、东方对艺术中美的追求,以艺术的空灵美与充实美为角度,探讨了艺术中空灵美与充实美之间的关系。空灵美的高境界与充实美的实诚和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文艺作品的整体。
文学艺术 两元 空灵美 境界 充实美
一、艺术精神的两元
艺术是一种技术,古代艺术家就是技术家(手工艺的大匠)。现代及将来的艺术应该特重技术。然而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人生(象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艺里。它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色彩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而这一切都是圆满的、自足的、必然的,因而是美的。
文艺站在道德和哲学的旁边能并立而无愧。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植于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它要有土腥气,要有时代的血肉,纵然它的头须伸进精神的光明高超的天空,指示生命的真谛。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然而它又需超凡入圣、独立于万象之表,凭它独创的形相,范畴一个世界,冰清玉洁,脱尽尘埃,这又是何等的空灵。
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而对空灵美和充实美,人们有一种近似本能的需求。
二、文艺的空灵之美
空灵美感的美成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廊,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杆,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即距离产生美。古人最懂得这种距离隔开之美,李商隐词:“画檐簪柳碧如城,一帘风雨里,过清明”。董其昌曾说:“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他们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
然而这还得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开了空艺术的心灵当如“空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谈如菊”,“神出古异,谈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精神淡泊,是艺术空灵美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的名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更能说明这一点。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荟说“酒正引人著胜地”,这使人人自远的酒正能引人著胜地,这胜地是什么呢?正是空灵的相反之面——充实美。充实之美正是我们要谈的下一个问题。
三、文艺的充实之美
在欧洲歌德的生活经历着人生多种境地,充实无比。在中国古代,杜甫的诗歌最为深厚有力,也是由于生活经验的充实和情感的极其丰富。
司空图形容着壮硕的艺术精神说:“无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溺满,万象在旁。”“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生气远山,不著死灰。秒造自然,伊谁与裁”。“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吞吐大荒,由道反气”。“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艺术家精力充实,气象万千,充实美油然而生,艺术创造追随真宰的创造。
中国山水画趋向简淡,然而简淡中包具无穷境界,倪云林画一树一石,千岩万壑不能过之。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惟其品著天际冥鸿,故出笔便如哀弦急管,声情并集,非大地观乐切中可得而拟议者也。
哀弦急管,声情并茂,这是何等繁复热闹的音乐,不料能在元人一树一石,一山一水中体会出来,元人造诣之高和南田体会之深,都显出中国艺术境界的最高成就!然而元人幽谈的境界背后仍潜隐着一种宇宙豪情,南田说:“群必求同,求同必相叫,相叫必与荒天古木,此画中所意也”。相叫火于荒天古木,这是沉痛超迈深邃热烈的人生境界。
叶燮在《原诗》里说:“可言之有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于事部灿然于前者也”。
为就是艺术心灵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后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它的最深意义灿然呈现于前。
总之,如上所叙,空灵美于充实美实在是一对孪生兄弟,无空灵则无充实可言,无充实则空灵无从可谈,它们是辩论统一的关系,互相对比、映衬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特别在中国的文艺,空灵美于充实美两方都曾尽力达到极高的成就。所以中国诗人尤爱把森林万象映射在太阳的背景上,境界丰实空灵,像一座灿烂的星天。
[1]《艺术美学》田川流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07. 01
[2]《美的历程》李泽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07.01
[3]《文艺美学》胡经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6. 01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