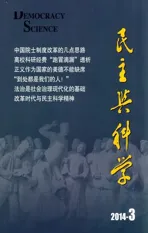法治变革的理想主义批判——读《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
2014-12-12丁国强
丁国强
左卫民《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观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考察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思考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司法改革、法律移植等问题,发出了久违的批判之声。刑事司法交织着各种利益纠葛、价值冲突和意见交错,触摸着法治的最敏感神经。刑事立法如何用中国话语、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实现符合中国国情民意的良法之治,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面对公民个体权利主张的迫切,刑事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社会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后面不仅有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冲动,而且也有企图影响个案的动机,这就使得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充满了利益博弈和话语权的较量。一些当事人、律师甚至采取上访、网络曝光、媒体发声等方式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从一些热点个案的处理来看,这些参与刑事诉讼的非正式方式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司法机关的犹豫迟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响应。出于对政治和社会效果的考虑,司法机关格外在乎舆情反应,并将之上升为民意来对待。左卫民认为,司法机关的这种响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诱发司法机构既定“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一书,着力考察影响法治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从而发现法治话语的复杂性和日常性,挖掘法治的思想渊源和价值取向。法治不仅仅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法治,而且是广大民众的法治。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法治决定了法治的历史和走向。因此,法治是由一个民族的生活所创造的。撇开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在法学理论上搞逻辑游戏,是难以触及法治本质的。法律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社会的理性和合意,这是社会运行的根本。
左卫民认为,以往由绝对的单一主体主导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格局已不复存在,立法、司法、诉讼参加人、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媒体都在中观、微观层面推动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进,并最终影响宏观制度的变革。律师对于刑事诉讼的制度形态的影响不可低估,他们的深度参与不仅使诉讼过程富有对抗意味,而且还强化了司法的互动性。司法机关需要对律师的行为予以回应,这一过程既是法律知识的对话过程,也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律师不仅要为当事人利益奔走,同时也要竭力维护自身的执业利益。公众和媒体的“意见洪流”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互联网为更多主体以设置公共议题的方式参与刑事诉讼实践提供了资源与管道。热点案件因其后面潜藏着社会矛盾和阶层利益,而成为社会各方面表达不同意见的切入点。媒体不仅可以通过案件报道吸引公众眼球,也满足其影响高层决策、推动制度变革的成就感。但是由于中国的媒体人过于年轻和浮躁,常常简单借用西方司法制度来批判中国的司法现实,对司法“黑暗”进行妖魔化想象,对诸如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等个案过度阐释,将司法机关推到有口莫辩的困境。一些并非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动辄进行制度批判,并不断抛出制度突变的构想,他们所勾勒的理想图景大多缺乏实证分析研究和本土资源支持,因而只能借助司法个案的炒作获得话语权。
不论如何,刑事诉讼制度已无法局限于法律运作,必须从政治、社会等层面来审视,以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刑事诉讼成为公众监督公权力的重要阵地,公众以极其敏感的神经质疑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方式滥用权力,对司法公开提出更高甚至有些苛刻的要求。这就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从吸纳民意中获取合法性支持。但是,社会心理往往与司法逻辑不合,司法对民意的尊重最终还是要纳入法律信仰、法律权威之下,而不能一味迁就公众情绪,要避免司法争议泛社会化,更不能把不稳定的公共舆论作为个别化的执法标尺。随着法治文化的发展,舆论对司法的评价也趋于理性、宽和。从整体而言,信任法治进步、理解司法程序、认同法律价值的公众意见比那些极端的个人表达更有生命力。司法机关应对网络围观的能力也不断提升。针对个案的具有特定诉求的舆论流、意见流,如果没有充分的法理支持,虽然传播得快,消散得也快,但是,如果不能用法理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股销蚀法治精神的潜在力量。一些网络微博大V、网络水军通过大量转发等手段,在特定的话语场内激发情绪和非理性,从而将司法个案操作成舆论热点,实质上已经成为干预司法的一种方式,舆论强势的一方如果达到目的,就势必会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造成威胁。不少网络意见不仅缺乏理解和宽容,而且有意挑战规则、抵抗法律秩序,以至于刑事个案在审理和传播过程中,夹杂了大量不符合法治精神的信息。刑事诉讼充满了评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甚至连法官本身也处于矛盾之中。法国最高法院院长文森特·拉曼达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二重性表现得十分突出。“有时法官被认为太宽容——他对罪犯太宽容却对受害者给予有限的同情;有时法官又被认为过于严苛不近人情——他把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看作无可救药的坏人,坚决站在公诉人一边。如果说法官的形象明显具有双重性,那是因为从远古时代起人类社会的环境就具有双重性:美德和罪恶并存,善恶交织,坏人也不能脱离好人而存在,就像夜晚和白天相辅相成,呼气和吸气轮流交替”。
黑格尔将对刑事犯罪的看法当作是一种文化。他说:“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经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犯罪或刑罚并没有变化,而是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当今社会,网络舆论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刑事诉讼文化。公众对刑事诉讼的认识,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文化的一部分。一般意义的司法公开已不能适应高强度的舆论关注。建立公开、理性、常态的意见交流平台成为迫切需要。左卫民认为,当前中国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立法精英、知识精英与公众之间没有形成有效有序的沟通格局,公众情感、公共舆论没有得到良性激发等问题。公众情感和精英认知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巨大差异会产生撕裂共识的负面效应。民粹主义容易将刑事诉讼实践引导到激进法治的道路上,在非理性的轨道上喊法治口号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对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达马斯卡命题进行了反思。美国比较刑事诉讼法学者达马斯卡认为,移植他国的程序制度,其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植根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我国刑事诉讼法30余年的发展变迁过程,既是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融合的过程,也是观念冲突、利益博弈的过程。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不仅关系到程序的正当性,而且也关系到司法资源的分配、司法权力的制衡、话语权力的平衡等。这些问题大大超出了刑事诉讼法学范畴,触及宪法层面乃至政治层面的敏感地带,呼应着社会转型的深刻变化。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注定不能在法律逻辑内部自我循环,而是必须呼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迁。当然,社会的复杂性与案件的复杂性是两回事,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对司法审判的理解和评价的复杂性。法国著名律师在《错案》一书中写道:“公众的舆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人也没有权力责问您,而您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办事。”这一论断在中国语境中显得太过迂阔。舆论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司法的态度甚至结论。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热点案件的传播不仅作用于司法审判,而且对社会管理甚至执政理念产生影响。一起案件的审判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信息量,如何有效剔除非理性的、人为策划的负面信息,是一个需要细细思量的问题。无论如何强调公开,司法审判不都应当演化为一场媒体审判。司法与舆论达成“合意”是危险的。不同人群对于司法审判的心理预期、价值评判大相径庭。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考》一书,对1996年、2012年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体现出的因受域外法治影响,“移植内容中面向未来的理想成分稍多一些”进行了反思。左卫民指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部分移植,存在未经深思熟虑就直接照搬的情况,其借鉴的理想成分略多一些,效果也不好判断。这一判断与那些“里程碑意义”的欢呼声相比是清醒的。碎片化移植造成了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虚假繁荣。立法吸收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排除合理怀疑”等只言片语,但是却并没有引入与之配套的机制。从苏联模式到英美模式,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始终处在主体性缺失的状态之中,对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缺乏自主性回应。法律移植的生命力无法靠“死磕派”的利益诉求坚持。法律实施是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过程,而并非是某一利益群体的自我陶醉。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是高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的问题并没有迎刃而解,司法理念、办案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刑事诉讼立法公开性的增强使得刑事诉讼法修改成为公共意见表达的平台,体现了国家与公众的互动。社会力量和社会意见的崛起,将刑事诉讼法修改由法律问题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左卫民指出,这种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存在着参与不平衡、理性沟通不够、专业理性欠缺等问题,致使立法过程难免受到工具主义、民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影响,交织着现实与理想、实务与部门、公众与法学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妥协,从而离“正义分配”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这里面既有立法技术不成熟的因素,也有急于求成、操之过急的因素。要防止应然与实然的脱节,就必须实现从价值取向到技术理性的全面完善,让法律制度的变革在厚实积累上进行,以免坠入法治形式化的陷阱,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不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