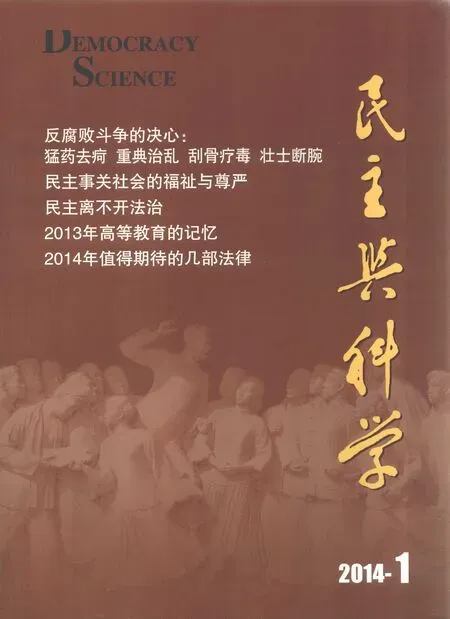为什么地方人大在立法上少有作为
2014-12-12秦前红
■秦前红
本年度召开的湖北省人大全体会议,有一项颇引人注目的议程:将在大会上审议《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本项议程之设立除了凸显湖北省对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重视外,更耐人寻味的是省级人大全体会议行使立法权近年来几乎少见。但愿湖北省人大此举能激活有关地方人大运作的关注。
一定层级的地方人大获得立法权并非人大制度降生即有,其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产生发展相始终。1954年,宪法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时,有人提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应该和全国人大一样设立常委会。这个意见未获采纳。因为当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没有立法权,治国思路上官方对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动员方式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社会治理所需的规范主要仰赖于政策供给。地方人大基本上处于无事可做的赋闲状态。越是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地区越小,越容易召开会议,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职能,由人民委员会(即政府)行使。所以在人民委员会以外另设常务机关实属多余。
人民委员会既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后的常设执行机关,又是政府,其所带来的问题便是,当政府舍弃建国之初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意识形态引导下的高度道德自觉进入国家管理的日常之治,既有权力不断膨胀的危险,更有因管理与被管理角色分配而导致的与公民利益的矛盾,此时若无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经常监督的机关,而听任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无疑既不能树立政府本身的公信力,又会影响人大自身权威的型塑。于是,1957年上半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的彭真同志提出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惜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个动议也沦为孤独呐喊。
到了1965年,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动议再起,提出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方面对此也取得共识。遗憾的是,人大与中国民主、法治一样是命运多舛,此项建议再遭夭折。从1966年8月到1974年12月,长达八年之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竟然没有开过会,地方人大由革命委员会代替。历经十年“文革”的劫难之后,痛定思痛,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慎重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于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承担起了繁重的立法任务。彭真亲担主任之职,并提出当前的工作就是加紧制定7部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在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时,“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呼声十分强烈。1979年5月17日,彭真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关于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有三个方案:一是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二是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三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邓小平在审阅报告时一锤定音:“我赞成第三个方案。”“县级以上地方设立常委会,是一个重大改革。” 这也表征了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的特殊况味,即领导人的见识与魄力往往决定了制度发展的路向。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7部法律。《决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当年,全国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人代会,选举产生了本级人大常委会。以后,又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逐步授权经济特权、省会所在的市和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法规制定权。
30年的实践证明,地方人大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权限的划分方面一直是纠结不清。根据有关统计,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90%以上的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近多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挤占地方人大空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原因在于:
第一,地方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划分不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由宪法、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组成。宪法、立法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修改基本法律,并制定普通法律。尽管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也有立法权限的交叉重合问题,但从法律文本上与立法原则上来看两者还是各有相对清晰的立法空间。立法法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未作任何区隔。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立法法之所以未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进行划分揆诸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中国采行一级多元的立法体制,乃为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展的需要,但法治统一为其目标所在。立法层次划分过多会妨碍这一目标的实现。2.同时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初衷便是为了补强地方人大运转不便、权能发挥实效不足的弊端。“实人大常委会、虚地方人大”的制度安排思路导致立法权限划分似无必要。3.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可以改变撤销同级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决定,这一规定事实上保证了地方人大在相同调整事项上的立法高于同级人大常委会,从而逻辑上使得地方人大可以规制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空间。
第二,地方人大的规模难题。中国目前具有地方立法制定权的省、市人大,其代表规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立法作为一种追求科学的事业,地方立法则更要因应实践性、及时性、地方性之需。如此繁重的使命交由一个巨量代表规模的机构未免有不堪承受之重。多人云集的地方代议机构要么陷入众声喧哗议而不决的困难境地,要么是沦入集体失语指望他人的公地悲剧。仅有立法之名而无立法之实的草率立法徒然耗费立法成本,且有损立法之公定力。
第三,现代立法为保证立法的品质,通常会设定精致的立法过程,在不同的立法过程控制之下最终达致立法宗旨的实现。一般而言,立法均要经过三读(三审)过程。部分社会高度关切之立法则还会经过更多立法程序。地方人大一般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如此会期制度下,如果让地方人大进行经常性立法活动,则必然使得立法严重滞后于实践之需。
第四,现代立法事务日趋专门化和专业化,为了弥补立法机构专业知识的缺陷,上世纪域外很多立法机构纷纷为其成员配置立法助理。依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之机理,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以其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先进性为首,以具有参政议政能力为辅。以某省人大代表组成为例,党政干部所占比例约5成左右。在如此代表结构之下,代表要么处于立法能力缺失状态,要么利益诉求的表达偏弱。加以地方性法规实行不力、权威性极度缺乏的状况,地方人大立法必定陷入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状态,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素其实完全不敷立法实际之需。通常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的会期大约在6至8天左右,在如此紧凑时间内,人大代表要完成听取并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人事任免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内容,立法事项的审议充其量不过半天左右的时间。主观和客观要素都决定了立法不可能在大会期间得到审慎讨论。
综上而论,地方人大行使立法权仅为满足民主正当性之需,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而言地方人大立法则有力不从心之感。未来地方人大制度的改革当以“人大为虚、常委会为实”作为目标。更为大胆的改革其实可在改变代表方式、缩小代表规模之下,实现代表大会与常委会的合一。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各自为政的现状其实对人大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实效性构成颇为尖锐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