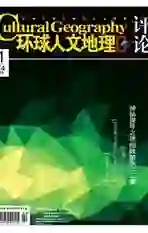浅谈古斯塔夫?马勒交响乐的研究理路
2014-12-08毛羽
毛羽
摘要:古斯塔夫·马勒的交响乐是“世界观音乐”的代表作。一百年来,对其的研究从未停滞,而是呈现出多种模式和视角。本文尝试从马勒交响乐的整体性特征入手,以由“符号意义”向“观念意义”的转化作为脉络,对马勒交响乐的研究理路作一探索。
关键词: 古斯塔夫·马勒;交响乐;世界观音乐;符号;互文性;“取独”;观念意义
引言
古斯塔夫·马勒曾说:“自贝多芬以来,现代音乐无不有其内在的解说。”[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交响乐。所谓“内在解说”([德]inneres Programm)相对于“外在解说”——浪漫主义以来作曲家为使听众不曲解其作品而写作的音乐会说明书——亦被称作“隐秘解说”,即由音乐材料逻辑所展现出的观念([德]Anschauung),其意义却未被作曲家在所谓的公开解说中予以说明,可待听众在放弃外在文字说明的“凝神静观”式聆赏中去体悟。行至十九世纪末,这种特殊的独立音乐[ ]被称为“世界观音乐”([德]Weltanschauungsmusik)或汉斯·艾斯勒所称的“世界观交响乐”。马勒的交响乐则是世界观音乐的代表作,在其封闭的音响空间中构建起一个“自在自为”的世界。
从马勒去世至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马勒交响乐的研究并未中断:二战前倾向于对其音乐进行基础性的材料分析;二战后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们开始从历史与社会角度解读其作品,以特奥多尔·阿多诺的《马勒:一种音乐观相学》及论文若干为代表;六十年代后至今日,为更全面并更深刻地了解这位“未来的同时代人”,更多学人对马勒的交响乐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基于“阿多诺范式”——例如埃格布莱希特与达努泽的马勒论著。抛开对作曲家生平、社会史、书信、手稿研究而不论,既往对马勒交响乐的研究可被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音乐形态的研究,如早至弗洛罗斯、近至茵多尔夫以“马勒交响乐”为名的著作;另一则是“阿多诺范式”的哲学与美学的释义,从音乐隐喻至一个更为开放和广泛的观念世界,如伯恩哈特·阿佩尔的《古斯塔夫·马勒交响乐中的大都市感性临摹:一种社会学研究》(1975)。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前者拘泥于对某一部作品的独立研究而忽略了马勒毕生交响乐创作的宏观脉络——尽管多数学者会关注到“魔法号角三部曲”——并局限于材料研究;后者试图跳出音乐分析的狭隘院墙而在人文学科的宏观范畴把握马勒的音乐,却时常脱离了对音乐材料的阐述,抑或如达尔文进化学说缺少“关键的环节”。笔者作为西方音乐之“局外人”所提及的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学者作为“局内人”视角的不同。“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由于国情、人文背景所限,缺乏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文献,几乎无法进行史学研究起步必需的资料研究(Quellenforschung),其后果可想而知,重复、转述西方音乐史学家的话语在所难免,这是任何有抱负的学者不愿看到的……中国人善于思辨的天性并不亚于德国人;开放性的结构、系统研究已为我们今后的音乐学事业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一些被“局内人”视作“想当然”却未被点透的关键问题,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却格外显著。
如同十九世纪多数作曲家,马勒的交响乐继承了巴赫、贝多芬以来动机“发展变异”的作品构成方式。但本文认为,与其他作曲家有所不同的是,马勒在交响乐中通常利用动机和主题构造音响“符号”,在音乐文本的互文性、曲式结构和叙事结构及风格的融汇与体裁的“取独”中实现由微观“符号意义”向宏观“观念意义”的转化以及多部作品世界观的多样统一。针对上述特征,对马勒交响乐的研究则可构建起相应的模式。
动机与主题
动机常指一个简单而在整部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音型,包含音高与节奏两个元素。主题则是由一个或几个动机相互结合的产物,短至一个乐句(《第一交响曲》[ ]第一乐章主部),长至多乐句的一个或几个段落[ ](《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动机、旋律、和声、调性与调式、织体以及更为细末的材料组织方式,都将影响主题的构成。“主题根本不是独立自决的。相反,它严格地受制于后面必然得出的结局。没有后面的结局,它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 ]换言之,一个主题的意义展现于它在整部作品中的陈述与发展方式。反之,则一个主题的陈述与发展的可能性与该主题自身的构成因素以及作曲家的技术和意图密不可分。
在马勒交响乐的研究中,动机与主题的归纳与分析至关重要。它们在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马勒的交响乐创作与其他作曲家的区别。例如《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1-42小节)中,首先呈现的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以细碎的音型演奏的旋律(1-16小节),c和声小调,其中蕴含了一个四度动机(5小节)。在19小节,木管演奏出一个新的旋律——作为低音弦乐主题对位,该主题此时重复演奏——而这个旋律以长音展现其气息宽广的旋律则是建立在两个和音动机的基础上:半减二和弦和四度动机。25小节小提琴等弦乐器进入后,音乐由和声小调转入爱奥里亚调式,也可将之理解为民间音乐常见的自然小调式。马勒交响乐主题构建的特点在此便可窥豹一斑:每一旋律的歌唱性较强,形象清晰;较前辈更多调性与调式的可能性;在同一母题段落的统领下存在多个子题以及动机,在层次多变的织体中共时性呈现,“通过使各种形式关系在一个更加统一的式样之内集中,而使这些关系得到控制和加强”[ ]。在马勒的一些交响乐中,例如《第二》、《第三》、《第六》等,一个主部主题原始陈述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就已达到甚或超过了贝多芬交响乐中的一个展开部,更是远多于浪漫主义早、中期的交响乐作曲家[ ]——尽管马勒从他们的创作中学到了很多内容——而这仅仅是宏大作品的一个开始、一个组成部分:这足以体现对马勒交响乐动机与主题归纳与分析的重要意义。
符号与符号意义
“象棋不会讲故事,数学不能激发感情。同样的,从纯美学的观点来看,音乐不会表现音乐以外的东西。”[ ]一个基本的音乐材料,例如一个动机、或主题,只表现其自身——抑或在叔本华哲学的意义上揭示作为世界本源的“意志”——而不是为某种间接展现“意志”的理念而存在的。在此,音乐可以借用圣奥古斯丁之言而被称作“aliquid stat pro aliquo”,即“代表一物之物”。但本文在此所要借鉴的符号概念则与之有别。一个符号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指号活动”的存在,即根据经验将在场之物指向不在场的意义。约翰·迪利因而称符号为“aliquid stat pro alio”,即“代表别物之物”。迪利认为,对符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门相关又相别的学科:一为索绪尔、巴特等欧陆学者从事的“符号论”(semiology),力图在人文学科中研究符号;另一为皮尔斯、西比奥克等北美学者推而广之的“符号学”(semiotics),其“探索的对象或者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符号,而是符号的作用,或者说是指号过程”[ ],并认为“指号过程”不只是人类、乃是整个生物界存在的基础。endprint
音乐哲学与美学中的符号论观点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苏珊·朗格的学说。其师恩斯特·卡西尔称艺术为人类的符号活动,朗格本人则借鉴了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观点将音乐称为“情感符号”。罗伯特·萨缪尔斯所著的《马勒<第六交响曲>:一项音乐符号学研究》(1995)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其在音乐分析领域引入符号论[ ]的方法,以之建模逐乐章研究马勒的《第六交响曲》。其中众所周知的定音鼓节奏“Motto”就被视作一个重要符号,支撑着这部交响乐的形式与意义。
“号角声”也是马勒交响乐中一个重要的符号,最初出现于《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的9-12小节。尽管在此这一动机由音色上与号角风马牛不相及的单簧管中音区陈述,其音型所蕴含的西方近代音乐文化语境——尤其是深深影响马勒童年的奥地利军乐——也足以令我们称之为“号角”。随后这一音型在该乐章的高潮部分、以及末乐章均有出现,并以小号对这一音型进行“原汁原味”的呈现,彰显出其作为号角声所蕴含的激亢情绪。
从符号分析到互文性研究
符号“代表别物之物”的概念注定将对在场的研究引向不在场。于是,自律性的材料研究进而获得了开放的横向延展与纵向深入。如果说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那么认识语言之时,主体也认识了自己。一个在场借由不在场获得解释,同时它也解释了不在场,形成互文性。芭芭拉·R·贝利《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隐秘解说》(1993)一文,试图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马勒《第二交响曲》中的音乐材料解释《第五交响曲》,视前者为后者的“隐秘解说”。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该作品第一乐章开头小号的三连音音型同贝多芬交响乐中所谓的“命运敲门”音型相对照。
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奥,马勒得天独厚地继承了精深的德奥音乐传统。其交响乐中,一方面体现在运用了大量前人的音乐材料,作为自身抒情写意的音乐符号,例如《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中的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音型用以展现某种缠绵缱绻的情与爱,再如《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并不显眼处所运用的中世纪圣咏《震怒之日》核心音型所隐喻的死亡,又如他在被自己喻为“献给整个德意志的弥撒曲”的《第八交响乐》中对巴赫时代复调音乐技术的浪漫主义探索;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德奥传统民间音乐的继承与发扬,其交响乐的主题原始陈述更多展现的是旋律性、可歌唱性,这与其早年深受奥地利乡野民歌影响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是,马勒与前辈有所不同的一点,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在于他在毕生的创作中形成了诸多符号的“范型”,它们在其多部交响乐、或一部交响乐的多个乐章中——以原型或变体的形式——出现,从而在一张宏大的符号关系网中实现了互文性。承前所述,《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270-271小节——展开部第四段落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震怒之日》的核心音型,柏辽兹在其《幻想交响曲》的第五乐章中对这首圣咏的首句进行了运用。马勒在此将圣咏原句进行浓缩,仅用前四音作为动机,并在隐喻意义上成为一个意喻“死亡”与“天主震怒”的符号,由之补充并拓展成为平行的双乐句。第五乐章的主部主题则以其同主音大调[ ]形式出现,与第一乐章相同,是一个平行双乐句。展开部的主要部分亦在这一动机贯穿引导下构成,经多次出现,最终在289小节以小调形式“原样”呈现,将这一象征着死亡和恐惧的音乐意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曲式结构与叙事结构
从对曲式结构的运用上来讲,作为交响乐作曲家的马勒是一位传统主义者。他对音乐材料的陈述并没有像同时期一些作曲家那样采用相对激进的手段,而是更多地依靠传统曲式的架构。但马勒之于曲式一如勃拉姆斯之于和声,在继承传统框架与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发展与扩充,以在确保音乐宏观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大音乐的信息量。“交响乐于我就是:以手头的一切[作曲]技术媒介构建起一个世界。”[ ]此外,诸如三部曲式、奏鸣曲式等传统曲式本身就是开放性的结构,仅在技术和美学层面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自身也是后人对前人作品架构在技术与美学的一般规律上做出的总结。在曲式结构的导引下发现音乐材料之间更为丰富的层次与逻辑则是要务。
曲式展现了作曲家如何“安置”材料,叙事结构一方面揭示了作曲家如何发展材料,另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如何理解音乐。国内音乐学者王旭青如是评价音乐叙事理论:
“音乐叙事理论视阈下的音乐文本分析在关注音乐文本形式层面的研究基础上,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价值判断等多方面的要素联系起来,借鉴阐释手段,关注听者、语境和意识形态,将特定的音乐文本置于开阔的视阈内,大大丰富了对音乐作品进行意义阐释的可能性,展现出这门正在成长的音乐分析理论的学术活力及当代性品格。”[ ]
尽管外乎音乐作品的文学性文本与音乐作品本身的关系众说纷纭(叔本华认为音乐表现歌词、文学作品的观点是本末倒置,基于其唯意志论观点,这些现象层面的言辞“绝不可离开这一从属的地位而使自己变成首要事项,使音乐成为只是表示唱词的手段”[ ]),材料的发展叙述着其自身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说:音乐叙事并非讲述诉诸文学的故事,而是材料自己的“故事”,一个纯粹而有序的音响世界。例如《第一交响曲》,各个乐章的主题无不建立在纯四度音程的动机上。音乐从极弱极高的一个音开始,由这个音生发第一个四度,消逝,然后这个四度继续衍变,生出第一个旋律雏形,继续推进,进入奏鸣曲式。马勒利用四度音程作为动机的核心组成旋律、主题,通过发展变异,探索了其在不同音乐关联域中不同意义表达的可能性。这部交响乐自身展现了一个由无至有、由一至多、由丰富至统一、由平庸至崇高的“世界”的自在自为、自圆其说。
风格的融汇与体裁的取独
“取独”是一个由中国文言文语法借鉴的概念。所谓“取独”,即取消独立性。在文言文中,当主谓短语作为主语、宾语或一个分句时,在主语和谓语之间运用虚词“之”,即取消句子独立性,表明它并不是独立的完整的句子,而是整个句子中的一个部分。“取独”语法存在一个前提,即被取独的分句可以作为独立句子。而当这个独立的句子融入一个更大句子成为其中一个成分时,则需要取独。endprint
马勒的交响乐蕴含着诸多对音乐风格的融汇,例如《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海顿风格,以及《第八交响曲》首部的巴洛克咏唱剧(Cantata)风格等。体裁的取独亦然。在交响乐中,体裁取独要求存在一个相对高级和一个相对低级的体裁。这里的高与低并非针对其美学品格,而是就二者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言。在马勒之前,一部交响乐的某个段落或某个乐章有另一音乐体裁的特征这一现象或许相对常见,但将某一体裁形式完全融入并将之取独,则是马勒交响乐特有的。例如《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在极大程度上是一首兰德勒舞曲。“兰德勒是对南德意志-阿尔卑斯山地区农民以慢3/4拍伴以有特色的手臂身段、歌唱、拍击和踏击的典型对舞的称谓。它以大量八分音符、常为循环构造的旋律为基础。”[ ]在该乐章,马勒对这些特征进行充分调用,塑造了典型的兰德勒形象。但它不是一支独立的舞曲,而是一个在宏观的音乐逻辑上与其后乐章保持着紧密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交响曲》第四乐章则完全来自《少年的魔法号角》之中的歌曲《原始之光》,未作任何变动。但在《第二交响曲》中,这首歌曲独立的思想意义在交响乐的关系脉络(Zusammenhang)中被取代了,上承一个带有讽刺性的谐谑曲乐章,下启崇高的终曲,并与《第三交响曲》中与之特征相近的第四乐章形成互文性,彰显其静穆的内省与无尽的渴望这一精神特质。《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同样来自马勒本人之前创作的一首男声艺术歌曲,马勒引用它,并没有围绕其原作的形式架构加以发展,而是将这一主题置入前文所述“四度动机”的关系网中。“醉翁之意不在酒”,歌曲主题或许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是严密的符号脉络所要开启的“自为世界”及其言说的终极意义。
宏观层面的观念意义
“观念意义”是相对于“符号意义”而言的。一部音乐作品的“观念意义”由音乐作品整体展现出来。“生根于语词建立的世界观概念的他律论维度表明,随着1800年前后自律论美学的范式转变,世界观音乐——在其形式中并愈发——同样强烈地依赖可言说的概念性。”[ ]将音乐作为“世界”的隐喻得以成行,即缘于音乐自身逻辑的陈述与发展同现实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同构。音乐材料的起、承、转、合实现了一个类似起因、经过、结果的叙事结构,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而一旦这个音乐的“世界”在鸣响中(即听者的聆听中)实现一系列能指向所指的转化,听者即从“扫禄”变成了“保禄”[ ],识得了这个向他开启的“世界”的逻各斯。
在马勒的交响乐中,观念意义的获得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微观与中观的研究而得出一部交响乐的意义。简单举例,如《第二交响乐》,在挣扎、畏惧中表达对灵魂升华、超越苦难的渴望。另一是通过上述的研究在更大层面的互文性上获得全部交响乐的某种意义。这些意义,凝练着作曲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早在中世纪,学者就将音乐分为头脑的音乐、人声的音乐与乐器的音乐,并认为头脑中的音乐是最高层次的音乐,而乐器的音乐是最低级的。时至今日,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千余年前音乐学者观点何等“落后”,却应由之认识到“音乐展现终极观念”这一命题由来已久。从事音乐学研究,我们更要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音乐家分别用着怎样的技术手段传递着怎样的观念。古斯塔夫·马勒已经故去百余年了,但对他音乐的研究却从未停止,而是日益充分、愈发深入。因为人们相信,尽管他的音乐作品数量有限,但这位交响乐巨人站在高山之巅指给后人的音乐之路,值得我们不懈地走下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