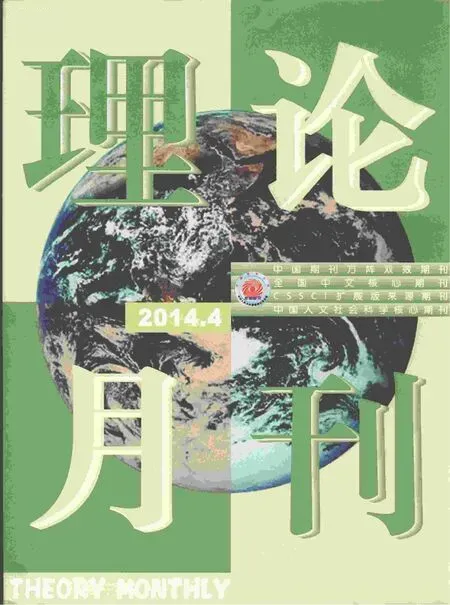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2014-12-04安启念
邵 鹏,安启念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2.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生态伦理思想起源于人类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哲学反思,表现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性批判精神。经济全球化和工业文明的扩张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生态伦理思想正是为人类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提出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的道德关系。以崇尚自然为基本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思想,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
一、道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向度
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是十分突出的。人文主义物理学家F·卡普拉(Capra)曾经指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1](P257)首先,“道法自然”体现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是道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庄子进一步指出:“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庄子·天运》)那么,自然作为最高的效法准则在于其“无为”的属性。在道家看来,“无为”既是一种“为”的方式,也在于“不为”或无所作为,但其结果是“无不为”。“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
其次,“无用之用”标示出生态伦理的意义。“无用之用”首先由庄子提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 他认为,世人所谓的“有用”、“无用”都是来自于人类既定的经验世界和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而“无用之用”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无用”是“有用”的无形支持,只有认识了无用的价值才具备言“用”的资格。如惠子的“大瓠”虽不适合做瓢,但如果把它做成“大樽”,可以“浮于江湖”;稀少而外形美丽的栎社树,但材质松散,是“不材之木”而“无所可用”。庄子认为,物各有所宜,关键是给物创设满足需要的最佳组合关系,才能充分满足万物各自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其后的道教指出万物是一个整体,每个物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作用,它们之间不存在贵贱的差别,人类无权任意侵犯其他物种。“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列子·说符》)总之,“无用之用”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采用多元的价值尺度来指导行为。
再次,“寡欲节用”的消费观彰显生态伦理价值观。道家认为,人只有以虚静、恬淡无为的境界控制欲望,才能够减少对物质资源的滥用,防止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产生。老子告知人们利用生态环境造福人类也要适可而止,要兼顾平衡,“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宝。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老子·第三十二章》)。庄子认为,能导致人的失性之处在于五色、五音、五臭、五味等欲望,“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庄子·天地》)。只有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才能驱除了外在之物的扰乱,回到人的自然本性中去。
最后,“贵生戒杀”是生态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道教继承了道家以生命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观,以生为人生第一要事,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太上老君内观经》)。《老子想尔注》甚至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 “贵生”思想将道德关怀的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了生命和自然界,形成了以一切生命存在作为保护对象的伦理原则,并把慈爱和同、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重要内容。《太平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三天内解经》等道经均强调“好生恶杀”,把“好生恶杀”与个人的“得道成仙”结合起来,并有严禁杀生、保护动植物的若干具体规定。“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太平经》)全真道认为“斫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重阳立教十五论》)是伤害大地的行为。
二、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关切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是反映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典型的形态,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旨归。儒家的天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切自然现象运行和变化的根源,它既是一种“自然之天”,又是一种“天之德性”,即天道和天德。天人合一具体包含四重含义:其一,天人合其德。人之德性的根源为天之德性,天人处于本一状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文言》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皆由天赋予,是人先天具有的德性。其二,天人合其性。人的知识和善性皆来源于天,人能够通过后天自觉发挥人心至诚之天性才能把握天道,达到人之性与天之性合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其三,人之性与天之性合其类。天作为化生万物、包孕万有的最高的本体,人之性与天之性同属一类和同其道理,自然的秩序类与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具有类似性。董仲舒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其四,人之性与天之性相感互应。天既作为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同时又是具有人格色彩的神灵之天。董仲舒以天人之性相互感应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找到天然的合理意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类通也,天人所同有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该思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观提供了哲学形而上的终极性依据,在深层意义上印证了儒家自然道德体系的本源性基础,表达了对理想境界的终极追求和人文道德关怀。
其次,民胞物与是儒家生态伦理的文化关怀。宋代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实践层面的落实。它内在地肯定了自然万物与人类本身的相通性,人不仅应以同胞关系泛爱众,更应以伙伴关系兼爱物,从而为合乎德性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也,乃混然中处。故大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程颢在提倡尊重天地的同时,又注入了一定的层次和等差意识,即人类理应对天地中的一切事物倾注更多的道德责任意识,从而可以超越万物与天地参。“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可以说,儒家把人类社会的仁爱用之于自然界,极力阐释“天道”中所蕴含的宇宙秩序:亲亲、仁民、爱物,仁者最终要靠“仁心”感通天地生命的大化流行,实现和谐的理想世界。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能够发挥道德主体性,以道德终极价值关怀为依归,依“仁道”以“推恩”方式仁及万物,创生一个和谐的道德理想世界。
再次,应时而中是儒家生态伦理的行为规范。儒家认为,如果人类社会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最终必致会遭到自然的惩罚的严重后果,所以制定了“应时而中”的行为规范。其一,“取物不尽物”。儒家主张保护生物的持续发展,反对因人类对动植物生态资源的掠夺而造成的物种灭绝。《礼记·月令》篇规定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天子不合围,诸候不掩群”。孔子指出:“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史记·孔子世家》其二,“取物以顺时”。儒家认为,要想做到“爱物”,人就必须“与四时合其序”,逆时、违时、失时、夺时等行为,都无法达到无饥和胜用的目的。孔子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论语·乡党》)。孟子根据动植物成长的规律,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粱惠王上》)。荀子则主张“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
最后,圣王之制是儒家生态伦理的立法爱护。《尚书》、《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均存在重视季节与动植物生长的密切关系的思想,为维持人类的基本需要必须制定相关礼制、法规、禁令的生态资源立法。荀子将其概括为“圣王之制”,对后来的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绍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如秦国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基本制度,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所载的律文基本与秦律内容极其相近。该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世俗生活中的重要行为规范。如古代社会中民间经常有封山育林的活动,具有传统所认可的效力。可以说,“圣王之制”的传统在政治实践层面保证了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并在民间的实践中,派生出勤俭节约的道德要求,并与佛教相结合派生出素食、不杀生、放生等一系列的爱护动物的生活实践。
三、佛教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意蕴
佛教的生态伦理观受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家的普遍称道。美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罗尔斯顿指出:“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是剥夺个体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和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 ”[2](P252)首先,缘起性空是佛教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佛教认为,万法即所有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因缘即条件结合而形成的,分散而灭。所谓的“因缘”,“因”是引生结果的直接内在原因,“缘”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在佛教看来,世界万物之间是一种互相含摄渗透的关系,一切对象世界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聚合体,生命体也是如此。华严宗提出的“法界缘起论”最为典型。所谓“法界缘起”,是指世间的一切现象均是由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随缘生起,而各种现象互为因果,相入(各种现象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即(各种不同性质现象可以转化成同一体),圆融无碍,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它以“六相圆融”理论说明一切事物的六种基本相状的相互依存关系。六相即总别、同异、成坏三对相状范畴;“六相圆融”是指人们从总别、同异、成坏三方面看待一切事物,认识到每一事物都处于总别相即、同异相即、成坏相即的圆融状态。这实际上是以整体与部分、同一与差别、生成与消灭来说明宇宙中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
其次,众生平等是佛教生态伦理的核心价值。佛教关于“平等”的涵义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平等、众生与无情平等。其中华严宗承认有情众生具有价值,类似于西方的生物平等论,肯定人类生命与有感觉的动物生命的价值平等;禅宗则类似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它肯定一切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而天台宗则类似于大地伦理学,它肯定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佛教的平等观既主张尊重生命,又强调敬畏自然,体现了生命观、自然观与理想价值观的统一,并通过佛教的教义和戒律传播与实践该观念。佛教把生命状态分为两种,即有情众生,包括人与动物等;无情众生,包括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佛教并没有“唯人独尊”,认为众生的生命本质是平等的,一切众生包括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等都有佛性,是“无情有性”的,不可以随意处置。
再次,依正不二确立佛教生态伦理的生态责任。佛教强调应该珍惜和合理利用自然财富,因为自然界的天灾与人世间的人祸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天台宗湛然提出了“依正不二”的思想,反映出对人类主体与生态环境的辩证性与互动性的注重,并成为佛教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依正不二,是指作为“正报”的有情众生与作为“依报”的国土世间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整体,“依报”的好坏,是由有情众生来决定的。如果有情众生都心存善念、勤行善业,则“依报”就会变得美好;否则就可能招致天灾。池田大作指出:“佛法的‘依正不二’原理,明确主张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 ”[3](P86)可以说,“依正不二”思想是佛教对人类公共道德责任的一种呼吁,现代生态危机正是由人类“共业”所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众生的共同努力。
最后,圆融无碍是佛教生态伦理的终极目标。佛教注重人与自然间的亲和融通关系,即事事无碍下的万物之圆融,希望人能够清除内心欲望及功利性追求,亲证自身与自然的圆融。佛教一直将现象界视为四大元素和谐共存的处所,“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楞严经》卷四)。天台宗善于在圆融思维的统摄下,让形式上存在诸种差别的自然万物达到本质的融通不二,如慧思的 “自性圆融”和 “圆融无二”(《大乘止观法门》),智顗的“法界圆融”和“三谛圆融”(《法华玄义》)。 华严宗则将“圆融”观发展到极致,提出了“六相圆融”、“十玄无碍”以及“华藏世界”等思想。方东美指出华严哲学的贡献在于“可以发展三方面的关系:首先是与神明的‘内在融通’关系,其次是与人类的‘互爱互助’关系,第三是与世界的‘参赞化育’关系。 ”[4](P323)禅宗则拓展了对圆融理念的理解,认为“天地一旨,万物一观,邪正虽殊,其性不二。”(《维摩诘经注》),从而达到“触境皆如”的状态,即人与世界万象之间构成的是互相映现,互相含摄的圆融之境。
四、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华文明所固有的农业文明特质的具体体现。从其经济基础来看“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 (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5](P399)在这个意义上,儒道佛的伦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人胜自然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并能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精神养料。
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并注入新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渊源。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共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形成的认识成果,也是在建设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成果。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号召我们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为复合生存目的和人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体系与实证策略系统,……它尤其注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6](P345)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思想,可以使我们充分把握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同时,在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来指导实践。
儒释道生态伦理思想虽然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尊重生命的共同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视角看来,三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即“儒家是一种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道家是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无为主义生态伦理观,佛家是一种破妄型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7](P68)儒家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的解释,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道家实现人尊重自然的思想,受到当代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佛教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家的普遍称道。
但是,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毕竟是华夏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并不是为应对严重生态环境危机而出现的,对于解决由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仍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道家一味强调顺应自然的“无为”论和反对利用科学技术的态度,带有盲目反文明的消极性。佛教则是从其主观的内心世界的所谓体验出发,在其生态理念中带有一些反科学的迷信色彩。因此,在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关键在于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要成为一种辩证的、理性的、动态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文明达成价值共识,这种共识要兼顾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理念。
其一,要对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意味着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够仅满足于人与自然的分裂的状态,而追求人与自然的相统一。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中不仅表现为不干涉自然万物的生长,更应体现出人尊重自然,循自然规律与法则办事。佛教的“慈悲”不应只是不杀生和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应加入人内心产生对自然的感受、发现和体验自然之美。现代的生态伦理本质上要求的是和谐是一种利益上的和谐、价值上的和谐与认同上的和谐。因而,我们在解读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时,应努力使其内在精神可操作化。
其二,要为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注入新的现代理念。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不能够作为强行约束和教化民众的工具,多元化价值观需要结合不同社会实存被引入,并充分保证个体的自由。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之间存在诸多契合之处,也存在一定不足,如儒家道德范围限定在人和社会的结构模式中,忽视对人—社会—自然多重关系进行道德思考;道家主张自然命定论,忽视主体的能力;佛家重精神解脱的价值取向而忽视解决实际问题等。因此,儒释道要从根本上确立兼顾民主、法治、公平等现代基本理念,并将现代生态伦理观念融入其中,为现代人认识生命意义提供参照,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伦理依据,则更易世人接受。
[1]王泽应.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2]邱仁宗.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4]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孙慕义.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7]任俊华,李朝运.人类中心主义、超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儒、道、佛学之生态伦理思想比论[J].理论学刊,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