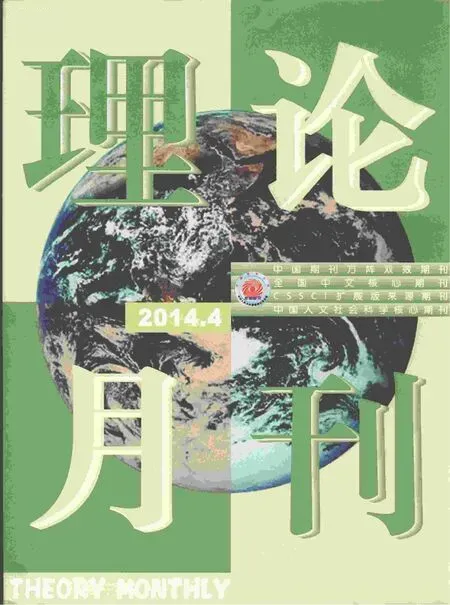论激发城市空间活力的伦理路径
2014-12-04李光玉高晓溪
李光玉 ,高晓溪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城市空间的生产既是美好生活的载体,也是生命体内蕴之活力的“外化”。历史上,空间形态随生产方式的嬗变呈现出异质性面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理性唤醒了沉睡的空间,挣脱了宗教意志的城市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城市空间也因生产要素的集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辐射力。面对汹涌的现代化浪潮,大规模空间生产就此拉开帷幕,但在现代化早期,恩格斯的笔触却勾勒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图景,“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到过这个世界1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1]显然,彼时强势的生产主义伦理所宰制的城市空间有着很强的功能主义取向,既非主体理想的实践生境,更为描绘出活力的生存图景。然而后工业社会笼罩下的城市空间则将问题演绎的更为复杂与综合,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符号化了空间也抽象了人,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映衬着单向度的城市主体,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符号化了空间斩断了与美好生活的联系,片段化、等级化与贫困化的城市空间呼唤着“活力”的反思,本文立足于空间、空间正义以及空间活力的三元辩证关系,尝试从伦理学视阈建构提升城市空间活力的现实路径。
一、以人为本,于日常生活中找寻活力的人性根基
美好生活与诗意栖居共同指向了现实之人,城市空间也因人而赋予了价值意义。一部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不过是人们按自己的目的不断追求、创造、构建的历史,人的生存、发展逻辑与空间生产的历史逻辑具有内在统一性,两种逻辑能否自洽自融,取决于日常生活是否包含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维度理解,以及能否将其内嵌于空间生产过程之中,凝结为动力之源、行为尺度与价值归旨。而城市空间的现状却传达着异化的现实,资本的喧宾夺主消解了丰富的主体,沉溺于消费主义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异化之人将全部的幸福定位于符号的获取,这一单纯的物的情感投射不仅剥夺了主体潜在的丰富性,也将承载着社会关系的空间抽象为单纯的符号性存在。因此,一个涉及权益诉求、身份认同、话语权利以及自由解放等主体性因素的伦理关怀被逻辑的彰显出来。此外,空间活力本质上是内涵社会关系之人将内蕴之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对象性实践为中介的一种空间注入,其自身并非机械的拼接,而是蕴生与“自由张扬与正义约束、主流价值与多元文化、自由自觉与社会控制的辩证统一”[2]的张力之中,因此,对空间活力的探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转换为空间生产之正义性与合理性的考量。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从动力、目的还是价值等不同视角来看,都是空间正义的旨趣,因为追求美好生活,就是人们空间生存生活及生产方式的最主要内容,它包含着每个公民合法、平等之基本权利的诉求。主体迷失的城市空间,终究只会沦为脱离实践和价值旨趣的自在之物,成为“仅仅是对世界终极本源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3]正如发展伦理学奠基人古莱所述 “侵害人类价值选择的发展是反发展。”[4]功能性与伦理性并存、正义性与合理性共在的空间生产,才能真正从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维度拓展人类美好生活空间的话语,才能真正塑造美好生活的载体,正如马克思所言“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5]本文认为,激发城市空间活力首先要从活力的源头即“现实的人”入手,活力的人性根基则潜藏于“存在着最广博、实用和最富有实践意义的哲学”[6]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方面,日常生活内涵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日常”意味着个体持久性的行为,“生活”则表明是在主体可及范围内的特定活动,即马克思笔下之为了“创造历史”而“生产的物质生活本身”。[7]人类的一切诉求,包括城市空间的开辟均源自日常生活的名义,只是随着人类由自我意识向意识自我的演进以及生产方式的进步,日趋丰富的日常生活派生出异质性因素,由于主体的执着迷恋,本源性之日常生活世界逐渐退居自觉的理性视野之外并隐退为生存的背景性因素,但人们最终却发现随日常生活消逝的是人类自身。胡塞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始了对工具理性喧宾夺主的批判:“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作为主观性而排斥出去,形成了一幅没有人生存于其中,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的世界图景。”[8]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城市空间的现实组成要素,它内涵着一种德性追求,即在物质生活空间之上的精神空间弥补人们价值的断裂。建构日常生活的德性,才能找回自由、平等和正义,实现真正的 “诗意的栖居”。“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实践逻辑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必须转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实践性本体论关怀。”[9]若对空间生产实践进行审视,则不难发现诸如空间隔离、空间贫困等表征背后潜藏的恰是 “经济和国家媒体控制下的系统,借助货币和官僚政治的手段,渗透到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10]城市生活好似一部功能化的机器,日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日常生活沦为社会组织中的纯粹客体,成为社会生活的风险迷宫。充斥其间的消费意识形态消弭了正义话语,风格式微、指涉消失与零度化的空间体验则多层次、多维度地阻碍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把握。因此,不论是主体的回归还是正义的彰显,亦或是活力的激发,都应在“日常生活”中探求。
二、价值导向,于情感道德间追求活力的精神源泉
城市空间活力的生成呼唤主体“情感能量”的注入与“价值导向”的支持。主体的气质、审美等精神状态的空间折射必然影响活力的样态,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与符合伦理要求的价值支撑既是主体实践的理想状态也是活力的传递前提。情感能量的驱动是指以非知识性、非逻辑性和无意识为特征的信仰、欲望、激情等非理性因素对主体内蕴之可能性的激活,而道德因素作为在人类长期实践活动中内化而成的社会关系,不仅因其“理性特征”贯穿实践过程始终,也具有以自觉性、逻辑性与过程性为特征的创新性,所以,“道德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力的发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1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是情感能量还是道德支撑都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推动或制约着主体的实践,这就为内蕴两者的空间生产提供了可能,主体既凭借实践将情感能量与内化的道德因素对象化于空间生产中,同时,所生产的空间也通过表征的社会关系制约着主体的实践样态,而所谓活力化的空间正是能够在情感与道德、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结合而成的具有辩证张力的精神系统中催生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现实生境。
就情感而言,不仅呈现为主体复杂而稳定的心理体验,更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其内容既包括直接参与到主体认识活动的心里形式,如意志、爱好、想象等,也包括不必通过自觉、逻辑、知识性的认知过程便可获得关于客体本质规定的心里形式,如灵感、顿悟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情感因素的作用,认为人类实践“懂得按着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么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但情感之于空间活力的作用机制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鼓励、认同的力量迸发主体积极拼搏与昂扬向上的精神以提升空间认识能力与生产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个体层面的活力生成离不开利益诉求实现时的情感体验。马克思曾提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人们在劳动实践活动中构建了社会关系,其中折射出的现实需要便是人类的利益诉求,而情感正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主体对空间正义的渴求既是利益诉求的呈现,也是城市空间理应赋予主体的生存形式,所以,以空间正义为原则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对通过正向情感的培育激发个体活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空间整体层面的活力生成离不开“集体意识”的认同与凝聚。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指认,“集体意识”是将分散个体连接成社会的核心概念,既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与纽带,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确立的前提。城市空间的开辟为人类开启了从小规模聚集向大规模的群集的新征程,一系列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渐次演进也就此拉开帷幕,而基于个体情感的“集体意识”不仅始终作为对内维持空间稳定,对外划清空间界限的“先验形式”,更重要的是为个体活力提供了空间延展的传导机制。
就道德而言,其自身之于空间活力的价值支撑源于二者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道德因主体层面的日常引导与社会关系层面的实践规范而凝结为活力的内在价值基点。首先,内涵道德因素的日常生活以价值的创造与终极意义的探寻为主旋律,若剥离日常生活的道德内核,主体只能因“苍白”的精神世界而呈现为未经启蒙的“尚未”;其次,相较于主体性明显的个体情感所结成的“集体意识”,道德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长久以来的积累、沉淀与内化,不仅因协调了多元化利益诉求而维系了持久的群体凝聚力,也有效的提供了主体能动性张扬的精神保障。另一方面,空间活力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完满概念,其自身“异化”与“自反”的避免也需要道德坐标的维系。诚然,空间生产、经济繁荣、资源聚集等均为城市生命力的表征,但科技的进步提供主体便利生活的同时也革新了个体的空间观感,以交通工具为例,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不断拓展着城市的空间尺度,使得对城市细部的阅读变得几乎不可能,而哈维笔下的“时空压缩”即时间在空间向度内的“坍塌”在这里获得了现实的体现。此外,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接管的空间生产使主体在商品化、同质化、平面化的空间中异化为符号性存在,诗意栖居只是资本编织的谎言,将幸福寄托于异化消费的理论结局只能是“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因此,空间活力的现实语境凸显了问题研究的伦理视阈,强调主体情感的注入与道德的支撑才是“健康”活力的精神源泉。
三、尊重差异,于正义的多样性中探求活力的实践保障
现代性的重估与传统价值的移位映衬着我国空间生产的差异性格局,尚未完全脱离的资本逻辑演绎着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矛盾:日益“碎片化”与“等级化”的空间标识着种族、身份、性别等差异性因素在将城市“科层化”为僵死空间的同时,也与资本形塑的以“可交换性”为唯一特性的空间不断生产着矛盾与对抗。具体而言,“差异性”体现为空间生产与历史连续性的断裂,虽然主体间最终利益趋同,但局部、眼前利益的同一镜像却因利益主体的多元、多寡的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出场语境、路径的不同而打破;空间阶层分化、空间生产与分配不公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在更广泛的视阈中体现的文化、社会资本对空间结构的塑造都是“差异性”与上述矛盾与对抗的空间表达。本文认为,差异化的空间样态既是利益分化主体从事的物质实践及所建构的文化样态、社会制度等的空间再现,又是相互冲突且异常复杂的差异性社会关系通过空间于主体间的表征。一方面,差异空间的现实存在为破除资本同质化生产逻辑的奴役,同时实现主体本真生活状态的回归提供了现实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为建构相应的差异性正义提出了理论挑战。笔者所理解的差异性正义,是以构建“美好生活”的总体性伦理原则为指导,通过差异性共识来形成的,确保不同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平等且动态地享有空间权利。“财富的创造依赖于社会协作和合作而非仅仅依赖于某种个体化的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13]差异性正义所凸显的是“有机团结的结构性前提、社会认同的精神性基础以及社会互动的实现方式”,[14]它不是将城市空间视为生存的竞技场,而是将“生活世界”作为其有效性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与哈贝马斯所讲的“交往理性”的现代生存空间相类似。“差异性正义”作为一种新的正义范式,即能迎合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现实逻辑,也丰富与拓展着空间正义的理论体系。其存在的根基在于“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内的陌生人之间存有正义的责任去构建并支撑集体行为的制度”,[15]即由差异化正义指导下的有机团结,在“老牛耕地与卫星上天同在,乡间小路与网络并存,人情关系与法治关系掺合,权力崇拜与市场经济结合”[16]的差异化空间中彰显活力意蕴。有机团结的实现既需要主体间性视阈中个体活力的支持,也需要差异化正义的规约。以差异性为本质特征的空间分化既逻辑的内涵于日益细密化的社会分工中,也是工业社会时代的必然现象,当前,以个体、阶层为主要维度的空间分化已经超过了作为表现形式的个体识别与功能区分而直接指向了空间整体的结构性现象,即空间分层与隔离。日益凸显的“个体主体性”贯彻到社会现实之中,切断了主体间联系纽带也虚化了空间共同体,但强加于主体的特殊活动范围阻碍了主体活力的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有机团结正是基于差异化空间语境,于主体间性视野中整合社会横向联系的建设性思路,“以相互交往的陌生人之间所负有的正义之责任来为社会团结提供论证。”[17]以差异化正义垂范空间生产,通过和谐空间关系来重塑空间纽带,强化异质主体间的社会联系,为主体乃至整体空间的活力激发创造条件。
四、生态弥合,于“自然-社会”的生态过程中实现活力的时代传承
人性化生活是空间生产的价值归旨,“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并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新塑造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18]空间城市化需以原始质料即自然空间之本体论地位的确认为逻辑前提,也就是说,空间生产以自然界辩证发展的理论图景及其规律的总体认知为先导,并遵循认识、改造、建构的致思路径,通过自然与人化空间之辩证张力而实现活力的激发为最终目标。因此,自然空间的存在样态直接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现实面貌,正如哈维所言,“整个世界中的生态与社会事业通常相互包含与暗示,人类实践行为不可能游离于生态事业之外。”这里内涵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确认了城市空间生产打开了一本“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的同时,也通过城市空间生态的构建拓展了自然生态的外延;其次,如何处理城市空间与原始、连续且在技术理性凸显的语境中不断“背景化”的自然空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关乎城市空间活力的关键问题。正如阿格尔笔下“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以权力、知识与实践为核心的集创新、变化与进步于一体的时代终究会以自然空间的“生态边界”被人类无限膨胀的理性所侵蚀而告终,现代化的结局也将以理性的“自反”而收场。因而,本文认为,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自然空间走向社会(城市)空间过程中的生态弥合过程既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化过程,也是城市空间生产由断裂走向弥合的过程。
当生产力的发展足以使人类摆脱生存之虑时,现代性的“隐忧”又因美好生活的孜孜以求而困扰着主体。过度人化的空间对自然空间的侵蚀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有生态,物种灭绝、自然灾害等虚化了人类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所以,空间生产的总体伦理原则即空间正义备受瞩目,尤其在生态维度上,将人化空间中的“德性”因素注入自然空间中以延伸伦理的外延,既为空间生产融入了人类自我关怀的情愫,又催生了尊重自然的情怀,将空间生产纳入“可持续”的发展视阈中,力图实现“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两者都不处在支配地位之正义图景的勾勒。”[19]此外,不同层次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样态描绘了城市空间的内部生态。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主体性实践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社会关系,而“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0]这也是为什么“空间的生产使它对相关行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21]当前的“空间隔离”剥夺了主体“进入空间的权利”,碎片化的城市空间映照着破碎的城市生活,正义的缺失加剧了生态的失衡,贫困的空间再生产的只能是空间的贫困,就像鳞次栉比的商业广场时刻传达着消费主体的呼唤一般,这种符号化的建构永远是对特定消费群体的谄媚;高耸的摩天大楼刷新城市天际线的同时似乎也在标识着群体间的不断拉大的心理尺度。因此,维持空间生态的平衡不论对“自然-社会”间的空间生产还是城市内部的空间重构均至关重要,但若将这一伦理关怀作“功利主义”解释,即人类利益视为生态平衡的出发点与归宿地,则不仅赋予了自然物的互利共生以道德意义,也将人类贬低为动物式的存在并永远束缚于自然必然性的苑囿。正如康德所言,人为自身立法是人的自由,符合伦理的生活本身即是人类之固有价值尺度,但与其说是伦理尺度使人之为人的生活,不如说这是主体自身活力彰显的结果,本文所探讨的空间活力也正是和谐化空间生态支持下的主体活力的空间化。
[1][7][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32,83.
[2][11][14]董慧.社会活力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3,187,211.
[3]王志刚.差异的正义: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诉求[J].社会主义研究,2012,(4).
[4]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
[6]张之沧.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
[8]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J].中国社会科学,1994,(3).
[9]李兰芬.论空间生产的意义问题 [J].社会科学辑刊,2011,(11).
[1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57.
[13]David Harvey,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 well,Oxford, 1996, p.97.
[15][17]马晓燕.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J].哲学动态,2011,(9).
[16]任平.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J].江海学刊,2011,(3).
[18]董慧.身体、城市及全球化:哈维对解放政治的空间构想[J].哲学研究,2012,(4).
[19]董慧.空间、生态与正义的辩证法-大卫·哈维的生态正义思想[J].哲学研究,2011,(8).
[20][21]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