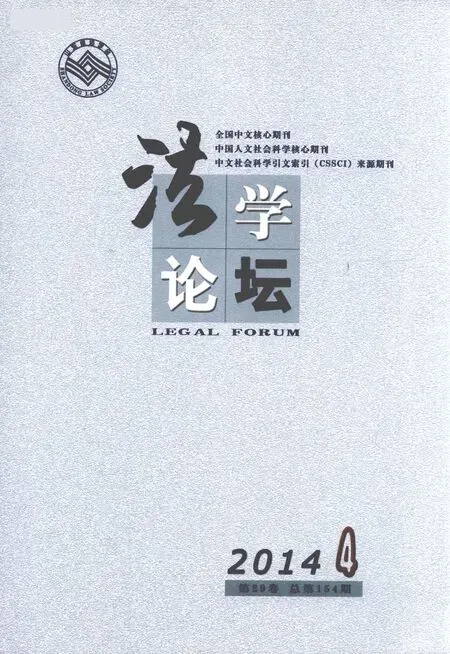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之检视——兼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4号裁定书
2014-12-03杜焕芳
杜焕芳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热点聚焦】
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之检视——兼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4号裁定书
杜焕芳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基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院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合同,具有独立性,应由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或者在法律选择无效的情况下由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去判断该协议是否有效。《民事诉讼法》不仅要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协议管辖条款,而且应该更加规范,而不是简单地援用国内案件的协议管辖条款,同时应明确选择法院协议的适用范围,及其法律效力的法律选择和判断要件。
涉外诉讼管辖;选择法院协议;效力认定;法律选择;民事诉讼法
一、问题的提出
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删掉了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协议管辖条款,而保留国内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条款,其法理基础何在?立法意图是要将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统一适用于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但是,这种“统一适用”的意图完全忽视了涉外民事诉讼与国内民事诉讼的差别。忽视了涉外诉讼管辖协议或者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作为一种争议解决的特殊协议的特殊性,其自身效力仍有准据法的确定问题。该准据法的确定可否遵循一般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则?是依法院地法还是按被选择法院地法?
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某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公司)与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国某公司(下称韩国公司)、第三人天津某公司网络游戏代理及许可合同纠纷案(下称山东公司案)中,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第21条约定:“本协议应当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国法律解释。由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所有争议应当在新加坡最终解决,且所有由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应当接受新加坡的司法管辖。”在发生协议内的争议后,山东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中,韩国公司对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尤其是双方对于协议选择外国司法机关管辖的效力问题有争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韩国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该院审查认为:本案为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虽然原告山东公司与被告韩国公司签订的《网络游戏许可协议》第21条约定产生的争议应当接受新加坡的司法管辖,但是双方同时约定“本协议应当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国法律解释”,双方在协议适用法律上选择中国法律为准据法。因此,双方协议管辖条款也必须符合选择的准据法即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据此,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应限定在与争议案件有实际联系的范围内。而本案山东公司与韩国公司协议约定的管辖地新加坡,既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也不是本案游戏许可协议的签订地、履行地、争议发生地,所以与本案争议无任何联系,其约定超出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限定范围,该约定管辖应属无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原告山东公司住所地法院,与本案有实际联系,在双方协议约定管辖无效的情况下,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参见2009年1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鲁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韩国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对于如何认定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或条款的效力,不同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不一致,即使在一国的民事诉讼中,也可能分别针对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而设置不同的立法要件,并作出不同的司法认定。我国1991年和2007年修正《民事诉讼法》即采用区分制,对于纯国内民事诉讼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依照“硬性要素”进行司法认定,而对于涉外民事诉讼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则按照“实际联系”进行司法审查。因此,是否支持该案当事人的主张,所需要解决的也是需要检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条款的立法理解;二是涉案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条款的司法判断,尤其是其独立性、法律适用和效力认定。结合山东公司案,笔者认为应从立法文本解释和国内外比较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从宽把握。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中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的进一步完善问题。
二、协议选择法院条款的立法理解
(一)协议选择法院的理论基础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之间就涉外民商事案件协议选择法院,法院由此获得案件的管辖权,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参见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这种管辖基础或管辖依据被称为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这项机制能够克服管辖冲突对跨管辖法域商事交往造成的不便,降低国际商事合同在各国法律差异、管辖权重叠和冲突法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见性等方面的风险。*参见Friedrech K. Juenger, 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 p. 214.是否承认协议管辖以及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辖,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参见李双元:《关于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若干问题的思考》,载顾倚龙主编:《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海事法律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当事人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因而从理论上说,除非是公共政策的原因,否则,任何对协议管辖所增添的附加条件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侵损,也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当事人就其争议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之管辖法院作合意选择或分配是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而当事人依法行使该权利的直接法律效果就是改变了地域管辖的效力,协议管辖可以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获得管辖权,也可以使原本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丧失管辖权。
从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类型来看,协议管辖属于由当事人选择的管辖,其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而非意思表示的形式;即使选择的形式有瑕疵也不至于影响其效力;也非意思表示的内容,只要能够认定该种选择是可确定的。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显然有他们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之所以在合同中选择某一国的法院来处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争议,或者是合同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或者是当事人利用第三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期望他们之间的争议能够获得公平公正的审理,或者是当事人期望利用第三国法院的特殊经验与技能从而解决某些特殊的合同争议。*参见王吉文:《2005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二)《民事诉讼法》第242条
从条文文本来理解,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可简化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法院管辖”,且对“选择”作了五个方面的限定:一是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至于人的身份、能力、家庭关系方面纠纷的当事人,则不得选择管辖法院;二是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三是协议选择的法院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四是协议管辖只能改变一般管辖和特别管辖,选择我国法院的,不得违反我国关于专属管辖的强制规定,因为协议管辖通常选择的是一国的“国际”管辖权;五是当事人只能通过协议选择一审法院,因而,若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我国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参见蒋新苗主编:《国际私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434页。换言之,从条文的文本来看,只要有违上述限定情形之一的,该选择即无效,显然这是最严格的解释。但是,如果按条款的效力来理解,上述五个方面的限制在实际效力上是存在差异的。限制“一”、“四”、“五”属于强行性规定,即足以影响选择法院协议的实际效力,而限制“二”和限制“三”不属于强行性规定,如有违反不足以影响选择法院协议的实际效力。
那么,如何解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与国内案件的协议管辖相比较,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5条对于国内案件的协议管辖在“实际联系的地点”方面有明确的范围规定。*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是第242条未作明确限定,因此不能套用国内案件的协议管辖的规定,将第242条的“实际联系”仅限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在涉外民事案件中,如果作此限定理解,就失去了选择法院协议的意义。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五种管辖依据或者属于一般管辖,或者属于特别管辖,没有选择法院协议也可以进行法定管辖。但是,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曾以苛刻的“实际联系要求”否定当事人选择的法院管辖,例如在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诉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和福建省琯头海运公司案中,厦门海事法院以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实际联系要求”为依据,否定了约定由荷兰鹿特丹法院管辖的管辖协议的效力。在浙江省工艺品进出口(工贸)集团公司诉金发船务有限公司案中,上海海事法院根据内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了约定由香港法院管辖的提单条款的可执行性。
笔者因此以为,按“事实联系说”来确定“实际联系”并不具有可取性。如果按“法律联系说”来确定之,则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双方当事人选择第三国法院并选择第三国法律,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具有“实际联系”。双方当事人选择第三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该国法律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履行乃至合同纠纷的解决产生了内在的密切联系。*参见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二是,双方当事人仅选择第三国法院,从目前淡化“实际联系”的发展趋势看,也可以认定为有效。协议管辖法院与案件关联性泛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充分发挥协议管辖的优越性,特别是在管辖的国际协调中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是“中立法院”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中的必然要求。*参见刘力:《我国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中“实际联系”辨析》,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三是,双方当事人仅选择第三国法律,但一方当事人选择第三国法院起诉,在没有其他法定管辖或酌定管辖的因素的情况下,则不宜认定为有效。*参见杜焕芳:《协议选择外国法院条款是否有效》,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2月24日。协议选择法律与协议选择法院可以分离且是两码事,分属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不同领域,前者属于立法管辖权范畴,而后者属于司法管辖权范畴。
三、协议选择法院条款的比较观察
不同的国家对于当事人协议管辖尤其是对选择外国法院管辖协议有不同的要求,效力认定方面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以下从域外国家做法、我国其他法律和国际公约三个角度来进行比较观察。
(一)域外国家的做法
外国管辖权条款通常为美国法院所支持。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M/S Bremen案*M/S 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 407 U. S. 1 (1972).成为支持外国法院选择协议的标志性案件。在此案中,最高法院法官以几乎一致的意见推翻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些判决支持美国法院的管辖权而反对当事人对伦敦高级法院的选择)。该案为以后的案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准:“一个通过自由协商而达成的国际私法协议,如不受到欺诈、不适当影响或过分的交易力量的影响,则应当被赋予效力……除非原告能清楚地表明对其执行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吴一鸣:《国际民事诉讼中的拒绝管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则改变了以往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规定了意大利法院管辖权的摒弃和创设。该法第4条第1、2、3款分别规定,如果当事人协议由意大利法院管辖,而且此类接受有书面证明,或被告未在其答辩陈述中作无权管辖抗辩而到庭应诉的,意大利法院应有权管辖;如果有书面证明而且诉讼涉及可让渡的权利,则一项选择外国法院或仲裁的协议,可以限制任何意大利法院的管辖权;如果该外国法院或仲裁员拒绝管辖或无法审理诉讼,则此种限制不具效力。
(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内地与香港判决执行安排》
在涉外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方面,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06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0次会议通过,法释[2008]9号。(以下简称《内地与香港判决执行安排》)作了特别规定。
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的规定,只要海事纠纷当事人均为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之间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与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相比较,该条款在协议选择法院的直接审查方面并无“实际联系”要求,但适用的情形仅限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外方当事人,且限于选择我国海事法院,以便扩大我国海事管辖权。从法理上解释,不仅海事纠纷的外国当事人之间,而且中外当事人之间也可以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且我国不一定要与纠纷有实际联系。在涉外海事诉讼中,协议管辖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海商合同中海洋货物运输合同(提单)、海上保险合同、打捞合同、拖航合同,通常都订有管辖权条款。关于这些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只要符合我国法院的有关规定,海事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该第8 条的规定突破和丰富了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42 条的规定,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出我国管辖权立法方面的新思路和新观点,有利于扩大影响,同时它为我国海事审判走向世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值得肯定。
按照《内地与香港判决执行安排》第3条的规定,“书面管辖协议”是指当事人为解决与特定法律关系有关的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争议,自该安排生效之日起,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协议。书面管辖协议可以由一份或者多份书面形式组成。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合同中的管辖协议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管辖协议条款的效力。该安排第9条还规定,对于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管辖协议无效。但选择法院已经判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效的除外……”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可见,《内地与香港判决执行安排》一方面未将“实际联系” 作为确定协议管辖是否有效的条件,另一方面,从间接审查管辖权的角度认定,协议选择法院的效力应由被选择法院地法决定,而非由法院地法决定。
(三)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囿于管辖权方面的限制,国际社会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上的国际合作一直步履维艰。美国已故教授冯·迈伦最早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提议制订一项全球性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并得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及其成员的赞同。*参见徐宏、郭晓梅:《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特委会会议情况》,载韩德培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创刊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557页。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于2005年6月30日通过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截止2010年2月19日,墨西哥已于2007年9月26日加入该公约,美国和欧盟分别于2009年1月19日和2009年4月1日签署该公约。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网http://www.hcch.net/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status&cid=98,登录时间:2013年4月5日。我国外交部全程参加了该公约的整个谈判过程,虽至今未签署,但该公约的做法可资参考。
首先,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1章“适用范围”第3条明确了“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所谓“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排他性地指定某一缔约国法院或者某一缔约国的一个或多个特定法院,来处理因某一特定法律关系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争议。除非当事人明确作出相反表示,他们选择法院的协议都将被视为是具有排他性的。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书面或其他可以证明的形式订立。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可以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来规定,也可以独立于合同,而单独起草这种特殊协议,从而独立于其他合同实体条款,当然,其效力不因合同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而受到质疑。这主要说明三点:一是,只要协议选择的法院是确定的,则该被选择的法院即是管辖案件的唯一法院,具有排他性。二是,选择法院的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非书面的。*参见王吉文:《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1页。三是,选择法院的协议具有独立性,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合同。
其次,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2章“管辖权”部分规定了四项内容:一是,当事人在协议中指定解决争议的法院有受理案件的管辖权(第5条第1款);二是,根据第5条第1款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基于争议应由其他法院管辖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第5条第2款);三是,如果协议中存在指定法院,非由当事人选择的法院没有管辖权,该法院必须中止或拒绝受理该案件(第6条);*参见杜焕芳:《协议选择外国法院条款是否有效》,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2月24日。四是,直接审查确认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应为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第6条a项)。这主要说明三点:一是,协议选择法院没有“实际联系”的要求,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意图是不要求“实际联系”,但该公约第19条也作了限制管辖权的声明规定:一国得声明其法院可拒绝审理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所适用的争议,如果除被选择法院的地点外,该国与当事人或争议并无联系。从已加入该公约的墨西哥来看,没有对此作出保留声明。二是,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对被选择法院来说不得拒绝,对未被选择法院来说不得受理,或者已经受理的要中止或拒绝受理。三是,无论是被选择的法院还是未被选择的法院,在审查自身直接管辖权时对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认定,应适用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而非受理案件法院所在国的法律。*参见Ronald A. Brand, Paul Herrup,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0-81.
最后,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3章“承认和执行”规定了两项内容:一是,一项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指定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应依本章在其他缔约国得到承认和执行。仅可基于本公约规定的理由而拒绝承认或执行(第8条第1款);二是,间接审查拒绝承认或执行的情形(第9条)。其中包括“协议依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为无效,除非被选择的法院已认定该协议为有效”。这主要说明两点:一是,以协议选择法院作出的判决在缔约国之间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二是,被请求承认或执行地的法院在审查间接管辖权时对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认定,同样应适用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而非承认或执行地法院所在国法律。*参见Ronald A. Brand, Paul Herrup,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1.
四、协议选择法院条款的司法认定
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4条专门规定了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权,但被2007年修正《民事诉讼法》作了删掉处理,没有继续沿用。从1991年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的立法背景来看,对之严加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随意选择法院,避免诉讼法院地点的不确定。从实际来看,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行使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但双方当事人选择法院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范畴。除了法定管辖和酌定管辖外,协议管辖应交由当事人决定,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其所选择的法院是排他性的还是非排他性的,则认定其所选择的法院是排他性的,这亦为国际上所肯定。*参见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29页。至于案件判决能否执行,则是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应承受的后果。
我国司法实践曾采纳过准据法联系标准,*例如,中化江苏连云港进出口公司与中东海星综合贸易公司买卖合同管辖权异议案,合同规定“本合同受瑞士有效法律管辖并据之进行解释”,“争执应提交瑞士苏黎士法院裁决”,但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均不在瑞士,江苏省高级法院通过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实际联系”的扩大解释,认定管辖协议是有效的,最高法院也认为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建立了某种实际联系,应认可协议管辖的效力。参见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8页。但近年来司法实践则倾向于采纳事实联系的客观标准,强调域外法院必须与讼争的特定法律关系有客观联系。再回到山东公司案上来观察,该涉案网络游戏许可协议第21条约定了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合同及合同解释的准据法——中国法;二是解决争议的方式——司法诉讼解决;三是解决争议的法域——新加坡法院。其中,第一项内容属于协议选择法律性质的条款,用以确定解决合同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准据法,第二、三项内容属于协议选择法院性质的条款。这两种性质的条款内容可以分离,且可以分别指向不同的法域。最高人民法院在终审裁定中指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与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行为,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判断其效力。对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条款的效力,应当依据法院地法进行判断;原审法院有关协议管辖条款必须符合选择的准据法所属国有关法律规定的裁定理由有误。”*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我国实务部门人士认为,立法规定的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原则是对当事人管辖意思自治的一种限制,如果运用法律选择标准对“实际联系”原则进行扩张解释,将导致当事人通过约定合同准据法的方式选择原本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实质上架空了我国法律对协议管辖的限制性要求,该种理解不符合立法本意。刘贵祥、沈红雨、黄西武:《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但是,如果我国法院对此案件依据我国法律对于《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严格文义解释,必然得出当事人之间选择法院的协议无效的粗暴结论。看似维护了我国的司法主权,保护了我国的当事人,但是实际上否定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意愿,也否定了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的司法管辖,而最终的判决还可能需要由被执行人所在地或其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院的承认及执行,其中包括对于原受理案件法院的间接司法管辖权的审查。*参见杜焕芳:《协议选择外国法院条款是否有效》,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2月24日。
该选择法院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合同,具有独立性,其约定是否有效,仍然存在着法律选择和准据法的判定问题。*关于法院选择协议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即程序性质论、合同性质论以及折衷的诉讼合同性质论,具体讨论参见焦燕:《法院选择协议的性质之辩与制度展开》,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该协议内容只是确定了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准据法,但并未确定选择法院协议的准据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后者来说,未必一定按照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国法——我国法律来判断。适用法院地法将无助于法院选择协议的立法目的之实现,甚至会构成实现该立法目的的严重阻碍。*参见焦燕:《法院选择协议的性质之辩与制度展开》,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早在第九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法院选择协议的准据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一种观点认为法院选择协议是管辖权的协议,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院选择协议是实体合同的一部分,应依据合同准据法而非法院地法以判断其效力。*参见R. H. Graveson, “The Ninth Hague Conferenc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0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61), pp.18, 28.从法理而言,由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或者在没有有效法律选择的情况下,由被选择法院所在地国的法律去判定该协议是否有效,是最适当的。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5条、第6条和第9条分别在审查直接管辖权和间接管辖权时对于认定协议选择法院的效力,均规定应依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而不适用法院地法律。*参见Trevor Hartley, Masato Dogauchi.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s Agreements, Prel. Doc. No. 26 of December 2004, pp.125, 149, 183.《内地与香港判决执行安排》在不予认可和执行的理由方面,对于管辖协议效力的间接审查依据,明确规定的亦是“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而非法院地法律。
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为何协议选择新加坡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该约定的出发点,是要避免可能由于国家保护主义而导致对有关争议的不公平解决。由第三国新加坡法院来管辖,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也符合经济效率标准。*有学者专门对管辖权等问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参见朱莉:《管辖权、法律选择方法与规则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1页。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在对山东公司案审查司法管辖权时,要么按照被选择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也就是新加坡法来认定,要么先决定不受理此案或中止审理,要求当事人按照事先协议的约定去新加坡法院进行司法解决,由后者根据新加坡法去判断该选择法院协议是否有效。如果认定有效,即由新加坡法院管辖,我国法院应尊重新加坡的司法管辖;如认定无效或者新加坡法院拒绝管辖,而我国有管辖因素的,或者当事人重新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的,则我国法院可以管辖。*参见杜焕芳:《协议选择外国法院条款是否有效》,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2月24日。在该案上诉审理过程中,笔者曾应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的邀请,提交了上述专家意见,遗憾的是,该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另外,韩国公司对此有何救济措施,可否要求法院发布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所谓禁诉令,是一国法院对系属该国法院管辖的当事人发出的,阻止他在外国法院提起或者继续进行已提起的、与在该国法院未决的诉讼相同或者相似的诉讼的限制性命令。参见欧福永:《国际民事诉讼中的禁诉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由于被诉至我国法院,韩国公司由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可否另行诉请损害赔偿?是向新加坡法院还是向我国法院提请救济或赔偿?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此均没有规定,笔者将另文讨论。
五、协议选择法院条款的完善建议
(一)应当重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修改研究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特定程序、专用程序,不同于一般国内民事诉讼程序。*参见蒋新苗主编:《国际私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涉外民事纠纷的诉讼解决不仅要确定司法管辖权、具体程序适用、准据法选择适用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而且要考虑具体纠纷类型和诉讼环节,这些问题之间有很强的逻辑联系,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集中规定,有利于法官系统掌握相关制度,有助于法官断案,更重要的是一个诉讼观念的问题。1991年至今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但是在管辖、送达、司法协助等方面,难以适应20年来涉外民事案件的复杂多样,不能跟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趋势,也无法高效解决涉外民事争议。
就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来看,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修改主要有三个方面:(1)删除《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和第243条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而统一适用国内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2)增加“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3)删去《民事诉讼法》第46章“财产保全”,而统一适用国内保全的相关规定。*参见邵明:《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之完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可见,这种小修小补的方式依然难以适应目前涉外民事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尤其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法院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等司法协助方面丝毫没有进步。
从学术界历次参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情况看,发出的声音主要来自民事诉讼法学界,中国国际私法学界的主动性不够、研究成果不多,这很不利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修改与完善。2011年10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系列研讨会议上,有学者提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可不设篇,一章即可;更有学者提出取消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放到相应篇章。2011年10月24日、2012年4月24日和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度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条款有减无增(除了增加电子送达方式外)。笔者在此呼吁相关学科、相关学界应联手起来,重视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修改和研究。
(二)恢复并完善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
从2012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来看,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管辖条款已从原有的4条(特别管辖、协议管辖、默示管辖和专属管辖)删减至2条(特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且删减后的条款一字未动。令人诧异的是,原有涉外民事诉讼默示管辖条款*原《民事诉讼法》第243条:“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国内民事诉讼程序第12章“第一审普通程序”第2节“审理前的准备”中可以找到痕迹,*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五、将第38条改为第126条,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但原有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则被删除。2012年修正《民事诉讼法》只在国内民事诉讼程序第2章“管辖”第2节“地域管辖”第34条规定了协议管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三、将第25条改为第34条,修改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相比之下,修改后的协议管辖条款扩大了适用范围,从“合同”扩大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该表述即原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适用范围的表述。但是,并未同时保留原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中的“实际联系”标准,而仍然沿用列举式的硬性要素标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的一般原则规定,*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该编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如果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当事人约定有选择法院协议的,法院应依据国内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条款来认定其效力,这不仅在认定条件上从原先的“实际联系”回到“硬性要素”,而且完全没有考虑选择法院协议在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中的不同。这既不利于为我国法院创造更好的对外司法环境,裁判更多具有真正国际性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性纠纷案件,也会因为生硬套用国内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条款,而忽视涉外合同或其他财产性纠纷案件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意图,从而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不仅要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协议管辖条款,而且应该更加规范,而不是简单地统一适用国内程序的协议管辖条款。一方面,在认定这种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上,应该借鉴海牙公约的规定,明确规定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如当事人无法律选择,则适用被选择法院地的法律。另一方面,在认定这种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判断因素上,应该借鉴《海事诉讼程序特别法》,既不规定“硬性要素”,也不规定“实际联系”,而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断;或者采用列举常见的“硬性要素”而不穷尽的方法。*这方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有所反映,该纪要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涉外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时,应该考虑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因素。总的精神要从宽把握,作有利于选择法院协议有效的规定或解释。同时,在立法技术上应取消仅仅规定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的单边做法,而应将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双边化,即规定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法院管辖。
因此,我国今后在修改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时,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有关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条款的司法解释时,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方案:第X条: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形式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法院管辖(或者)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国家法院管辖。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该协议选择的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合同中的选择法院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无效或者不存在,不影响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选择法院协议,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被选择法院所在地法律。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Examination on the Clause of Choice of Court in Foreign——Related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 A Perspective of Shandong Jufeng Network Case
Author&unit:DU Huanfang
(Faculty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Except statutory and discretionary jurisdiction, foreign-related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parties. As a special contract, th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is so independent that its validity is governed by the law chosen by the parties or by the law where the country of choice of court situated. Amendments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not only provide clause of the foreign-related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but also rule it more standardized, rather than simply apply provision of jurisdiction by agreement in domestic c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mak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more clear, and stipulate its legal effect, confirmative elements and choice of law.
foreign related judicial jurisdicti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effective elements; lex causae; civil procedure law
2014-04-28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修改理念与制度完善研究》(12BFX137)的阶段性成果。
杜焕芳(1976-),男,浙江上虞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私法。
D997
A
1009-8003(2014)04-009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