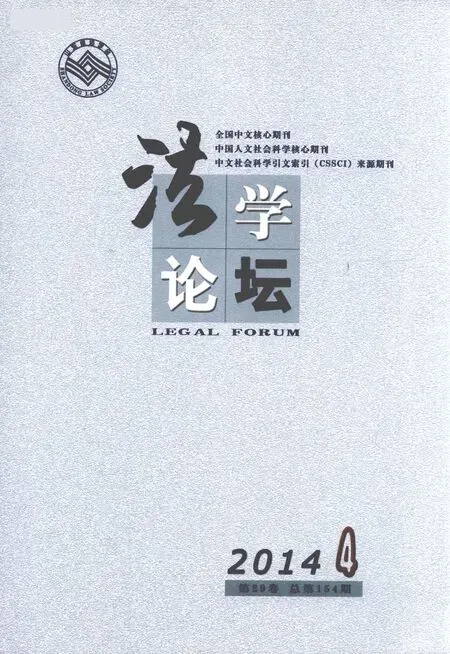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研究
2014-12-03马忆南
马忆南,罗 玲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法编辑室,北京 100871)
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研究
马忆南,罗 玲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法编辑室,北京 100871)
裁判离婚理由立法,深受一国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也反映了一国的婚姻文化和价值取向。近代以来,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经历了从有责主义到无责主义的发展过程。现代各国一般采破裂主义,在立法模式上多选择彻底的破裂主义,或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我国现行婚姻法通过概括加例示的方式规定了感情破裂的离婚理由,这种破裂主义离婚标准体现了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价值取向。但是,“关系破裂说”较之“感情破裂说”更科学,也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国现行裁判离婚理由的立法既要对我国优秀立法传统进行继承,也要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完善。
裁判离婚理由;破裂主义;立法建议
一、引言
裁判离婚理由可以说是“一国离婚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反映着该国离婚制度的立法宗旨和其所采取的立法主义”。*陈明侠、薛宁兰:《关于离婚自由与我国裁判离婚标准的几点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4期。裁判离婚理由扮演着多方面的角色:首先,从立法角度来看,裁判离婚理由是离婚法对是否准予离婚这一问题做出的法律规范,同时裁判离婚理由表明了立法者所认可的能够引起婚姻解除后果的法律事实,因此也被称为法定离婚理由;其次,裁判离婚理由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律依据;最后,从审判的角度来看,裁判离婚理由也是法官据以裁判解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唯一标准和依据。可以说,“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曹诗权:《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
而在婚姻法中对裁判离婚理由做出规定,这本身已经承认婚姻是可以解除的,体现了立法者对婚姻自由的尊重;另一方面,通过对离婚标准做出限定,避免了离婚的随意性,对稳定社会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外国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的发展
(一)裁判离婚理由立法主义的发展
近现代以来外国裁判离婚理由立法主义经历了从有责主义到无责主义的发展过程。
1、 有责主义。有责主义,也称过错主义,是指基于婚姻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准许离婚。1792年的法国离婚法准许一方提出合乎法定理由的离婚。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更是明确列举了可以诉请离婚的具体过错情形。*《拿破仑民法典》第229-232条规定:夫以妻通奸为理由,妻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实行姘度为理由,夫妻双方以他方对自己有重大暴行、虐待与侮辱为理由,夫妻双方以他方受名誉刑的宣告为理由,得诉请离婚。李浩培等译:《拿破仑民法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有责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婚姻的解除是基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的;二是过错一方的离婚自由受到限制。将过错引入婚姻关系中,符合当时社会将婚姻视为一种民事契约的观念。*1791年《法国宪法》第7条规定:法律只承认婚姻为民事契约关系。见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onstitution-de-1791.508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有责主义的立法较之前的禁止离婚主义和专权离婚主义是一个莫大的进步,它使当事人有机会从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并且离婚不再是丈夫的专权。
但是过错主义的立法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很显然的,这种立法模式“将离婚视为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不是失败婚姻的必然结果。”*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而且将离婚权作为无过错方的特权,这使得无过错方可以通过不离婚的方式来报复过错方,甚至要挟过错方,这将使过错方和无过错方都被困于已经死亡的婚姻中。而这种立法模式也决定了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无过错方必须证明对方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那就必须采取各种方式收集相关证据证明对方的过错(这种证据收集的过程极有可能侵犯他人隐私),这一立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证据而非婚姻本身成为法庭审判的核心。同时在庭审中,无过错方必须再次回顾对方的过错,再次面对曾经遭受的痛苦。这样一种互相揭发的审理过程使得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互相指责,发生争吵,甚至互相报复,这种将离婚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放在对立面的立法模式“有污染婚姻诉讼之嫌。同时还对子女会有不良影响”。*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2、 无责主义(破裂主义)。无责主义,是指非因当事人的主观原因,而是由于客观存在的、妨碍婚姻维系的事实致使婚姻无法维持而允许双方当事人离婚。例如一方有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一方失踪,分居达一定期限等。这些事项本身是不可归责于配偶任意一方的,但是由于这些事项本身使得婚姻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不再具备,对婚姻的继续维持造成妨碍,因此配偶一方得据此诉请离婚。
在无责主义发展初期,主要是通过列举方式对允许离婚的客观情形进行规定。而随着离婚法的发展,“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成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参见夏吟兰:《离婚自由与限制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破裂主义,现已成为世界各国离婚立法的基本趋势。破裂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不问离婚的具体事由,只要当事人诉请难以继续共同生活,法院确认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且不可挽救就可判决离婚。
破裂主义最早见于1907年《瑞士民法典》,该法典在例示性规定之外又于第142条概括性规定,因严重损害婚姻关系的事件,配偶双方均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共同生活时,配偶中的任何一方均可诉请离婚。这一规定被认为是“开现代破裂离婚主义之先河”。*陈苇:《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破裂主义”逐渐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并采纳。“此抽象的破裂主义之采用,不仅超越了法系,也超越了社会体制。”*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破裂主义”将关注点从婚姻中一方的道德问题转向婚姻本身维系的问题上,更为关注当事人婚姻的质量和婚姻存续的可能性,较“过错主义”而言,“破裂主义”并没有那么浓厚的道德色彩,法律在婚姻的当事人之间扮演中立的角色,并不进行道德评价。但“破裂主义”是抽象的,何为“婚姻关系破裂”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量度的标准,较之“过错主义”和列举式下的“无责主义”,没有具体标准的“破裂主义”给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无形中给离婚制度增添了随意性和轻率性。
(二)当代外国裁判离婚理由的主要立法模式
1、 彻底的破裂主义模式。在破裂主义的大趋势下,现行立法例中,主要有两种立法倾向:一是实行彻底的破裂主义。例如在德国,《关于改革婚姻法和家庭法的第一号法律》颁布后,自1977年起,在离婚原因上实行破裂原则,离婚不再以双方或一方的过错为要件。*参见曹艳芝:《德国离婚法的改革》,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6期。配偶双方的共同生活已不复存在且不能预期双方恢复共同生活的,即为婚姻破裂,可以诉请离婚。*《德国民法典》第1565条规定:婚姻已破裂的,可以离婚。配偶双方的共同生活已不复存在且不能预期双方恢复共同生活的,即为婚姻破裂。但德国离婚法的破裂主义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德国民法典》第1565条第2款继而规定:配偶双方分居未满1年的,仅在婚姻的延续由于另一方自身的原因而对于申请的一方会意味着苦不堪言的苛刻时,才能离婚。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而对于婚姻破裂的推定,德国是通过分居制度来实现的。*《德国民法典》第1566条规定:配偶双方1年以来分居且双方申请离婚或被申请的一方同意离婚的,不可辩驳地推定婚姻已破裂;配偶双方三年以来分居的,不可辩驳地推定婚姻已破裂。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英国采用的也是彻底的破裂主义的立法模式,并通过规定反省与考虑期的方式对婚姻关系破裂作出认定。*1996年《英国家庭法》对《离婚改革法》进行改革,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婚姻视为破裂: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做出声明,称该婚姻已经破裂;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作出声明的反省与考虑期已届满,而且提出离婚申请的申请人同时宣布:对婚姻破裂已经过反省且考虑了当事人对今后安排的要求,仍然认为婚姻无法维持。反省与考虑期为9个月,自法院收到声明之后的14天起算。详见《英国家庭法》,张雪忠等译,载中国法学会研究会:《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从上述立法例可以看出,彻底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下离婚的标准是唯一的、确定的,即婚姻确已破裂。但是这个标准显得相当抽象且不好把握,因此法律必须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为婚姻确已破裂作出量度,例如分居时间,或者反省与考虑期。通过这种量化的方式,使得法官可以直接得出婚姻是否破裂的结论从而作出是否准许离婚的判决。这种标准简单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易于掌握。同时离婚法设置的分居时间或者反省与考虑期也有利于帮助婚姻当事人理性地思考婚姻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避免盲目草率的离婚决定。但这种标准并不能将现实生活中所有婚姻解体的原因都涵盖进去,而这一原则本身也并不关注这些具体的婚姻破裂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不能在婚姻破裂的具体原因发生之后直接得出婚姻破裂的结论,当事人可能必须继续维持已经死亡的婚姻以达到可以离婚的分居时间或反省与考虑期。当事人的痛苦并不能得到立即的解除,而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从死亡的婚姻中走出去。
2、 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的模式。第二种立法倾向是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例如法国,《法国民法典》规定了三种不同情形:夫妻双方相互同意离婚;共同生活破裂;因有过错。*《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因共同生活破裂而离婚的情形同德国法,是根据分居时间来判断的,如夫妻事实上分开生活已达六年,一方配偶得以共同生活持续中断而请求离婚。因过错而离婚是指夫妻一方,因另一方反复地或者严重地违反婚姻权利与义务的事实,致使夫妻共同生活不能忍受时,得请求离婚。它适用于通奸、拒绝同居、严重侮辱、严重干涉对方宗教自由、变性等情形。参见《法国民法典》(上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27页。应当注意到的是,法国法定离婚理由中的过错并不像早期的过错主义一样有那么浓重的道德色彩,或者说并不只关注于夫妻之间是否忠贞。这里的过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是指过错方的行为是否已经反复或严重地违反婚姻权利与义务,致使夫妻共同生活不能忍受。*例如法国都埃法院1984年的判决就认为夫妻一方极其频繁地从事工会活动,长期不归家,也可以构成这种对婚姻义务的严重的或者反复的违反。参见《法国民法典》(上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日本民法在这一问题上也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日本民法将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裁判离婚。对于裁判离婚,《日本民法》第770条列举了五种情形,分别是配偶有不贞行为;被配偶恶意遗弃;配偶生死不明达三年以上;配偶患强度精神病且无康复希望;其他难以继续婚姻的重大事由。同时日本民法强调即使存在前四种事由,但法院考虑有关情况,认为继续婚姻为相当时,可以驳回离婚请求。参见《日本民法》,曹为、王书江译,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日本民法》其后虽有修改,但这一条文并无变动,见http://www.houko.com/00/01/M29/08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
从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的立法例来看,立法的方式并不统一,例如法国法采取的是概括立法模式,而日本法则采取例示性立法模式。而对于具体如何认定婚姻破裂,以及将何种情形归为一方配偶的过错,由于文化和观念不同也不一样。这种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的立法模式给诉请离婚的婚姻当事人提供了多样化的救济途径,同时他们也可以无须经过漫长的分居或考虑期就可以获得判决。另一方面法官也获得了更多的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判断婚姻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继而判断是否应当准许离婚,而不仅仅是根据分居时间的长短机械地断定是否同意当事人的请求。从法国法和日本法的规定也可以看出,显然过错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在与破裂主义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剥离了早期浓重的道德特别是性道德色彩,现在立法中规定的过错情形更多的是一种证据,法官需要据此来判断当事人的共同生活是否真的难以维持,不能忍受,而不是机械地认为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判决离婚。但如前所述,它并不能摆脱过错主义的一些问题,例如给原告巨大的证据压力,又如原被告之间的对抗性。
三、我国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的发展
清朝末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关于离婚的规定深受1898年《日本民法典》*参见《日本民法》,曹为、王书江译,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的影响,开始从有责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婚姻的解体问题。*大清民律草案第1362条。参见《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杨立新点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该草案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开始逐渐将关注点放到了过错上,因夫妻一方有某种法律上的过错而准许离婚;同时受宗法社会传统的影响,也兼顾了家族主义下婚姻的目的性。但是,该草案虽然同时赋予了夫妻提起离婚的权利,但是在对夫妻的性道德要求上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
中华民国的民法*民国民律草案第1052条。参见《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杨立新点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延续了大清民律草案以有责主义为主,兼顾目的主义的做法。但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该法不再将家族视为婚姻的目的,而是将婚姻本身作为目的,即因某种情势婚姻本身难以为继而准许离异。同时,该法“从形式上剔除了古代法定离婚理由中丈夫专权的规定,夫妻双方在主张离婚的理由上基本一致,不因性别而存在差异,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离婚理由对夫妻双方规定不一致的做法,消除了对男女两性在性道德方面的双重标准。”*许莉:《〈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裁判离婚理由及立法论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法律并不完善。1950年《婚姻法》第17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一规定彻底抛弃了限制离婚主义的观点,采取自由离婚主义,并赋予夫妻双方平等的离婚权利。而这一点也为之后的立法所承袭。“但另一方面,该法并未对裁判离婚理由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离婚理由的问题,一直存在‘正当理由论’和‘感情论’的争论。”*马忆南:《二十世纪之中国婚姻家庭法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感情论”一方认为法院判决离婚应当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标准。而“正当理由论”则认为只有存在“正当理由”法院才应当准许离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离婚的正当理由大多是一方政治或思想意识上的严重错误。但当时的学者认为应当“反对满足因资产阶级思想而提出的离婚请求。凡一方严重破坏共产主义道德,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或有其他违法犯罪等行为,使夫妻关系恶化以致对方据此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与满足这种正义要求。如果有罪过的一方提出离婚,这时有决定意义的是对方的态度。”参见刘云祥:《关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当前的离婚问题——与幽桐同志商榷》,载《法学》1958年第3期,第55-58页。
1980年制定的新《婚姻法》结束了“正当理由说”和“感情说”的争论,采取了“感情破裂说”的观点。*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但关于离婚理由问题的争论并未平息,一场“感情破裂说”和“关系破裂说”之间的争论甚嚣尘上,延续至今。
持“感情破裂说”的学者,“主要还是从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提出的‘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里找根据。”*马忆南:《中国法上判决离婚理由的理论与实践》,载《法政理论》(日本)2006年第1期。认为“如果在‘感情破裂’之外再加入其他条件,实际上是把感情因素挤到了极为次要的地位,而将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由‘感情破裂’改变为‘婚姻关系破裂’则正是这种表现之一。”*肖雪慧:《反对在“感情破裂”之外附加离婚条件》,载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5页。
而持“关系破裂说”的学者们则认为,感情破裂说存在固有的不足之处:第一,法律不能对夫妻感情直接进行调整,法律只可能对已经存在的婚姻关系进行调整;第二,夫妻感情是十分主观的,而且具有极强的私密性,法官难以捉摸,会导致离婚审判的随意和不统一;第三,感情并不是婚姻生活的全部,也不是离异的唯一理由;第四,“感情确已破裂”这一标准以夫妻感情为前提,但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必然满足。同时从司法实践看,因婚姻的基本功能和目的难以实现而非感情破裂而判决离婚的情况长期存在,如因一方失踪而判决离婚的。*参见曹诗权:《裁判离婚标准的评价与选择》,载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6页。
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之时,“关系破裂说”的学者主张应当将判决离婚的理由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但是这一观点并未被有关立法部门接受。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仍以“感情破裂”作为裁判离婚的法定理由。
(二)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裁判离婚理由
现行《婚姻法》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概括性地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应准予离婚,这是“感情破裂说”在法律上的体现,也是符合当今世界离婚立法主义的主流趋势的。婚姻的双方当事人若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关系难以为继,即可以提出离婚,而不需要受其他条件的限制。当事人双方都享有诉请离婚的权利,这也是婚姻自由的一种保障。而对法官来说,只需要判断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其婚姻关系是否难以维持,即可判断是否准许双方当事人离婚。只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应当准许离婚,而并非是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才准许离婚。婚姻自由在这里得到了绝对的尊重。
二是,这一条文通过例示性的规定举出了属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几种情形。*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同时通过例示性规定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一规定渊源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该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可以被“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时,选择了其中4种情形上升为法律成为婚姻法中的例示性情形。
从这种例示性情形的选择上,首先可以看出立法者并不倾向于将一些导致婚姻难以维系的纯粹客观的障碍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司法解释中诸如一方患有精神病、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等客观情形并未被列入2001年婚姻法,而仅仅保留了一方被宣告失踪这一种情形。其次,这种例示性情形的选择体现了一种向过错主义回归的倾向。除兜底条款外,我国现行《婚姻法》列举的四项可以被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里,有三种都属于一方有过错的情形,而只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这一款是典型的破裂主义的规定。
将2001年婚姻法中的法定离婚理由与1980年婚姻法中的法定离婚理由对比可以发现,裁判离婚标准仍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离婚理由的立法理念则从彻底的破裂主义向兼采过错主义和破裂主义倾斜,而立法模式也从概括式改为概括规定加例示情形。
四、我国裁判离婚理由立法展望
(一) 未来裁判离婚理由的立法模式
法律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的目的,也体现了立法者所希望引导的价值观念。而离婚法作为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受一国或地区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裁判离婚理由体现了我国的立法宗旨,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同时深受我国文化习俗的影响。
那么,在裁判离婚的立法模式上究竟是采用过错主义还是破裂主义,在破裂主义里是采“感情破裂说”还是采“婚姻关系破裂说”,首先要注意的是所采纳的立法模式是否与我国离婚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思想相符,是否体现了我国在离婚立法上的价值取向。
1、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新中国离婚立法的核心思想。*“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婚姻法起,到现行的2001年《婚姻法》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早在1950年,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就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阐述。详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载张培田:《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3-919页。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婚姻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爱情,以永久生活为目的而合法结合。婚姻需要夫妻之间相互扶持协力。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消亡,共同生活难以为继,强行维持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无论是对当事人而言还是对家庭、社会而言都是不利的。法律必须提供一种途径使当事人从这种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保障离婚自由,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维护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同时保障离婚自由也意味着离婚并不是一种专权。离婚不应当成为婚姻一方当事人的特权,更不应当成为一方当事人压制报复另一方的武器。婚姻的双方当事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离婚权。“夫妻任何一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有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均可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离婚。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是现代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杨大文:《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制定之时,“离婚自由”已经成为我国婚姻法所保障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1950年婚姻法制定之时,起草者们已经将之定义为是一部“根本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也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的婚姻法”。*邓颖超于1950年5月14日在中国张家口市委、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为学习1950年《婚姻法》召开的扩大干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它所保障的离婚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婚姻法“在文字上很漂亮地写着”*邓颖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的“婚姻自由”,而是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男女任何一方均可以平等主张的离婚自由。而在现行《婚姻法》修改颁布之际,立法者也强调“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和不结婚自由。”*阎军、吴坤:《修改婚姻法焦点问题诠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等答记者问》,载《吉林人大》2001年第7期。
但是保障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对离婚自由毫无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的限制,是离婚自由衡平机制中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种限制是法律为了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实现,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所设立的。”*夏吟兰:《离婚衡平机制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近年来,“闪婚”、“闪离”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负责任的“速食婚姻”态度在社会蔓延。轻率、肆意地处理离婚问题,不仅是对自己、对家庭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也可能扰乱家庭和社会秩序。因为离婚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关系的终止,还伴随着财产问题、子女问题等等。法律不能任由婚姻当事人自主、轻率地决定婚姻的存续,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规制离婚自由。
但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除了“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外,“稳固婚姻关系”也应当是我国离婚法的价值取向。英国法律委员会在1966年的有关离婚理由改革的报告Reform of the grounds of divorce: the field of choice里写到,一部好的离婚法应该实现的目标是:巩固而非破坏婚姻的稳定性,而当一段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时,其徒有的法律外衣应当在最大的公平和最小的怨恨、悲痛和羞耻中被摧毁。同时表示良好的婚姻法应该能够确保离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而使当事人努力地维系婚姻的成功,特别是,克服暂时的困难。*Reform of the Grounds of Divorce: the Field of Choice (1966, Law Com. No.6), The Law Commission of UK, Paras. 15 and 16. See http://www.worldlii.org/ew/other/EWLC/1966/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该法律委员会在1990年关于离婚理由的法律文件The Ground for Divorce中同样将挽救未破裂的婚姻关系作为离婚法的第一目标。*The Ground for Divorce (1990, Law Com. No.192),The Law Commission of UK, p.10. See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hc8990/hc06/0636/0636.pdf.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已经死亡的婚姻应当被埋葬,但是尚未死亡的婚姻是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挽救的,法律应当鼓励夫妻为挽救未死亡的婚姻而做出的努力,这种鼓励包括程序上的和实体法上的。例如在程序上设置调解制度就是对这种和好行为的鼓励。而在实体法上,离婚理由的设定也应当反映立法者的这一价值取向。
2、立法模式的选择。从“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角度看,破裂主义的离婚立法模式是符合我国离婚立法的中心思想的。在破裂主义之下,倘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共同生活难以维持,且不可挽回,那么婚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诉请离婚,而法院也应据此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而在法官对离婚案件做出裁判时,法官应该审慎地了解夫妻婚姻关系的现状,只有当婚姻是无可挽回地破灭时,才能判决离婚。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婚姻的解体是因为一方的过错导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过错主义就是合适的。如前所述,彻底的过错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诉请离婚只能由无过错方提出,当离婚成为了无过错方的专权,离婚自由就很难得到保障。
“破裂”一词也意味着法律对未彻底破裂、未死亡的婚姻持支持、维护的态度,即便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一方可能存在过错,或者由于一些客观情势的影响,婚姻关系的关系存在困难,但是法律仍然鼓励双方当事人为克服这些困难做出努力,为维系婚姻关系做出努力。
而在我国,在坚持破裂主义立法模式之下,是选择“感情破裂说”还是“关系破裂说”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作者看来,“感情破裂说”反映了婚姻解体的主观方面的原因,但是正如“关系破裂说”所坚持的一样,感情毕竟是属于婚姻当事人之间的主观心理状态,法官只能通过外部迹象来判断而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当事人隐秘的心理活动,让法官通过主观臆断来裁判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合适;另一方面,婚姻解体所关系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感情,还关系到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中所确立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法官并不能裁断当事人感情的有无,而只能通过法律来判断婚姻这种民事关系是否应当被解除。从逻辑上来说,“关系破裂说”较之“感情破裂说”更为严谨科学。
在2001年修改之时,新婚姻法的制定者对这一问题曾经做出过回应,认为在离婚条件上,2001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实质条件跟1980年婚姻法的精神、原则、条件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变化。”*阎军、吴坤:《修改婚姻法焦点问题诠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等答记者问》,载《吉林人大》2001年第7期。虽然当时的立法者认为在裁判离婚理由问题上2001年婚姻法规定的“感情破裂”标准是承袭1980年婚姻法而来的,但从我国《婚姻法》修改的历史来看,1980年婚姻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裁判离婚标准实则是一种偶然。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裁判离婚标准问题上就存在着“正当理由论”和“感情论”的争辩,但当时“正当理由论”实际上是司法审判的指导。*1950年陈绍禹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便对正当理由论进行了肯定并加以阐述,同年法制委员会在《关于婚姻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肯定了这一标准。而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吉林省磐石县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更是重申了这一标准。详见金眉:《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2页。直到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加入“感情完全破裂”的规定与“正当理由”一起作为法定离婚标准。而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则明确将“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和能否恢复和好”作为裁判离婚标准。从这一规定看,采用的是“关系破裂说”。但1980年婚姻法却又采用了“感情破裂说”。结合当时我国的社会现状和法律研究情况,可以看出,1980年婚姻法的立法者们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该法的法定离婚理由,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感情破裂说”优于“关系破裂说”,实则是一种立法的偶然选择。
笔者了解到,在大多数离婚案件中,法官是不可能探寻到原被告双方感情的真实状况以及对婚姻关系维系的真实态度的,而只能从原被告在庭审时的陈述、原被告在矛盾发生后的举动等客观情状来做出判断。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坚称“感情破裂”是裁判离婚标准,但是法官的逻辑思路上却是从客观层面出发,考虑夫妻关系的现状,夫妻对婚姻关系维系的态度,从而对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做出判断,这一推断本身均是基于客观情况做出的,而并不是对双方隐秘的内心感情活动的判断。因此与其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所采的是“感情破裂说”,不如说是“关系破裂说”。
(二)未来裁判离婚理由的立法内容
1、 现行规定的优点。1980年《婚姻法》采用的是概括性规定,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采用的是概括规定加例示情形的立法模式。如前所述,这两种立法模式在域外立法中都有适用。域外立法例中采用概括性规定的如德国、英国,一般会相应规定一定的分居时间或考虑期作为可量度的标准,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抽象的“破裂”用具体的方式确定下来。可以认为,如果经过漫长的考虑期或者分居期,婚姻当事人仍然认为共同生活难以继续,无法挽回,那么可以确定婚姻确实已经破裂,将婚姻当事人囿于死亡的婚姻中并无意义。这种考虑期或分居期的设置可以避免草率、随性的离异,同时也证明了婚姻破裂的事实。而在采取概括加例示规定的国家,例示情形一般都是配偶一方的严重的会危及夫妻感情的过错或者是某种客观的危及婚姻继续存续的情形,这种例示情形本身往往就说明了婚姻破裂的原因,法官可以根据例示情形发生与否来判断婚姻是否已经破裂。
1980年《婚姻法》采用的是概括性规定,该法只抽象地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但是如何认定感情确已破裂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判断感情是否破裂全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的可操作空间太大,标准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而相较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则通过例示情形列举了一些可能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更具有可操作性。
可以说我国1980年《婚姻法》采用的是无因破裂的立法模式,即不问离婚原因如何,只要审判人员认为婚姻破裂就可判决离婚,而2001年《婚姻法》更类似一种有因破裂的立法模式,即当事人需要提出充分的或法定的离婚原因来确证婚姻已经破裂。“有因破裂制度可以使婚姻当事人和法庭都能注意到离婚的道德合理性,这有利于控制那些轻率的离异和不道德意图的实现。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作为判定婚姻破裂的客观标准,也授予了审判人员一个明确的、可资遵循的法律界限,便于执行,又可以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张思沛:《离婚理由的比较分析》,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1期。《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感情破裂的具体标准,但其所规定的例示情形实际上给司法审判人员划定了判断的标准,当原被告的之间的状态达到例示情形规定的相似程度时,可以推定原被告的感情确已破裂。
另外,抽象的概括规定的立法模式中一般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分居期或考虑期来判断婚姻是否破裂无法挽救,因此当事人往往并不能立即得到救济。而例示性规定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如果发生了例示性情形,法官可以据此来判断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感情是否破裂,立即使当事人从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而并不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分居时间或考虑期才能确定。
2、 现行规定的不足:
(1)裁判标准过于模糊,不可预期。虽然笔者认为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更类似于一种有因破裂的离婚立法模式,但正如前所述,在立法者看来,2001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实质条件跟1980年婚姻法的精神、原则、条件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变化。”*阎军、吴坤:《修改婚姻法焦点问题诠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等答记者问》,载《吉林人大》2001年第7期。也即是说2001年《婚姻法》所坚持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该法规定的例示情形只是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划定了一个衡量标准,只是列举了几种可以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示例。但是从前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原告并不是依据《婚姻法》所规定的具体情形来起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需要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对夫妻感情的现状作出评判。而“夫妻感情”毕竟是非常主观的,法官也只能根据外部情状对“夫妻关系”作出判断,而无法对“夫妻感情”作出判断。法律规定的标准过于含糊,那么司法判决的随意性就难以避免。而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感情破裂”这一非常主观的标准使当事人难于对法官的司法活动做出准确的预期,当事人也无法为自己的诉讼活动做出努力,一个人要如何证明自己的感情呢?这样的司法活动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完全不可预测的。
(2)裁判标准不协调、不统一。“我国离婚标准的规范形式与内容和效力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和整合。”*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现行《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具体的例示情形,但《婚姻法》规定的唯一的法定离婚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例示情形只能作为婚姻破裂的证据来加以证明,而不是说只要存在例示情形,法官就可以断定夫妻感情破裂。在这种概括加例示规定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共同生活难以继续才是离婚的裁判标准,而不能将例示情形作为裁判的标准,否则,适用的就是过错主义而不是破裂主义。而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是只要有所述情形之一,调解无效,就可以推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这种立法语言留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法律规定的例示情形就是离婚原因,只要发生了这一情形,法院就可以据此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这与我国坚持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不相融合。
同时我国现行《婚姻法》在第32条第3款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一规定与第2款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裁判离婚标准是并列的,但是很显然,一方被宣告失踪并不表示夫妻感情破裂,而只能说明夫妻关系难以维系,无法再维持共同生活,夫妻关系破裂。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立法者坚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裁判离婚的唯一标准,而事实上,在同一条文中,在同样的裁判离婚的情况下,该法采用了“感情破裂”和“关系破裂”两种判断标准,这其实也从侧面说明该法采用“感情破裂说”并不是基于非常审慎的考虑做出的。
(3)例示情形的选择不科学。如前所述,例示情形其实给审判法官划定了一个参考标准,即原被告之间的婚姻状态达到例示情形所描述的程度时,可以据此对夫妻感情状况作出推定。但从我国现行《婚姻法》所选取的例示情形来看,一则多数例示情形有着浓重的过错主义色彩,二则例示情形规定的情况并不符合离婚案件的实际情形。
首先,该法所规定的例示情形将关注点主要放在婚姻的过错方,特别是过错方的道德品质问题上,而非感情破裂的问题上。虽然说我国法定离婚理由采取的是破裂原则,但是通过这种例示规定,法律无意中扮演了道德评判的角色,根据例示规定作出的离婚判决,往往直接将婚姻的一方定位为过错方。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例示规定应当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人现阶段离婚诉讼的实际情况,应当是现阶段中国民众在诉请离婚时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情形。但实际上,现行《婚姻法》所例示出来的离婚理由,并不能代表现阶段中国民众诉请离婚的常态。笔者的调查显示,在2002年山东省烟台市13个基层法院审理的2884起离婚案件中,被法院认定为重婚的只有1起,认定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为3起,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只有36起。这个比例与这三种情形在我国立法上的重要地位并不吻合。而大多数当事人诉请离婚的理由是“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无法共同生活”。*马忆南:《婚姻法第32条实证分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卷。而2010年,学者们分别对哈尔滨、上海、北京三地法院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件进行调研的结果也显示,三地区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不断;二是性格不合,没有共同语言;三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四是酗酒、赌博、吸毒等恶习;五是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六是不思进取,好吃懒做,对家庭不负责任。*参见司丹:《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社会性别分析》,载《学术交流》2011年第9期。
从上述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婚姻法》所选择的例示情形并不能代表现阶段中国民众诉请离婚的通常情形。而且在立法中作出这种例示规定可能会误导民众,让人产生社会道德败坏的感受。从2001年《婚姻法》修订前后的一些情况来看,当时《婚姻法》选择这些情形加以规定是根据全国妇联、广东和上海等地的情况作出的,*参见胡康生:《修改完善婚姻法需要研究的六大问题》,载《法制日报》2000年7月13日。并不能代表全国普遍情形。类似的例示情形并不独我国有此规定,但是在域外立法例中,这种过错情形通常是作为法定离婚理由直接规定的,也即是说法官并不需要据此情形推定出夫妻感情破裂再判决准予离婚,而是可以根据这一情形本身直接判决准予离婚。这便是我国离婚法中例示情形与域外立法的主要不同。在我国离婚法中,例示情形是作为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衡量标准出现的,它给法官设定了一种心理预期,即只有达到例示情形所规定的程度才可以推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实际上是增加了离婚的难度,也增加了原告的证明压力。
(4)分居标准的限定过于含糊。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2002年笔者在对烟台法院的调查中显示在2884起离婚案件中以该项请求离婚的为732起,其中有387起是第二次起诉离婚,而在这732起案件中,只有413起分居达二年以上。这说明,分居尚未成为中国人证明夫妻感情破裂或夫妻关系破裂的重要证据。*参见马忆南:《婚姻法第32条实证分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卷。而在2010年学者们对三地法院的调查中,分居已经成为离婚理由的第三主要事项。*参见司丹:《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社会性别分析》,载《学术交流》2011年第9期。这说明修改后的《婚姻法》被更多民众所了解适用。
而在将分居作为主要的法定离婚理由规定的国家,往往会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1567条规定:“(1)在配偶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家庭的共同生活且可看出一方因拒绝过婚姻的共同生活而不欲恢复家庭的共同生活的,配偶双方即为分居。即使配偶双方在婚姻住宅内分居,家庭的共同生活也不复存在。(2)配偶双方为和好而短暂地共同生活,并不使第1566条所规定的期间中断或停止。”*《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但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分居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没有规定分居的含义,分居时间的计算,分居的中断等等,这会使法官的判断产生很强的随意性。有学者对分居这一问题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分居实质标准的理解不一,对分居起算时间的认定标准也不相同。*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许春彬:《分居认定标准研究——以2009—2010年河南省部分基层法院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增加了原告的举证压力。这种举证压力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是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标准过于主观、过于含糊。我国法定离婚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但是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认定感情破裂的标准,这就使得原告无从收集证据,而这一标准的含糊也使得法官很难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夫妻感情是否已经破裂,因为他们无法从原告的证据中找出能反映他们内心感情活动的例证抑或具体的符合法律例示情形的情状。因此,大部分的法官在无法做出确定判断时,只能通过认定“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或“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来做出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其次,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例示情形过于严苛。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例示情形给“感情破裂”界定了一个很高的判断标准,这无形中就加大了原告的证明难度,原告必须提出非常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夫妻感情的破裂程度已经达到与例示情形相仿的程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
(6)缺乏对特殊情况的明确规定。与域外立法相比,我国离婚立法并未规定破裂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指虽然一方存在过错行为,但婚姻存续期间,另一方当事人已经对配偶的这种行为表示了原谅、宽恕,或者这种过错行为本身就是在另一方配偶的默许、同意下进行时,法官不能根据这种情形就认定婚姻确已破裂。例如《加拿大离婚法》第11条规定,法院应当确信原告并未事先对被告的行为表示默许或在事后表示宽恕,否则,应当驳回原告的离婚申请,但是,法院认为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应当准许离婚的除外。*Divorce Act of Canada (1985), Article 11(c), see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D-3.4/.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这一例外规定总体来说与我国的立法架构并不太契合,我国无论是民事法律还是刑事法律中关于宽恕、原谅的立法都不成熟,在婚姻法中进行这样的规定并不合适。而且,这种规定也并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而另一种例外情形是,虽然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认定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但为了维护当事人一方、家庭、未成年子女等的利益,而判决不准离婚。
这一点在德、日民法中都有体现,例如《日本民法》规定即使存在前四种事由,但法院考虑有关情况,认为继续婚姻为相当时,可以驳回离婚请求。*参见《日本民法》,曹为、王书江译,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日本民法其后虽有修改,但这一条文并无变动,见http://www.houko.com/00/01/M29/08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18日。而《德国民法典》第1568条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拒绝离婚一方的利益考虑,也相应规定了苛刻条款。*《德国民法典》第1568条规定:“为婚生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如果且只要由于特殊原因而例外地有必要维持婚姻,或者,如果且只要离婚基于非正常情况而对于拒绝离婚的被申请人会意味着较为严峻的苛刻,以至在考虑到申请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也显得例外地有必要维持婚姻的,即使婚姻已破裂,也不应该离婚。”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页。
这是因为,婚姻缔结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婚姻不仅仅是夫妻双方之间的感情问题,还关系到子女问题、财产问题等等,离婚会对已经形成并确立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产生巨大的变化,倘若这种变动明显地会影响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例如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时,法律就需要对它进行干涉。这种例外规定对我国离婚法来说有可资借鉴之处,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有的规定也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取向,例如对现役军人的配偶的离婚权的限制*《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是对军人婚姻权利的保护;而在女方处于怀孕、分娩或中止妊娠等特殊情况下,对男方离婚权进行限制的规定*《婚姻法》第34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则是从保护妇女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五、结语
在笔者看来,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裁判离婚理由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前所述,作者认为,无论是从法律逻辑来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关系破裂说”较之“感情破裂说”更具可操作性,更客观,也更可预期。
从“关系破裂说”的角度来看,当配偶双方的共同生活已不复存在且不能预期双方恢复共同生活的,即可认定为婚姻关系破裂,应当判决准予离婚。这意味着,从夫妻关系的现状来看,配偶双方已不在维系共同生活,而从夫妻关系的未来来看,并不能预期双方能恢复共同生活。
那么如何对“关系破裂”这一标准进行具体限定呢?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分居期加兜底条款的方式加以规定,即:首先,规定当夫妻之间分居达到一定时间时,可以认定婚姻关系破裂。这有两点优势:一是标准明确,易于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需要考虑分居这一情况即可做出判决,而这一情况本身又是十分客观的、可量化的标准;二是分居期的设定其实也给婚姻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和好的机会,使双方在矛盾发生之后能有时间来冷静思考,而不是冲动、轻率地诉请离婚。倘若双方经过分居期仍没能修复婚姻关系,那么也表明“不能预期双方恢复共同生活”,婚姻关系彻底破裂。但倘若要采纳分居期的规定,也就意味着法律应该同步对分居的实质标准、分居时间的计算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其次,笔者认为在分居期的规定之外,还应当加入一条兜底条款,以保证在配偶一方或双方的行为反复或严重地损害婚姻关系,违反夫妻间权利与义务,致使共同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配偶一方可以诉请离婚来解除婚姻关系,而无须经过漫长的分居期。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那些矛盾非常严重的当事人而言的,例如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迟到的”判决其实是对他们权利的侵害。
从“维护婚姻关系”的立法价值出发,笔者认为,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中应当体现法律是鼓励双方当事人为挽救尚未死亡的婚姻做出努力的。因此在法定离婚理由中,应该表明法律支持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来缓和、解决双方的纠纷矛盾,为挽救婚姻关系或者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做出努力。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A Study on the Legal Grounds for Divorce
Author&unit:MA Yinan1,LUO Ling2
(1.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2.Peking University Press,Beijing 100871,China)
The legal grounds for divorce is not only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conception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untry’s matrimonial cul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In modern times, the legal grounds for divorce has developed from fault principle to no-fault principle. Irrevocable marital breakdown of marriage is mostly adopted in modern countries. Some countries provide marital breakdown as the sole ground for divorce, while some other countries also recognize fault-based divorce. Marriage Law of PRC provides “mutual affection no longer exists” as the sole ground for divorce through general and instantiated rules.The legal grounds for divorce in Marriage Law of PRC reflect the legislators’ value orientation that the freedom of divorce should be guaranteed and a rash divorce oppose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doctrine of marital breakdown is more scientific than that of breakdown of mutual affection and more practical in the justice practice of China. Therefore, the author further puts forward somelegislative proposals.
legal grounds for divorce; marital breakdow;nlegislative proposals
2014-06-06
马忆南(1961-),女,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法学;罗玲(1989-),女,安徽安庆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法编辑室编辑,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D923.9
A
1009-8003(2014)04-00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