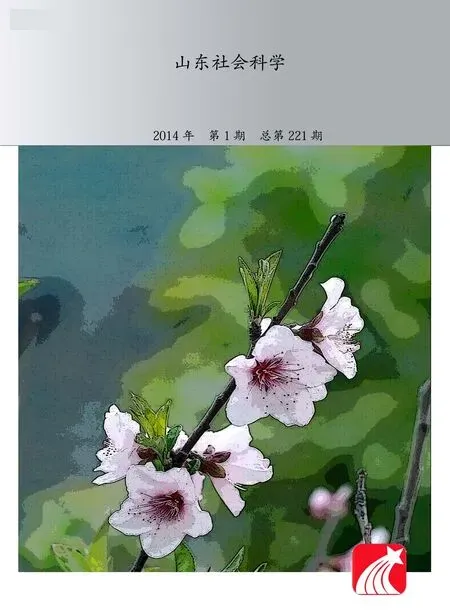诗僧惠休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2014-12-03王树平包得义
王树平 包得义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据敦煌文献和学人相关研究成果可知,敦煌佛教高僧释悟真于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奉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命,以使团中佛教界代表的身份至长安觐见唐宣宗。整个使团在京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悟真也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在此期间,悟真与两街名僧大德及诸朝官有诗歌赠答,敦煌遗书S.4654中就保存了这些京城大德所作的几首赠诗,前贤已有校录。[注]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55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其中一首由“左街保寿寺内供奉讲论大德景导”创作的《赠沙洲悟真上人兼送师》的诗歌中有云:“经讲三乘鹙子辩,诗吟五字惠休才。”乃是作者称赞悟真深解佛理,辩才无碍,同时又善于写诗,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之辞。“诗吟五字惠休才”一句中,作者以惠休来比拟悟真,于是一系列疑问便产生了:惠休是何人?其有何特殊之处?为何以惠休来指称悟真?笔者以这些问题为起点,结合前贤研究成果,展开相关论述,望有助于治敦煌文学和佛教文学者。
一、惠休生平
惠休即南朝刘宋时期的释惠休。[注]惠休,亦有作“慧休”者。行文中一律作“惠休”,征引的文献中则保持原貌。其生平事迹僧传中不见记载,史籍中略有提及。《宋书·徐湛之传》中记其行止云:“(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徐湛之)……出为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善于为政,威惠并行。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注][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7页。这是论惠休者最常引用的文献。[注]《南史·徐羡之传》中亦有相似记载,内容更简。据此,我们仅知释惠休俗姓汤,擅长作文,辞采绮丽,尝参与徐湛之发起的文士集会;后奉宋武帝敕命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除了这些粗线条的勾勒外,我们难有所获。
而冯惟讷《诗纪》中惠休小传云“惠休字茂远,位至扬州刺史”,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袭用。有学者指出:“字茂远之说不见他书,但当有据而非虚构。‘扬州刺史’下显脱‘从事史’三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小传袭之而未核,误同。”[注]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7页。显然,已有学者对现存文献中有关惠休的字号及其还俗后的官职的记载存有疑问。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围绕以下问题对惠休生平事迹重新考述。
关于惠休字号的出典。惠休“字茂远”之说确实有据,并非“不见他书”。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上《俗学无裨录·宋彭城寺慧琳毁法被流目盲事(慧休附)》中记载惠休事迹较详:“慧休,字茂远,俗姓汤,住长干寺。流宕倜傥,嗜酒好色,轻释侣,慕俗意。秉笔造牍,文辞斐然,非直黑衣吞音,亦是世上杜口。于是名誉顿上,才锋挺出,清艳之美,有逾古歌,流转入东,皆良咏纸贵,赏叹绝伦。自以微贱,不欲罢道。当时有清贤胜流,皆共赏爱之。至宋世祖孝武,始敕令还俗,补扬州文学从事。意气既高,甚有惭愧。会出补勾容令,不得意而卒。出沈约《宋书》。”[注][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51册,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809页。释怀信谓此段内容出自沈约《宋书》,然今本《宋书》无此内容。然其比《宋书·徐湛之传》中的内容详实得多。除说惠休俗姓汤外,还明确交代其字茂远,住长干寺。至此,学者“字茂远之说不见他书”之惑可得解除。而且,文献还交代惠休生性倜傥放荡,嗜酒好色,戒行不严。又爱好写作,文辞斐然,其作品“清艳之美有逾古歌”,一经写出,便广为流传,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以致当时清贤胜流“皆共赏爱之”,突出了惠休诗作曾风靡一时。
关于惠休还俗之因及大致时间。据前揭《释门自镜录》材料可知,惠休虽有慕俗之意,自己却“不欲罢道”,而是奉敕还俗,事出无奈。《宋书·夷蛮传》载宋武帝于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下诏沙汰沙门:“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注][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6-2387页。宋武帝《沙汰僧徒诏》亦见载于《初学记》卷二三、《广弘明集》卷二四,唯个别文字略有出入。虽然“此制竟不能行”,但作为一个“自非戒行精苦”的僧人,惠休很有可能于此时被敕令还俗。倘若此推论成立,则惠休还俗的时间大约在大明二年或者稍后。
《宋书》中记载孝武帝下达沙汰诏书并敕令惠休还俗的原因尚有所隐晦,但唐释神清《北山录》卷九《异学》中的记载则要具体得多:复有狂狷之夫,弃乎本教,聊览坟索,游行内侮,若豕负涂,洁则忌之。(其有辞亲慕道,割爱为僧,而不知励己进修,全弃教典,专心外习,吟咏风骚,而于本教反生轻侮,故我高德顾之,忌如秽物……)如宋慧琳、慧休之流也……慧休为文,名冠上才。嗜酒色,无仪法。孝武以其污沙门行,诏勒还俗,补扬州文学从事,患不得志,终于句容令焉。 (括号内文字为释慧宝所作注文——笔者注)[注][唐]释神清:《北山录》,《大正藏》第5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629页。正是由于惠休“专心外习,吟咏风骚,而于本教反生轻侮”,且嗜酒好色,戒行不精,无僧人仪法,故而被宋武帝认为有污沙门仪范,敕令其还俗。总之,在刘宋时期,有些僧徒溺于流俗,不能遵奉戒行,甚或参与军事谋反,危及朝廷统治,故统治者对僧侣严加科禁,进行沙汰。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本身戒行不严、嗜酒好色的惠休被敕命还俗在所难免。
关于惠休还俗后的官职。对于冯惟讷《诗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惠休“位至扬州刺史”之说,有学者指出“扬州刺史”下显脱“从事史”三字。[注]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7页。对于惠休还俗后的官职确实是逯承冯误,《宋书》、《南史》中俱作“位至扬州从事史”。查《隋书·百官志上》可知文学从事是州刺史属官之一,[注][唐]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9页。故而佛教典籍《释门自镜录》、《北山录》言惠休还俗后“补扬州文学从事”的记载较史书中“扬州从事史”更为具体清楚。惠休还俗后补授扬州文学从事一职仍然与其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有关。惠休虽“慕俗意”,然还俗为官非其所愿,“意气既高,甚有惭愧”,因此患不得志。
此外,沈玉成、曹道衡先生在《汤惠休事迹》一文中,通过江淹《杂拟三十首》来推测惠休的卒年,认为“惠休之卒当晚于鲍照”,“其卒年当在宋季”,[注]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6页。论述极为有理。据丁福林先生考证,鲍照卒于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则惠休之卒亦当在此后。[注]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综上,惠休虽生卒年不详,但其生平可得而说。惠休,亦作慧休,俗姓汤,字茂远,住长干寺。生性倜傥放荡,嗜酒好色,轻忽释侣,有慕俗之意。又性爱作文,专心吟咏,文风华丽,作品广为流传,世人多共赏爱。宋元嘉二十四年,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于广陵招集文士聚会,惠休亦在邀请之列。后有不良僧人参与谋反,致使宋孝武帝于大明二年下诏沙汰沙门,惠休很有可能于此时被敕令还俗。嗣后,惠休曾任扬州文学从事史。惠休虽“慕俗意”,然还俗做官,非其本愿,患不得志,且心甚惭愧,刘宋末终于任句容令时。时人及后人每称惠休,多作“休上人”,想必是其一生为僧时间颇长,而其卒当在还俗后不久,故我们不妨将惠休视为刘宋时期一个特殊的诗僧。
二、惠休与文人的交游
惠休性爱作文,名冠上才,才锋挺出,“当时有清贤胜流,皆共赏爱之”。今可考见惠休与当时文士有交往者,有徐湛之、鲍照、吴迈远、谢超宗等人。
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伎乐之妙,冠绝一时。据《高僧传》卷七《僧镜传》、《慧通传》记载,徐湛之曾奉僧镜、慧通为师,可知其为嗜佛之文士。元嘉二十四年,徐湛之出为南兖州刺史时,修整旧楼,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此时,湛之与惠休交往甚厚。徐湛之任南兖州刺史的具体时间《宋书·文帝纪》记载较详:“(元嘉二十四年)九月……辛未,以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且同卷亦记载此后南兖州刺史人员的调动变化:“(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甲辰,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注][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页。此与《宋书·徐湛之传》中“(元嘉)二十六年,复入为丹阳尹,领太子詹事、将军如故”记载相符。据此可知,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是在元嘉二十四年九月至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十月,之后他升任丹阳尹。因此,惠休与徐湛之交往的时间当在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期间,即在元嘉二十四年九月至元嘉二十六年十月之间。地缘相近、喜好文学且又尊崇佛教的徐湛之,在其辖区听到释惠休的文名后,必定会招揽结识。在徐湛之发起的文士游玩聚会中,惠休也欣然受邀参与。由“湛之与之甚厚”可知,二人来往频繁,并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徐湛之为丹阳尹之后,二人相距渐远,是否仍有往来,则难以断定。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的文学家,与同时的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鲍照集》卷八现存《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两首诗,文集中也附有惠休《赠鲍侍郎》一诗,可知鲍照和惠休之间有诗歌酬唱,交往甚是密切。且二人诗歌风格相近,世有“休、鲍之论”。丁福林《鲍照年谱》将此三诗系于元嘉十五年:“在荆州期间,鲍照与僧人释惠休相往还,作《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二诗。”并分析立论之由[注]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颇有见地。因此,惠休与鲍照的交往时间当在元嘉十二年至十六年(公元435—439年)之间。惠休与鲍照的文学交游对后世影响颇大,唐代尤其明显。
吴迈远是宋明帝时人,好为篇章,“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注][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76页。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桂阳王刘休范起兵造反,吴迈远于其时尝为其写作檄文,故而在“桂阳之乱”平定后,吴迈远受到牵连而被诛灭九族。[注][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5页。钟嵘《诗品》中“宋朝请吴迈远”条云:“吴善於风人答赠……汤〔惠〕休谓远曰:‘我诗可谓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谓庶兄’。”[注]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诗品》中说“吴善于风人答赠”,今观其所传世11首诗歌,内容多男女思念的赠答之辞,与惠休之诗歌内容极其相似。惠休与吴迈远诗风相近,且有交往,遂引发出这段关于论定他们诗歌之间关系的文坛趣事。
《南齐书·谢超宗传》云:“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宋临川内史。父凤,元嘉中坐灵运事,同徙岭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还。与慧休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注][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35页。此“慧休道人”者,即为释惠休。据此可知在宋末元嘉以后,惠休与谢超宗有过交往。此外,据《高僧传》卷八《道盛传》、《道慧传》可知,谢超宗敬重道盛、道慧,且慧卒“谢超宗为造碑文”。这也就意味着谢超宗亦喜爱佛教,礼敬僧人,颇有其祖谢灵运的遗风,而这或许亦是其礼遇惠休之因。
三、惠休文学创作及其文风
惠休一生著作颇丰,所著诗歌亦当不少,然而据逯钦立先生所辑流传至今的诗歌只有11首,为《怨诗行》、《秋思引》、《江南思》、《杨花曲》三首、《白纻歌》三首、《楚明妃曲》、《赠鲍侍郎》。这些传世的的诗歌是惠休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弥足珍贵。
惠休现存11首作品中,除了《赠鲍侍郎》一诗外,其余10首都仿作乐府民歌,深受乐府曲调的影响[注]包得义:《南朝诗僧康宝月及其诗歌考论》,《求索》2013年第1期。,主要表现男女相思怨別之情。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怨诗行》源于曹子建《七哀诗》,而《七哀诗》在《乐府诗集》中就题作《怨诗行》,曹诗给后来的《怨诗行》之写作确定了一个专门描写闺怨题材的基调。惠休的《怨诗行》亦不例外,抒发深闺少妇自感芳年易逝、思远之情无以传达的忧伤。惠休此诗模仿曹子建《七哀诗》之痕迹非常明显,例如开头直接套用子建成句“明月照高楼”,最后四句则又化用其末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之意,只是变化了一下所用的意象。由此可以推知,惠休对于前代著名文人的诗作多有揣摩,同时也说明了文人诗对僧侣诗文创作的影响。明钟惺《古诗归》卷一二评价此诗云:“妍而深,幽而动,艳情三昧。”清沈德潜《古诗源》中曰:“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证禅也。”道出了作为僧人的惠休创作艳情诗的卓异之处。[注]赵卫、李南:《诗歌解读的评价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秋思引》则是惠休表现男女相思之情的诗歌,诗云:“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肃肃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楚辞》对惠休文学创作的影响。晋宋以来,《楚辞》一直很受文人喜欢,而惠休又身处江南,自然受其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惠休的这首《秋思引》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王运熙先生指出,“根据现存作品,最早称得上七绝滥觞的作品是鲍照的《夜听妓》和汤惠休的《秋思引》。”[注]张慧:《中国传统戏曲中的音乐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正因为有此重要意义,惠休此作自当在我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惠休还作有《楚明妃曲》,诗云:“琼台彩楹,桂寝雕甍。金闺流耀,玉牖含英。香芬幽蔼,珠彩珍荣。文罗秋翠,纨绮春轻。骖驾鸾鹤,往来仙灵。含姿绵视,微笑相迎。结兰枝,送目成,当年为君荣。”这是一首杂言体诗,三言、四言、五言混杂,以四言为主。这首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清新脱俗、高雅美丽而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形象。
惠休创作了大量以表现男女相思为内容的诗歌,故而钟嵘《诗品》中说:“惠休淫靡,情过其才。”对此,当时已有一些正统文人表达了不满,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注][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1页。在颜延之看来,惠休的诗歌,就是那种在僻陋的民间小巷中传唱的歌谣,不仅难登大雅之堂,而且不利于教化后辈。颜延之的诗歌讲究雕章琢句,自然不满甚至鄙视惠休模仿民歌的做法。另据史料记载,颜延之对不合沙门仪法的僧人也极度厌恶,释法琳就是其中一例。[注][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2页。由此看来,颜氏批评惠休的诗作,很可能与他是佛教的护法之士有关。
对于惠休其人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如是评价:“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注][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8页。这不失为公允之论。惠休、鲍照在当时以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很高的文名,且影响了当时不少作家的创作,江淹就是其中之一。
四、惠休诗歌的文学影响
上文考论了惠休的生平、交往及其文学创作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来解答敦煌遗书诗歌中以惠休指称悟真的原因。
敦煌遗书中标明作者为释悟真或者经过考证确定为悟真的文学作品,有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14篇,见P.4660、P.4896;《翟家碑》、《沙洲释门索法律窟铭》,见P.4660;《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碑》,见S.6161、S.6973、S.3329、P.2762、S.11564缀合卷;《张族庆寺文》、《俗讲庄严回向文》,见P.3770;《十二时》及《五更转》十七首并序,今只存序文,诗歌佚失;《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注]此名称采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的拟名。,见P.3720、P.3886、S.4654;《奉酬判官七言》诗一首,见P.3681;《唐和尚百岁书并序》,见S.930、P.2748、P.3054、P.4026;《四首恩义颂》四言赞辞一首,见P.2187。此外,敦煌遗书中还存有一些可能是悟真的作品。[注]苏红燕:《南北朝别集论述》,《求索》2013年第3期。我们看到,在已知的敦煌文献中,悟真创作了《十二时》、《五更转》、《百岁书》等组诗,还有赠答两街大德、奉酬判官的诗歌,算得上是一个高产的作家。
悟真和惠休都是僧人,且都善于写作诗歌,在这点上二者具有共通性,故用惠休来指称悟真从身份上来讲并无不妥。然而此乃浅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惠休在唐代还具有重要的文化符号意义。我们发现,惠休与鲍照的交往在后世常为人称赞。惠休、鲍照,一释一儒,其密切之往还非为相互间探讨佛法、研习经义,而主要是进行文学上的唱和交流。他们这种儒、释融洽相处的关系,给后代的文士和僧人(尤其是有文名的僧人)之间的交往起到了模范作用,以至于后世文人常用“汤休”、“休上人”、“休公”、“汤师”来代称其所交往的当世诗僧,这在唐代尤其明显。这类记载大量见于从唐玄宗至唐僖宗一百多年间的诗歌创作中。
玄宗开元年间,李白《赠僧行融》有云:“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又《酬裴侍御留岫师弹琴见寄》云:“君同鲍明远,邀彼休上人。” 均言及鲍照与惠休的交往。
肃宗至德二年陷贼时,杜甫过大云寺,所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云:“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乾元二年过访赞公,所作《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之一云:“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二诗皆借汤休以比赞公。
大历年间,李嘉佑避地江南,作《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推崇释灵一的佛学和诗才:“法许庐山远,诗传休上人。”大历三、四年间,司空曙仕为主簿,卢纶在洛阳作《洛阳早春忆吉中孚校书司空曙主簿因寄清江上人》云:“年来百事皆无绪,唯与汤师结净因”,《送恒上操上人归江外觐省》云:“还同惠休去,儒者亦沾巾”,又《酬灵澈上人》云:“走马城中头雪白,若为将面见汤师。”
宪宗元和初年,刘禹锡在朗州作《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云:“凭将杂拟三十首,寄予江南汤慧休。”刘禹锡以江淹自比,以惠休比灵澈。
元和十一年左右,柳宗元得到灵澈上人的讣闻,作《闻彻上人亡寄杨丈侍郎》,云:“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珰。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
穆宗长庆年间,广宣上人诗名大盛,与朝士往还者不少,尤与刘禹锡为最善,刘作《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示之》,云:“碧云佳句久传芳,曾向成都住草堂。”李益《赠宣大师》云:“一国沙弥独解诗,人人道胜惠休师。”广宣上人尝归西川,与西川幕府文人往还,段文昌作《还别业寻龙华山寺广宣上人》,云:“正与休师方话旧,风烟几度入楼中。”杨巨源作《送定法师归蜀,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云:“凤城初日照红楼,禁寺公卿识惠休。”
唐僖宗乾符年间,李洞《题晰上人贾岛诗卷》云:“贾生诗卷惠休装,百叶莲花万里香。”吴融《酬僧》云:“吾师既续惠休才,况值高秋万象开。”李郢《伤贾岛无可》云:“却到京师事事伤,惠休归寂贾生亡。”
惠休善为诗文,其作为文人与僧人交往的模范形象在唐代文学界有着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由于诗歌的繁荣和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呈现一种新的社会面貌,出现了许多才华横逸的诗僧,遂构成唐代诗人一大枝派。唐代释子周游天下,讲艺论道,“以文章接才子”成为一时风尚。因此,善为诗文的惠休受到唐代才士的热捧,惠休之名便成了诗僧的代称,具有了一种文化符号意义,并在诗歌中反复、大量出现。这些诗篇或以惠休、鲍照之间赠诗酬唱、以文相会的良好关系来喻指作者、他人与僧人之间的交游往还,或以“汤师”、“惠休”来直接指称当代诗僧,如清江、灵彻、贾岛、广宣等便是显证。
惠休可谓是一位“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杰出诗僧。宋杨亿《慧初道人归青州养亲》诗云:“遥知北海孔文举,应重江南汤惠休”,释惠洪有《金华超不群用前韵作诗见赠,亦和三首,超不群剪发参黄檗》其二云:“疑非蓬发休上人,定是秃头杨德祖。”(《石门文字禅》卷三)亦可见惠休影响之深远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