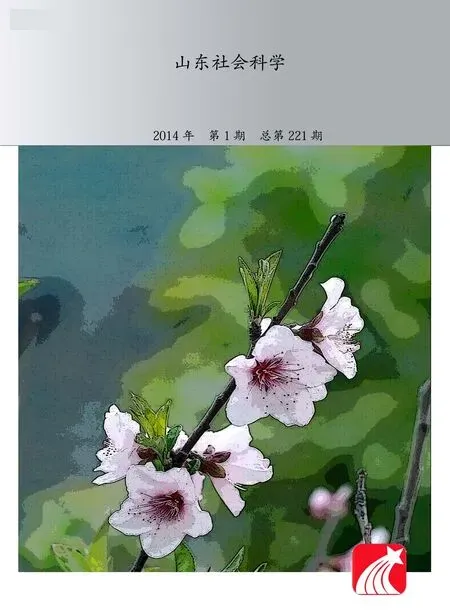华裔女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质
2014-12-03杨敏
杨 敏
(四川师范大学 基础教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为一门独立自足的新学科开辟了美国文学新领域。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以及伍慧明等感受到了来自族裔以及男权的双重压迫,但她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不同时期的话语策略成功地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美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当代美国华裔女性的创作以多元视角丰富了我们对美国华裔女性认知方式的看法和理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兴盛为美国亚裔研究、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从文化和诗学语境层面,对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全方位的解构,目的是挖掘她们的文学作品中更深刻的表达内涵,以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对华裔女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质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深嵌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之中的社会及文化结构,以理解将这些作品塑造成形的叙事和艺术实践,并最终阐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份寻求过程之中的混同与融合趋势。
一、美国华裔女性身份的迷失与抗争
文化身份一直是处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发展的华裔文学的永恒主题。美国华裔女性生长在美国,血液中又有着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背景,这种双重性的特点极易引起两种文化或两个世界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在其中,美国的华裔妇女受到两种文化夹击的程度更重,在中国伦理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相融相斥的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完善自我和寻求自我认同。我们知道,民族文化是以民族、国家为根本框架的,具有地理上的意义。美国华裔女性步出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而生活于美国,但“依母脐带”仍然使其存续原有的母体文化,长期生活于美国又使其适应于美国文化,而美国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华裔女性们身上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钟文化属性。[注]蔡青:《华裔女性文学身份探寻的文化阐释——以美国华裔女性为例》,《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4期。当前世界正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作为中国人文学中一个独具魅力的群体,美国华裔女作家作品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
美国华裔女作家因为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作为女性的敏锐眼光,她们发现了所有在美的华裔女性所面临的一个最困扰的问题,那就是陷入身份含糊不清、不被认可的状态。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华裔女性形象的悲惨遭遇,以及她们对追求幸福的强烈渴望。美国华裔女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们的身份认同与艺术追求。无论她们是崇尚“美国化”,还是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作品中随处可见身处“世界之间”的华裔美国女性面对“身份”问题时弃婴般的痛苦挣扎。为此,她们竭力重塑华裔美国女性历史,构建华裔美国女性光辉美好的未来。她们的作品对于华裔美国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先、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作用。华裔美国女性面对帝国主义的内部殖民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但随着被殖民女性的逐渐觉醒,她们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殖民主义进行抵抗和颠覆,积极地建构多元文化语境下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女性的身份迷失既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父权有关,同时也与美国强势文化所灌输的“种族自憎”有关;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在再现华族文化时,复制了美国强势文化的“东方主义”凝视,在执着于女性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歪曲或背离了自己的族裔性,最终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华裔美国女性身份。其中以刘绮芬、谭恩美、汤婷婷和林玉玲为代表的当代北美华裔女作家就属于这一类型,她们以英语或法语为创作语言,借助母女关系的镜像设置,在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视觉批判意识,显示了反男权、反东方主义、反他者化的鲜明立场。但是,北美华裔女作家在借“看母亲”追求自主性时,内化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强势话语,将东方女性再度“他者化”,也暴露了华裔女性写作的局限性。美国华裔女作家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赢得了赞赏,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耀。但是在这些荣耀的背后,却存在着尴尬的文化僵局。她们为了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确立女性主体意识,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和批判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把华裔男人描写成了残忍、低能、只会欺负本族裔女性的形象,这一切遭到了男性主体意识的对抗和华裔男性作家的强烈批评。
人生在世,总要努力构建与众不同的身份。因而,寻求身份便成为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热衷的一个主题。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美国华裔妇女如何探寻她们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成为美国华裔女作家关注的对象。[注]刘志芳、郭静怡:《当代美国华裔女性自传体小说与文化批评》,《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谭恩美是当今美国文坛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华裔女作家。她的成名作《喜福会》由十六个相互连贯的小故事组成,《喜福会》是以描写边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名篇佳作。谭恩美以自己作为边缘人的亲身体验,用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对书中四对美籍华裔母女进行了生动细腻的描写,揭示了她们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小说文本通过移民美国的四位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对中国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传承显示出华裔女性追寻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精神之旅。小说通过“母亲”与“文化”的文化隐喻,以及母女关系背后的文化斗争,揭示了美国华裔女性在种族、性别夹缝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进一步揭示出美国华裔女性在主体建构中身份的矛盾与迷失,为美国华裔女性身份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刻板印象下的美国华裔女性自卑形象
刻板形象是指人类对于某些特定类型人、事、物的一种概括的看法。刻板形象大多是负面的先入为主的,并不代表这个类型的人、事、物都有这样的特质。而美国华裔女性的刻板形象是西方霸权的一种表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西方的优越性和东方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种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多民族移民国家,在以英裔白人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处于从属地位和社会的边缘地带。[注]蔡青、徐曼:《跨越与协商——美国华裔女性自传体书写研究》,《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随着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用自己的创作表达了对种族身份认同的诉求,逐渐走出边缘,形成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独特的创作传统,使人们得以从多维角度挖掘和探索人类生存意义的复杂性。
赛义德将东方主义发展的轨迹和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学者与作家们在建构与强化东方主义中作出了“贡献”。在今天,某些西方人一方面仍然抱着他们亘古以来的偏见——东方人是不讲科学、迷信、非理性、愚昧、幼稚的;另一方面还利用媒体和其他手段来强化东方文化的“他者”形象,从而造成刻板印象下的华裔女性自卑形象。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塑造的第二代华裔女儿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因为将刻板印象内化而形成的自卑。《喜福会》描述了华裔美国女性在中美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汇的过程中对其身份构建的心路历程,从而解构父权制,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注]刘心莲:《论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的文类特征》,《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自卑”只是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产生的表面失衡,而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族裔身份的迷失。谭恩美试图通过描述处于夹缝状态的华裔女儿们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建立自信、走出自卑的情景。她作品中的这几位华裔女儿形象尽管有落入刻板印象窠臼之处,却是作者基于真实生活所独创的新华人形象,而且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庞大的霸权话语,这种独创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注]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再如《千金》,它是华裔美国作家林露德的第一部传记体小说,塑造了一位早期进入美国西部的华人女性开拓者。女主人公腊露自尊自爱、坚毅刚强,她的一生坎坷曲折,她的精神贵逾千金。这部小说中对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界的困境,及其身份从“无声—有声”的转变,最终获得声音这一系列的变化而不断获得学术界的关注。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以对身份认同与“他者”地位的拆解为创作主题,致力于揭示美国华裔女性在宿主文化圈里所遭遇的西方白人男权主流文化的排斥与压制。美国华裔女性通过其特有方式打破沉默,赢得自己的话语权,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盛行对于华裔女性的刻板化印象起了渗透、抵抗甚至颠覆作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自身经历出发,在她们的文本中,通过描写各类疾病,折射出创作主体对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等多方面的反思。揭示了处在男权社会与主流文化双重压迫下他者地位的女性所受到的身心摧残与伤害;这不仅体现了华裔女性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反抗意识,更体现了后学语境下女性对自我身份超越性别、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的执着探寻。如林小琴的戏剧《苦甘蔗》为我们再现了一段华裔在美国的历史,也呈现了真实的、同以往刻板形象截然不同的华裔女性形象。
三、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双重女性形象
文化差异是永久的命题,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一种赖以生存的文化融合模式,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既反映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思想,表现生活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环境中母女两代人所受到的男权制的迫害,同时又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新面貌。这些华裔女性作家们借助对两性之间从冲突走向融合过程的书写,反映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相处应具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追求。
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影响下的文化碰撞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种必然存在。不同于美国华裔男性作家强调相异文化主体间的硬性冲突,华裔女性文学则对不同文化表现出一种接受吸纳、兼收并蓄、融合共生的期望。这是华裔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和时代潮流共同孕育的一种文化、族裔新态度[注]薛小惠:《语言就是力量——从〈女勇士〉看一位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寻求》,《外语教学》2010年第1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看,《接骨师之女》中的“失语”和“文化认同”问题,在异质文化下第三世界女性从“失语”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自我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化逐步达到融合。《华女阿五》主要描述一位华裔女性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由社会边缘跻身主流社会的。在对待中美文化方面,主人公经历了从对立走向和解的渐进过程,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父母对美国文化的排斥也因女儿取得的成就而逐渐淡化,乃至融合。“华女阿五”打破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女性的偏见,冲出了唐人街父权制的天罗地网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人格上获得独立,这对于在美国文化中被压制、被妖魔化的华裔女性而言,“华女阿五”的形象提供了具体而存在的文本,可以积极建构美国文化的华裔女性形象。美国华裔女性必须要与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失语症以及女性在华裔社会的失语症做斗争。也就是说,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自身经历出发,在她们的文本中,通过描写各类疾病,折射出创作主体对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等多方面的反思。揭示了处在男权社会与主流文化双重压迫下他者地位的女性所受到的身心摧残与伤害;这不仅体现了华裔女性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反抗意识,更体现了后学语境下女性对自我身份超越性别、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的执着探寻。
汤婷婷作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先锋和“女勇士”,她率先运用中国文化资源进行华裔情感表述,在她的作品里,女性意识更是契合了盛行于美国社会的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潮,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确立女性主体意识,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和批判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注]王健、王军:《评美国华裔女性小说家的女性主义写作》,《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汤亭亭的首部小说《女勇士》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叙述者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中国与美国、过去与现代之间,描写了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同时把中国历史传说中的花木兰和蔡琰树为自己的榜样,为自己作为华裔在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确立了身份定位:融入美国文化,战胜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做出自己的业绩,成为新时代的女权主义勇士。通过极富想象力的虚构与简洁的白描手法,展示了一个生活在美国唐人街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女性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故事中流露着华裔女性血液里的果敢与担当,以及后来融入美国社会的蜕变过程,刻画了华裔妇女反抗父权、种族等压迫和抑制的伟大形象。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们不再抱怨她们的从属地位或者不平等对待,而是更多地关心如何成为一个新的华裔女性,并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华裔女性。《女勇士》表明了双重族裔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的华裔女性在寻找个人身份位置时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汤亭亭所塑造的华裔女性形象既是她自身的真实写照,更是华裔女性成长艰辛的真实写照;汤亭亭的《女勇士》既表达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更加表达了为她们争取话语权的渴望,以及在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基础上和谐相处、平等交流的愿望。在华裔美国女性身处“男权中心话语”和“白人霸权话语”的双重压迫之中的语境下,《女勇士》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对男权话语进行了直接的批判,打破了女性沉默无言的状态,并通过对传统故事的巧妙改写,颠覆了白人话语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重塑了华裔美国女性的自我。《女勇士》中花木兰的形象反映了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追求性别平等的旨趣,体现了混合基督教善恶论的美国地缘政治意识,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背景则衬托出花木兰东方“他者”形象。《中国佬》则是汤婷婷的代表作,无论在通俗文学市场还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都令人瞩目。汤婷婷在讲述一批中国早期移民在美国艰辛的生存故事的同时,将笔下主人公沉默无语的描写贯穿全书的始终。作者通过这批中国早期移民尴尬的生存经历,着重揭示了沉默在该书中所蕴含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象征意义。
四 美国华裔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
20世纪的女权主义以强烈的性别色彩和主体意识为妇女谋求解放,但是其单一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立场却导致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分化。与西方经典女性主义强调性别作为女性主体性的唯一要素不同,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认为,不仅性别,而且种族、文化、阶级等诸多因素都参与了女性主体建构。[注]郑光锐:《双重文化下自我认同的嬗变轨迹——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男性形象解读》,《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女性遭受本族在内的所有男性的压迫,同时也受到包括白人女性在内的所有白人的歧视。她们被双重边缘化,面临自我身份的危机。这种语境促使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和男权制社会的双重压迫下,通过女性特殊的视角和女性独特的叙事手法,重构美国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文本对象不仅宣扬了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借以表达作者们自己的强烈意愿,同时也给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美国文化这个“色拉碗”中成功地嵌入中国的元素。从美国华裔早期女作家艾迪丝·茂德·伊顿姐妹开始追溯,对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碧莲等女作家作品的文本策略作历时解读,充分显示华裔美国女作家在以文学实现其性别、族裔身份重建的过程中,文学场内、外动力机制对华裔女性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来自几代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有着复调特征的文本。正是这种复调结构,让不同背景下的华裔女性在美国白人社会里用大合唱的方式发出了强大的声音。在双重文化处境里,这些华裔女作家在经历与异族文化冲突和磨擦过程之后,如何撷取中西文化上的特点来适应美国情境和完成女性主体认同的建构就成了她们作品中的创作主题[注]蒲若茜、饶芃子:《华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悖论》,《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即在特定复杂的多元异质文化背景下只有通过和解和理解,华裔女性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我们以谭恩美的自我身份构建为例加以分析。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她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华裔的生活体验,也参与构建了美国华裔文化,深受不同族裔、年龄及文化教育背景的读者的喜爱,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发表以来影响巨大,掀起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又一次高潮。《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无论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母亲们,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都被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双重边缘化了。她们处在两种文化的罅隙中,带有尴尬的双重“他者”身份。在该小说中谭恩美以独特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华裔美国女性母女两代人在男权社会、中美两种文化冲突融合中对自己独特身份的认识,最终认识到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是确立华裔女性移民自我身份的最大障碍,只有消解东西方二者之间的文化对立才能建构华裔女性的独特自我身份:将自我身份建构为联接东西方文化,不排斥任何一方、促进二者的融合。这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和第二代华裔女性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注]阎瑾、杜军:《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构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求索》2012年第3期。《喜福会》通过不同侧面、角度描述了四对华裔移民母女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在多元文化冲突与并存的美国社会背景下华裔女性移民对于自我身份认定的疑虑,彷徨,反思,认定以及最终的情感归属。四位母亲作为第一代华裔移民,早期的中国成长生活经历与后来的美国生活环境构成强烈反差,使其时常对自我身份认定产生种种疑虑彷徨甚至危机。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象的代表,四位母亲又在平时生活的点滴中对各自的女儿无意识地带来各种中国式的文化熏陶和影响。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她们的女儿们同样经历着多元文化冲击带来的彷徨、疑惑,也像她们的母亲一样需要在不同的人生经历诸如爱情、婚姻、子女等问题上重新寻求自我身份认定的答案和情感的最终归属。小说结尾以开放式的结构,通过描述其中一位女儿最终在中国和失散多年的姐妹重逢团聚,深情表达出华裔女性在自我身份认定中强烈的中国式情感归属,更加深刻诠释出华裔女性移民体内那无法割舍的故国情结。
美国文化中有关“沉默”的种族中心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给跨越两种文化的华裔美国人带来心灵的冲击和阵痛。美国华裔女性同样曾经经历过,也正在经历着声音的政治,而这正是贯穿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的主题之一。为了追索自我身份的认同,她们通过写作挖掘历史,重塑历史,在各种强迫禁声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华裔女作家在文本创作过程中,通过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言说方式,在异质文化语境中探索了少数族裔自我身份问题,突破了传统的窠臼,实现了对传统华裔女性文学的继承与超越,为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