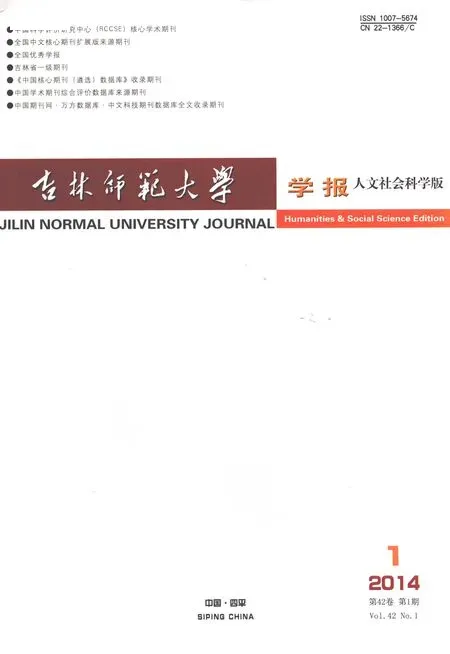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
——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2014-11-30柳泽明著吴忠良译
柳泽明著,吴忠良译
(1.吉林师范大学 满族文化研究所,吉林 四平 136000;2.日本早稻田大学 文学学术院,日本 东京 1620052)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
——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柳泽明1,2著,吴忠良1译
(1.吉林师范大学 满族文化研究所,吉林 四平 136000;2.日本早稻田大学 文学学术院,日本 东京 1620052)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黑龙江;驻防八旗;汉人;民族
如果论述清代中国内地的“满汉关系”,主要是以在庞大而又复杂的汉人社会中、较少数的、被统合在八旗中的满洲人为中心,当然还有其他各民族的参入,在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问题就成为了“满汉关系”问题的核心。但是在东北,尤其是在吉林与黑龙江,情况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在吉林与黑龙江,17世纪以后至19世纪前半期,其情况与中国内地相反,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成为基础,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向那里流入和渗透的过程是其主要内容。所以,那里没有出现内地那种只有汉文化单方面影响其他民族集团的现象,而是在两者间呈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再具体点说的话,吉林和黑龙江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吉林在雍正年间已经设立了永吉州等民治机构,而在黑龙江,如果除去商人向城市的流入,直至19世纪前半期,看不到民人的显著增加。黑龙江正式成立民治机构是在推行招民开垦政策的19世纪后半期。
本文通过几个事例,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并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作为史料,主要利用西清的 《黑龙江外记》(1810年左右,以下简称《外记》),还有清代历朝的《实录》,方式济的《沙龙纪略》(1710 年代),以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档案史料。
一、黑龙江地区八旗制的展开与居民构成
为了全面掌握黑龙江地区非汉人居民的构成,本章对该地区八旗制的展开过程作一个概观。
(一)驻防八旗的设置与扩充
三藩之乱基本平息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了抵抗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进出,康熙帝任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把阿穆尔河沿岸的黑龙江城(瑷珲)作为前方基地,攻略俄罗斯方面的据点雅克萨,经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清除了阿穆尔河流域的俄罗斯势力。这期间,从宁古塔和吉林调动相当数量牛录的满洲及汉军进驻了黑龙江城。满洲牛录的大部分是从阿穆尔河中游地区至乌苏里江流域一带南下的人们为母体编成的新满洲牛录。这些牛录的约半数,随着黑龙江将军的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向新建的墨尔根城的移动,以及随后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向齐齐哈尔的移驻,最终移动到了齐齐哈尔[1]。
另外,居住在嫩江至大兴安岭一带的、后面要提到的构成布特哈组织的索伦人及达呼尔人的一部分也于康熙20年代逐次被编入了黑龙江、墨尔根两城的驻防八旗。还有,康熙三十年(1691年),居住在嫩江西岸齐齐哈尔村一带的达呼尔壮丁1000人被编成16个牛录,于东岸的卜奎站所在地新建的城里驻防。这个城取名达呼尔的旧村名,被称作齐齐哈尔①楠木贤道:《康熙三十年达斡尔驻防佐领的编设》,《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77-93页;同:《齐齐哈尔驻防锡伯佐领的编设过程》,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山川出版社,1995年,325-347页。。其后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由于准噶尔的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而引起战乱,清朝把呼伦贝尔方面的巴尔虎人的一部分转移到嫩江流域,把他们编成8个牛录。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又被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其余的,如下文所要提到的,于雍正十年(1732年)移动到了呼伦贝尔[2]。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了监查盗采人参,在松花江北岸的呼兰设置了驻防。驻防兵由齐齐哈尔各牛录中抽出的壮丁320名整编成的5个牛录,以及在吉林管辖下的伯都讷的瓜尔察壮丁180名为母体形成的3个牛录构成。
驻防各城的牛录数及“民族”构成,因时期而变化。在《外记》里,关于3个驻防城的牛录数,如表1所述②关于呼兰驻防牛录,如本文所提到的,认为是由各民族混合构成的,《外记》中没有提及其民族构成。。

表1
驻防八旗官兵的俸禄、钱粮被用银两支付,但他们并不只依赖这些,还耕种城周围的土地来生活。因此,旗地到底扩大到什么范围,很难作详细的论证。例如,因至今还保留着满语口语而闻名的富裕县三家子村(齐齐哈尔北约50公里)的满族,被认为原来是所属于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其旁边的登科村的达斡尔族,据笔者于2005年进行的调查,他们原属于齐齐哈尔镶黄旗。还有,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卷六中提到,“黑龙江左岸四十余屯,旗户数百,有索伦,有俄伦春”,从中可以了解到阿穆尔河左岸的 “江东六十四屯”也主要是被旗人开拓出来的。
(二)“准八旗组织”的发展
1.布特哈八旗
从1630年代至1650年代,原来居住在阿穆尔河上游及结雅河流域的索伦人和达呼尔人的大多数,南下到嫩江至大兴安岭一带。清朝把他们编成牛录,设立了管理几个乃至10个左右牛录的4个阿巴(aba),3 个甲喇(jalan)。这个组织整体被称作布特哈(满洲语,狩猎之意),这是因为各牛录的壮丁从事贡貂。康熙二十年代以后,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中的鄂伦春人也逐次被编成牛录,编入布特哈。随着新的集团的编入以及人口增长,布特哈的牛录数也逐渐增加,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阿巴(aba)被增设后变成5个。雍正十年(1732年),牛录数达到了108个。同年,3000名壮丁被抽调到呼伦贝尔,其余的人被重新整编成 61 个牛录,各阿巴(aba)、甲喇(jalan)分到了八旗的旗色。其详细如表2③《雍正十年八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等呈理藩院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732:376-391。[3]。

表2
布特哈壮丁与驻防八旗不同,不被给予俸饷,平时从事农耕、畜牧、狩猎等,以维持生计。各丁只有每年交纳貂皮一张的义务。其居住地分布于嫩江干流至大小兴安岭的广袤地区。但是,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从各牛录中选拔出2000名壮丁,给予他们驻防八旗半额的俸饷。
2.呼伦贝尔八旗
雍正十至十三年(1732年—1735年),作为防备准噶尔军东进的对策之一,在大兴安岭西北的呼伦贝尔一带,重新设置了八旗组织。具体是,首先在雍正十年(1732年),从布特哈抽出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巴尔虎壮丁3000名,移动到呼伦贝尔后组成八旗50个牛录。这被通称为“索伦八旗”,是现在的鄂温克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大部分居民的起源。但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达呼尔和索伦的一部分返回布特哈,剩下的1440名壮丁被重新编为24个牛录。这24个牛录的体制,基本上被承续到清末。另外,清朝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次年间,把分属于喀尔喀车臣汗部各旗的巴尔虎人约3700户抽出来,移到呼伦贝尔,编成八旗40个牛录(披甲2400名)。这被称为“新巴尔虎八旗”,是现在新巴尔虎左、右旗的起源。支给呼伦贝尔官兵的俸饷是驻防八旗的半额,也未设立驻防据点,平时散居,主要从事游牧。[4]
二、汉系居民的类别与来历
黑龙江地区的汉系居民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非自发性迁入者和自发性迁入者。属于前者的有以下几种。第一,在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中,被授予一定公职的人。汉军旗人是最典型的例子。正如《外记》卷三中记载的那样,“旗下八部落外,来自内地编入军籍者,营、站、屯三项也。……三者流人戍卒子孙,而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故皆无仕进之例,不应役则自食其力”,可以认为水手、站丁、官庄的屯丁也被包括在其中。第二,私自隶属于旗人,从事耕种旗地或家务劳动等的奴仆。作为奴仆的来源,有的是官方赏与的流人,有的是旗人自己购买的。奴仆基本上附载于主人的户籍,所以也被称为“户下人”。第三,是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型的人,例如,流人中既没有被指派特定的公差,也不是奴仆的人;或者是被主人放出自立门户的奴仆等。自发性迁入者是纯粹的民人。这在黑龙江主要是以商人为主,18世纪起就在盛京和吉林成为问题的农业移民,直至19世纪前半期为止,在黑龙江基本上看不到。
(一)承担公务者
1.汉军八旗。黑龙江管辖下的汉军牛录,是康熙二十年代和俄罗斯的战役时从盛京和吉林方面移驻过来的,如在前表1中所看到的,在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瑷珲),一共被配置了8个牛录。据《外记》卷三中的记载,“汉军,其先多出山左,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有之。其豪族崔、王两姓,崔尤盛,号崔半城”,可以推测他们的祖籍是山东,但由于史料不足,很难详细地考察他们的来历。
2.水手。黑龙江管辖之下,在齐齐哈尔和瑷珲设有水师基地。在齐齐哈尔设有水师营总管,其属下有统辖各地水师的四品至六品的官员,据《外记》卷三的记载,汉军旗人被委以此任。据《龙沙纪略》记载,额设的水手人数为,齐齐哈尔319人,瑷珲429人;据《外记》卷三记载,齐齐哈尔275人,瑷珲427人,另外,墨尔根44人,呼兰40人,而且为了造船在吉林还驻有308人①以上数字均包含了领催。。《龙沙纪略》“经制”记载,“水手皆流人充役”;《高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七,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乙巳条记载,“齐齐哈尔等处水师营內,除三藩人外,俱系发遣人犯子孙”,可以看到他们的母体基本上是三藩的降兵和流人。还有,《黑龙江述略》卷三中可以看到,“黑龙江水师,始于康熙二十一年,罗刹据雅克萨城,调乌喇宁古塔兵,并置造作船舰,于黑龙江、呼玛儿等处监守。……皆乌喇、宁古塔人充当水手,后遂定为经制之师”,好像初设时,从吉林、宁古塔方面移动来的水手成了他们的基础。但是,不是所有的水手都是汉人,也有被流放的旗人被充为水手的例子②《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衙门咨奉天将军衙门文》内记载,“在盛京驻防的巴尔虎领催,因盗采人参之罪,在瑷珲被充为水手”,《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727:95-96。。支给水手的饷银是每月一两,既有如《外记》卷三记载的,“水手许充番子、仵作,间有委放笔帖式者”的情况,也有水手担任行政末端事务,以及被赏与奴仆的事情③《仁宗实录》卷176,嘉庆十二年三月己巳条。。通常,水手不能回原籍,但在乾隆朝初期,清朝推行汉军旗人及旗下开户人“出旗为民”政策时,水手也成为其对象。据《高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七,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乙巳条记载,当时黑龙江辖下水手810人之内,希望回原籍的有324人。也就是说,比起作为民人回归原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继续作水手。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瑷珲水师营的水手出现了稍有不足的现象,所以决定把旗分佐领的另记档案人转移到了水师营壮丁的档案,水手欠缺时以其填补之④《高宗实录》卷639,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条。。通览上述,与站丁和屯丁相比,水手和驻防八旗(尤其是汉军)的关系更为紧密,可以说他们接近于正规的兵丁。
3.站丁。据《外记》卷二等记载,黑龙江辖下的驿站网络大体如下。首先,是从齐齐哈尔东北的宁年站开始,经过齐齐哈尔城内的卜奎站去往吉林方面的,到达茂兴站,共10站,和吉林所辖的伯都讷相联接,这些被称为“下站”,站官驻扎于齐齐哈尔。其次,是和宁年站东北连接的拉哈站开始,经由墨尔根到达瑗珲的10站,这些被称为“上站”,站官驻扎在墨尔根。上下站为干线。随着雍正年间在呼伦贝尔和呼兰的驻防设置,设立了从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现在的海拉尔)的10台,以及从乌兰诺尔站到达呼兰的6台。上下20站,各站设领催1名,站丁26名(但是,卜奎站多3名),到达呼兰的支线上的6台,各台设领催1名,台丁9名。站官从旗人中遴选,根据前面已经引用的《外记》卷三的记载“吴、尚、耿三藩旧戸,站上居多”来看,领催和台站丁主要是由旧三藩的人员构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某档案记载,“在齐齐哈尔和墨尔根之间的喀木尼喀站的某丁,为了把父亲接来,并把在山海关的家宅和田地卖掉,申请休假”⑤《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九日黑龙江将军、副都统咨盛京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717:161-162。。虽然不太清楚其具体情况,但是此记事在传达了该壮丁可能和吴藩有关联的同时,表明台站丁拥有管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台站丁没有饷银,耕种台站周围的土地来维持生活。卜奎站和墨尔根站在城内,其他各站,都在人口稀薄的地方形成了独自的村落,如《外记》所载,“上下站壮丁,自为聚落。毎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过客。私开旅店,间有亦之。过此则黄沙极目,白草蔽人,不至各站,想闻鸡犬声不得”。很可能是出于此种原因,站丁和其他居民之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集团。伪满洲国时期的《龙江省富裕县事情》虽然是后期的史料,但其中记载,“站人是原来被流放到当地的人的子孙,因为不专心耕种,所以穷人较多。据说,一般比较懒惰,女人同男人一样劳动,好像多少有点被普通汉民所歧视”①伪满洲帝国地方事情大系刊行会:《龙江省富裕县事情》,1936年,19-20页。。
4.屯丁。在东北各地,为了生产军粮以及各城官仓的储备用粮,设置了官庄。据《龙沙纪略》“经制”记载,黑龙江辖下共有官庄31处,各庄设有屯丁20名②但是,周藤吉之推测20名应是10名之误(周藤吉之:《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的研究》,河出书房,1944年,382页)。。其后,官庄又被扩充,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版《盛京通志》记载,官庄的总数是136,每庄屯丁10名。此数字与《外记》卷三的记载一致。屯丁也没有饷银等,他们耕种庄田,每丁纳粮30石 (嘉庆九年〔1804年〕以后是22石)。总而言之,屯丁是官营农场的农奴,但是对于他们的生活,官方给予一定的福利。例如,据雍正十年(1732)的档案记载,为了瑷珲管辖下无妻的屯丁(从名字看好像是汉人),拿出30两银,买了旗下的寡妇(好像是非汉人)送与他们做妻子③《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副都统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13-1732:21。。还有,如在第二章第(三)节中要提到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制定了屯丁中一部分提出申请的人可以复归原籍。从这些事实来看,屯丁的身份和流动性要高于水手和台站丁。
(二)奴仆
奴仆(aha)在齐齐哈尔等驻防八旗,以及布特哈和呼伦贝尔的兵丁处都普遍存在。黑龙江地区奴仆的起源相当古老。康熙十五年(1676)年,经过齐齐哈尔一带的俄罗斯大使斯帕法理记述了如下内容:
当地的村落里,居住着很多作为契丹人〔китайцы〕奴隶的尼堪〔汉〕人。 他们对我的、既懂契丹语又懂尼堪语的翻译说,契丹人从尼堪人那里抢夺的事情是假的,事实上,他们两次败给尼堪人,帝国里只剩下妻子和孩子,失去了所有的人。于是,现在博格达汗为了从蒙古人那里收集军队,正在派遣人员④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Матe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1608-1683,Москва,1969,с.497。。
这个记述是齐齐哈尔建城以前的事情,所以斯帕法理所说的“契丹人”,应该是指当时齐齐哈尔一带的主要居民达呼尔等。有意思的事,奴仆们散布袒护三藩的传言这一信息,因为没有其他史料,所以无法确定他们的来历。只能推测他们是达呼尔人、索伦人进京贡貂时得到的赏与,或者是他们买来的。
黑龙江地区的驻防体制确立之后,奴仆的供应也以各种方式得到延续,有官方给有功者及贫困者赏与奴仆的事情,也有旗人、布特哈壮丁自己购买奴仆的情况。康熙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将索伦人和巴尔虎人编入驻防八旗时,好像有组织地进行了奴仆的赏与,例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把贫困的巴尔虎人录用于披甲时,曾有过“给予他们甲、盔等器具,以及奴仆、家畜等,皆照以前让贫困的索伦人披甲时给予的样子支给”的决定⑤《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奏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694:390-401。。如《龙沙纪略》“饮食”记载,“今流人之赏旗者,且倍于兵”,官方赏与的奴仆的主要来源是流人。但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档案中有,“为了购入给予巴尔虎人的奴仆,官员去往盛京”的记载。由此可以了解到,还有购买奴仆用作赏与的事情⑥《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黑龙江副都统咨盛京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697:131-132。。还有,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档案记载,到北京送岁贡貂皮的布特哈人报告了购买男人、女人、孩子等约100人,归途中夜间在八沟(平泉)宿营时被人袭击,奴仆的一部分被抢走一事,布特哈人称,“以前,布特哈人送公课貂皮时,即使是买奴仆,也是少量的。这几年来,多少富裕起来的人,即使不是他的班,也都过来买很多人,进行倒卖而得利”⑦《月折档》10(1):327-332,Dokina奏(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呈览)。。
传达作为生产力的奴仆的重要性的史料并不少。例如,《龙沙纪略》“风俗”中记载,“居人置奴婢,价尝十倍于中土。奴婢多者为富,以其能致富也”;《高宗实录》卷四十五,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乙酉条内记载,“发与口外驻防兵丁为奴之犯,闻彼地兵丁,有藉以使用颇得其力者”。
从内地流放过来的人当中,作为奴仆被赏与的基本上是汉人。因为,以前真正的旗人也有作为奴仆的例子,但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旗人只在被流放的旗里做公差,做奴仆的事情被中止了⑧《高宗实录》卷26,乾隆元年九月甲辰条。。尽管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奴仆都是汉人。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准噶尔的战争中,把俘虏的、投降的明噶特、特楞古特、奇尔吉斯等约600人,作为奴仆分给了布特哈和呼伦贝尔的兵丁⑨《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八日署副都统衔总管等呈黑龙江将军衙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4-1757:236-265。。
通常对奴仆的管理并不严格。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某个档案记载,山东莱州府的民人Lo Tan,控告S姚en San、Sal等 5 人杀害了他在墨尔根开酒家的表弟。据称,S姚en San等人是布特哈壮丁的奴仆,S姚en San在卖牛肉的回子的店里拨牛皮的时候,原告Lo Tan指责他用的小刀是自己表弟Pan Kui-ioi的,这是事件的起因⑩《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墨尔根城副都统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3-1715:89-101。。这个史料暗示,奴仆离开主人的家,有相当自由的行动。另外,奴仆在法律方面并不是完全没有权利。雍正十年(1732年)的某个档案记载,有个被给予给布特哈壮丁做奴仆的,叫Yoo jul的人,到齐齐哈尔的将军衙门,状告他的主人要把他和他的妻子拆散,准备把他卖掉①《雍正十年六月七日署索伦达呼尔总管等呈黑龙江将军衙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13-1732:206-210。。这个史料暗示,不能卖掉被赏与的奴仆,而且奴仆可以向官衙控诉主人的不法行为。
内地来的流人中,虽然有受牵连于文字狱和科场案件的读书人,但大多数是一般的刑犯,其中也有“教匪洋盗”之类。即使把这类人作为奴仆赏给主人,主人管束他们好像也很困难。《外记》卷六中,例举了几个主人被性格不好的奴仆所折磨的实例后,作了如下记述:
黔奴俗号花脸子……诸城皆有,齐齐哈尔最众。……其无赖乃聚赌窝娼,窃马牛为事,甚或结识将校,勾引工商,兴讼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犹以给奴为恩,得奴为喜,強卖逼赎,诸弊丛生,是在当時者思患豫防,涣其群尔约之以法,所关于地方不小也。
正如西清所担忧,嘉庆十八年(1813年),墨尔根的遣奴等正在筹划纠结人众,进行抢掠时被发现②《仁宗实录》卷266,嘉庆十八年二月丁巳条。,结果,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往吉林、黑龙江的流放被终止③《宣宗实录》卷3,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己酉条。。
(三)流人,放出家奴
如本文在开头部分中提到的那样,在齐齐哈尔等城市有既不担任公职,也不是奴仆的居民。他们是不符合“为奴”而被定为“安插”的流人,被赦免后不回原籍的流人,出于某种情况从主人处被放出、开户的家奴,以及他们的子孙等。《高宗实录》卷一千零八十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庚寅条内记载:
惟节年奉部发遣人犯及放出旗奴所带子女,渐俱长成,相联姻戚,在各城居住,已有数百名之多。查边陲之地,积储粮谷,最为紧要。应于齐齐哈尔地方,增添官屯数处,领催一名,其余丁口,俱载入各城官屯冊內,以备挑補。
由此可以知道,为了吸收居住在各城的流人及放出家奴的子女而增设官庄之事。另外,同书卷一千一百七十八,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癸亥条内有如下内容:
惟新设十庄屯丁,除旗人家生奴仆,原系土著,俱能耐劳,亦各安分,其余屯丁,系遣犯隨来之子,及来历不明之民人,游惰者多,纳粮时往往拮据。臣查其情形,多愿回籍者。……请先将闲散余丁,陆续遣回,年终报部存案。再齐齐哈尔等处,绝嗣旗人之家生奴仆,及开戶家奴,虽各立产业,安分度日,但亦不可无专管之人,请入于官屯。将年壯者选为额丁,以補遣回民人之数。
也就是说,因为“遣犯隨来之子”及“来历不明之民人”内,“游惰者”多,经常抵抗纳粮,所以逐次使之回归民籍,其空缺用主家绝嗣的奴仆,或者用开户的家奴来填充。《外记》卷三中记载的“屯丁请还籍听之”,也表明了这种情况。还有,被放出的屯丁被禁止居留于黑龙江境内④《仁宗实录》卷126,嘉庆九年二月癸酉条。。
但是,处理被陆续不断地送来的流人,成了棘手的问题。《仁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嘉庆十年(1805年)八月壬辰条内记载,“据秀林面奏,近年来闽广等省案犯往吉林安插者,有三百余名,闻黑龙江较比更多。此等人犯均系犷悍无赖之徒,到配后无人管束,又无口食,三五成群,易於滋事为匪等语”,被指示以“或有旷土可耕,借给籽种,俾令自食其力,或拨衙门充当水火夫役,酌给口食”,作为对策。但是,如《外记》卷六内所记载,“约计齐齐哈尔今有三千名,余城亦千名以外,盖久未停遣,东来者日众,游手聚居,是在拨遣鈐束之有法耳”,由于流人被连续不断的大量的发遣过来,使问题很难有根本性的解决。同书卷三内还记载,“流人遇赦不归,例入官地安插,否则自入伯都讷民籍,然后可居境内,非是者谓之浮民,境内不留也。然今齐齐哈尔浮民无数,商贩私立家业者亦不少,皆例所禁”,由此可以了解到,被赦免后不回原籍的流人,作为“浮人”在齐齐哈尔聚集了很多。同书卷六中还记载,“黔奴……黠者赎身自便,网鱼採木耳,趁觅衣食,稍有立业,致聚妇生子,称小康者”,表明奴仆中有人赎身后自己谋生。本来,作为奴仆被赏与的流人的赎身是违法的⑤《仁宗实录》卷235,嘉庆十五年十月乙未条。,但是,穷困的主人为了换取金钱,把奴仆放出的事例好像很多。从上面的例子中能理解到,流人中有经营事业而得到安定生活的人。同书卷7记载,据说有名的勇将海兰察年轻时,曾为朱姓流人驾车,往来于奉天和吉林之间。
(四)民人
在没有民治机关的黑龙江,从很早以前就有商人等流入城市。《龙沙纪略》“屋宇”中记载齐齐哈尔有木城和土城两重城郭,还记载了“入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同书“经制”内还记载了“商贾往来无定,亦立冊以稽”,由此能了解到商人被登录在独自的档册中,但是这当然不是正规的民籍。如《高宗实录》卷一千零八十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庚寅条内记载,“黑龙江地方,屡经奉谕,禁止流民棲止,除往来贸易者,并无携带家口居住之人”,民人为了贸易被允许往来,但是带领家族定居则受到禁止。《外记》卷五内记载,“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山西商人已经很多了。还有,后来的《黑龙江述略》卷六内记载,“汉民至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其肆中执事,不杂一外籍人,各城皆设焉”,可以窥知,山西商人的网络已在这里扎根。但是,看18世纪前半期的档案,当时山西商人的活动还不显著。例如,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提到的关于杀人事件的档案内,作为原告的山东莱州府民人供述到,“我是康熙三十七年去墨尔根城经商,四十一年返回家,四十四年带来我姑姑的儿子Pan Kui-ioi,在墨尔根城经营酒家”。还有,雍正七年(1729年)的某个档案中记载,因盗窃嫌疑被逮捕的济州府德州的民人Cang U说,“投奔同省东昌府聊城县民人Joo Da-peng过来的。Joo Da-peng在齐齐哈尔开了剃头店”①《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黑龙江副都统咨黑龙江将军衙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9-1730:2-7。。从这些事例来看,在早期,少数的山东一带的民人到来后做些零碎的生意,这种形式是较普遍的。
三、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汉系居民与其他集团的相互影响
由于相关史料较少,所以很难从总体上重建汉系居民和其他集团之间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相互关系。所以,下面试着从几个侧面对其加以若干的考察。
首先,根据《外记》等的记述,可以窥知在齐齐哈尔等城市,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有了文化上的融合,但是,并没有单方面的吸收、同化对方的性质,而是相互的。例如,《外记》卷六中,关于当时的语言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土人于国语,满洲生知,先天之学也。汉军等部学知,后天之学也”,另一方面,如下文中要提到的,还有满洲旗人通晓汉语的记载。此书还记载到,两者在婚姻、祭祀等种种习俗上,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非常相近。
另外,有关汉军旗人与其他汉系居民间的关系,虽然不是黑龙江的例子,但是传达了康熙二十年代的宁古塔状况的,如杨宾的《柳边纪略》卷四中有很有意思的记载,“汉人以罪至者,虽与汉军不同,然毎与汉军为伍。在满洲与异齐满洲,则总呼为汉人,汉军亦不以此自别,盖与京师汉军,有截然不同者矣”。这个记事揭示了在中国内地汉军旗人强调自己和一般汉人(民人)不同的、作为旗人的自我认同性。与此相比,在汉人称不上是多数派的东北,汉军旗人超越了行政上的确定地位的差异,有和流人等一体化的倾向。可以认为,在黑龙江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
有关在儒学及古典的教养、写作方面,在《外记》卷六中能看到 “汉军知习汉书,然能执笔为文者绝少,其能尊礼文士以书传家者尤不易得”的记载,说明汉军旗人的水平并不高。但是,其下又有“近则水师营四品官果君德兴,……闻谪戍者讲四子书,爱之,遂命子弟悉读汉书”的记载,说明一部分汉军旗人通过与流人接触,志愿于学问。嘉庆元年(1796年),在齐齐哈尔设立了讲授汉书的八旗义学,上文中提到的果德兴成为了学长,流人龚光瓒(常州人)充当了老师。在这个义学中,《外记》的作者西清也执教过一段时间②西清本人是满洲镶蓝旗人,是乾隆、嘉庆朝的名臣鄂尔泰的曾孙。。另外,据说流人中教汉书维持生计的人很多,但是在墨尔根及瑗珲,因为那里的教师很少,所以他们雇佣晋商充当了教师。这样,中国内地的学术,被这些流人及商人等的外来者传播过来,很可能主要以汉军旗人作为媒介,逐渐渗透到了旗人社会。
但是,达呼尔、巴尔虎等其他的集团则如《外记》卷六所记载的,“达呼尔、巴尔虎自相婚姻,或与蒙古通”,他们与满洲、汉军旗人划一界限,在各自的集团内部保持一致的倾向较强。同书卷七还记载,齐齐哈尔达呼尔的某个马甲,与“蒙馆老生”交往,逐渐知道“书理”,在祭祀祖先时设立了灵牌,但是被“同类目为怪物,不恤也”,这种人的存在属于例外。
在驻防八旗、布特哈旗人在郊外开拓的村庄里,各集团的独立性更高。上文中提到的台站各自形成了独自的村落,旗人也大体上以每旗或每牛录聚集到一起构筑了村落,这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区别。举出具体显示这种情况的证据是很难的,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引用的《龙江省富裕县事情》中记载,“完全没有各种族间的倾轧,但是语言、习惯不同,村庄也不同,很难说他们之间在感情方面的融合是完整的”,可以说这是个旁证③伪满洲帝国地方事情大系刊行会:《龙江省富裕县事情》,1936年,20页。笔者于2005年访问了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和墨尔根(现在的嫩江市)之间的富裕县、讷河市,还有在嫩江西岸的阿荣旗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几个村庄,确认了每个村庄都有相当古老的起源,该集团一直以来占据着当地人口的大多数。。郊外的旗人平时接触的汉人是奴仆,但是据定宜庄所说,奴仆分散在各个家庭,从其社会地位看,被其主家的民族成份所同化的倾向较强。[5]
尽管那样,从大局看,汉文化的影响在全体黑龙江地区逐渐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其表现在口语方面。原来,在黑龙江,直至19世纪前半期,公文书几乎全部是只用满文来书写。另外,因为索伦人、达呼尔人没有固有的文字,所以不仅在满洲旗人之间,即使是在他们之间,满文书籍也有某种程度的普及,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确认。[6]也就是说,作为书写语言的满洲语曾经是通用语言。但是,在口语方面的情况则不同,满洲语未必一定有过作为通用语言的机能。《外记》卷六中记载,“晋商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盖皆童而习之,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山西商人能通各民族语言,但是因为和满洲人能用汉语交流,所以通满洲语的人就少了。同书另一面还记载了,“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布特哈近岁能汉语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伦貝尔则实不能”,可以窥见,在呼伦贝尔以外的地区,汉语正逐渐确立作为共同语的地位。关于在生活文化、社会习俗方面,虽然也有能看到类似情况的可能,但是想把那些作为今后探讨的课题。
[1]松浦茂.清朝的阿穆尔政策与少数民族[M].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300-301.
[2]柳泽明.陈巴尔虎的起源与变迁[J].社会科学讨究,1999(2):87-111.
[3]承志.清朝统治下的鄂伦春佐领编制与布特哈社会的一个方面[J].东洋史研究,2001(3):1-38.
[4]柳泽明.清代黑龙江八旗制的展开与民族的再编[J].历史学研究,1997(698):10-21.
[5]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247.
[6]加藤直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满文资料[J].满族史研究通信,1993(3):25-33.
[责任编辑:薛柏成]
The Eight Banners of Garrison and the Han People of the Northeast in Qing Dynasty——Take Hei Longjiang Province as the Center
(Japan)Akira Yanagisawa1,2Translated Wu Zhong-liang1Traslation
(1.Institute of Manchu,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2.Faculty of Letters,Arts and Sciences,Waseda University,Tokyo 1620052,Japan)
After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the Northeast which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eight banners in garrison as the core of the non-chinese society;but there were a few Han people in various forms there,so each ethnic group presented the comparing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By several examples,this paper will discuss before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the Hans,in Hei Longjiang province,with which type of form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and then discus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ow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Qing Dynasty; Hei Longjiang; Eight Banners of Garrison; the Hans; nation
K249
A
1007-5674(2014)01-0008-07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2
2013-11-15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3B99)
柳泽明(1961—),男,日本东京都人,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清史,满学;吴忠良(1972—),男,吉林镇赉人,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清史,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