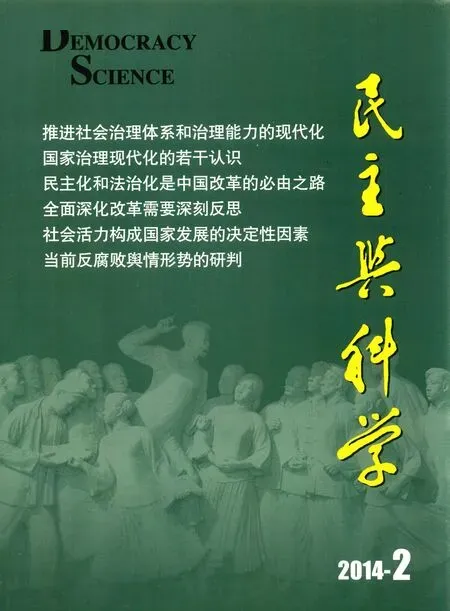社会参与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2014-11-29■李凡
■李 凡
中国从上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会逐渐加大。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先是各种“苛捐杂费”所造成的“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局面的出现,从而产生了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第一轮冲突。城市也多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国企职工的下岗问题。在中央的干预之下,特别是免除了农业税之后,农村基层政府与社会的矛盾有了缓解的机会。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为了追求政绩,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入作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的趋势越来越强,这样就不断的出现地方政府抢占社会土地,强拆居民房子的事件,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地区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这样就出现了第二轮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冲突的发展。社会公众不断的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不满的处理方式是加以压力,强制社会服从。这使得基层政治越来越紧张,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地方不仅没有得到化解,反而不断扩大。
面对社会的参与要求和改革压力,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用进取的积极态度来主动引导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是用防守的态度、划清敌我的态度来消极的对待社会,这就在政治上出现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一切以维稳为中心。
然而,也有一些政府愿意采用改革的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让社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扩大社会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的参与。
这些参与,有些围绕着农村和城市的社区进行,也有一些是在政府层面上进行,例如人大会议上对预算和政府事务的监督,要求政府事务公开等等。同时,在社会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事务也进行公开的改革,包括政府预算、政府信息、政府政策的公开已经在全国一些地方逐步进行。虽然这些公开不够完整、及时,但是政府事务公开的方向已经启动,而且不可回避。
其实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出现和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矛盾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冲突。有的地方政府是采用与社会对话的方法,扩大社会公众参与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例如,广东在处理乌坎冲突问题上就坚持用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用回归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北京,麦子店街道也试图用社会公众参与“问政”的方式,扩大公众社会参与。这是改革导向下的政治参与,其中,最为成功的例子是浙江温岭“民主恳谈”。
“民主恳谈”最初是1999年6月台州市委宣传部和温岭市委宣传部联合在温岭松门镇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教育中创造的、以会议对话和讨论为基本形式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此后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活动:民主沟通会、乡镇政府决策听证会、乡镇党委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建代表回复会,等等。此后,这一形式不断变化,逐渐将“民主恳谈会”发展和转变成基层政府和社会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
之后,地方政府将民主恳谈与政府的预算改革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民主恳谈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加以克服。同时,让社会和国家就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利益和发展交换意见,进行面对面的对话,非常有助于互相了解和化解矛盾。
温岭所进行的改革代表了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人所进行的一种努力,就是要通过扩大社会的公共参与的空间,逐渐地拿出一部分政府权力给社会,通过这种权力的释放,减缓基层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温岭多年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他们的改革有以下的一些现实的意义:
首先,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对话系统。现在在温岭,政府与社会可以就任何问题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意见交换,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可以在意见交换和讨论中,达到妥协、谅解。这种对话方式已经常态化,不仅可以在政府预算上进行,也可以在其它问题上进行,例如工资分配等。
其次,建立了一个参与式预算制度。参与式预算是当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社会直接民主的方式。温岭完善了人大对预算的审议过程,进而将公共参与引入到政府制定预算的过程中,这样就做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参与式预算的方式,在政府编制预算和人大审议预算中都有社会进行参与。这给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第三,建立了一个基层人大运行的模式。多年来在进行预算改革的探讨中,温岭启动了基层人大,尤其是乡镇人大,将一个原来曾被称为橡皮图章式的人大制度激活,逐渐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人大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说明在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中,人大是可以加以充分利用的制度资源。
第四,探讨了有效的中国政治改革方式。政治改革是近些年大家谈得最多的事情,但是到底怎么改争议非常大,比如有人认为要从选举改;有人认为要从党内民主改;有人认为要从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来改,例如司法制度。这些改革的方式,在嘴上容易说,但是在目前复杂的矛盾中,难得成功。但从中国现实中加以检验的话,我们可以说温岭找到了一个中等程度的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让改革启动起来。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中国现实的政治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