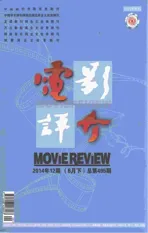《西厢记》思想价值新探
2014-11-21李静
李 静
自元末明初,《西厢记》就被称作“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先贤时俊对《西厢记》主题的探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每戡先生在《五大名剧论》中提出:“作者以犀利的毫锋,深入地鞭挞了整个封建时代,尤其是唐代更为严厉的‘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这种罪恶的封建婚姻制度。”[1]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所接受。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唐代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真实状况,深入探讨《西厢记》的思想价值。
一、《西厢记》主题说
《西厢记》取材唐代,源于元稹《莺莺传》,讲述贫寒书生张生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在普救寺一见钟情,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与张生交往、相恋以致“自荐枕席”,然最终被科考中第的张生抛弃的爱情悲剧故事。这个故事广泛流传,经过宋代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不断改编传唱,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到了元代王实甫的笔下,在丰富的艺术积累基础上以杂剧形式对西厢故事进行了再创造,不仅以文采惊倒四座,其对张生与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改写,更使得《西厢记》成为“反封建反礼教”之才子佳人爱情剧的典范。
关于《西厢记》主题的“反封建”说发轫于郭沫若,其在1921年撰写的《<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中评价《西厢记》为:“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普遍地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这一说法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如宋之的在其《论<西厢记>》一文中认为《西厢记》:“描写了封建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力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的,充满了曲折但也充满了痛苦、胜利和喜悦的一篇宏伟的诗篇。”因之,“《西厢记》的艺术力量就在于:王实甫以毒辣的讽刺,火一样的嘲笑,尖锐的指责,抨击和烧毁了看来是强大无比的封建统治阶级底封建观念和封建力量。”段启明在《西厢论稿》一书中道:“《王西厢》也是通过崔、张二人双双追求幸福爱情并最终获得美满结果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统治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思想。”
王季思首先承继郭氏之说认为《西厢记》歌颂了青年男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表现出反封建之思想价值,在之后的研究中则注意到“王西厢”所反映的思想“董西厢”中已经有了,“王西厢”之可贵处,在于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口号,喊出了广大群众之心声。此后研究者的目光逐渐背离反封建说,而向主情说聚集。如季丹在《论<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一文中认为王实甫“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伟大美好的祝福。这种升华不仅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学作品创作,也引导了无数代人的爱情观,不愧为‘天下夺魁’的旷世佳作。”邹尤《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一文反对《西厢记》主题的反封建说,认为“贯穿王实甫《西厢记》的思想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义’。”齐涛的《<西厢记>老夫人形象简论》一文则倡导关注戏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反对拔高戏剧思想和主题,指出:“《西厢记》的主题并非‘反封建’,作者王实甫创作时也只是延续了《莺莺传》原作的创作主旨,即铺叙了一段青年男女‘倚翠偷期’式的风流韵事。”
随着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对《西厢记》主题思想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从更深广的社会背景层面提出了一些较有创见的观点。以董每戡为代表,其在《<西厢记>发覆》一文中指出《西厢记》“跟元明清三代所有的反封建制度的作品迥然不同”,老夫人赖婚行为的背后,并非一般观念中的门当户对,而是唐代门阀制度下的残酷婚姻制度,是唐代大姓自为婚娶的社会事实,是一种迥异于其它历史年代的历史真实,这一点也正是《王西厢》能够超越之前的西厢故事,成为天下名剧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这种说法深刻披露了西厢故事蕴含的历史社会背景,将《西厢记》之思想价值推向了新的高度,因之取代笼统的反封建说而成为《西厢记》主题说之一大主流。此后,学界在言及《西厢记》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时,大致不离唐代婚姻门第观念之顽固。
二、唐代门阀制度
门第婚姻伴随着门第政治的产生而形成,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婚姻形态。士族特权阶层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门第,享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权,极力排斥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姻,以保持自身家族血统的纯洁,达到垄断世袭权益的目的。然而这种门第婚姻在经历了东晋的鼎盛后,由于士族自身的腐朽等原因,南朝时期便逐渐走向衰落,到了隋唐,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均田制也以现任官品占田,这便意味着以世袭特权为重要标志的旧士族已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土壤。
唐朝前期,由于婚姻讲求门第的观念作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性心理并不会立即消亡,所以旧士族仍极力标榜门第,不愿与异姓为婚,“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2]然而,这种理想在士族阶层失去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而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屡被打破,主要表现为:其一,士族与官宦新贵联姻逐步上升。官宦新贵趋附士族传统的社会声望,以与士族联姻为荣耀,士族则欲借与官宦新贵的姻亲关系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来维护其旧望不减。譬如,高宗时的宰相李敬玄本毫州寒门,“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3]
其二,与卑族进行财婚。山东士族从北魏到隋唐,政治经济上不断衰落,其所标榜的“自相为婚”已不像昔日门第辉煌时般行之如律,山东士族开始与外族通婚,但自矜尊贵的心理又使其高挂门第,婚媾时以重纳聘财弥补门第之差:“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衰落,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昏”。[4]
其三,与皇室联姻逐步上升。唐朝统治者一方面不满于旧士族高抬门第,自相矜伐,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孤傲不羁的关东士族进行抑制;另一方面却又对社会上崇尚门第的风尚欲拒还迎,不断打破自己的禁令与士族联姻。而关东士族虽自诩门第高华,不屑与皇室为婚,但在皇权的压力下、政治经济日趋没落的窘态中其婚姻态度也不断地妥协。如博陵崔恭礼曾尚高祖女真定公主,太宗也曾将“门称著姓”的崔宏道女册封为才人,崔铣尚中宗安定公主,崔嵩尚玄宗咸宜公主,崔杞尚顺宗东阳公主。[5]
到了唐代中后期,以安史之乱为起点,士族势力更是迅速衰落,加之中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唐末黄巢起义等事件使得社会战乱不断,至五代时期士族势力彻底衰亡。首先,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久,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且安史之乱的主战场集中在崔、卢、李、郑、王等关东士族的聚集区,士族因此多遭兵燹,饱受战火荼毒,不免举族迁徙,避处江淮,更有部分士族因此家破人亡。《太平广记》卷三三五《李叔霁》条载:“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在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颇能反映出赵郡李氏在战火波及下丢家弃业、妻死子亡的惨状,关东士族在安史之乱中所受的打击致使其元气大伤,许多士族就此衰落。而唐末的纷飞战火,更使得旧士族进一步遭受致命的打击,难怪至晚唐五代时,人们对所谓高门著姓甚至给予了嘲讽:“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其次,科举制度日益发展完善,自武后专政大崇文章之选使得以进士科进身之新兴阶级崛起后,旧士族依靠门荫入仕举步维艰,安史之乱后,“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6]门荫的衰落,标志着社会门第观念逐渐淡薄,越来越多的旧士族子弟依靠科举入仕,使得王朝上层官员“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拥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7]此时的旧士族显已变质,通过科举致仕的旧士族子弟,已由家族利益的代表者转而成为李唐王朝的拥护者,其鲜明的政治特征性逐渐消失,既然旧士族的性质已然改变,那么以其作为衡量标准的婚姻门第观念自然要走向衰亡。
三、《西厢记》反映的历史真实
《西厢记》中崔老夫人在“报家门”时便交待:“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扶柩至博陵安葬”,可知《西厢记》中的崔姓乃是七大姓中最为显赫的博陵崔家,如此身份设置便注定了“大姓自为婚娶,耻与他姓为婚”的门第婚姻观念,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老夫人的思想中的。
《西厢记》源于《莺莺传》,《莺莺传》开篇云:“唐贞元中,有张生者,……”可知故事发生在唐代贞元年间,此时已是唐代中后期,《西厢记》中虽然没有明确指明故事发生时间,但既取材于同一故事,则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不至有较大变动,加之《西厢记》中崔老夫人在第一本“楔子”的开场白中自报家门,又道莺莺“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莺莺的父亲当上相国,越来越多的士族子弟转向科举取仕时,即《西厢记》的取材背景,更应是士族阶层在唐统治者的不断打击下与自身的历史传承中迅速衰落的时期。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夫人的心态必然会随着旧士族阶层的没落与婚姻门第观念的衰亡而浮沉。老夫人出场时其生活境况已相当凄凉,崔相国“不幸因病告殂”,曾经“食前方丈,从者数百”的高门大户如今只剩下“至亲三四口”,她的娘家境况也从郑恒口中道出,“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因家中无人,来得迟了……”在旧士族已无法依靠世袭特权来保障家族的利益时,先人的亡逝,政治经济上的无依无靠只能造成家道中落,一派凋零之景象。昔日门庭若市,今日门可罗雀,战乱中还险遭家破人亡之危机,历经如此沧桑变故的老夫人心中难免形成极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必然时时折磨着久经世故的老夫人,老夫人定然明了旧士族之风光早已是“昨日之日不可留”,她的夫君崔相国在日虽然辉煌无比,却是旧士族以妥协于唐朝选制、维护李姓皇室为前提换来的一世之繁荣,虽然他们依旧想若无其事地标榜自己的族望,却改变不了自己已然悄悄变质的事实。理想与现实的冲击,必然使老夫人不断地挣扎与退让,最终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现实。
正是老夫人的这种矛盾心态,构成了《西厢记》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从普救寺被围时的许婚到事后的赖婚,从拷红折的许婚①,到郑恒欺骗后的赖婚,最终为张生与莺莺主婚,这其中既是对现实环境的挣扎与妥协,也暗含老夫人思想中婚姻门第观念的挣扎与退却,更侧面反映出唐代士族阶层的浮沉与衰亡。至于《西厢记》的结局,历来被认为是《西厢记》创作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因为其以“张珙金榜高中脱去白衣的身份,使崔张门当户对而最终实现团圆”,这是作者“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一种妥协,或者可以说是皈依和认可。”笔者却认为,金榜高中、迎娶莺莺之张生,是唐代安史乱后进士科新兴阶级崛起之代表,“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西厢记》之结局,既非王实甫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妥协,又非所谓“浪漫主义的理想”,而是唐代新兴阶级与旧士族在历史中升沉转变之概状的反映。
所以说,在对待莺莺的婚事上,老夫人一开始是想维护相国家谱的,因此会有普救寺许婚后的赖婚,但士族大姓日益没落的现状毕竟时时困扰着老夫人,此时莺莺与张生私通的事实又摆在其眼前,就造成了老夫人在拷红折中的缴械投降,不管此后老夫人在矛盾中患得患失,又做了如何的挣扎,士族阶层没落乃至消亡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这也就决定着故事的结局,必然是老夫人彻底地妥协与溃败。崔张爱情的胜利,是唐代门第婚姻衰落乃至最终消亡的最好注脚。
[1]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8.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69,2755.
[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5·高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841.
[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44 –3666.
[6](宋)王溥.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37.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