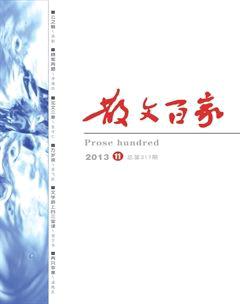孝婿父亲
2014-11-20袁学骏
袁学骏
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或说好闺女不如好女婿。我的父亲是一个好儿子,也是一个好女婿。
我姥爷是本村西头的,我家则在南头东小街,来往过十字街也不过三百米。他姓王,是他爷爷那辈从西边韩庄迁来的。他爹和他都是独苗,可姥姥又只生了我母亲,后来再也没有一男半女。我小时候,姥爷动不动就对姥姥发火。我在他们那头时碰到了几次,见慈祥的姥爷转脸就变成了凶神,对姥姥大声吼叫着。我本来就胆儿小,一见这场面,心里很害怕。我知道,他待见孩子,对我和我们弟兄姐妹八个一直都是笑呵呵的。有一次我问娘,为什么姥爷好对姥姥发大火。娘忧郁地说,是嫌你姥姥没有生小子,断了王家的根。不久的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你姥爷想要一个外甥,俺们商量把你过继给他吧。我说,过继了就得姓王,可不如姓袁好。娘说,你就还姓袁,以后你姥爷给你娶媳妇,你就打发他们入土为安,那处房子就是你的了。于是,我就嗯了一声。几天后,父亲就把我的名儿由五队拨到姥爷的三队去了,打饭便去三队的食堂里,放假干活也和西头的孩子们在一起了。姥爷很高兴欢迎我过继给他养老,姥姥更是乐得合不上嘴。姥爷还在地里逮蝈蝈、蛐蛐,变着法地哄我高兴。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
我虽然过了继,父亲也不是事先说定的养老女婿,但父亲却是真正关心和为姥爷姥姥养老送终的人。当年,由于母亲是独生女,姥爷一定要在本村为闺女找婆家,就找到我们人多的一家了。村里人都说,你算找对了,这一定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女婿。父亲也真的不负姥姥姥爷择婿的苦心。
记得平时有事没事的,父亲总要去西头姥爷家转转,看缺什么,担水不担水。没事就回来,有活儿就做。人们说,亲儿子行孝也不过如此。姥爷姥姥也从粮食上、布匹穿戴上不断接济我们,减轻了父母的经济压力。1963年,下暴雨,发大水,父亲西头、南头两头跑。一个半夜,大雨倾盆,姥爷的房子钻了山,水顺着南墙往下冲。我当时初中毕业,被大队派到县北的滹沱河上护堤去了。姥爷就戴上草帽,拿着两块砖,蹬梯子上房去赌窟窿。下来时,一不小心蹬空了,啪嚓摔了下来,腿疼得很厉害。他就喊姥姥,快来拉我。姥姥出来拉不动他,就去后邻喊纪保林来,才把姥爷背到屋里。这时,父亲赶到了,他上房去把窟窿堵死,下来便去找赤脚医生。大雨滂沱,医生迟迟不到,父亲就又蹚着水打着伞去催。医生终于来了,一摸姥爷的腿说,膝盖摔崩了,先好好躺着,吃点药止疼吧。父亲便守在姥爷身边。姥爷对我母亲和孩子们更不放心,就催他回南头去。父亲说,那头的房子顶了木头,不会有事。就一直呆到天亮,又去公社医院请来医生。这医生诊断的也是膝盖崩裂,只有做手术、打铁扒子。姥爷说,六十多的人了,还值得打铁扒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只要能拄棍走就行。后来,医生只给他打了石膏夹板。几个月后拆了石膏,膝盖没有长好。这中间的医疗费用,都是父亲主动拿的。姥姥要塞给父亲10块钱,他坚决不要。从此,姥爷就拄起拐棍,下地劳动就不行了。队上便让他去看枣树趟或给他坐着能做的活儿。父亲便对母亲说,他姥爷身体不行了,该咱接济他们了。从此,凡是碾米磨面、队上分粮分菜、各种背背扛扛的事,只要我不在,父亲全包了下来。母亲也是两头忙。姥爷的邻居们都说,你给闺女寻本村的婆家可沾光得济了。
姥爷的北屋被大水冲得裂了缝。父亲就张罗着准备拆盖。一天,他指挥着乡亲们把姥姥家的东西搬出来,让老两口住到了小西屋,北屋当天就拆了个平。接着,父亲就丈量尺寸,拣出坏木料,购买新檩条、椽子和苇箔,又请来木匠们凿檩铆,做新窗户。姥爷拄着棍转来转去,帮着父亲指点着。要打房基了,才发现房基下面是抗战时的地道,原来房子裂缝也是水灌地道塌陷造成的。父亲就找人往下挖。到一丈深的时候,他就跳下去试探是否已经到底,还叫人扔下木夯。他用夯试了试已经是实的,却仍然分拨儿打夯。再填上土再打,直打到与地面平。父亲说,这回牢靠了。我家翻盖房子,父亲是主事的,也没有费过这么大的事。他和牲口棚的伙计们说清了,白天你们喂,黑家我值班。姥爷的房子原来是土坯墙,这回盖成了表砖房,也比原来高了宽了些。姥爷姥姥住进去觉得很敞亮。因为不光高了,四壁也抹了白灰,在屋里觉得天明得早黑得晚了。姥姥对父亲说,没有你,俺说不定要砸死在屋里。没想到不久姥姥得了一种叫寻衣摸床的病,头过年便去世了。那时,我已经考上正定师范。姥爷见我远走高飞了,就对父亲说,你大的落到了北京,二的也指望不上了,我要了你三的吧。这样,弟弟就替我跟了姥爷。一封电报拍去,说姥姥病危,我就赶紧请假回去。一进村就奔姥爷家,见门口挂着白幡,知道姥姥过世了。父亲在院里忙里忙外。我进了屋,就趴在姥姥灵床上哭“见不了面的姥姥哇”。一会儿,姥爷说,行了行了,吃点饭去吧。吃着饭,想起小时姥姥给我烙饼煎鸡蛋,泪水更止不住了。第二天,哥哥也从北京赶了回来。晚上,父亲把我们弟兄三个叫在一起说,你仨听着,现在你姥爷要了三的,可打幡摔瓦要分一分工。便对哥哥说,你是头大的你打幡。又对我说,你是二的你摔瓦,这样让乡亲们看着好看。还说,以后这里的庄户还归三的。我们都表示同意。第二天中午,按着乡俗出大殡,我第一次身穿白衣重孝,大声呼唤着姥姥;第一次拿着有黑字咒语的青瓦,在胡同口那圆圆的柱定石前跪下,狠狠地一摔,便瓦片飞溅。围观的人们说,摔得真烂,是大孝子。后来姥爷去世,父亲也让哥哥打幡我摔瓦,弟弟继承家业。外人都说这家子真好,弟兄们不争不抢。父亲听了别提多体面了。
弟弟结婚,按父亲和姥爷的商量。先在南头我家,过年时便搬到姥爷家去。这场婚礼,全是父亲一手操办的。记得每年正月初一上坟,身体尚好的父亲总是先去村南姥姥的坟上化纸放炮。姥爷去世后,虽然有过继的弟弟给姥爷上坟,但父亲仍然先去村南的,再到西南我们袁家祖坟上。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上坟一般都靠我们和我们的子侄了。但父亲总嘱咐我们:上坟要先去村南。这已经成了我家的一个规矩。
父亲落了个好人名声,也有个好女婿的口碑。后来,我的妻子也是独生女,便无形中受了家风的熏陶,在二十年前就把岳父岳母从乡下接来省城。进入新世纪,儿子成了家,儿媳妇也是独生女。我便在他们新婚典礼上告诉儿子,将来孝顺你丈母娘比孝顺我们更重要。儿子说,没问题。生了孙子,一次饭桌上讨论起孙子将来会找什么样的对象,都说可能又是一个独生女。我一想,这会儿人们少生优育,孙子当好女婿的机率甚高。看来,我们当好女婿的家风要代代相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