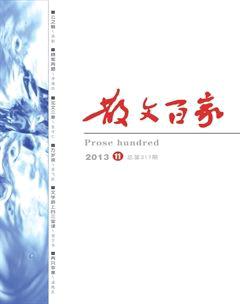栽种光明
2014-11-20刘月新
刘月新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圣经》
不幸的海伦·凯勒偏偏是个才女,她对光明的渴望渗透每一个细胞直至骨髓,因此用骨头雕刻了耀眼光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它教人惜福,惜光,惜缘,珍爱世间万物。当有一天母亲的“光明”出现问题,我即刻就想到了她——此时母亲的感受不就是海伦的感受吗?只是海伦把那锥心的痛与渴望变成美丽文字滋养世人,母亲文化低浅就只能郁闷忧伤而再无排解的良方。我愈加理解了病中的母亲。
母亲原本拥有一片光明,并尽情享受上天的这份恩赐。一天,当光明突然想离开,她就惊慌失措——她被突如其来的黑暗与恐惧一并吞没。
在B市一家眼科医院,术后三天的母亲,早上做完检查,回病房吃饭。暂时揭去纱布,眼前展现了一片光明——这是母亲始料不及的——光明以最快的速度又回到她身边。
这屋里真敞亮啊!
母亲这么快就恢复了视力?哥哥惊诧着。
娘,你看,东墙上有什么东西没有?
有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幅画——一盆菊花,白色的。
母亲像个识字小学生,用手指着,一字一顿。
母亲住的病房,床头对着的墙上,挂着一幅精美小画。
娘,你看月新手里拿了什么?
母亲和哥哥坐在床头。兴奋的哥哥让买饭回来的我定定站在门口,让极度兴奋的母亲接受一次检验。
月新左手端了个饭盒——右手也端了个饭盒。
你看两个饭盒都是什么颜色,上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母亲用手指划着,一一说了出来。
十天前,母亲晨起来到院子里,想看看韭菜、小葱、生菜又蹿出多高,这是那几天她清晨的功课。望一眼,没看见;又望一眼,还是没看见。母亲纳闷了。她闭了闭眼,然后使劲睁开,再看平日里正一点一点绽放着绿色的菜畦,眼前出现的是大片大片模糊的红。天哪!我的眼——
在我和哥哥工作的小城,母亲被诊断患了眼底出血。
又是眼底!
此时的母亲,该是怎样的绝望与焦灼!她肯定在埋怨上天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十年前那一幕定像还魂似的又浮在她眼前。也许,它根本就不曾离开过,就像空气中的尘埃像潜伏在体内的毒素。
2005年寒春的一天,母亲从灶堂抬眼看南邻的屋顶,怎么看那烟囱都是双的——弯弯曲曲、模模糊糊的双。再转眼看窗棂,窗棂也尽是一片扭曲的放大的模糊。
母亲一脚跌进黑暗。
在北京同仁医院,母亲得以及时救治。
那一次,是母亲的右眼有疾——眼底缺血。
母亲眼病得到有效控制,右眼视力却直线降了下来。
右眼看不清,还有左眼呢。老天爷帮忙,可别让我瞎了眼。母亲退而求其次。她老人家毕竟不是海伦·凯勒。
相隔十年,不曾想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母亲的左眼。
这一次,不是眼底缺血,是出血。
眼科大夫给母亲打了止血药,又开了口服药和滴眼液,叮嘱慢慢观察,待两个月后再确定是否手术。
难道光明真要离开母亲?
这慢慢观察,本意是沉住气、静下心来观察;言外之意是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睡怎么睡,一天中生活的结构节奏无需改变。可这是母亲的眼出了毛病啊!母亲处在极度惊慌与焦灼中,我们哪能平心静气地“慢慢观察”?
去北京同仁医院!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母亲愁苦地直摇头:我这糟烂身子哪能再坐到北京?无情岁月风卷残云般消磨着母亲,使她像秋后一株收割了果实的朽高粱,随时都有坍塌倒地化为污泥的可能。
小城有家眼科医院,周末有天津专家来坐诊手术。带母亲去检查,一位沉稳的女大夫给出建议,保守治疗吧。
母亲看似一日三餐平平静静,其实不是。她的话很少,眼神散漫、空洞无物,漠漠里透着怯怯与不安。
我在客厅、阳台,养了许多花。之前的二十年间,戒了烟的母亲,养花成了她的最爱。如今,只是偶尔在花们面前驻足片刻,说声“长得可真大”,如此而已。那些诱人的绿,娇艳的红,都不能打动母亲。不,不是母亲心性惰懒、趣味索然,是病魔对母亲的掠夺,是母亲被掠夺后的无能为力。母亲眼底出血,心底也出血。我从身后看着蹒跚的母亲,心就一揪一揪的疼。我真想揪住那个夺去母亲光明的家伙,狠狠揍它一顿,再把光明双手交还给母亲。现实是多么残忍!
母亲也酷爱电视。父亲说,你娘每晚趴在被窝头上跟电视对命,人家不说再见她就不睡觉。而今,母亲对墙上的电视视而不见。我不敢造次——母亲来了这数日,我给电视放了长假,让它领着里面的动物与自然、青衣与花旦统统到世界各地旅游去了。
看来,我的眼即便是治好,也不能绣花割鞋垫了。
真是的,哪里有病不好,单单让我的眼出毛病。
可怜的母亲,就在儿女们眼前孤独着,寂寞着,惶恐着,焦灼着。
母亲的大半生,掐两头去中间,爱好趋向比较鲜明。中间阶段是苦中作乐,职业是挖沟、挑河、修抬田、挣工分,业余爱好是打草晒草搂葛挠、养猪养羊养蚕,绝活是编织小竹筐。而两头则是,让绣花、养花、割鞋垫填充的。童年的母亲,衣食无忧。她的爹爹开洋布店,常跑天津卫,她就有了独特的绣花条件。母亲绣的各色旗袍、花兜肚、窗帘、洋枕头,我幼时都见过,那真是龙飞凤舞、花枝招展鸟语花香的大展示。母亲绣花时常哼着《苏三起解》、《秦雪梅吊孝》,还有别的。嗓音尖尖的,像从针眼里挤出,再在屋里一圈一圈地绕。看我羡羡地瞅她,就放下针线,翘起兰花指,提眉瞪眼(母亲的双眼皮底下,有一对好看明亮的大眼睛)唱上三两句,又继续她的龙飞凤舞。母亲绣的枕头,有圆身方头的,有腹部扁平的,我把扁枕叫做洋枕头。枕头上火红的石榴像真的,美丽的凤凰像活的,山水菊花牡丹蜂蝶相衬映。属于我的那只小洋枕,白底上绿草青青,野花盛开,一只白绒球似的小猫咪从一侧跳出,胡须奓立,双目圆瞪,歪首举爪去扑捉一对翩翩的花蝴蝶。这只洋枕成了我幼年不离手的行头。奶奶一句话惹我不高兴了,就抱起枕头往娘的屋里跑;娘惹我生气了,抱起枕头又气嘟嘟跑进奶奶的屋。一明两暗一个套间的土坯房里,我抱着小洋枕来回穿梭,脚下踏出一条明晃晃的道。每每这时,别人就打趣,小芳,你这是干啥啊?我生气呢!
我们兄妹小时穿的鞋,鞋面是粗布的,鞋帮的前脸却给母亲打造得像披了彩的盔甲。母亲总是割出凤凰牡丹祥云和金鱼图案来。晚年的母亲,带着满身伤痕从田野回归家庭,她老人家又拾起当年绣花的手艺——割鞋垫。我明白,母亲是割舍不下钟爱了大半生的刺绣艺术。年年都送女儿鞋垫——福字喜字吉祥字,花草鸟鱼五彩云。姥姥满心欢喜地送,外甥女欢天喜地地接,还有我的丈夫的。一年一年,衣橱的袋子里满满的都是鞋垫。不忍心跟母亲说开,她就充满自豪与自信地照做不误。
母亲常常动情地说,我就是喜欢绣花。
喜欢绣花的母亲,突然在某一天将要失去绣花的资本。这对母亲来说,不啻从健壮的肢体中抽去一根筋。
我们兄妹几个围着母亲坐。母亲幽幽地说,我的眼要是真瞎了可咋办呢?神情是那样的落寞与无助。
瞎了不用怕,我每天用根棍牵着你。孝顺的妹妹此时还不忘冷幽默。
我正好内退,有的是时间,就天天守着你。细心的哥哥动了真感情。
我也立马表态,真那样的话,我就不上班了,保证不会扔了你。
母亲笑了,笑得开心知足。我相信母亲,相信我们的话。
但是,我还是看见母亲的心里翻腾着,满满的都是不甘。
黑暗与黑暗的恐怖,笼罩着母亲和全家人的心。
母亲在我们家住着“慢慢观察”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心无旁骛地静观病态,倒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打探撞荡。听说B市有家眼科医院,便匆匆赶去实地考察,并意外获悉有知名眼科大夫周末过来会诊手术。就带母亲去做检查。
检查的结果,决定当晚实施手术。
我和哥哥做此决定时,是那样的毅然决然,想想自己都感动。后来一想,不免又有些莽撞和慌不择路。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突然没有了眼睛。我坐在母亲脚下哭,母亲木木地在原地打转,像被施了魔法,一句话也不说。醒来,更加惶恐。人要能做到遇事不慌,真是一种修炼啊!
动身前两天,母亲从我们交谈中听出有可能要做手术,吓得一直没合眼,这是术后母亲说的。母亲有个误解,她认为做眼底手术,需把眼珠子拨拉到一边去,手术刀在黑洞洞的眼窝里连削带剐,要不怎么叫眼底手术呢?
这一天是2014年3月22日。
晚上,母亲被领进手术室。一小时五十分钟后,又被轻轻送出。从手术室走出来的母亲,左眼给纱布紧紧包裹着。
我和哥哥庄严地从医生手里接过母亲,就像接过一个神圣的希望。
我想,怎么着你们俩也陪我进去吧,竟一个也没有。
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可啥都听见了。医生又是剪子又是刀子的,咔嚓,咔嚓,围着眼眶一遭一遭地绞啊。
母亲轻轻地埋怨,像有小锤一下一下敲打着我的心。我睁开我的明眼,透过暗夜,仿佛看见手术室里一个挣扎的灵魂在哀嚎。置身于黑暗中的母亲,恐慌与无助任其放大蔓延,竟没有一块能使其缓冲抑或落脚的温厚之地。
我们歉疚着无奈一笑,娘,那是手术室啊,哪是我们随便就能进去的。
也是。没有多少住院经历的母亲,就笑了。
我只是一个人在里头没着没落的,心里慌呢。
上午,母亲依着床头输液,眯着那只并不明亮的右眼。
我咋看到被子上有只眼呢?
啊?我以为母亲在说梦话,随即又惶惑起来:难道是恍梦成真?
跟眼一般大,就是眼的样子。莫非昨晚上医生没把眼珠子扒拉过来?莫非眼珠子还翻着个儿?
母亲并没有发烧。可她为何会出现如此幻觉呢?看来,这个关键部位的手术把母亲给吓着了。
母亲真是老了。
在家我常抱怨,人家的眼都不出毛病,单单我的眼出毛病,来这一看,都是眼有毛病的。你看,老头陪着老婆的,老婆陪着老头的,儿女陪着爹娘的,爹娘陪着孩子的。像是有谁招呼着,把这些人都给集合来了。
你看那个小小子,也就四岁吧。这么小咋也得眼病呢?刚才看见孩子在楼道里哭,他娘抱着,他爹守着。唉,大人闹眼病像掉进无底洞,孩子不更要命吗?孩子不好受就哭,可这眼病偏偏又不能哭,还不如大人替他病呢。
父母不但愿意替孩子去病,甚至愿意替孩子去死。我和哥哥都是做父母的人了,能掂出母亲这话的分量。反过来,做儿女的又能做到几分呢?
老了的母亲依然可爱,自己在病中照常牵挂着别人。
其实,我对光明是很在意的。我曾细细观察过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些宇宙星体,因其特性,都让我景仰,让我感恩。太阳胸怀博大,普照世间万物。作为享受恩惠的渺小之人,面对她,就像一个肉身面对崇拜的神。月亮洁身自好,一抹清辉洒向大地,给人带来多少光明和勇气、诗意和遐想。星星虽小但众多,且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不卑不亢。有了她们,我们生活的地球才有了光明、阳光和温暖,有了绿色、生机和万物的再生,有了永恒。还有一种光明,同样让我神往。她像蜡烛、像灯火,普普通通,看似微不足道。或许因了她的普通和微不足道,因了她跟每个人贴得太紧太近,一些人就忽略了她。她虽然渺小、微不足道,却温暖温柔,有温度,有生命,还能传递、传承。扯一缕栽在心里,用心灵去滋养,日积月累,她就会生根发芽,就会放出光明。
上小学二年级时,一桩小事几乎影响了我一生。一天,班长党代一阵风旋进教室,后面跟了年轻的班主任。老师说,同学们静一静,风云同学的新铅笔丢了,都看看自己的书包,谁见到就给她,好学生不拿别人的东西。全班同学都抬起头,你看我我看你。党代给老师出主意,让人们拍手“嗷嗷”,看谁脸红就是谁偷了,再不行就翻。老师不置可否,党代就带头拍手“嗷嗷”起来。这一“嗷嗷”不要紧,我的脸上突突冒火,脖子变粗变硬。那一刻,我真怨娘把我生得跟别人不一样,只恨桌子没洞、地上没缝。当党代真的从我书包里翻出一支铅笔时,我懵了。至今,都不清楚当时是怎么回的家。从此,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吓出了病。我不敢再去上学。
是母亲把我从黑暗中领了出来。
母亲认定是有人陷害我。她牵着我跟随老师走进教室,说,孩子们,听说从小芳书包里翻出了新铅笔。我知道,那不是她的。可也不是她偷的,自个的孩子我知道她。如果真是她偷的,今儿个当着你们的面我就把她打死,我可不要偷东西的孩子。
后来,想起这事,觉得母亲有些强词夺理。但母亲那一顿声嘶力竭的吼,确实给我壮了胆。几年以后,母亲跟党代母亲在地里相遇,她告诉母亲,当年“拾”铅笔那事,是学校一位教师(风云的爷爷)指使她家党代干的。那人,是我的本家爷爷。
这天,在走廊里看到隔壁男孩,眼上蒙了纱布。他也做了手术。我微笑着看他和他的母亲,年轻的母亲也还我一个温柔的笑。小孩站在窗前看院子里的汽车,他没有哭。
母亲手术的成功,使得病房火爆起来。母亲说。
你们没有白花钱,我成不了废人,你们也少受累啊!
这个医院真好,像住旅馆,又宽敞,又干净。我和母亲和哥哥住的单间病房。
娘,不把你的眼彻底治好,咱就不回家了。哥哥在逗母亲。
说的是呢。我真舍不得走了。
住在有母亲的医院里,心从未有过的平静。
只是有一点不好。别的医院病房里都有电视,这家省级标准的医院,单单少了这样。哥哥似在抱怨。
挺聪明个孩子咋说傻话呢。这是个啥医院,你不知道啊?一帮瞎子,等着手术的,做了手术的,哪个能看电视呢?
我和哥哥笑了。
住院以来,母亲的话似乎特别多。白天说,晚上也说。说她的过去,说我们的过去,还有别的。她感叹着,悲伤着,惋惜着,兴奋着,自豪着。头两天我想制止母亲多说,怕面目表情太丰富影响刀口愈合,可母亲根本就不听劝。她说好容易逮着你们,有多少年没这么说话了。我这是因祸得福呢。
听了这些,我的眼和心都湿润了。我想哥哥也是。
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一天天变老。有好多事情,在母亲儿女之间不知不觉就调了个个儿。儿女对母亲的依恋依赖,正渐渐被母亲对儿女的依恋依赖所替代。想想这些,觉得又悲哀,又崇高!
陪母亲住院,心是那样的虔诚。我变得越发殷勤多礼。不管在病房走廊食堂开水间,或是检查室,都是挓挲着手走路,时刻准备扶别人一把。在电梯口,我抢先一步按下按钮;在电梯里,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在开水间,我先帮别人打上开水,不管他是年老还是年轻,也不管眼上是否蒙了纱布。我的心里暖暖的,亮亮的。
一天上午,给母亲检查完毕,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院了。望着医生真诚和蔼的脸,我和母亲和哥哥都微微一愣——我们竟没有做好出院的思想准备。
待拾掇完东西准备下楼,母亲一遍一遍环顾厮守了十天的病房,似有万般不舍。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问我,有两天没听到那小小子哭了,昨个在楼道里问他娘,说手术蛮好,他也该出院了吧?
母亲又说,待下次来复查,不知能不能再见到这些人。
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就要做那么多事情。可见,一个失去了光明的人,是多么渴望得到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光明啊!
再见了医院,再见了医生!谢谢你们!拜拜!母亲喃喃着语无伦次,像个得意忘形的孩子。也谢谢你们俩!回过身来的母亲微笑着,身披万道霞光。她那激动心情的肆意释放,真是可爱又动人。
栽种光明吧,在你我的心里。
其实,不管你的眼睛是否有疾,只要心里有光明,你就拥有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