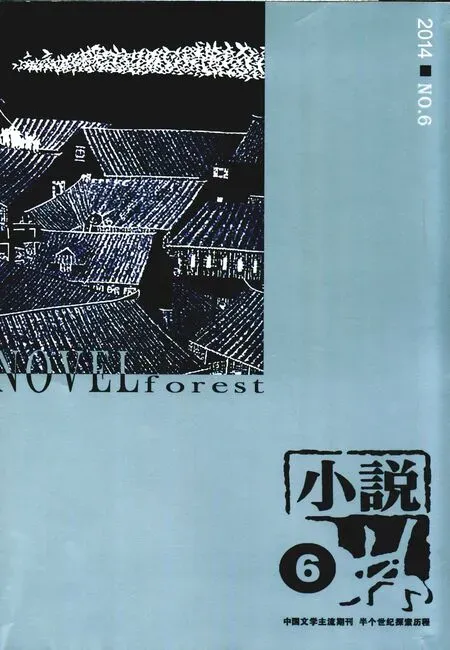《雨城》创作谈
2014-11-17◎丁墨
◎丁 墨
《雨城》创作谈
◎丁 墨
如果将人生分作几个阶段,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叫做等待。等待有很多种,等待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这篇小说是在张家口的一间旅馆写下的,我不是张家口人,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工作。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影视。在四月份的时候,导演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要拍摄一部家乡的电影。导演是张家口人,也是我的师哥,这部戏也将是他的九十分钟处女作。七月份北京的事宜交接完毕后,我便背着沉重的行李北上到张家口,火车路过河北的一些城市并不怎么发达,所以张家口在我脑海里形成的第一幅画面是一个满是牛羊的乡镇。下了火车才发现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个城市在我们国家能算的上是四线城市。
到达宾馆房间,见到了导演,还有一位长头发的中年男性,他是导演请来的制片主任,我们都称呼他方老。方老年近六十,在影视圈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大上好几年。我在方老的第一印象是一名送水工,我那时刚下剧组,肤色偏黑。要说到张家口的送水工,我不得不佩服是我见过最牛的,双休日不给送,上午不给送,电话打晚了不给送。有时候想想恨不能我们自己去装好水背回来。
剧组开拍前我在张家口从事的工作是导演助理,有时候都担心干顺手后忘了自己还是一名演员,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我陪着导演、制片人和制片主任去找过的投资方便有十来家,之前他们还找过几家。张家口人的思维还很滞后,并且大多数持观望和好奇的态度,更有冷眼相对的。作为新人我和导演只能默默忍受,方老是干过大戏的,和很多知名导演合作过,每次谈判回来总是骂骂咧咧,我便到走廊尽头的窗口发呆。小说里的钟楼和金狮子便是在那个窗口发现的,我每天在那个窗口要站上四到五个小时,尽管如此,导演工作室传来的争吵声也是不绝于耳。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一点点过去,站在窗口的我衣物越穿越厚,工作室的争吵声越来越小,窗外的钟楼和金狮也失去了光泽,而拍摄的资金如同笼罩在我们上空的乌云久久不能散去。这个城市被山环抱,窗外不远处便有一座,我是总想去爬爬的,但一直没有去。小说里海的尽头的原型便是那座山。
等待是个相当虐心的过程,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锐气消磨殆尽。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总是“等几天”“再等几天”。他们不知道,制片主任最先定好的班底——摄影、美术等等,在这些个“等几天”里渐渐地离开了,他们也要生活,要挣钱养家,要买房买车,要养子养老,投资方要考虑利益回报,要你请客吃饭,要考察你的实力,要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要……
在与投资方见面及通电话的这几个月,我发现见面和电话,虽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没有大的实质上的不同。有的人认为见面更放心,实际上则不然,因为那时候他无处遁形被逼到桌面上,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好听话,还不如在电话里咬文嚼字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没签订合同,话语里的真实性便不置可否。我们被晃了太多次了,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与“欺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赤裸裸的现实和残酷的等待是对人性尖酸的考验,这个过程毫无享受可言。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印钞机,眼睛里面全是钱,但是,这有错吗?!也许钱更真实,至少它不说谎。
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一只人偶,四肢和中枢神经被一根细细的电话线远程操控着,“他们”即使不在场也能精确地摆弄我的躯体,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我的个性和冷静在渐渐流逝,我的脸像一朵还没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等待着凋零,我的表情逐渐单一僵化,一张写满窘迫的肉皮已经常态化。我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我的眼神开始失焦,世界变成了灰色,这时候我才发现在外面行走的人,头上都有细细的白线,同我头上被牵引的一样,只不过有的多有的少而已。
晚上总是会有些奇怪的梦在脑海里翻转,有时候白天也做,时常醒来身上便有一些细汗。那时候我是要披上风衣去走廊尽头的窗口眺望大山,我是总想去爬爬山的。
前几部小说《木偶娜娜》《白鸦》《月牙儿》讲的是主人公金文一生的三个时期,《雨城》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金熊是金文的儿子,但是剧情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名字上的联系,只是本人的一个爱好,它就像一根命运线一样牵动着生命,小说与作者,作者与生活,这一切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