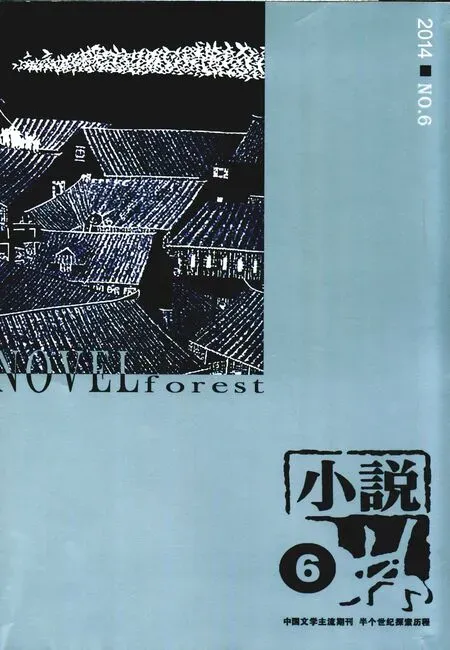药材铺
2014-11-17◎徐岩
◎徐 岩
药材铺
◎徐 岩
1
每周五的下午三点,女人骑一辆旧自行车,来药材铺诊病抓药。
药材铺的店面不是很大,四五十平方米。店子无窗,仅有两块门板上嵌着乌麻玻璃,打开了就代表着正在营业中。值得一提的是悬在两扇门上面的那块匾,烫了金色的漆字,上面的落款和印章却用了朱红色,也是特意刻上去的。
整条街都是沉旧的气息,店铺一间挨着一间,全部都是老房子,有些像名扬海外的巴洛克建筑群,也有些像南方小镇的老街,斑驳古朴。
铺子是有全套的经营执照的,里面靠墙摆了一拉溜的木架子。架子有两人高,只差一点就要顶到棚顶了。无数个书包大小的木头匣子装在木架上,用来盛那些中草药。而每个木头匣子的面上都用油漆写上一味中草药的名称,什么狗脊、地龙、余甘子之类,很有韵味也很有意思。
其实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呢,那就是铺子里的两个人的衣着打扮,让你看了有些懵懂。男人年纪大,穿一袭长衫,有些像剧场里说相声的喜剧演员。女人岁数小些,穿件半截子白大褂,喜欢在屋地的中央走圈。
穿长衫的男人和穿白大褂的女人都能给客人抓药,一味一味的秤好了倒在事先摊开了的纸片上,不多斤两也不少一钱。虽说两个人都能抓药,但两个人却都不是药材铺的老板,不是老板那就是员工了呗,替人家打工的干活也就得仔细一些。
铺子里的秤很小,有两种,大点的有秤杆秤盘。秤杆细如孩子上学时用的铅笔,秤盘也小,跟平时吃饺子盛酱油醋时用的小碟子。再有一种就是搁置在柜台上的天平了,是用来秤更少的药剂的。这天平也是药材铺的道具,摆在柜台上就是给人看的,以示买卖的公平。
就是这样,有客人来抓药时,两个人或者一个抓药一个下单子收钱,或者两个人一起忙活。他们的举动是默契的,也是麻利的。药材铺几十平方米的小屋子因了他们的忙碌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两人间是有称呼的,穿长衫的男人管穿白大褂的女人叫大平护士,大平护士则称他为陆大夫。小小的药材铺里虽然只有这么两个人,却职称齐全,开药房吗,是不亚于开诊所行医的,也得医生护士齐备,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药材铺开在了居民区里,其宗旨是为民所用,生意相对来说,还是挺红火的。
2
女人每周五的下午都是准点来药材铺抓药,骑她那辆旧式的永久牌自行车。女人长得清秀,乍一看有些像林青霞。也像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歌手。一条肥腿裤配件蓝工作服,给人干净利落的感觉。
女人来抓的药永远都是一个偏方,都被陆大夫和大平护士在心里背熟了,背得滚瓜烂熟。药是治哮喘的,五味子加一服黄芪,土木香二两、小茴香七钱、甘草半斤、胡桃仁四两半、瞌藤子五钱。拨均匀了包好,分四次喝下。
女人抓药的时候话很少,几乎是不说,就站在柜台边上看着陆大夫给她称药。包完了就付钱,然后将药放在提来的一个手袋里。
女人出药材铺之后,会推着那辆自行车走上一段路,直到出了胡同口,才抬腿上车,蹬了走远。她的背影正好被刚刚降落的太阳点染了一回,竟是很美的一种金色。金色由大变小,渐渐地远去。
陆大夫就看呆了,他倚在门板上,许久都不想把眼睛收回来。
这会儿,收拾称盘的护士大平会说,我猜想,准是给她母亲抓药,这女人蛮孝顺的。
陆大夫还是没有把视线收回来,就接了大平的话说,何以见得啊?
护士大平则说,药是治哮喘的,剂量又大,可见患者是位老人。
陆大夫却说,你言差矣,药是给男人喝的。
护士大平说我怎么会相信你呢?
陆大夫没有说答案,只是转过身来朝正在弯腰收拾柜台的大平狡黠的一笑。
药材铺就做了一天以来的第九单生意。四服药卖了三十二块钱。去掉成本挣十五块钱只多不少。
大平噼里啪啦打算盘子拢账的时候,穿长衫的男人点了根烟卷,边吸边想着什么,他的脸上已经泛起了一丝倦容。
在药材铺里,大平护士有时候也管陆大夫叫大叔。可能两个人的辈分在那摆着呢。大平叫的时候陆大夫也不生气,本来岁数就有些偏大吗,她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一天到晚的就他们俩人,说耳鬓厮磨夸张了点,但说朝夕相处就不能说不贴切。要知道药材铺的老板是不经常来的,月初或者月底的时候能露上一面就不错了。有时候连着好几个月不来一回呢,就在电话里吩咐把卖药材赚的钱打进银行卡里。
陆大夫和大平护士两个人都知道,人家是有更大的买卖需要亲自打理呢。那可是一桩大买卖。但具体是什么买卖,两个人却不知晓了。他们从没问过,店主也从来没提起过。
可有人读到这就会提出疑问,说店主这不成甩手掌柜了吗?那进药怎么办呢?
店主是信任穿长衫的男人老陆的,也信任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大平,一两个年头了,整个的把店铺交到了他们俩手里,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经营着,扶困帮贫,救死扶伤。要说他们卖的每一味药材都是治病的,得把患者的痛楚去掉,得把病人的病情减轻。称出去一百剂药也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正因为如此严谨如此敬业如此守信和如此细心,药材铺的生意才红火得一直开着,没有在几次医药行业经营整改时被勒令关门。
药材铺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存在于道外十一道街的偏巷子里。
3
离药材铺不是很远的胡同口,是一家浴房,门上一块招牌叫小红洗浴。廊檐下依次悬了几盏红灯笼,是那种日式的筒状灯笼,每个上面都用金线绣了个福字,极为显眼。
陆大夫每周都要光顾一回小红洗浴,去那里的热水池子里泡个澡,再找那个梳短头发的扬州来的搓澡师傅搓上一搓,浑身的筋骨就会无比的舒坦。
陆大夫是单身一个人,年纪快奔五十岁使劲了,可身子骨倒还硬朗,据说他的家不在城里,而是有很远的路程。陆大夫起先是奔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来的,从那边的医院退休后就来北方谋生路。因为南方的医生惯于用中草药给患者诊病,再加上多年来的临床试验,陆大夫就在用草药方面有了手艺,很得店老板的认可。
小红洗浴的老板是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模样长得挺俊,男人在监狱里蹲着呢,也就落了个逍遥自在。大家伙都知道她姓杜,叫杜岭红,名字中既有男人气又有女人气,多少的有些怪异。杜老板喜欢打麻将,吃了午饭就到浴池二楼的包房里开个间,支上麻将桌,打个昏天黑地。女人性格泼辣,谁惹着她了张开口就骂,可唯独对药材铺的陆大夫好,只要陆大夫来澡堂子洗澡,女人都会停下手里的麻将一会儿,去休息大厅跟陆大夫打个招呼,敬上一壶好茶。其中的玄机只有她们两个人知道,女老板是陆大夫的病人,她每个月都要吃一两服陆大夫给抓的药,治肾虚。倒不是抓药的钱能省多少,只是那药吃着好使,拿杜岭红的话说,吃了陆大夫抓的药浑身热乎,感觉轻松多了。
当时,女老板去临街的药材铺找陆大夫诊病时,还有些不好意思,介绍病情时显得极其委婉。陆大夫却很爽直地给她说了病理分析,然后下单子开药,手拍胸脯子说不到半年就能治好。
果然,女老板服药仨月多,病就有所减轻,使得她甚是欣喜。就给陆大夫买烟卷抽买好酒喝,还时不常就请陆大夫下小酒馆。在她看来,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陆大夫不就是她的恩人吗,她找人打听过,这病不去根的话就得发展成尿毒症,是对其生命有直接威胁的。
陆大夫在酒馆喝了小酒之后,就有些昏昏然,万分激动地拉了女老板的手想做成好事,却被女人拒绝了。女老板很直率地说她都有几年没碰男人了,都是这病闹的,由肾拐带妇科,着实痛苦了一阵子。但是,女老板却跟陆大夫说,你要是想做那件事就来我开的浴池吧,妹子帮你找,保你满意。
陆大夫果真在一次酒后去了小浴池,泡澡搓背之后被服务生带到了二楼的小包间里。再由服务生叫来一位女孩给其按摩,中间,两人成就了那件好事。陆大夫不差钱,临走时掏给女孩两张百元票子,算是酬谢。那女孩也没有推辞,收了一张退给他一张,笑着说是红姐吩咐的,给陆哥打折。
连着去了两次后,陆大夫知道了经常给他按摩的女孩叫云云,好像姓侯。陆大夫问过一次,从女孩的表情上看可能是假名,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陆大夫单身一个人,从南方来这北边的城市里当医生,算是给人家药材铺打工吧,钱赚得多和少无所谓,关键是生活上得充实,千万不能寂寞。
药材铺的老板是他的一个表亲,岁数上比他小,赚钱上却有门道。开药材铺是一方面,还往一些边境城市倒腾紧俏的药品,不管多大的业务都是他一个人跑,赚或赔都一个人挺着。
陆大夫想好了,他只干三年,等干满三个年头了就回南方老家去,颐养天年。
4
每个月中第三个周五的傍晚,周师傅会驾驶一辆半新不旧的大卡车来给药材铺送货。一辆车两个人几大纸箱的药材,人是他和小徒弟丁四,一个聋哑孩子,听说中学还没毕业呢就被父母给送到周师傅门下当小工了。货是药材铺的老板在外省采办好的,雇了周师傅给运回来,他自己却不护送。多半是按照陆大夫开具的单子配的货,其中中草药居多,兼容一些少许的西药片。
陆大夫和周师傅两人将单子交接后,便打开车厢卸货,周师傅站在车上边往下递货,丁四和护士大平两人往铺子里搬,陆大夫在门口验数。二十分钟后几个人才忙完,护士大平按单子给周师傅结运费,陆大夫坐门口一把木椅子上吸烟,丁四咕嘟嘟喝凉开水。然后四个人锁店铺去胡同口的王记小酒馆吃饭,两个炖菜加肉包子,吃得热火朝天。这顿饭由护士大平结账,是药材铺的老板在家时就定下的规矩,来送货了不但要结账还得管饭,做买卖么咋也得活络些,太死性了赚不到大钱。
包子是刚出笼的,山东包子,个大馅多,味道鲜美极了。一屉十个,丁四自己就得吃两屉,还不算菜和稀粥。三个人都不拦他,任由他吃,半大孩子吗,正长身体的时候,你不让他吃饱咋行?护士大平的饭量小,三两个包子就撑得不能再夹菜了。她便捧一杯热水不紧不慢地喝,看周师傅和陆大夫两人喝酒。两人的酒量都不大,每人只一玻璃杯,二两左右,喝了解乏。其实周师傅酒量还可以,但他不能多喝,因为饭后还要开车去城西的一家小旅馆宿营,睡一宿明天再去附近的货栈装车,然后往外省返。
周师傅说过丁四的一些情况,说这孩子的身世也挺可怜,父亲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母亲也没工作,只好送他出来当学徒。一个聋哑孩子一般的活计都干不了啊,还算幸运跟了周师傅混口饭吃。周师傅说这孩子倔,性格又孤僻,三年两年的把他调理成一个干活的好把式,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大平护士说跟聋哑人就得多交流,她丈夫有个表弟也是聋哑人,脾气相当暴躁,在镇砖瓦厂干活时因为计件问题跟老板打架,砸了人家吉普车的风挡玻璃。
三个人说这个话题时,丁四只顾埋头吃饭,好像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似的。
陆大夫跟周师傅打听药材铺老板的情况,周师傅说好像得在南方待一段时间,是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主要是忙买卖呀。陆大夫苦笑了一下说,忙买卖,多好的借口,孰不知是在忙乎另外的女人吧。
周师傅没接陆大夫的话茬,把杯中的一口白酒喝光,掏烟卷吸起来。
几个人都吃完了,护士大平再往塑料袋里装剩饭剩菜,并张罗着结账。
护士大平起身去结账时,陆大夫小声问周师傅,那紧缺的针剂带齐了没有?周师傅点头说齐了,总共三盒,都压在药箱底下,有红枸杞的箱子里。周师傅说这药真是越来越难淘弄了,价码长了不说,连大医院都限量了,没有关系是弄不出来的。
陆大夫趁酒馆里的几个人不注意,将几张钞票塞到周师傅手里,朝他使了个眼色,方起身朝门外走。周师傅也没客气,将钱紧紧攥在手里,吸着烟跟在后边出门。丁四早已经把卡车打着火,正提只水桶给卡车的水箱里加水。
四个人分手时,天已夜幕四合,城市跟漆封的火车皮般闷热,令人喘息。
周师傅开着车消失之后,陆大夫步行回药材铺,护士大平则往附近的公交车站点乘车,回城南的家。
陆大夫回到药材铺后,醉意全无,他喝了一大茶缸子凉茶水后,就忙不迭地锁了门,开始倒腾新进的药品。陆大夫把那三盒针剂捧在手里时,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来。
5
女人依旧骑着自行车来药材铺抓药。
陆大夫用小秤盘一样一样给她配备,五味子、黄芪、小茴香、甘草,一一摊开在展开的牛皮纸上。治哮喘的,一配就是四服,两天一服,用温水冲好了喝下。
陆大夫不抬头只管低头问女人,病人有无好转?女人说稍稍见好,但还是咳嗽,痰也多。陆大夫就拿笔在处方上加上柴胡和板蓝根两味药剂,然后继续配药。陆大夫把四服药包好,依次用纸绳捆扎好,再递到女人手上时说,坚持吃药,再多喝些白开水,如果吃过这几服药后仍不见明显好转,我去瞧一下病人吧。
女人付了两张钱,是大面值的新钞票,陆大夫为其找零后送她出门。然后,陆大夫把那两张新钞票放到自己的钱夹里,再抽出两张旧钱放到护士大平经管着的钱匣子里。
陆大夫吸了根烟卷之后,就拿手机给一个人挂电话,他说货到了,看啥时候有空闲来取吧。
陆大夫挂了电话后,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瞧着那三盒针剂,小声地叹了口气。
来取针剂的人也是陆大夫的一个患者,四十左右岁的男人,矮小身材,剃平头。打人眼的是他精瘦的身子骨,跟麻秆似的,有二级风就能刮个跟头。
陆大夫称来取针剂的人胡科长,从他穿的衣着看是在税务局当差,人和善,脸上总是挂着些许的微笑。胡科长手里提着两瓶德惠烧白酒和一大纸口袋炒熟的葵花子,是带给陆大夫的。酒许是别人孝敬他的,葵花子也是顺手从胡同口郭家炒货铺拿的,没人会要他钱的,税官吗恭敬着还来不及呢,那还敢得罪呀。
胡科长付了针剂钱,拉着陆大夫去外面喝酒,说都有阵子没跟哥喝酒了,咱俩就去吃水爆肚。
陆大夫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同意了。他收了钱匣子,再关了门,然后跟胡科长去酒馆里喝酒。在酒桌上陆大夫问胡科长,怎么没约你那两个哥们儿呢?胡科长说老三出国了,带新娶的媳妇游欧洲六国去了,纯粹的度蜜月。小万最近上岗挺勤,说是搞什么清扫“黄赌毒”战役呢,当警察的也没个闲工夫。
陆大夫说你把小万兄弟的电话号码给我,哪天得让他再来店铺一趟,我帮他淘弄了治肩周炎的偏方,给他配几服药吃吃,他不总是念叨肩周疼吗?
胡科长把小万的电话从自己手机里调出来,写在纸片上交给陆大夫,然后倒酒敬陆大夫说,难得陆大哥是个好人,兄弟们的事你都放在心上,来喝酒吧。
两人吃了两盘水爆肚、一盘熘肚领,喝了三壶小烧,极其尽兴。
这期间,护士大平给陆大夫打来电话,说她明天请假,乡下来亲戚到城里看病,得陪着去。
陆大夫说行啊,你就忙你的吧,药材铺不还有你陆叔呢吗,放心吧你就。
酒足之后,胡科长跟陆大夫说,他的病好像越来越重了,就是每天扎上一针也不管用。话说白了,是管用不了多长时间,有时会疼一个整夜,你说咱这人是不是废了。
陆大夫说别没信心,你得有与天斗、与地斗、与病斗的决心才行。
陆大夫说完话就看见胡科长一个大男人,眼眶里竟噙着几滴泪水,整张脸都涨红了,他的心就跟着颤了一下。
6
陆大夫又一次去小红浴池泡澡时,叫了按摩小姐云云,反正口袋里揣着胡科长给他的一沓钱呢。去除三盒针剂的药钱,胡还多给了他三百元,既是酬谢,也是打点,你想啊紧缺的药品花平价是买不到的。
陆大夫按到一半的时候,裆下那个物件就雄武起来,他有点掌控不住,就扯了云云翻到床上。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云云的衣裤,待自己的家伙顺利入港后便急不可待地动作起来。云云倒没有挣扎,闭上眼睛做出幸福状,配合他做完那件事。
也就是三两分钟的事,陆大夫就结束战斗了。他躺在云云身边吸烟卷,边吸边说自己真是老了,老得快不中用了。云云倒是懂事,一边帮他按后背一边说,不老,你是雄风依旧在呀。
陆大夫吸完一根烟后,掏两张钱塞给云云,嘱咐她给自己弄壶新茶来,休息一阵再说。
陆大夫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觉得累,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五十多岁的年纪了,对自己还那么放纵,是有些不应该。但他转念一想,他的所作所为又是可以令人原谅的。在南方他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可就在他要退休之际,做服装生意的老婆却另有新欢了,竟然跟了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男人。陆大夫没有跟她吵闹,他很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两人分手那天,陆大夫问跟了自己半辈子的女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女人回答他说,是命运的捉弄呗。陆大夫听出了女人话里的意思,女人是走错了路回不了头了,她无可奈何呀。陆大夫说要见见那个大男孩,女人拒绝了他的要求,女人说你在哪方面都比不过人家的,你唯一比他强的一点就是忠实,对妻子对儿女和对家庭及事业的忠实。
老婆给他留下了一笔钱,算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念想,陆大夫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到老了却把女人混丢了。儿子在外省读研究生,女人再一走,就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了。所以一退休,就跑到北方这座城市帮表弟忙,经营起药材铺来。
陆大夫这次来北方也想寻机找个伴,退休了自己是有一笔工资的,帮表弟经营药材铺又能挣一些,条件是没的说。他刚来时跟表弟也提起过,表弟答应帮他踅摸,可一时半会儿的没合适的,就撂下了。
云云把新沏的茶水送过来,还给陆大夫拿来了热毛巾,额外还有一小盘水果,有小柿子和苹果片,是浴池的老板娘杜岭红让送的。
云云放下茶水和水果后没有走,坐在陆大夫身边不说话,脸上满是红晕。陆大夫喝了半杯茶水后问云云是不是有事情要说?云云顿了顿才点了头。之后,云云说她哥哥被抓了,在河沟街派出所,人家通知她去取人呢。陆大夫知道云云的哥也在城里打工,是在一家建筑工地当泥瓦匠,是因为包工头欠他们工钱而跟其干仗动手伤了人。
陆大夫说是不是得罚钱呀?云云点头说是,办案的警察说要罚三千块钱呢,不交钱不放人。陆大夫便问云云差多少,云云说差一千五百块吧,她手上正好有一千多块钱,找姐妹们借都没凑上。
陆大夫说你哥摊事那个派出所正好归道外分局管,分局里我认识一个姓万的警察,看他能不能帮着给你讲个情,兴许能少罚点。陆大夫说完就拿手机给小万拨号,真就打通了。陆大夫跟小万说了云云哥哥的事情,说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
十几分钟后,小万打来电话告诉陆大夫说他找领导了,领导给说了句话,派出所那边答应减掉一千块钱,交两千就行了。并说已由分局出面,责成那个包工头子,一周内必须解决拖欠工人们的工钱。
陆大夫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到云云手里说,快去吧,到派出所找一个姓王的所长,提一下分局姓刘的领导即可。
云云眼睛立马就湿了,她抓了陆大夫的手哽咽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7
晚上九点,陆大夫跟胡科长及其分局的民警小万三个人聚在了江边的大排档烧烤摊上。时间之所以这么晚,是小万的原因,他晚上加班,有夜巡任务,八点四十五结束才赶过来。
三个人还是吃烤串喝啤酒,唠些家常嗑。陆大夫给小万配了三服药,专门治肩周炎的,说吃四个疗程就差不多见效果,也得勤活动加之辅助治疗。小万要付钱,被陆大夫给挡了,说刚刚不还求你给办了件事吗,没来得及谢呢,岂有收你药钱之理。小万说你那件事不算啥事,完全在可通融的范围之内吗。话说回来,那个包工头也是挺招人恨的,在外面胡吃海喝泡女人不说,拖欠工人血汗钱,你说不找修理吗。
胡科长说了他们单位另外的一件事,他说是税务稽查所的一个副所长,没所长他主持工作。权力一大就不会用了,原则的事也摆不明白了。在查区属一个单位资金管理不善时,本来是立了案开始侦察的,却被人家给俘虏了,仅仅用一个漂亮女人便把他拉下了水。
胡科长讲到这时,陆大夫的脸暗地里红了一下,他以为是说的自己。虽说自己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去小红浴池跟按摩小姐云云的事不恰好能对上号吗?况且自己还帮女孩办事,帮她从派出所里往外面捞人,还替人家出资,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明白人在做糊涂事吗。
烧烤摊上的食客渐少时,陆大夫小声地跟小万说了他憋在心里很久的一件事。他从钱夹里掏出几张新钞票来,推给小万,让他辨认一下钱的真假和号码。陆大夫说上个月电视里不是滚动播出一起抢劫案吗,建设路的一个邮政储蓄所被蒙面歹徒持刀抢了八万块钱。其中有三万块钱是刚出印钞厂的新币,每一张都是连号的。小万明白了陆大夫说的话,他把那几张新钱收起来,问陆大夫钱是哪来的?
陆大夫便把每周都来她家里买药材的那个女人说了出来,并说她买的是治哮喘的药,剂量挺大,不像是老太太吃的。
小万说这案子到现在没破不说,竟没有一丁点的线索,从储蓄所的录像看,是两个蒙面男人做的案,但只有身体的轮廓,看不清面孔。当时保卫干部在阻止歹徒作案时,忍着被刀刺中的剧痛拉响了警报,吓得两名歹徒赶紧携款逃窜。
小万拿手机给他分局的同事发了条信息,把几张钞票的号码也发了过去。很快,同事那边就回复了,说钱币的号码正好跟被抢的钱币号吻合。
小万很高兴,说案子有转机了,再有十分钟分局的车会来接他们仨,分局的领导等着听汇报呢。三个人就举杯碰撞,满饮了此杯。三个人都挺兴奋,陆大夫说想不到咱小白人、咱小平民百姓也能为破案出力。胡科长插话说,这要是真的,你也算是为民除害了,三个人就笑。
最后由小万结账,三人花销不到五十块钱,算是对陆大夫给他配药的答谢。
分手时胡科长偷着问陆大夫,他用的那种针剂能多搞到些不?他最近对这种针剂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要是好整就多整一些备用着。
陆大夫说开始要批条了,超过五盒就得卫生局医政科审批,而且还得公安局备案。我建议你还是换点口服的西药片吧,针剂用多了会上瘾的,也伤身体。
8
落雨的一天里,药材铺的老板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年轻女人,给大家介绍说是老板娘。女人长得妖艳,岁数也小,话语少却有主见,她说从即日起药材铺由她来管理,生意上的事要共同商量,做买卖就得齐心协力才有得赚。
老板把陆大夫单独约到铺子外面,跟他说铺子的租赁期限还有五个月,租赁期满后他就不开了,关门大吉。陆大夫说生意挺好的,干吗要关门呢,难道钱咬手吗?老板说表哥您不知道,这新娶回来的女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们俩是在歌舞厅认识的,起初只是玩玩,没想到被她粘上了。
陆大夫吸了口烟说,凡事都得从辩证的角度看,人家毕竟把一个女人的身子都给了你,还比你小那么些岁数,咋就说是粘上你呢?做事要讲良心,男人吗。我建议你药材铺到期限后,别关门大吉,就送给女人让她经营算了。一呢人家没白喜欢你一场,二呢也给她留了条退路,从陪舞小姐到开店铺老板娘,也算有了正经的事做。
老板想了想后说,表兄您说得也不无道理,那我就得有些损失了。
陆大夫笑了,说人生在世,哪一个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得有失,相得益彰啊。
两人互相看着都笑了。
下午太阳光弱一点时,那个买药的女人又来了,她仍旧骑着那辆自行车。抓了药后付给护士大平的又是两张新钞票。在一旁看药方的陆大夫问了女人几句话,他说药吃着还有效果吗?你男人的病是不是好多了?陆大夫的话把女人问得愣了神,好半天她才吞吞吐吐地说,药是给俺娘吃的,啥男人不男人的。
陆大夫赶紧道歉,说他记错了。送女人出药材铺门后,陆大夫把女人付药费的钱从护士大平手里换过来,说留着新钱周末随礼用。然后出门,骑上大平的自行车朝女人走的方向追过去。
二十分钟左右,陆大夫弄清了女人住的地方,城西华侨名苑小区外围的一处平房里。陆大夫看着女人推着自行车进了那家院子后,才转身往回走。
两天后,药材铺新来的老板娘把护士大平辞退了,原因很简单,每天来买药的人也没几个,没必要雇那么多人。新来的老板娘答应给陆大夫每月加二百块钱的工资,店铺有他一个人守着就行了,到年底找明白人给盘个价,把药材铺兑出去,换成钱开家小美发厅也不错啊。
陆大夫没说什么,他看着护士大平收拾东西,心里不是滋味。药材铺开业两年多,是这个叫大平的女人跟他一起经营每一单生意,帮自己那个表弟赚钱。陆大夫很满足,从南方来应这份差事,为的就是忘掉和老婆间的烦恼,也为的是自己能有个事做,填充那些退休后纷至沓来的无边的寂寞。护士大平人也非常好,干活勤快,讲究卫生,很适合在药材铺工作。陆大夫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丈夫有病在家里躺着,还有个孩子念书,全家只靠她的工资维持生活,不容易的一个女人。
陆大夫趁女老板出去办事的机会,把五百块钱塞给护士大平,说是老板吩咐的,算是给你的一点补贴。陆大夫很诚恳地跟大平说,回就回吧,我也干不了几个月,年底铺子就会被关掉,这新来的女老板实在不是个做事的人。
护士大平笑着说没事,其实她早就想辞掉这份工作了,主要是赚的钱少,不够家里用的。刚好上礼拜她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另外的一份工作,是去离家很近的一个诊所当护士,每月能给一千三百块呢。
陆大夫说那就好,比在咱这药材铺强多了,以后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陆哥兴许能帮上你的。
9
晚上陆大夫约了分局的民警小万,两人在胡同口的小酒馆里喝酒时,陆大夫把女人买药付的那两张新钞票掏出来递给小万看。小万很兴奋地告诉陆大夫说,那几张钱经过比对,真就是邮政储蓄所被抢的钱。分局已派出专案组去查买药的女人了,并把你侦察到的那个地址监控起来,用不了几天证据齐全了就能收网。
小万说局领导说案子破后得好好感谢你呢,案子破了你可是首功一件。
陆大夫笑着说,啥功不功的,只是尽了咱老百姓的责任而已。
酒后陆大夫回药材铺睡觉,原本想去小红的浴池泡个澡按个摩的,下午云云打来电话约他去洗澡,说要还他钱。云云的语声甜润,很温和地说都想陆叔了。陆大夫也想云云了,有些时日没碰她的身体了,打定主意想去,可奈于云云说还他钱那句话,还是取消了去按摩的想法,猴急地好像忙着取借款似的。陆大夫决定明天晚上去,好好地洗个澡放松一下。
夜深一点时,陆大夫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在外屋的药材铺里翻东西。陆大夫爬起身抓到手电筒时觉得脑袋瓜子疼,想是酒喝多了的缘故,口也渴,有股子口干舌燥的感觉。陆大夫拉开通向外间的小门,便被突现的一幕惊住了。外间的药材铺里灯被打开了,两个蒙面人正弯腰翻找什么,盛药的纸盒子和木箱凌乱地扔了一地。
陆大夫知道是来打劫的了,想退回里屋已来不及,陆大夫站在门口的一瞬间就被其中一个蒙面人发现了,并且持刀冲他奔过来。陆大夫语调发颤地问他们找什么,他可以帮忙。蒙面人扯了陆大夫的衣袖拽到屋中间,问他治哮喘的得用哪几味药,让他立马给配上十五服。
站在门边灯影下的蒙面人很苗条,眼睛始终不敢往陆大夫这边看。药配齐后装在一个纸箱里捆好了,被持刀的那个蒙面人拎了往外走。陆大夫吓了满脑门子汗,找毛巾擦了擦后坐在椅子上喘息,半天他才掏出手机给小万打电话,拨通后陆大夫说店里遇到抢劫的了,抢走了一大包治哮喘的中草药。
陆大夫挂上电话,掏出纸烟点上火刚吸一口时,门开了,其中的一个蒙面人又返了回来,拿刀逼住陆大夫说你他妈的还敢报案,不由分说地朝他屁股和背部刺了两刀,然后夺门而去。
小万和同事开车赶到药材铺时,陆大夫已经昏迷不醒了。送医院抢救过来后,陆大夫跟小万说,两个蒙面人中有一个身材瘦削的好像是那个来买药的女人。
小万说已经收网了,你说的正是那个女人,她和她表弟是来给其丈夫弄药的,她们想连夜逃出去,奔内蒙古大草原的一个远房亲戚处躲藏。抢钱的两个歹徒就是女人的丈夫和她表弟,她丈夫作案时被保卫干部按响了报警器后受到了惊吓,多年患下的哮喘病犯了,离开药物治疗就会要了命般。
陆大夫听后,长吁了一口气,他躺在病床上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小万说,你先睡会吧,天一亮我们分局的几位领导就来看你,他们要当面感谢你呢。
陆大夫说谢啥谢,等伤一好,我就回南方了,自己开个诊所赚钱过日子。这当英雄的想法挺好,可就是一实践起来有些吓人。
徐岩,男,吉林九台人。1987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三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并译介法国和日本,著作有《临界有雪》《胡布图河》等多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现供职于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