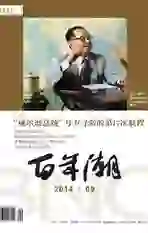从“天南一支笔”到“一卷书雄百万兵”
2014-11-15周绍莲
周绍莲
“天南一支笔”李曰垓
艾思奇故居的大门上写着毛泽东给艾思奇的评价“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这八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
李曰垓,1881年3月4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性格沉静、聪敏、好思。11岁即通读《资治通鉴》,并对这本史学巨著做出如下评价:此书阐述兴衰之迹、治乱之数,简而详尽,深解其意。1903年,23岁的李曰垓和同乡李根源、张德溶、张德泽、张德洋一起,带着七两纹银,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走了七天,到昆明参加省乡试,未中。他和李根源考取了新开办的云南高等学堂,成为云南高等学堂的第一期学生。来到昆明,李曰垓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阔。在这里,他师从云南著名学者陈荣昌(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司,即校长),主修陈先生主讲的经史策论,辅修辞章,深得陈的赏识。陈先生说曰垓“能励学”,并对他寄予厚望。这期间,李曰垓还接触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和同学罗佩金等人组织秘密小组,宣传革命思想,树立了匡世救国的民主革命理想。1905年,因成绩优异被校长陈荣昌推荐到京师大学堂深造。当年云南被推荐的考生,只有李曰垓一人被录取,成为京师大学堂这年新开设的经济特科的学生。在京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黄兴、居正、胡汉民等人,阅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倾心于孙中山的论著,接受民主共和的思想,成为留日滇籍学生创办的滇话报社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为柳亚子创立的文学团体“南社”撰写宣传民主思想、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文章,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他的文章势如江河奔腾,气挟风雷。他的书法刚劲俊秀,如剑扫大地。1908年,他从京师大学堂毕业,授举人。1909年,李曰垓被滇督委任为总理永(昌)顺(宁)普(洱)镇沿边学务中书科中书。他取道香港、缅甸回云南。在缅甸仰光遇见了黄兴、吕志伊等人,在黄兴的鼓励下,由族叔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云南省土民学堂总办、省立蒙自中学监督,在今保山、腾冲等沿边地区开设学堂,兴办边地教育,创办土民学校128所,招收各民族学生近4000人,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人才,启发民智,宣传革命,为沿边地区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曰垓倡导教育平等。他的一副著名书法哲理名联:“除尽无明无等等 观深自在自如如”,至今仍镶嵌在滇西名校腾冲一中的碑廊里。这幅作品不仅体现了他的书法造诣,更体现了他的文学、哲学、佛学修养,还表达了他追求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他参与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并在护国运动中担任护国军秘书长,后任云南军政部次长、民政厅长、第一殖边督办。大学者章太炎曾赠赞誉联:“曾经作色犯大帅,还是昂藏一丈夫”。在云南军政界,李曰垓是一位难得的通才,在文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诗文书法俱佳,著有《天地一庵诗文集》五卷、《汗漫录》三卷、《梓畅书牍》五卷。被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
李曰垓对云南建树颇多,护国战争中以掷地有声的言辞和文章而名垂青史。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23日,蔡锷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曰垓起草讨袁檄文,并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25日誓师,为出师有名,蔡锷主张用“讨逆”或“讨贼”,李曰垓不同意,他陈述道:“讨袁关系国家存亡,已非一般叛逆可比,而是护卫国家之义举,应以护国立名。”蔡锷听后也赞成此意,于是定“护国”之名,这就是护国军的来历。全国爱国志士对此纷纷响应。
云南护国首义前后所发通告,多由李曰垓撰写。尤其是云南独立后,文函繁多,有关宣告独立的通电、敦促各省举义的通电、声讨袁逆及檄告其罪状的通电、致华侨特述举义情形的通电、致驻外国各公使支持举义的通电、致驻华各外国使领馆的通电,以及各种对内对外通电及文告等,多出自李曰垓的手中。

“一卷书雄百万兵”——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哲学家艾思奇是李曰垓的次子,生于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民主气息的家庭里,艾思奇深受父辈和长兄的影响。李曰垓在京师大学堂研修过中国古代哲学,对哲学的意义和作用有较深的认识。在读中学的时候,艾思奇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哲学。李曰垓曾这样教导子女们:“我在大学所习为文科,并偏重于政法和哲学。今世变已亟,文法之弊,流于空虚。做人需有一技之长,自不愁无饭之地。我盼你们弟兄,能各习科学一种,于国于己,方有着落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云南省一中举行示威游行,唐继尧下令抓捕学生运动骨干,当时就读省一中的艾思奇成了主要抓捕对象。艾思奇乔装出逃,取道越南到苏州见到了流亡中的父亲。艾思奇在宗伯李根源家里避难期间,父亲教他读《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父亲对这些经典中深奥哲理的讲解,引起艾思奇研究哲学的兴趣,艾思奇后来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跟李曰垓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曰垓要求孩子们读书应力求弄懂,反对囫囵吞枣,半途而废,主张无论写诗做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可以说是践行了父亲的教导。
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1927年春至1928年春,在日本学习日语、补习功课准备考试期间,经中共东京支部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他以极大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还有黑格尔的《逻辑学》。为能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他除了学习日语外还学习了德语,1928年因患胃病回国。1930年再度赴日本,考入福岗高等工业学校,他利用课余时间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以及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理论学习和对现实的思考使艾思奇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父亲的“工业救国”之路,在民族没有独立、人民没有自由的情境之下是难以实现的。他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弃工从文,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激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毅然回国。1934年,年轻的艾思奇创作了《大众哲学》,这时他年仅24岁,但《大众哲学》成为他众多著作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虽不完美,却因通俗易懂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艾思奇曾戏称《大众哲学》是“一块干烧的大饼”,它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事例,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扫除了以往哲学晦涩玄奥的色彩,使哲学从书斋走向人民大众,为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开了先河,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作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将何去何从?很多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思想深处产生了种种疑惑和焦灼不安,多少在黑暗中徘徊、摸索的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启发和影响下,奔向革命,奔向抗日前线,奔向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艾思奇到了延安,成了毛泽东的哲学顾问。1941年,毛泽东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1959年,毛泽东外出带走的一批书当中,《大众哲学》赫然在目。

艾思奇故居展室的墙上题有这样一首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又题注“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年,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的思想威力”。题赠这首诗的马璧教授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曾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干校系主任。1981年马璧从台湾回到大陆,并于1984年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谈道:“蒋介石的统治在大陆崩溃退至台湾以后,曾不止一次在台湾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他曾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说,蒋介石曾将《大众哲学》放在案头常常翻阅,他还推荐蒋经国也要读这本书,在理论总结方面曾经特别地提出让大家学习《大众哲学》。蒋曾经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大众哲学》这块“干烧大饼”在发挥了“雄兵百万”的威力。在学术界,大家把艾思奇称为中国“哲学大众化第一人,思想方法论第一人,哲学教科书编写第一人,大师长期从教第一人”。这“四个第一人”,是对艾思奇对中国哲学大众化的贡献的肯定。
从“天南一支笔”李曰垓到艾思奇的“一卷书雄百万兵”,从中可以找到一种精神的向度,一种绵长而又坚韧的民族精神,一种责任与担当的文脉传承和爱国爱乡、追求进步的精神之光!(责编:王 兵)
(作者是腾冲一中历史教师)